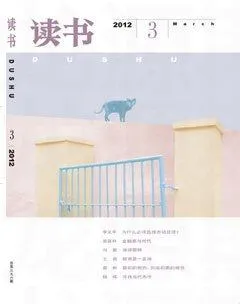最初的契約:回國初期的穆旦
一、“獻禮”的熱情
據說,在美國留學期間,詩人穆旦就曾對歸國后的情形有過設想,繼在西南聯大學過俄語之后,又一連三個學期選修俄文課程,背誦俄文字典,翻譯普希金詩歌,“譯詩將是他貢獻給中國的禮物”(傅樂淑:《憶穆旦好學不倦的精神》)。同時,為《文學原理》“做了不少翻譯筆記”;且有意識地關注新中國的現實,“就是在撰寫學位論文的緊張階段,還一次次閱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周與良觀點,轉引自李方:《穆旦〔查良錚〕年譜》)。
一九五三年初,穆旦與妻子周與良幾經輾轉,經香港、九龍、深圳、廣州、上海,終于回到新中國的首都北京。在上海期間,他們曾與多年不見的好朋友蕭珊等人會面,周與良后來曾就此有過回憶——
她見到我們非常高興,她說歡迎我們回到新中國,愿良錚為祖國的文化繁榮做貢獻。當她談到解放后,各方面都在學習蘇聯時,良錚說他準備翻譯俄國文學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她很驚奇地說:你不是搞英國文學的嗎?又是詩人,怎么又想介紹俄國文學了?良錚告訴她,他在美國學習時,也學了俄語和俄國文學的課程,準備回國后,介紹俄國文學作品給中國讀者。我記得當時他們談得很高興,蕭珊同志還鼓勵他盡快地多搞翻譯。我們回到北京后,良錚就日以繼夜地翻譯季摩菲耶夫著的《文學原理》。(周與良:《懷念良錚》)
好朋友“驚奇”于穆旦的轉向,而好朋友的鼓勵顯然加深了穆旦對于時局的認識。而因為這樣一些因素,回國之后的穆旦最初所進行的翻譯活動,被普遍認為蘊涵了順應政治文化的意圖——一種向新中國“獻禮”的熱情。放置到當時語境當中,這樣一種“獻禮”心態同時無疑也是當時相當多經歷了“舊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心態,蕭珊的熱情鼓勵即可在“獻禮”層面來認識。
但蕭珊所給予的熱情鼓勵多半是單純的、不設防的,時代的風雨及其可能產生的復雜后果多半并未考慮在內——兩年后,其時穆旦已被卷入“外文系事件”之中,處境已較為糟糕。穆旦的舊友楊苡到上海。這期間,彼此共同的朋友靳以特意囑咐她轉告蕭珊在說話、處事等方面要注意。所謂“注意”,用今天的話說大致即是低調,即便才華出眾,也不能太張揚。楊苡與蕭珊有過徹夜長談,其中也談到穆旦。楊苡后來有回憶:“為了我們一個共同的好友,一個絕頂聰明、勤奮用功的才從美國回來誠心誠意想為祖國做點貢獻的詩人,我認為必須保護他,不要忙著為他出版書,以免招人嫉恨,引起麻煩。她卻天真地拒絕了我的擔心。”(《淮海路淮海坊五十九號》)
生性“天真”的蕭珊所給予的鼓勵以及大力幫助顯然大大促進了穆旦的翻譯熱情。而穆旦原本是帶著“獻禮”心態回國的,時間既然多有延遲,工作落實之后乃至在等待工作過程中所展開的積極工作可算作是一種爭取時間的緊迫感的體現。周與良稱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八年是穆旦譯詩的“黃金時代”:“當時他年富力強,精力過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課,參加各種會議,晚上和所有業余時間都用于埋頭譯詩。”(周與良:《懷念良錚》)周與良在不同時期對于丈夫的翻譯行為有過多次回憶,其核心要素是強調穆旦對于翻譯的那樣一種近于偏執的投入。而在親近穆旦的朋友看來,這種極其熱情而勤奮的工作乃是要尋求一種證明:“他想證明給沒回來的人看,回來了是多么好。”(楊苡觀點,見易彬:《“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學四人談穆旦》)
從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八年,穆旦共翻譯出版譯著約二十五種(包括出版改制之后新印的)。譯著的順利出版,自然得力于在平明出版社等出版機構任職的巴金、蕭珊等人的大力幫助,而這也表明穆旦的熱情并沒有虛擲,新的體制正在不斷構建途中的“新中國”以一種積極的姿態接納了他。
二、初到南開
但從重新踏上中國國境的那一刻起,穆旦應該就已感受到了形勢的嚴峻性。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居留北京等待分配工作的穆旦填寫了一份“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登記表”,包括社會關系、“在國內外參加過何種社會活動”、“回國經歷情形”、“在國外對新中國的認識及回國動機”、“你在回國后有何感想”等方面信息。“登記表”實際上是交出自己的過去、現狀以及對于未來的想象。而這還不過是一個開始,現存穆旦檔案之中,有五份類似的表格及三份長篇思想總結材料。可以想象,它們不過是眾多材料的一部分而已。
在北京期間,穆旦又見到了昔日的朋友,如在新華社工作的江瑞熙、杜運燮、梁再冰等人。梁再冰后來在檢舉材料《關于我所了解的查良錚的一部分歷史情況以及查良錚和杜運燮解放后來往的情況》(一九五五)中稱,當時穆旦曾談到了“今后的職業問題”:
[穆旦]向我們表示,他不愿到學校去教書,或做機關工作,只想做一個“個人”職業文學翻譯,翻點東西拿稿費。同時,我們知道,他在美國時把俄文學得很好。當時我們都反對他搞“個人”翻譯,勸他到學校教書,以便更快地改造自己。
在去南開之前,穆旦或許曾經試圖找過“最適合自己”的“寫作和研究”機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而朋友們的這種規勸對于穆旦的擇業應是有所影響,在猶豫和矛盾之中,穆旦最終和妻子周與良一道回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天津,任南開大學外文系英文組副教授,周與良則去了生物系微生物教研室。按照舊友巫寧坤的說法,穆旦夫婦是在他的“慫恿”下接受南開大學聘書的,當時南開師資緊缺,巫寧坤也私心“希望有老朋友來做伴”(《旗——憶良錚》)。穆旦本人一九五五年十月所作《歷史思想自傳》中的說法則是:
在答應此事時心中有矛盾。自覺寫作和研究最適合自己,而教書,過去十多年前教過,頗為不佳,現在口才及能力是否勝任,毫無把握。但不教書似又無他項工作,而且南開大學又可和愛人一起工作,因此便答應了。
“十多年前教過”指的無疑是西南聯大任助教的經歷,將教學效果認定為“頗為不佳”,看起來,當初短暫的助教經歷似乎給穆旦的心里留下了某種陰影。“毫無把握”則可理解為對于前途的判斷。
其實,穆旦與南開大學有很深的淵源,他在南開中學度過了六年時光,南開中學與南開大學同屬南開系列,當年一些老師后來已是南開大學的教授,如孟志蓀即任中文系古典文學教授。更何況,抗戰爆發之后,南開大學與穆旦當時就讀的清華大學合并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穆旦與不少南開師生都有過直接的交道。當初在西南聯大任教的哲學系馮文潛教授、歷史系鄭天挺教授等人,仍在南開任教。
一九五四年,穆旦搬到南開大學東村七十號,與舊友巫寧坤為鄰,“周末往往相聚小飲,放言無忌”,或領著巫寧坤“騎自行車去逛舊城的南市”——“當年上南開中學時的舊游之地”,“欣賞與當前政治宣傳無關的民間藝人表演”(巫寧坤:《一滴淚》)。據稱,東村住房是南開大學最早的教師宿舍。當年張伯苓校長即住此。抗戰時期,東村房屋被毀,“戰后重建,屋前有小花園,屋內地板木質很好,比較講究”。后來,房屋又“修葺多次,高級設備已拆改殆盡”(《魏宏運自訂年譜》)。“高級設備”被拆改應是和新中國的整體語境有關,即對于一種樸素的物質生活的追求,“高級”會被認為是一種享樂或奢華。盡管如此,穆旦夫婦、巫寧坤等留學歸來的人士初到南開大學時的住房待遇應該還是比較好的。
但是看起來,穆旦在南開的工作并不順心。工資待遇比預想中的要低,按照梁再冰的說法,在和江瑞熙等友人聊天的時候,穆旦可能用比較激烈的口氣談及過此事。對于所安排的課程,可能也覺得難以承擔——在一九五五年十月所做的交代材料《歷史思想自傳》中,穆旦寫道:
上課一二次,即對自己的教書能力異常灰心,無英文口才。一星期后改換課程,為重點課,又無教學法,更無法應付。一月后即暑假,決意辭去教書職,屢與系領導表示,未獲準。領導責備我不努力,我則認為領導不理解我實在無教書才能,因此情緒消沉。在美國時的一腔熱情,回國后反而低落了。
周與良后來的回憶觀點正相反,穆旦“課教得好”,“受學生歡迎”(見李方:《穆旦〔查良錚〕年譜》)。何以會形成這種差異呢?是寫交代材料者慣于貶低自己,而寫追憶文章者慣于抬高親人?這已難以斷定,但穆旦與學生的交流多半并不順暢——五十年代的外文系學生,與三四十年代西南聯大外文系的學生已是天壤之別。因為主管天津文藝的方紀的緣故而當時得以與穆旦“認識、談詩、聊天、喝咖啡”的周良沛,后來曾在《穆旦漫議》(二○○一)中憶及穆旦與學生交往的情形:
我不止一次聽他親口當著好幾個人講:他拿著自己過去的詩,請他在“南開”的學生看,這些學生和他寫這些詩時的年齡不相上下,也是學外語,且喜愛文學,愛讀詩的,都坦率得可愛的對他講:他們讀得頭疼,讀不懂,不知所云。他們表示自己喜愛的,恰恰是現在有的評家用以和穆旦相比而看作不入流的作品。這對穆旦的震動太大了。他不是怪自己學生水平太低,而是反思自己對奧登等的模仿太過了。怨自己對人民群眾的不了解。相信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詩。他愿多讀點當時的年輕朋友反映新生活的作品,由此思考些問題再動筆。
在這段追憶之中,學生的態度和穆旦的反應都別有意味。“現在有的評家用以和穆旦相比而看做不入流的作品”是一個含糊說法,從當時的文化生態來看,所指應非外國詩人的作品,而多半是當時或稍早中國詩人的作品,這些“學外語,且喜歡文學,愛讀詩的”的年輕學子“不懂”穆旦,表明穆旦并沒有被“新時代”所接受,也表明他們對于過去的“穆旦”并不知情——實際上,當初和那些大學生年紀差不多的周良沛在回憶中即表示當時對穆旦“一無所知”。
時代已經被厚厚的壁障隔離開來,新舊時代造設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同時也造設了兩種不同的閱讀和興趣。這樣的景狀或可稱之為一種歷史的吊詭:時代以一種近乎強制的方式阻斷了詩歌美學因素的發展——按常理推斷,新事的產生與舊質的消亡同樣是形成藝術張力的因素,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新”與“舊”這樣二元對立的事物顯然是難以并存的——置身其中的個體近乎必然地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而從中國社會的實際進程看,對置身于五十年代政治文化語境的知識個體而言,“新”其實是唯一的選擇——唯有選擇“新事”,才有可能將“舊質”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降到最低點。
穆旦本人的反應呢?在這段話里,“反思”、“怨”、“相信”、“愿”、“思考”等詞的主語無一例外都是穆旦。據此描述,在遭受現實碰壁之后,穆旦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寫作。一九五三年初回到新中國的穆旦直到一九五七年才發表詩歌作品,并不急于寫作,更不用說發表作品,應該即是“反思”的立場使然。
但時代的負壓還是時時襲來。初到南開的穆旦所遭遇的,除了上述諸種因素,還有一張更大、更為嚴密的時代之網——各種“硬性規定的政治學習”。按照巫寧坤在回憶錄《一滴淚》中的記載:
生活中最頭痛的事是硬性規定的政治學習,每周兩三個下午。規定的學習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黨報社論、黨中央文件等等。每次開小組會,首先洗耳恭聽一名積極分子朗讀文件……接著進行討論,人人都得發言,暴露思想,聯系實際,說明學習文件如何幫助自己認識錯誤,提高覺悟。沉默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沉默就被認為抵制思想改造……大家發言都小心翼翼,聽上去都很真摯。小組長認真記錄,散會后向負責政治學習的黨員干部匯報。
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師還得上“馬列主義夜大學”。一位年輕的男教師每周兩次從北京來,朗讀他在新建的人民大學聽蘇聯專家講授馬列主義的筆記,一字一句,照本宣科。我們得做筆記,因為期終還有考試。
穆旦本人又作何等反應呢?前面提到舊友蕭珊在穆旦剛回國時所給予的熱情鼓勵,穆旦這一時期心緒最為直率的呈現,目前也僅保留在致蕭珊的信中。種種情況表明,穆旦的書信寫作量其實是比較大的,但實際存留下來的數量著實有限,《穆旦詩文集》僅錄五十年代的兩封,都是寫給蕭珊的。
一九五三年×月十八日,穆旦復信針對蕭珊來信中發牢騷說自己的信“太冷淡平淡了”,傳達了一種內心寂寞的困惑——
我為什么這么無味呢?我自己也在問自己……尤其在我感到外界整個很寂寞的時候,但也許是因為我太受到寂寞,于是連對“朋友”,也竟仿佛那么枯索無味……
……我們的憂郁感許是太濃厚了一點。憂郁或可,但是不要自傷身體。
三、“文學原理”與“普希金”
不難發現穆旦的微妙處境:初看之下,署名“查良錚”的譯著較快、較多出版顯示了新中國對于穆旦的積極接納;但是,在現實生活層面,幾乎可說是從穆旦進入到新中國的那一刻起,政治磨難就像影子一般緊緊跟隨著。
在這樣一個的大時代之下,個人如何自處呢?“自處”是一個較高級別的詞,暗含了某種獨立的精神品性。那么,退一步說,個人如何應對大時代呢?
在穆旦的譯著中,最先出版的是蘇聯文藝理論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第一部《文學概論》和第二部《怎樣分析文學作品》。這是一本什么樣的書呢?何以它成為穆旦最初的翻譯選擇呢?
《文學原理》是蘇聯最早的具有大學教材性質的文藝理論著作,從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直出版,影響很大。新中國成立初期,當時教育部將它列為大學語言文學系及師范院校語言文學系的教科書。
按照周與良的說法,回國之后、分配到南開之前,穆旦即開始夜以繼日地翻譯這本書。譯書速度很快,及到一九五三年六月穆旦在填寫《高等學校教師調查表》時,譯述方面即有《文學原理》“在譯出中,即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印出”的說法。實際出版是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先出版的是前兩部,第三部《文學發展過程》稍晚,是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出版機構均是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各部分均有內容介紹,綜合而言,即“主要是論文學的本質、特性及法則”;“確定了文學的思維性,形象性,藝術性及黨性;識別了文學的不同的類型及其內在的原因;闡明了現代以及過去文學對于我們所具有的社會的,政治的和美學的意義”;“指出研究文學作品并不就是單獨地研究它的思想,或個性,或語言,而是要在作品各部分的有機的關聯中去透視這一切”;“建立分析文學發展過程所應依歸的原則和方法。作者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經驗為出發點,指出文學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所體現的一系列具體的、概括的形式”。
基于前述背景,有研究認為對于《文學原理》的翻譯是一種“調整”,即“通過此書的翻譯來調整自己,了解和熟悉現實主義的文學觀念和創作方法,學習這一與新的文化環境相適應的文學話語方式”。與此相關,對《文學原理》的翻譯與對普希金、雪萊等人作品的翻譯,被區格為具有時間先后順序的兩種不同類型,文藝理論著作在前,文學作品在后。由翻譯《文學原理》到開始翻譯普希金等人的文學作品被認為是一種“轉變”或“回歸”,即“翻譯選擇在現實文化需要和個人藝術興趣兩端之間,開始向后者傾斜”(宋炳輝:《新中國的穆旦》)。
這樣的說法自是很有道理,調整自己的藝術趣味,努力適應新的文化環境,掌握新的文學話語方式,是新中國成立后作家、知識分子的普遍境遇,前述獻禮心態的描述即是從這一層面入手的。但是,一些細節做出了提示,這一選擇并非是絕對化的。歸國初期穆旦所選擇的翻譯對象都是俄語作品,它們可分為兩類:文藝理論著作(季摩菲耶夫)和文學作品(普希金)。兩者在出版時間上確有先后之別,但是,表象背后還有可堪推敲之處:
一是,兩者的翻譯時間本身并不截然存在先后之別,實際上,如果前面引述的材料屬實的話,滯留美國期間,穆旦還只是在為翻譯《文學原理》做筆記準備,普希金的詩則是已經開始翻譯,“普希金”走在前面。回國之后,一九五三年六月,《文學原理》還是“在譯出中”;九月份的時候,普希金詩集《波爾塔瓦》已譯好,穆旦在給蕭珊的信中即曾談到此書,蕭珊也曾請卞之琳閱看譯稿(據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十月五日蕭珊致巴金的信)。
一是,對穆旦而言,學習俄語雖然已有較長一段時間,但是,俄語畢竟是新語種,有一個適應過程,明晰刻板的理論文字比充滿個人興味的詩歌的翻譯難度較詩歌小,詩歌翻譯上的推敲功夫顯然是大得多,翻譯的時間跨度很可能要更長。
一是,從出版看,在當時中國,蘇聯文藝思潮占據主流位置,《文學原理》是蘇聯的文藝理論著作,又是新中國教育部指定的大學的教科書。這樣一種政治機制與實際需求無疑使得《文學原理》的出版周期更短。
因此,綜合考量之,兩者出版的先后順序并不一定具備“政治文化”選擇的必然性。當然,如是推斷并非要否認穆旦對于政治文化的選擇,而是想強調問題的復雜性——個體在面對復雜的時代語境時所產生的復雜心境。
譯著出版之后的反響應該說都是非常不錯的,從目前所能查證的資料看,所譯《文學原理》第一部《文學概論》和第二部《怎樣分析文學作品》均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出版,前書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共有八次印刷,累計印數為五萬四千冊;后書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共有六次印刷,累計印數為七萬二千冊。第三部《文學發展過程》為一九五四年二月出版,至八月共印刷四次,累計印三萬五千冊。及到一九五五年七月,三書合為《文學原理:文學底科學基礎》出版,初印數為八千冊。粗略統計,該書的總印數在十七萬冊左右。
普希金系列譯著,包括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所出的《波爾塔瓦》、《青銅騎士》、《高加索的俘虜》、《歐根·奧涅金》、《普希金抒情詩集》、《加甫利頌》,以及一九五七年所出的《普希金抒情詩一集》、《普希金抒情詩二集》等,第一版的印數多半在萬冊以上,總印數當有數十萬冊之多。
出版很順利,印數也很可觀,但對于“文學原理”和“普希金”,穆旦當時即有一種自我認識。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其時,《文學原理》的前兩部應該已進入出版流程之中,穆旦在給蕭珊的信中同時談到了“文學原理”和“普希金”:
關于《文學原理》一書,不必提了,我覺得很慚愧。譯詩,我或許把握多一點,但能否合乎理想,很難說……我對于詩的翻譯,有些“偏執”,不愿編輯先生們加以修改。自然,我自己先得鄭重其事:這一點我也已意會到。如果我不在這方面“顯出本事”,那就完了。
“普希金”方面,穆旦雖只是如實地談到了多部普希金詩集的翻譯和出版計劃,但與前面的話題放在同一段落,還是顯示出了一種自我期待,即能“鄭重其事”地在翻譯方面“顯出本事”來。而對于《文學原理》的不滿意,還可見于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九日穆旦給蕭珊的信中所談,“準備用心校對一下”《文學原理》,這也可視為對于當初倉促翻譯的自我檢討。
關于《文學原理》,還可特別提及的是,穆旦所依據的翻譯底本為“莫斯科教育——教學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版”。但這是一本有缺陷、“一再地受到批評”的書,《譯者的話》即指出該書在蘇聯出版五年來,“曾經一再地受到批評”,在蘇聯文藝界引起了“熱烈討論”。它有兩個“嚴重錯誤”,一是“企圖從典型性區別各種文學潮流,借以建立各種文學潮流的概念化的公式”;一是“對于典型性的看法和解釋,在實質上和唯心論的美學相近似”。盡管如此,“譯者認為仍然有介紹的價值”,書中珍貴的意見可以為中國文藝界提供參考,而它的缺陷一經指出,“也可以幫助我們少走許多彎路”。這等邏輯大概只有放到當時的文化語境之中才能獲得解釋:明明知道書是有“嚴重錯誤”的,何以仍將其譯出呢?還是出于文化建設的需要。
相比之下,“普希金”顯然更加有力、也更為持久地促進了穆旦作為翻譯家形象的確立,和大多數出版物一樣,穆旦譯著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八○年基本上已停止出版,但“普希金”已經深深地嵌進了不少讀者的心靈,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后的精神荒蕪的狀態之下,在文學讀物嚴重匱乏的年代里,查譯名著曾經秘密流傳,“查良錚”之名也成為讀者仰慕、尋找的對象,穆旦本人就曾親身遇見。慕名登門拜訪普希金詩歌的譯者“查良錚”的也有不少。穆旦后來受到“鼓舞”,在身體摔傷之后仍加大翻譯的力度,這等故事,另文再述。
當然,也需要注意一點,譯著大量出版的背后其實都有一重時代助推力,《文學原理》出版背后的文學體制因素乃至政治需求,普希金系列出版與新中國文化建設方面的貧瘠狀態,都是可以進一步深究的。實際上,完全可以說,所謂印數也具有迷惑性或欺騙性,并不能解釋全部的問題,在當時形勢之下,作為教材的《文學原理》由“查良錚”所譯,或由他人所譯,其實并不存在差別,出版后迅即再版以及較大印數都是有保障的。從一般讀者的精神需求而言,普希金由誰來譯,較大的印數以及再版也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對一般讀者而言,“查良錚”不過是一個新的譯者的名字而已。
但是,歷史最終還是劃開了界限:“查良錚”并不是一個偶爾出現就消逝無蹤的名字,在“查良錚”這里,翻譯乃是一項與生命等齊的偉大事業,其翻譯形象已經深深地嵌入了歷史的厚壁,成為不同時代的讀者、研究者捧讀和研究的對象。
四、看似平靜的生活
盡管磨難在或顯或微地發生,盡管穆旦對于組織的工作安排、人事安排等方面也有意見,有情緒,但從表面來看,從一九五三年初回國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卷入“外文系事件”這近兩年的時間里,穆旦的生活大致是平靜的。在課堂上,所授課程包括(英)文學選讀,英譯中及中譯英,文藝學引論等;課后,政治學習自然是必須的,其他時間則多半是埋頭于翻譯。
至于“穆旦”之名,從一九五三年初回國之后四年間,一直未曾出現,而目前所能看到的穆旦在新中國公開發表的文字,也已是一九五六年中段了——一篇署名“良錚”的文章,一般讀者或許根本就不會將其與“穆旦”聯系起來。從四十年代穆旦對于重要事件的處理方法來看,這種不急于發言的態度——甚至可說是某種警惕心理,無疑是相一致的。
但是,在一個嘈雜的時代之中,穆旦何以能安坐于南開的書齋呢?除了個人在察知了政治形勢之后而有意沉默之外,多半也可說是一種歷史的慣性與歷史的壓力使然。
粗略地說,在進入到新中國之后,發言積極的文化界人士有兩類:一類原本就是政治進步的著名人士、文藝界領導,他們必須在不同場合發言;另一類的政治立場原本較為灰暗,他們急于發言,以獲得政治新生。這兩類人,詩人群體之中的典型代表,前者如艾青,后者如馮至。
艾青是第一屆政協國歌、國徽、國旗圖案設計組組長,可謂新中國政治文化事業的直接參與者、經濟建設的歌者、世界和平事業的使者,他的足跡遍布大江南北、世界各地,寫下了大批作品,出版了多部作品集(艾青如何日復一日地被卷入政治事務、社會文化活動之中,可參見葉錦所著《艾青年譜長編》一九四九年之后數年的條目)。心態浮躁、寫作快速,作品質量自然無法保證,用艾青本人后來的話說即是,“大都是浮淺的頌歌”(艾青:《域外集·序》)。
艾青本人當時即意識到了這種“危機”,并稱“有信心去克服它”(《沸騰的生活和詩》,《文藝報》一九五六年第三期)。當時的讀者以及文藝界的領導對于艾青的寫作也并不滿意,現今文章引述較多的材料是一九五六年三月的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擴大會上,周揚在報告《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學》中明確提出的艾青“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歌唱”的問題,這些都可說是歷史的慣性使然,即寫作者認為自己有積極表現新時代的使命,批評者也認為那些知名的寫作者必須承擔這種責任。
馮至呢?這位原西南聯大、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在大革命面前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憂慮,是“生存”的壓力;對于新的革命情勢和政治話語似乎并不那么敏感。僅舉一例,一九四八年三月,《大眾文藝叢刊》已刊載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等多篇宏文,不僅大肆批判了非左翼作家的寫作,對于左翼內部的作家也進行了清算,應該說,文章背后的政治旨向已經相當清晰,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馮至卻仍在與沈從文、朱光潛等被點名批判的人士一道探討“今日文學的方向”,還在設想文學在受政治影響之外,“還可以修正政治”,就像是紅綠燈的相互制衡一樣(天津版《大公報·星期文藝》,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這種言論固然顯示了可貴的自由主義的姿態,其在政治上的不敏感也可見一斑。但與沈從文等人明顯不同的是,進入到新中國之后,馮至表現自己的姿態非常積極。表態文章、交代材料并不在少數,如《寫于文代會開會前》等。在一段時間之內,他“被認為是可以信任的,是知識分子中的左派”。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代表大會上,其身份是北京代表團副團長,會上也被選為全國文聯委員和文學工作者協會理事。《馮至傳》作者陸耀東認為:“這不僅是對馮至文學成就和貢獻的認同,也是對他政治表現的肯定。”之后,馮至擔任了一系列行政職務,并且頻頻享受出國訪問的待遇(陸耀東:《馮至傳》)。
政治上的表現得到肯定,及到詩歌創作之中,馮至也在極力尋求一種“政治正確性”。一九五八年,馮至出版了詩集《西郊集》,其《后記》談到對于自己的作品“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但一種“政治正確性”的意識使他變得理直氣壯:
但我愿意再重復前邊說過的一句話,隨著中國的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才又重新寫起詩來。這說明,新中國并不曾“凍結”我寫詩,而恰恰相反,對于我正是春風解凍。這些詩在質量上也是粗糙的,但是比起我解放前的詩,我是走上了正確的道路,這道路不是旁的,就是一切為了人民,不是為了自己。在這美好的今天,詩人若不為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利益而歌唱,那么無論有多么新奇的感覺或巧妙的比喻,都不免是徒勞無益,枉費心機。
從上面的簡單勾勒不難看出,在一種強大的歷史慣性的支配之下,寫作者、批評者以及時代語境之間,實際上構成了某種合謀的關系,構成了寫作者無從掙脫的歷史壓力,它直接影響到寫作者的寫作行為、寫作心理、文學觀念等等。
穆旦呢?“穆旦”之名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方才露面,實際次數也僅有三次。很顯然,在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或者說意識形態的建構——體系之中,“穆旦”基本上可歸入可有可無的角色。也即,由于詩名較小等多重原因,處于文化位置邊緣地帶的穆旦所承負的歷史壓力顯然比艾青、馮至等人要小得多——小到幾乎可以忽視的程度,惟其如此,他才可以安坐在南開大學校園之內,做一名不得志的教師,一位勤奮的翻譯者,而無須頻頻通過寫作來“表態”——實際上也可以說,正是由于名聲較小,早年穆旦的政治立場的危險性也僅僅是一度拘囿于南開校園之內。
從一個更長的歷史語境來看,穆旦本人的有意隱沒、時代慣性的無意忽略,共同塑型了一個“沉默的詩人”的形象,就這樣,有意或無意地,穆旦與時代之間達成了某種契約——當然,就像人們所熟知的那樣,這一契約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涌動。
(《穆旦評傳》,易彬著,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二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