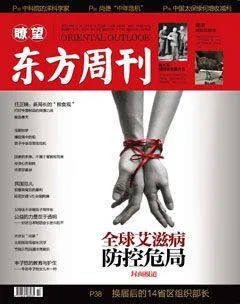楊天石:坦然研究蔣介石

寒風凜冽的日子,王府井附近的東廠胡同里一派清凈。76歲的楊天石,一大早就來到位于此地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不足30平方米的辦公室里,他與本刊記者說起有關歷史研究的種種經歷。
說到激動之處,楊天石每每起身,從擺滿一屋的書架上迅速找出史籍,準確翻到一處作為印證。這似乎秉承了他的一貫態度:“可以反對我的觀點,但你不能推翻這個史實。”這就是以精確于史實的治學態度在史學界著稱的“楊公”。
對楊天石而言,沒有新史料,就不會有新觀點。如今,在涉足辛亥革命研究五十余年后,他才憑借新的史料,出版了《帝制的終結》一書。
在楊天石的治史領域中,當下最受社會關注的是蔣介石研究。2006年3月,寄存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的手稿本開放,他受邀成為最早的讀者之一。而實際上,他研究蔣介石日記前后已經30余年。
到2012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已37年。此前一段時間,一些出版界人士找到楊天石家中,建議他盡早撰寫一部蔣介石傳記,但楊天石卻始終未動筆。問及緣由,楊天石告訴本刊記者:“很多蔣介石的資料還沒仔細看,很多問題還沒仔細研究,所以還沒寫。”
“柔軟”的詩人進入近代史研究所
1955年,楊天石考入北大中文系,希望經由新聞記者的道路成為文學作家。他寫了《我走了故鄉》等兩首詩歌,準備加入北大詩社,結果北大團委審稿后認為他的詩作太過柔軟,缺少鋼鐵般的精神和情感。
沉浸美學的楊天石,1960年畢業時被分配至北京八一農業機械學校教書,那是個培養郊區拖拉機手的訓練班。1962年1月,該校下馬,楊天石調到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任教。次年與同窗學友劉彥成共同完成《南社》一書的寫作。中華書局于1964年將此書排出清樣,因“文革”毀版未印。然而,未能出版的此書卻令楊天石得以與近代史,尤其是以后的蔣介石研究結緣。
1970年代初,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恢復業務,承擔了編撰中華民國史方面書籍的任務,需要研究南社,近代史所領導決定邀請楊天石兼職參與編寫《中華民國史》書目。
楊天石一口答應,因為近代史所有太多他想看的資料。此后,他每天等北師附中的課一結束,就騎著自行車,趕去近代史所。當時近代史人才稀缺,一位研究員將其負責的中華民國史兩章中的一章交由楊天石完成。到1978年4月正式調入近代史研究所,楊天石已經不拿一分錢工資,給近代史所打了4年多的臨時工。
“剛進入近代史研究所的那個階段,可說是民國史研究鼎盛的時期,因為民國史1950年代就列入了國家規劃。到197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在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上又再次提出修民國史這個任務,并交給了近代史所。”楊天石說。

意外發現蔣介石日記
歷史學上長期存在一個爭論:“以論帶史”還是“論從史出”。楊天石持第二種意見。對他而言,在歷史學的大樓中,史料是基石,沒有扎實的資料,歷史學是建在沙灘上的。沒有新資料,絕不發表新文章,是他給自己定下的原則。到了檔案館或資料館,他總是盡力要找沒人看過的資料。
1990年,楊天石到紐約訪問,一見到哈佛燕京學社館長就說:“我知道你們這有很多資料,但是大家都看的我就不看了,你們這有沒有未看的民國史資料。”館長答說:館里有胡漢民的書信、電報,沒人看過。楊天石一聽,當即決定“就看這個”。
楊天石在哈佛的訪問時間只有兩周,胡漢民資料搬來一看,竟有幾十大本,其中包括胡漢民想用軍事行動推翻南京國民政府的內容,涉及反蔣風潮背后有胡漢民因素。這些意外讀到的資料令楊天石大喜過望,他整天在館里摘錄不停,午飯也不出門,回國后寫了3萬字的研究文章《胡漢民的軍事反蔣行動》。
從鮮有人仔細讀的史料中找到新發現是楊天石的傳統。早在1985年,楊天石就用這個方法在日本外務省檔案中發現一個“秘密”,在那里保存的畢永年日記中,楊天石讀到了康有為曾派畢永年到袁世凱的軍隊里,準備等袁世凱到頤和園見慈禧時,趁機刺殺慈禧的內容。
通過其他史料的佐證,楊天石確定日記中記載的內容可以采用,因此發表了《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確證》,該文引起了戊戌變法研究領域的一次震動。
對蔣介石日記的執著研究也是這樣。1982年,楊天石在近代所的研究重點轉向蔣介石。某天,他在位于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資料,檔案館管理員在給楊天石取資料的過程中,突然從一堆資料里掉出一卷日記。雖然上面沒有名字,但楊天石粗一看便判斷與蔣介石有關。這卷日記是分類摘抄本,包括黨政軍事等內容,并非日記原本,但楊天石從中看到了蔣介石少年時代的老師、以后智囊秘書之一的毛思誠的字跡。
毛思誠1925年4月任黃埔軍校秘書處少校秘書,此后十多年一直在蔣介石身邊,蔣介石曾把44部日記、手卷、畢業文憑、公牘等都交由毛思誠保管,毛說那是“外間所不克見,而為歷來珍秘之故楮”。
“文革”期間,寧波“紅小兵”把毛思誠宅邸的墻砸開,發現了砌在里面的上述資料。這批檔案幸未被毀,從寧波送杭州并經由公安部被送到第二檔案館保存。
從毛思誠家的抄家清單在楊天石的眼中成了一份蔣介石研究目錄。1988年,他發表了第一篇蔣介石研究的文章《中山艦事件之謎》,指出“中山艦事件”并非蔣介石的陰謀,而是國民黨右派的陰謀,蔣介石是誤信謠言。蔣介石曾在“中山艦事件”后說過大意為“現在不能講真相,等我死后看我日記”的話。而有關日記終于在事件發生的60多年后展現到了研究者面前。
胡喬木讀了《中山艦事件之謎》,稱之為“有世界水平的文章”,號召研究黨史的人學習。
從那以后,楊天石沉浸于蔣介石日記,發表了許多蔣介石研究的論文。隨著研究的深入,楊天石發現第二檔案館保留的資料有缺憾,那就是蔣介石日記只保存了1931年之前的,此后的年份缺失。2002年以后,他去臺灣尋訪,在那里發現了蔣介石日記的五種摘錄本,通過這些資料,他所研究的蔣介石日記推進到了1942年。
從臺灣“黨史館”調“機密文件”
為了找資料,楊天石去臺灣已經十多次。“印象最深的是前兩次”,他告訴本刊記者。
“第一次去臺灣的時候參觀過‘國史館’蔣介石檔案,但館長只給我們看了裝蔣介石檔案的箱子。直到第二次去才開放檔案,允許看。”楊天石說。
第二次從臺灣回大陸,楊天石帶了兩箱資料。到北京機場,海關檢查人員對這一大堆資料發生了懷疑。“問我這是什么,我說是臺灣的資料,我當時出去是去臺灣、美國和俄羅斯搜集編寫抗日戰爭史的資料。海關官員說,你這個問題我們還沒遇到過,一下扣了我十幾本書。”楊天石回憶說。
對被扣下的《臺灣義勇隊在大陸》,楊天石解釋說,臺灣義勇隊是在大陸抵抗日軍的組織。海關官員答,“我不懂,得送審”。
兩個星期后,海關方面的人員將被扣的大部分資料還給了楊天石,道歉說:“我們的工作人員知識不夠,請你原諒”。
流產的合作計劃
海內外的蔣介石研究者中不乏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比如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教授汪榮祖。2004年,汪榮祖與臺灣學者李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出版發行。
在此書出版前,學術圈內流傳著一個說法:汪榮祖曾提出兩岸三地合作,共同撰寫《蔣介石評傳》,海外是汪榮祖,臺灣是李敖,大陸是楊天石。結果沒合作成。
本刊記者就此事向楊天石求證,楊天石表示,“確有此事”。他透露汪榮祖是自己的好友,1990年代,楊天石赴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汪榮祖是邀請人之一。兩人因為討論戊戌變法而相識相知,訪問期間,楊天石還在汪榮祖家里住了十多天。
當時,汪榮祖提出合作撰寫“評傳”,作為相知甚厚的老友,楊天石開始的時候同意參加。“為什么最后沒有參加呢,原因是他們寫得比較快,我的寫作原則是掌握了所有我認為必須掌握的資料后才動筆。當時很多蔣介石的資料我還沒看,我寫得太慢。”楊天石說。
雖然這次合作流產了,但楊天石并不覺得惋惜。當時《蔣介石評傳》剛一問世,一位臺灣的朋友就打電話給楊天石說:“幸虧你沒參加,參加了你也不能跟他們合作。他們書的基本觀點和你有很大區別”。
很快,楊天石收到了這本未能參與的作品,“一看《蔣介石評傳》序言,我就對作者的心態了然了。‘我終于結束了蔣介石,我也結束了我快意恩仇的一頁。他死了,我也度過了青春歲月,我老了。’李敖在序言中如此表達,寫這樣一部書是他的‘復仇之作’。”楊天石是心態平靜的研究者,“史學家不能這樣,要擺脫個人恩怨。歷史其實是科學。”
楊天石堅持“還原歷史”,這是排列第一的研究目的。“至于自己的著作能起什么作用,那是客觀的。我寫蔣介石的書兩岸基本上都能接受。也許,李敖不能接受。”楊天石笑言。
“彼此對罵的話不能當成結論”
隨著坊間“民國熱”的興起,國內對于民國史包括蔣介石的研究氛圍變得越來越開放。楊天石對此深有感觸。2002年出版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是楊天石研究蔣介石的第一本書。這本書的大部分研究根據毛思誠家所存的資料進行,也確立了他在蔣介石研究方面的權威。
楊天石希望通過這部作品糾正過去對蔣介石不夠全面的評價,但意料之中的爭議之激烈還是出乎了意料。“有些人攻擊我,說社科院有個楊天石,吹捧蔣介石。其實我對蔣介石的看法是八個字:既有大過又有大功。”
當時楊天石是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雜志主編,他在這個位置上干到了2005年才正式卸任。
中國社科院院長陳奎元從頭到尾讀了《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說這本書是一本扎實的學術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
楊天石說,此后,這本書終于能平靜地面對讀者。隨后出版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一書被全國31家媒體共同推選為2008年十大好書之一。
瀏覽當當網等圖書網站的書評,本刊記者發現參與該書評論的讀者不少。“我有充分的信心,因為選擇的史料都是經過反復推敲的。”楊天石說。
楊天石在2011年的新作《帝制的終結》中,再次提出了和學界主流觀點不一樣的看法。
出版前,楊天石心里也曾惴惴不安,擔心該書能否出版,也擔心出版后會不會挨批。“到2011年10月9日,心才算放下。當日,胡錦濤主席發表紀念辛亥革命的講話,我認真仔細地研讀了,認為我的觀點和中央的提法并無矛盾。”
“中央講過‘捐棄前嫌’,也講過‘撫平歷史創傷’,如果按照這個角度看民國史研究,看蔣介石研究,我們就找到了未來的方向,現在我是坦然地研究蔣介石”。
“過去我們是在打架的時候做研究,兩個人打架的時候什么狠毒的話都會說,但是彼此對罵的話不能當成結論。”
在楊天石看來,民國史研究、蔣介石研究的改變,是站在科學基礎上的,“這些新的轉變,是有利于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