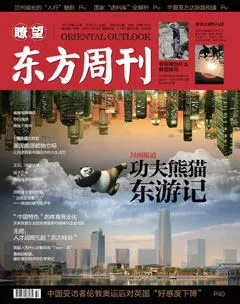魯朗的秘密:藏東南生物多樣性考察記
2012-12-29 00:00:00彭茜
瞭望東方周刊 2012年32期

在林芝的魯朗地區(qū),有著藏東南最好的原始森林。這片自然秘境廣泛分布著青藏高原特有的植物、昆蟲、鳥獸,還有世代棲息于此的工布藏族
從拉薩沿318國道一路往東至林芝地區(qū),沿途是低矮灌叢、高山草甸到蓊郁森林的景致變換。植被愈豐,空氣漸潤。不時有騎行川藏線的驢友和運送物資的卡車經(jīng)過。
翻過海拔5012米的米拉山口,便是林芝地界。尼洋河從山口發(fā)源,綿延309公里匯入雅魯藏布江。雅魯藏布大峽谷的水汽通道效應(yīng)在米拉山已是強弩之末,雨水大部分降到了米拉山以東,造就了藏東南的林濤花海。
據(jù)統(tǒng)計,藏東一林芝地區(qū)林地面積達374萬公頃,森林面積264萬公頃,森林覆蓋率達46.09%,是我國第三大林區(qū),也是我國保護最完整的原始森林之一。
在林芝的魯朗地區(qū),有著藏東南最好的原始森林。這片自然秘境廣泛分布著青藏高原特有的植物、昆蟲、鳥獸,還有世代棲,息于此的工布藏族(工布是林芝地區(qū)的古稱)。
2012年7月,一項針對魯朗地區(qū)生物多樣性的科學(xué)考察展開。來自“影像生物多樣性調(diào)查所(IBE)”的生態(tài)攝影師和公益機構(gòu)“西藏生物影像調(diào)查(TBIS)”的科考人員歷時半個多月,從海拔4500米的德木拉山口行至海拔3000多米的東久溝,徒步穿越考察了魯朗五寨花海,以影像的方式記錄了魯朗特有和珍稀瀕危物種的分布范圍、生態(tài)習(xí)性,以及這塊土地上的人類生活。
“希望此次拍攝和考察能給當(dāng)?shù)乇Wo區(qū)、林業(yè)局一些有益的建議,更希望通過這種視覺化方式把鮮活的自然之美展現(xiàn)給公眾。”此次科考隊隊長、影像生物多樣性調(diào)查所(IBE)負責(zé)人徐健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在中國科學(xué)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長楊永平看來,過去,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多停留在科學(xué)家和政府層面,缺乏生動的表述,而這次科考以影像記錄的形式讓科學(xué)走出象牙塔,使大眾可以感受到科學(xué)家的研究之美,有利于生態(tài)保護事業(yè)的持續(xù)發(fā)展。
植物:“俠女”綠絨蒿及其他
“亂抹鎏黃染對山,孤芳桀驁扯裙藍eqhterl3JFW/uH12MKO99dW/kr5CLZFqdvEuyfM3tN4=,杜鵑碎夢限風(fēng)寒。急雨常聆新葉語,垂虹喜妒彩花妍,流云奇色舞闌珊。”
這闕暗含塔黃、綠絨蒿、高山杜鵑等高原植物名稱的《浣溪沙?到魯朗拜峰臺》,是生態(tài)攝影師王辰的即興之作。從海拔4500米的德木拉山口拜峰臺一路下行至海拔3500米的魯朗花海,適應(yīng)不同海拔生長的各種奇異植物讓這位癡迷傳統(tǒng)文化的植物學(xué)碩士詩興大發(fā)。
這一路,幾乎涵蓋了北半球的所有氣候帶和植被類型,是高山生態(tài)研究的典型山區(qū)。海拔梯度的劇烈變化提供了藏東南生物多樣性的完整序列,因此成為此次魯朗科考的主要路線之一。
拜峰臺是高山草甸地帶,空氣稀薄,終年氣溫寒冷。雅魯藏布大峽谷的通道效應(yīng)使大片水汽一波波向山口涌來。云霧飄渺中三座白塔矗立,經(jīng)幡翻飛,這是藏族在高山埡口處祭祀神靈的傳統(tǒng)。低矮處則是灰背杜鵑的海洋,紫色的小花若隱若現(xiàn)。
王辰一眼便在碎石和灌叢間發(fā)現(xiàn)一株傲然挺立的藍色花朵——似多刺綠絨蒿,是林芝地區(qū)的特有物種。
這種綠絨蒿往往生長在海拔4000米以上,藍色的絲綢質(zhì)地的花瓣掛滿雨滴,身披褐色的小刺。在王辰眼中,這正是金庸小說里“青衫磊落險峰行”的俠女。
“藏地相傳有綠絨蒿生長之地,流出的水清澈圣潔,喝了能醫(yī)病。”王辰說。
埡口處高山草甸兩側(cè)的山坡是流石的匯聚。大塊巖石被風(fēng)霜雨雪侵蝕成碎塊,石塊從陡峭的山體滑落,形成流石灘。灰色的碎石堆中玉樹臨風(fēng)般挺立著數(shù)十株亮黃色塔形植物,多有一人多高,基部葉片很大,向上漸小。這就是分布在藏東南的高山植物一塔黃,其醒目的外形是為滿足高海拔地帶吸引昆蟲傳粉之需。
“塔黃因為形態(tài)獨特,在當(dāng)?shù)乇环Q為‘山神的禮物’,即便要食用它時,(人們)也會留下柱頭部分。”王辰邊說邊用相機記錄拍下周邊環(huán)境和塔黃的植株細節(jié)。
沿著遍布落石和倒木的小道繼續(xù)下行,海拔4000米處出現(xiàn)一大片高山杜鵑灌叢,拳頭大小的淡粉色花朵在雨中顧盼生姿,面積和密集程度之大讓王辰驚嘆不已。
海拔3800米附近則是林芝云杉和冷杉的海洋。
海拔陡降500米,來到接近山腳處的魯朗花海。這里曾是一片森林,由于人類上百年來的放牧活動,逐漸演變成一片開闊的林間亞高山草甸。
盛夏時節(jié)的魯朗百花盛開,黃色的雜色鐘報春垂著鈴鐺般的腦袋,覆蓋了大片草甸。紫色的金脈鳶尾也成群地生長,還有散落在草地中的馬先蒿、金絲桃等花兒作為點綴。
“與雅魯藏布大峽谷各種物種基因的交流匯集不同,各個物種在魯朗變得很穩(wěn)定,典型物種變成了優(yōu)勢種群,形成了大片的植物群落。”王辰說。這種植物群落構(gòu)成的景觀為以后發(fā)展生態(tài)旅游提供了契機。
本次科考共拍攝了200多種高等植物。高原四大花卉之中的三種:報春花、杜鵑花、綠絨蒿均被記錄。
拍鳥:相機就是我們的槍
為了更方便地記錄山地垂直帶的動植物,科考隊在海拔4500米的拜峰臺扎營,夜宿于此。
埡口受水汽通道影響,氣候變化極快,一場倏忽而至的地形雨讓隊員們紛紛躲進帳篷,吃起牦牛肉和土豆炒制的路餐,卻遲遲未見鳥類攝影師郭亮歸隊。
畢業(yè)于北大生物系的郭亮是IBE的核心成員,師從著名動物學(xué)家、大熊貓研究專家潘文石。保護區(qū)的鳥類是他的拍攝主題。
科考隊員們戲稱郭亮為“特種兵”,因為他總是身著迷彩服,背著600ram的“大炮筒’迷彩鏡頭,在清晨或傍晚出去“打鳥”,他那本枕邊書《中國鳥類野外手冊》已被翻得破爛。
雨停之時,眾人才見郭亮滿身掛著水珠走進帳篷,難掩臉上的興奮:“終于拍到了黑胸歌鴝!”
黑胸歌鴝是分布于西藏東南部的一種高山鳥類,夏季棲于亞高山林至林線以上的灌叢和矮樹叢。因為其上體全灰,眉紋白,腹部雪白,被稱為“烏云蓋雪”。此鳥喉部還有一抹寶石紅,叫聲婉轉(zhuǎn),優(yōu)雅可愛。
“7月是鳥類育雛的季節(jié),黑胸歌鴝習(xí)慣把巢筑在埡口處的灌叢下。”郭亮說,他用望遠鏡確定了它的活動范圍后,便在十多米外靜靜蹲守。
守了兩個多小時后,驟雨初停。黑胸歌鴝跳上灌叢晾曬羽毛,郭亮抓拍了一張?zhí)貙憽?br/> 在埡口的灌叢中,郭亮還偶遇一個藍額紅尾鴝的巢,里面還有四枚小小的鳥蛋。但是他只看了一眼便匆匆離開。
“在鳥類的繁殖季節(jié)要特別注意,不能刻意尋找它們的巢,如果被鳥兒發(fā)現(xiàn)有人類干擾過它們的巢,就會棄巢而去。”郭亮說。
海拔越高,鳥類的繁殖季節(jié)就越晚。高海拔的鳥類還在孵化,低海拔的小鳥已經(jīng)可以隨著鳥媽媽出去覓食了。除了埡口處的灌叢,魯朗廣袤的原始森林由于較少受到人類活動干擾,為鳥類棲息提供了極好的生境。
每日,郭亮都扛著“大炮筒”沿山路而下,如獨行俠般避開眾人去找鳥。在他看來,對該區(qū)域鳥類的搜尋要多次重復(fù)同一條線路,直至發(fā)現(xiàn)鳥類的數(shù)量經(jīng)歷一個倒‘U’型曲線的變化,才是對生物多樣性的科學(xué)記錄。
靠聽聲辨位和目力搜尋,他又記錄到了黑鵯、白頸鶇、灰腹噪鹛、白眉朱雀等多種林中鳥類,它們翱翔于天際或佇立枝頭的瞬間都被定格在相機中。
“涉及鳥類的生物多樣性調(diào)查曾經(jīng)或用氣槍、或用粘網(wǎng)捕鳥鑒定。如今相機就是我們的槍,先記錄下鳥兒的美麗,讓公眾喜愛,然后再慢慢滲透保護的意識。”郭亮說。在此次科考中,他共拍攝到60多種鳥類,其中有藏馬雞、四川雉鶉等國家級重點保護動物。
“微觀之美”:昆蟲記
這片原始森林也是昆蟲的樂土。
科研結(jié)果顯示,藏東南山地自第四紀(jì)以來有過多次冰期,但雅魯藏布大峽谷的水汽通道使得很多低海拔區(qū)域成為昆蟲的天然避難所。在林芝地區(qū)的墨脫、波密、林芝、米林四個縣及周邊區(qū)域,有20目206科1985種昆蟲;昆蟲科目主要集中在鱗翅目、同翅目、鞘翅目和膜翅目,占總科數(shù)的56.31%。
魯朗林海中有很多橫生的倒木。揭開樹皮上厚重的苔蘚,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微觀王國:腐木上生活著大量的植食性昆蟲,同時還棲息著很多它們的天敵。
生態(tài)攝影師雷波是位發(fā)現(xiàn)“微觀之美”的高手,帶上100mm的百微鏡頭和自制閃光燈,他記錄下了50多種昆蟲圖片,昆蟲的復(fù)眼、腿腳絨毛、翅膀上的紋路都纖毫畢現(xiàn),極具質(zhì)感。
“除了相機,不帶走任何東西。”這是他一直遵循的生態(tài)攝影原則。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極為脆弱的青藏高原,不采標(biāo)本、帶回拍攝產(chǎn)生的垃圾都是對當(dāng)?shù)丨h(huán)境的保護。
一次拍攝過程中,由于昆蟲爬行太快而無法拍出細節(jié)。一旁的協(xié)作急了,一把抓過蟲子,放在雷波面前讓他拍攝。
雷波連連擺手,在他看來,“每個角落都有漂亮的場景,需要發(fā)現(xiàn)自然的美,而不是通過人為去布景”。
“物種的多樣性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拍攝題材,自然總帶給你無法想象的驚喜,僅僅是那些變幻莫測的自然光線就值得你研究七八年。”雷波說。
遺憾的是,科考隊此次沒有拍攝記錄到獸類。
“冬秋季節(jié)拍到大型動物的可能性更大,夏季它們會躲到海拔更高的地方。”科考隊長徐健說。考察地離公路和人類居住區(qū)相對較近也是一方面原因。
魯朗的人:工布藏族
對于世代生活在魯朗林海的工布藏族人來說,“靠山吃山”是從祖輩沿襲至今的習(xí)慣。
千百年來,當(dāng)?shù)厝硕加嗅鳙C的習(xí)俗,林中的獐子、熊、血雉、野山羊都是獵手們的槍下之物。彼時進入林中總要十二分小心,因為不經(jīng)意間就會遇上獵手設(shè)下的陷阱或獵夾。
如今,禁獵令實施17年后,尚能從家家戶戶保存的弓箭中覓得當(dāng)年狩獵的痕跡。只不過當(dāng)年的“射獵之箭”已經(jīng)變成了“競技之箭”。流傳千年的“工布響箭”——圓錐形的木制箭頭上有多個小孔,射出后會因氣流作用發(fā)出尖銳的哨聲——已成為當(dāng)?shù)毓?jié)慶時的一項競技活動。
有趣的是,越來越多的工布人家開始持有韓國產(chǎn)的弓箭,制作精良的專業(yè)弓箭可以幫助他們在射箭競技中取得佳績。
1998年,西藏自治區(qū)政府對林區(qū)全面實施禁伐,昔日以販賣木材為生的“木頭財政”也開始淡出藏東林區(qū)。曾經(jīng)的獵手成了今日的護林員。當(dāng)?shù)剞r(nóng)牧民組成護林隊,每日背著干糧上山巡邏,阻止亂砍濫伐、盜獵等行為,消除森林火災(zāi)隱患。
山腳下的工布藏族村落,多就地取材,以木石結(jié)構(gòu)搭建居所。由于氣候濕潤多雨,這里的建筑與西藏其他地區(qū)的民居不同,多是尖頂,利于排水。尖屋頂之下即為通風(fēng)的儲藏室。曾經(jīng)這里堆滿動物毛皮、干肉和擦得锃亮的獵槍,如今則多成為晾曬藏藥材的場所。
工布藏族人正以另一種方式獲取這片山林的饋贈——采集林下資源。
幾乎每個工布藏族人心中都有份采藥月歷:五月采野草莓根,六七月采綠絨蒿、手掌參,八月采紅景天、桃兒七。
在魯朗鎮(zhèn)東巴才村,科考隊員們遇到了20歲的藏族姑娘達娃卓瑪。她剛剛參加完高考,暑假幾乎都是在山林里度過的。
早晨9點,她開著摩托車載著媽媽上山挖手掌參。這種長相酷似手掌的參類既可入藥,也是制作魯朗美食“石鍋雞”的主料。她們用小鋤頭從地里挖出根部,裝滿一袋,晚上八點才歸家。
對達娃卓瑪來說,綠絨蒿、紅景天相對更易采集,直接連根拔起后曬干,然后等待拉薩藏藥廠一年一度的收購。
一場大雨過后,魯朗廣袤的林海中青岡菌、大腳菇、松茸等菌類紛紛露頭。達娃卓瑪?shù)哪棠炭倳诖藭r提著口袋出現(xiàn)在林中。她認得五種食用菌,撿回的蘑菇一部分被她熬制成鮮美的菌湯,一部分被達娃卓瑪?shù)拿妹媚玫侥襄劝屯叻逵^景臺賣給游客。
對于這樣的一戶家庭來說,除了以放牧和農(nóng)耕維持生計,采集藏藥材和菌類是補貼家用的重要手段。盡管一天辛勞換來的是看起來并不豐厚的收入:松蘿一斤賣5元,綠絨蒿一斤20元,紅景天一斤30元,菌類一斤50至60元。
東巴才村和鄰近的五個村子幾乎家家采藥,曾在東巴才村當(dāng)了22年村長的達瓦正在擔(dān)心一些不恰當(dāng)?shù)牟杉绞綄⒔o當(dāng)?shù)厣鷳B(tài)帶來危害。在他的記憶里,祖輩采集綠絨蒿等植物時只砍去地上部分,而保留地下的根莖使其繼續(xù)生長。如今,村里人多采用連根拔除的采集方式。
“高海拔植物年生長量很低,不像水稻一年一季。‘?dāng)夭莩牟杉遣豢沙掷m(xù)的。”中國科學(xué)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長楊永平對本刊記者說。
魯朗的原始森林中有著多達1046種的植物,達瓦說,必須盡快找到保護它們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