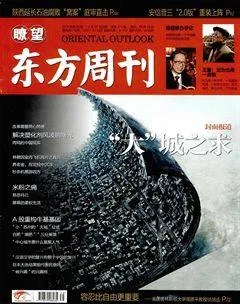“漢語漢字的復興有賴于中國的復興”
“‘普北班’20年來培訓了3000名美國著名高校學員,訓練了1200名新師資,已成為美國高校舉辦在華高校短期漢語培訓班的成功樣板。”2012年7月14日,北京師范大學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漢語合作項目(“普北班”)20周年紀念會上,作為創始人的周質平說到“普北班”20年的成長時頗為自豪。
“普北班”是“普林斯頓北京暑期漢語培訓班”的簡稱,旨在通過兩個月的強化教學全面提高學生的漢語水平。成立于1993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合辦。北師大主要負責提供住宿和教室,每年有2-4個老師參加教學。其他如招生、課程設置、培訓班的運作程序、教師招聘和培訓、教師酬金的發放等都由普林斯頓大學負責。
據周質平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這種中美高校間合作新模式的可行性最初曾受到種種質疑,但經過20年的實踐,如今,包括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杜克大學在內的美國諸多高校也都紛紛采取了這種模式和中國高校合作辦學。
“‘普北班’目前在對外漢語教學領域可以說是歷史最悠久、質量最高、辦學態度最嚴謹的班。”周質平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普北班”每年面向美國及全世界招收150-160名學生。如今,這些學生已遍及美國政府機構、學術機構、商業機構等各個領域。“我們每年帶著一批美國學生來中國學習生活兩個月,大概也對加深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有一定的貢獻吧。”周質平說。
在這個生于上海、長在臺灣、大半輩子呆在美國的華人學者看來,能到中國內地來教漢語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語言誓約
“夏天,如果你在北京師范大學附近看到洋人和洋人之間互相講中文,肯定是‘普北班’的學生。”周質平說。
“普北班”有一項特殊規定:開班之前,每個學生都要簽訂一份“語言誓約”。其中明確要求,學生在北京學習期間,不得使用英語或其他母語,只能說漢語。如果被發現說漢語以外的其他語言,會被開除,學費不退還。教師雖然沒有“誓約”,但若被發現用英語教學或談話也會受到批評。
“語言誓約”的傳統源自周質平曾經任教的美國明德大學暑期中文學校。
上世紀70年代,周質平從臺灣赴美,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1983年,他開始接觸對外漢語教學工作,出任美國明德大學暑期中文學校的校長。
明德大學是位于美國東北部佛蒙特州的一所文理學院,1966年,明德大學開辦暑期中文學校,秉承了美國中文教學的先行者、語言學大師趙元任先生倡導的大小班結合、大班講解練習、小班集中操練的教學方式。對很多美國人來說,在美國境內學漢語,明德暑期中文學校往往是首選。
這種“沉浸式教學”是明德暑期中文學校的最大特色,旨在為學生營造全中文的學習環境,簽訂“語言誓約”亦出自這樣的考慮。
“這個方法固然好,可是你在美國東北角搞一個中文沉浸式的教學,怎么也真不了,大環境畢竟還是英語環境。”執掌明德暑期中文學校9年后,周質平希望能到中國開展真正的、中文環境的沉浸式教學法。
在周質平的多方奔走下,1992年,普林斯頓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達成合作協議,成立了“普北班”。翌年暑假,第一批來自全美各著名大學的100多名本科生、研究生到“普北班”學習。
“既然你們來參加這個班,就要用漢語拼音和簡化字”
在“普北班”,周質平一直努力推廣簡化字和漢語拼音。
“我覺得中國的文字在海外始終沒有統一,所以我想把簡化字在海外和港臺地區推廣。”周質平說。
在他看來,現在中國內地用的都是簡化字,語言文字就應該跟著多數人走,這沒有什么好爭議的。這是給自己方便,也是給別人方便。“你在那里堅持二十世紀早期的書寫方式,會造成很大的不便利。”
“我和美國學生說,繁體字是二十世紀中期之前中國人用的,簡化字是二十世紀中期以后中國人用的字,毫無疑義要學中國人現在用的中文。”
“普北班”中一些來自港臺的學生,對于繁體字有依戀情結,對簡化字和漢語拼音則比較抗拒。
“我對來參加這個班的學生包括港臺學生都明確說明,既然你們來參加這個班,就要用漢語拼音和簡化字。文字上的統一我覺得是很重要的。所以‘普北班’所有的教材都使用簡化字。”
周質平給港臺學生以英文舉例:現在有兩種英文,一個是美國大陸的英文,一個是夏威夷的英文,夏威夷的英文發音和拼法都和美國大陸有一定的出入,你要學哪一種?如果你要堅持學夏威夷的英文,那么一旦到了美國大陸,會造成很大的不便。
“有了這樣的類比,他們對于簡化字和拼音的抗拒都會慢慢消解,這也是我們這個班的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獲。”周質平說。
教材風波
周質平向本刊記者回憶,“普北班”創辦早期也曾經遇到一些“矛盾或者不協調”,主要集中體現在教材上。
2000年,北京師范大學一位對外漢語教師在《北京社會科學》上撰文,指“普北班”的教科書中“滲透了美國和臺灣的意識形態”。北師大受到一定的壓力,希望周質平他們修改教材。
“《紐約時報》曾經就此登了一則消息,之后美國的很多媒體和刊物,如《美國高等教育年刊》、CNN等都報道采訪了這件事。我自己也寫了一篇名為《阿Q,義和團與對外漢語教學》的文章作了回應。”周質平回憶。
“比如我們一篇課文是給剛到中國的美國學生學習的,講到‘廁所里沒有衛生紙’。他們覺得這個不合適:為什么一定要用這樣的題目來敘述中國呢?”
最后,為了能讓這個班繼續辦下去,周質平們對教材做了一些修改。
“我覺得對外漢語的一個主要職能是教外國人怎么把漢語說好,怎么說得對,字正腔圓。至于他們對中國的事情怎么想,那是他們的事情。”周質平說。
外國學生開始發現中文是“有用”的
在周質平看來,與其他的漢語教學機構相比,“普北班”最大的特點,在于施行的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教學方法。
“我們不搞一些時髦的理論。從80年代開始,在美國有一些影響很大的教學法,如‘能力語言教學法’、‘任務法’等,這些我們都沒有采用。我們主要實行小班制。我們相信學習語言還是要從具體的聽說開始,而不是講一些非常空泛的所謂文化議題。”
針對過去幾十年來在對外漢語教學界中存在的“重流利而輕準確”“重功能而輕結構”等傾向,“普北班”始終堅持“準確”且不忽視結構。
“現在很多語言學習班往往會開設諸如‘商業中文’之類的課程,在我看來,只有中文商用,而沒有商用中文。這種過分專業化的語言訓練,往往是為了迎合某些學生急功近利的心態。”
“普北班”如今已走過了20年,回顧這些年,周質平說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漢語漢字的復興有賴于中國的復興,而不是中國的復興有賴于漢語漢字的改革”。
“早年美國學生學習漢語往往是一種學術上的興趣,還有一些是獵奇,對李小龍、陰陽八卦等有興趣。而現在很多美國學生學習中文,是覺得中文是一種有用的語言,能對他們將來的工作有所提升。這是很值得中國人驕傲的。”
他舉自己所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為例,“現在選讀中文的學生數量僅次于西班牙文,甚至超過了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這是在我40年前剛到美國時所不能預見的。這樣的改變當然是因為中國國力加強了,中國的崛起引發了西方世界對中國語言文字的重視,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