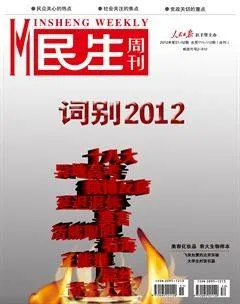雙重國籍是與非


俏江南創始人張蘭的“雙重國籍”事件,由一起看似簡單的雙重身份之爭(政協委員、外國國籍)演變成一個公共事件,并由此掀開了雙重國籍亂象的冰山一角。
“放棄一國國籍就等于放棄一國的福利。在加拿大持有護照,在中國分享醫保、房補等福利,可以便利地穿梭在兩國之間。”作為擁有雙重國籍的人員之一,王晴曾經樂此不疲地享受著由此帶來的權利、福利和便利。然而,令她沒有想到的是,在她利用雙重國籍為自己換來更多社會資本的背后,是難以掙脫的枷鎖和痛楚。
無形的枷鎖
2012年7月26日,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貝爾斯大街的王晴急匆匆趕回中國,懇請北京市朝陽區民政局依法撤銷2009年5月31日核發的行政行為——“京朝離字050901949號”《離婚證》。
王晴在發往朝陽區民政局的《撤銷<離婚證>申請書》中這樣寫道:加入加拿大國籍后,和丈夫李文良每年都在北京生活、居住一段時間,因夫妻感情并不合睦,2009年5月31日,雙方隱瞞已經加入加拿大國籍的事實,持無效的中國身份證辦理了《離婚證》。
王晴申請撤銷《離婚證》的依據是,根據《婚姻登記條例》相關規定,民政部門僅能辦理中國公民的離婚登記。王晴與李文良夫婦分別于2001年和2002年加入加拿大國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9條規定,兩人在加入加拿大國籍時已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王晴為什么要自曝中國公民身份的喪失,并推翻自愿在朝陽區民政局領取核發的《離婚證》呢?
王晴的代理律師周新廣告訴《民生周刊》記者,事實上,兩人于2009年在國內辦理《離婚證》,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假離婚”鬧劇。
“假離婚”前,李文良告訴王晴,在國內辦理《離婚證》只是做做樣子,是和過去的不愉快做個告別,更何況兩個人都已經是加拿大國籍人員,回到加拿大以后仍然是夫妻,可以重新開始新的生活。王晴認為既然是假離婚,在簽訂《離婚協議》時,有關財產分割和孩子的撫養權方面并沒有過多留意。
回到加拿大后,由于感情徹底破裂,2009年9月,兩人向加拿大當地法庭再度提交了離婚申請。
2010年,王晴和李文良在加拿大依照本國的法律規定辦理了離婚。加拿大國家法律規定,在辦理離婚案件時,涉及分割財產和孩子撫養權的問題需另行起訴。
那么,上述二人在中國辦理《離婚證》時所達成的財產分割和孩子撫養問題協議是否有效呢?
2011年底,因財產分割和孩子撫養權問題,王晴和李文良在加拿大對簿公堂。李文良出示了朝陽區民政局核發的《離婚證》及《離婚協議書》,加拿大法官知曉中國是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國家,對《離婚證》的合法性產生了較大的質疑。為了確保判決的合法,加拿大法官要求中國政府機關或司法機構依照中國法律對《離婚證》的效力進行法律上的確認。
周新廣律師分析認為,李文良是鉆了雙重國籍的空子,在中國辦理的《離婚協議》中隱藏了財產,占有了孩子的撫養權。
潛規則盛行
事實上,從90年代末開始,雙重國籍現象已經日益演化成人盡皆知的潛規則,既無人監管,也無法合法化。
《民生周刊》記者采訪部分移民英、美、加拿大等國多位同時持有中國國籍的華人后了解到,他們尋求雙重國籍的原因是,自豪于某一國家的公民身份,但同時也希望能夠保有另一國家住房、醫療、購置不動產、投資、旅行等優惠及便利條件。
2011年,《民生周刊》記者在浙江采訪了解到,王明夫婦幾年前因留學而移民澳大利亞,但仍在國內做著建筑行業生意。作為外商,他享受了中國國內各種政策優惠。但他坦言,自己并沒有放棄中國國籍,因為在國內做生意和生活,作為外國人還是有諸多不方便,澳大利亞國民身份只在需要的時候才被使用;更多時候,他仍然是中國人。
那么現在困擾中國的雙重國籍是如何形成的呢?
民政專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介紹,有兩類情況導致了雙重國籍的出現:一是留學人員或以其他方式移居國外的中國人在取得外國國籍后,并不報告,仍然保留中國身份證及戶口,回國后繼續使用中國公民的身份證;二是中國公民在境外加入外國國籍后,向我駐外使領館申請退出中國國籍,而由于外交部門和公安部門的信息分享不太及時,導致公安機關未能及時注銷已入外國國籍者的中國國籍信息,造成雙重國籍。
有關專家認為,《國籍法》第9條規定:“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該法第14條同時規定:“中國國籍的取得、喪失和恢復,除第9條規定以外,必須辦理申請手續。”兩條法律條款之間存在著矛盾。也就是說按照第9條的規定,定居國外并取得外國國籍而喪失中國國籍的人,無需根據第14條的規定辦理喪失或者退出中國國籍的申請手續,其國籍變動即可生效。
有專家認為,因“個人不報告”而具有雙重國籍者,根據現行《國籍法》,其責任并不在個人。對此,應該從完善《國籍法》的配套制度建設著手,以法規或部門規章的形式規定:定居國外并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而喪失中國國籍者,其國籍變動無需經申請或審批即可生效,但當事人應向中國的主管部門通報或進行登記。
加強監管
圍繞雙重國籍,從來不缺少爭論。
歷史上,中國的雙重國籍問題經歷了“默認”至“廢除”的演變。
夏學鑾告訴《民生周刊》記者,在清王朝晚期和民國時期,中國承認雙重國籍和無國籍;20世紀50年代之前,中國對雙重國籍采取“默認”的態度。在解放初期的一段時間,相關政策也是非常寬松的。
20世紀50年代,印尼等東南亞國家實行排擠和迫害華人政策,為了保護華僑,中國政府和印尼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于雙重國籍的條約》,廢除雙重國籍。
周恩來總理在1955年的亞非會議期間曾以外長身份與印尼外長簽訂了解決華僑國籍問題的條約,規定海外華僑在一人一國籍的原則下,自愿選籍,并由此奠定中國實行一人一籍的國籍政策。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單一國籍制在越來越國際化的生活中漸漸成為了障礙,有九成的新移民并不愿意放棄中國國籍。近幾年,多有商界、文化界、知識界高層人士通過與中央高層見面的渠道呼吁實施雙重國籍,這一問題也數次被高層討論。雙重國籍能否在中國獲得承認并使其合法化呢?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向《民生周刊》記者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現階段我國不宜確立雙重國籍制度。就個人而言,單一國籍更有利于維護海外華人的利益,可以更好地保護海外華人在國外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更充分地尋求當地的司法救濟。
但著有《中國移民史》、《中國人口發展史》等專著的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卻認為,如果國籍政策不放開,無法留住那些甘愿為中國服務的國際高端人才,解決不了人才流失的問題。
按照美國《華爾街日報》2010年1月援引美國政府有關研究機構的最新統計數據,畢業5年以上仍然留在美國的外國理工科博士生,中國高達92%。而絕大多數亞洲國家博士畢業生在美滯留比例多在百分之三四十以下,泰國甚至只有7%。中國目前每年有超過20萬人選擇出國留學,而且規模將會越來越大。由此看來,反對雙重國籍并不能阻止人才流失,因為如果一個人具備移民歐美的條件和主觀意愿,即使剝奪本國國籍還是會選擇移民;同時,因為失去了祖籍國的國籍,他們往往還把本可能想部分保留在祖籍國的產業干脆全部轉移到海外。
然而,有關專家分析認為,《國籍法》的修改,涉及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話題。短期內放開國籍政策的可能性不大。而雙重國籍帶來的實際收益,比較顯見的也只是吸引人才歸國。
馬懷德認為,既然雙重國籍在中國無法使之合法化,那么就要認真監管,按照《國籍法》的規定嚴格“堵死”雙重國籍的潛規則現象,以維護法律的嚴肅性。
“中國政府應該在出入境的方式上加強管理,能夠及時獲得國外的相關信息。”馬懷德表示,海外華人在中國生產生活時應提交相關身份證明,同時進行嚴格管理。
2012年6月30日新通過的《出入境管理法》明確規定:國家建立統一的出入境管理信息平臺,實現有關管理部門信息共享。
此外,據公安部消息,在移民管理方面,中方將與各國同行深入挖掘合作潛力,共同提高移民管理能力,促進人員合法有序流動,有效應對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問題帶來的挑戰。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晴、李文良、王明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