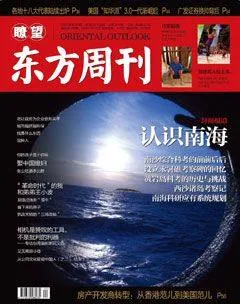勿讓政府為企業債務買單
日前,中國社科院李揚副院長領銜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國整體債務水平雖相對較低,但企業債務水平已經超過警戒線達到105.4%,在所研究的20個樣本國家中最高。這項研究反映了中國經濟運行中的部分現實。
如長期來看,中國企業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發揮了比較積極的作用,與家庭部門的消費相比,企業部門的投資扮演了更突出的角色。不過這種狀況已經開始有所轉變,2012年一季度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達到60.3%,投資對GDP的貢獻率是44.1%。
再如,中國的金融系統更近于“基于銀行的金融系統”,而非“基于市場的金融系統”。與資本市場相比,銀行渠道是中國企業更重要的融資來源。
以上現實是相互聯系的。當消費處于較低水平,人們對產品需求的多樣性
要求不高,主要集中在滿足較低需求層次的商品之上。這類商品的供求周期相對穩定,企業生產這些商品能夠獲得的回報主要來自規模報酬。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產品及服務消費的個性化、新穎化程度也與日俱增,企業需要以更多的創新去對位變動不居的需求,一旦開發出適銷對路的產品與服務,則可能獲得極大的回報,但若經營失敗,破產的風險也高。與此相關的不確定性,很難由長于平滑風險、期待穩定回報的銀行來吸收。此時就需要一個足夠規模的高效率的金融市場,來將企業系統以創新迎合多樣性需求產生的不確定性分散掉。
在這個金融市場中,有的人眼光卓越,能夠迅速發現有價值的企業并加以投資,由此分享其創新收益;另一些人投資失敗,承擔損失。整體來看,只要企業系統的創新是成功的,其產生的超額回報規模遠大于失敗的損失,那么企業系統和金融系統就能夠實現良性互動。
企業債務水平過高表面上反映了金融系統由銀行導向向市場導向轉變的滯后,或者說資本市場發展的滯后,但實際上對應著企業系統本身創新能力的不足。
只有不再滿足于向國內國際市場提供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低端制造業產品,而力求開發自身核心競爭力去迎合乃至“創造”新市場,這樣的企業才會對高效的金融市場提出迫切的要求,才會吸引更多有眼光的投資人加入到金融市場之中。
對金融市場或投資人來說,如何通過這個機制把具備創新能力的企業識別出來非常關鍵,也難以做到。但從游戲規則來看,把那些缺乏創新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企業淘汰出去,是有可能并且至關重要。
盡管我國2001年就出臺了《虧損上市公司暫停上市和終止上市實施辦法》,但退出機制一直不順暢。十年之后,證監會還要不斷出臺文件來繼續推進“上市公司退市機制建設”。按照現有的規則,該退出的很難及時退出,造成上市企業魚龍混雜,提升了投資者判斷和識別的難度,也分散了那些真正有創新能力的企業所應當獲得的資源。這種局面如果長期得不到改變,最終后果就是“劣企驅逐良企”、“市場淪為賭場”。
過高的企業債務,除了經過企業系統創新和金融系統轉變而逐漸部分轉化為股權融資之外,還有可能由企業債務轉變為政府債務。三大評級公司之一的惠譽,于5月14日發出警告,可能在未來12~18個月下調中國的信用評級,主要是因為中央政府正承擔地方政府及銀行的不良債務,這些債務將轉移到中央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上。地方政府和銀行所承擔的不良債務,相當部分是對企業部門的不良債權。
解決企業債務水平過高的問題,不是簡單的轉變債務主體就可以一了百了。這樣做只會導致分散的風險向系統化的風險集聚,一旦突破臨界點,將帶來巨大的宏觀經濟風險。只有加強微觀層面企業創新能力的培育和制度層面金融市場規則的建構,營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才能在經濟結構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中,實現企業系統與金融系統的平穩過渡,以及與之相關的企業財務結構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