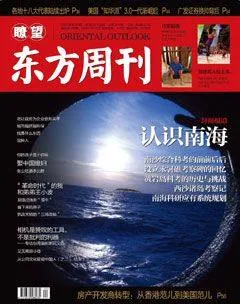認識南海

主要采訪對象:本文涉及采訪對象(按照在本組報道中出現順序):
同濟大學海洋地質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 劉志飛
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南海開放共享航次首席科學家 尚曉東
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重大研究計劃“南海深海過程演變”負責人 汪品先
大連理工大學教授、“973”項目“深海工程結構的極端環境作用與全壽命服役安全”負責人 滕斌
中國海洋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徐志良
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環境監測中心教授 柯東勝
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員 丁永耀
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員、南沙綜合科學考察負責人 陳清潮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質研究員 趙煥庭
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珊瑚礁地質研究員 朱袁智
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地質地貌方向高級工程師 宋朝景
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地貌方向高級工程師 許宗潘
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質方向高級工程師 黃成發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李寶田
6月中旬,一艘法國考察船將搭載來自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出海。作為目前中國最大南海科學研究項目的一部分,他們由獅城新加坡北上,縱貫至南海北部海域,然后折回。
強大的資金支持是中國科學家得以成行的關鍵因素。這個2011年啟動的“南海深海過程演變”計劃預算1. 5億元人民幣,使得平均每天超過15萬元的考察經費得以落實。
用老科學家們的說法,幾十年的夢想成真。
其實僅僅就在3年前,2009年,當項目負責人、中國科學院院士汪品先第一次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提出申請時,并沒有得到批準。
那一年,這個領域的“重大研究計劃”被“黑河流域生態- - -水文過程集成研究”奪得。后者希望“為國家內陸河流域水安全、生態安全以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理論和科技支撐”。
“有些人提出問題:南海問題為什么要進行深海研究?研究近海不是也可以嗎?”汪品先的助手、同濟大學海洋地質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劉志飛向《望東方周刊》回憶說。
那個時候,已經陸續在南海北部陸坡深海區發現天然氣、天然氣水合物。作為一門尖端科學,來自北美、歐洲的科學家也紛紛前往南海,希望對1990年發現的“深部生物圈”有所突破。
正如此次航行必須搭乘外國考察船一樣,直到今天,中國科學家的南海之旅仍然需要更為強力的鼓勵和支持,“我們的船和設備只能得到10米深的巖心,法國的可以在兩小時之內得到四五十米深。”劉志飛比較說。
認識南海,已經是幾代科學工作者的夢想。《望東方周刊》拜訪的數位科學家都講述了自己的南海故事,以及對那片夢想之海的喜愛。值得欣慰的是,他們的期望正在成為現實。
中國人南海研究的一大步,也許只是人類海洋科學歷程的一小步。但是對于今日中國而言,認識南海,理應成為科學界乃至全體國人的共識與任務。

一船難求
對于今天中國有多少科學工作者在研究南海,從狹義到廣義有不同估計:近萬人至10萬人不等。為他們提供經費的南海科學項目主要集中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國家科技部、中國科學院、國土資源部及歸其領導的國家海洋局。
“南海深海過程演變”計劃是所有項目中最大的。作為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重大研究計劃,它將自2011年起到2018年,每年投入3000萬到4000萬元,研究南海形成的根本問題。“每年都有不同的科學家申請不同的科技立項。此外,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還有20多個南海科考小項目。”劉志飛說。
科技部的南海重大項目主要依托“973”計劃,即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國土資源部的項目主要調查基本信息,此外就是中國海油的能源科學項目。
中國科學院的南海項目主要由中科院海洋所、南海海洋研究所承擔。作為中國最好的海洋研究機構,它們擁有顯示自身地位的標志:考察船。劉志飛說,通常情況下只有達到千萬級的項目才用得起考察船。在高校里,也只有中國海洋大學擁有自己的考察船。
船,是海洋科學研究的基礎。“我們南海所有30多年,對最遠的南沙已經有30多個科考航次。在整個南海海域有七八十個航次。”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員尚曉東說。他目前擔任2012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南海開放共享航次首席科學家,“南海所一共3艘考察船,一艘每天燃油費就要花費10萬元。”
南海開放共享航次就是為了解決“船少”的問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于2009年開始試點資助“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海洋科學調查船時費”,用1000萬元資助了5次共享航行。其中由南海海洋研究所牽頭的一次,有十幾個單位的50多人,歷時32天,涉及20多個項目。
尚曉東說,這些考察以基礎研究為主,除南海外也包括黃海、東海和渤海等。在 2012年的9個航次、約300天中有3個涉及南海海域,根據以往經驗可以搭乘幾十個項目。
2012年共享航次計劃發布兩個月,就收到200多份申請,幾乎涵蓋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所有的基金項目類型。總之,“一票難求”。
09轉折
就南海的基礎科學研究而言,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項目散布最廣,分散在各個與南海研究有關的科研機構、高校。
“一直以來,我國研究南海領域的科考項目十分傳統和分散,比如要回答南海如何形成等基礎問題都很難做到。要對重點科學問題進行攻關和探索,很少有機構和項目的人力、財力能夠接濟得上。”中科院院士汪品先告訴《望東方周刊》。
2001年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設立了重大研究計劃。此類項目集中交叉學科力量、周期相對較長。汪品先自2007年開始醞釀,兩年后第一次提出申請,未能如愿。
不過第二年,項目終于通過評估,成為中國海洋領域有史以來最大的科研計劃。
劉志飛所在的同濟大學海洋地質國家重點實驗室,2008年經費在60萬到80萬之間,2009年增至500萬,2010年和2011年分別撥款700萬、1000萬元。“也賦予了我們寬松的自主權,學校覺得哪些領域需要重點投入,便可自主決定。以往都要提出申請,長年累月等候回復”。
2009年前后,可以說是中國海洋研究、特別是南海研究的一個分水嶺。以“973”項目為例,2004年到2008年有6個關于海洋的項目,其中標題含有“南海”的一個,即“南海大陸邊緣動力學及油氣資源潛力”。2009至今,“973”中已有9個海洋相關項目,3個為南海研究。
同樣感受到近年來轉變的還有滕斌,大連理工大學教授,目前主持一項“973”項目- - -“深海工程結構的極端環境作用與全壽命服役安全”。
這其實是一個深海開發的保障研究。在宏觀層面上講,它關注海洋環境、風流量和內波等情況。具體而言,就是海洋環境對作業平臺的影響,比如平臺的結構、強度,受力后的累計效應以及損傷等等。
2012年5月,“海洋石油981”在南海開鉆,滕斌的同事就在現場,他則自己在實驗室里處理前方傳回的數據。
“之前的基礎科學項目多是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那邊申請,大概有20%的項目能夠拿到研究資金。”滕斌告訴本刊記者,他做此類研究已有20多年,經費從開始的十幾萬元提高到目前的千萬元級別。
據滕斌介紹,這一領域的研究是一個世界性課題, “原來我們并沒有往深海里去發展,‘海洋石油981’之前的只達到300米水深。”他表示,這一項目也并不專門針對南海。
但隨著對于南海關注度的提高,這個海域必須是重點,“首先是中國的能源需求越來越大,陸地上的開采已經差不多了,進口越來越多,開發南海顯得非常急迫;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一些南海周邊國家都在搶資源,這一點也加速我們下決心,保護我們的海洋。”
“深海工程結構的極端環境作用與全壽命服役安全”自2011年11月立項,至2016年結束,預算3200萬元人民幣。
滕斌認為,就一個院校科研項目而言,它與西方水平相差不多,還有自己的特色和先進之處。但是“在大型工程實施方面,引入國際商業元素后就感到有差距。比如西方大型船級社通常規模大,做的研究很全,這一點就跟西方有差距。”
從開采鳥糞開始的研究
“我國對南海的研究,早期可以追溯到民國時期。民國初年就有一些專家開始對南海進行研究。”中國海洋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徐志良告訴《望東方周刊》,這些工作開始主要集中在更好開采鳥糞和漁業生產商。
到1933年,廣東省建設廳已經制定出建設西沙群島開發計劃。3年后,根據在香港召開的遠東氣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