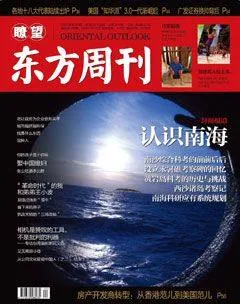張公吃酒李公醉
在《水滸傳》里,西門慶很早就死了---他跟潘金蓮?fù)禋g,害死武大郎,被武松殺死在獅子樓。這算是惡有惡報、大快人心。但《金瓶梅》的作者看不起如此幼稚淺薄的故事:一個惡霸富豪占取了賣餅漢子的老婆,算得了什么事情呢?正義如此容易得到伸張,世界就不像個世界了!
于是《金瓶梅》從這里開始改寫。在獅子樓上,多出個向西門慶報訊的皂隸李外傳。當武松告官不應(yīng)、自來尋仇時,機警的西門慶遠遠看見,趕緊跳窗逃走了。武松殺不了西門慶,力氣無處用,提起李外傳從酒樓窗中扔到當街;猶不解恨,又下得樓來往他兜襠踢上兩腳,于是嗚呼哀哉,斷氣身亡。眾人以為他認錯了人,告訴他此人不是西門慶,武松的回答十分滑稽:“我問他,如何不說?我所以打他。原來不經(jīng)打,就死了。”死原來是李外傳的錯:他不經(jīng)打。小說于此感嘆到:“張公吃酒李公醉。”
當時武松的身份,乃是清河縣的巡捕都頭,相當于縣公安局的刑警大隊長。此前,他曾在景陽岡打虎,是為民除害的英雄,又曾為知縣押送金銀到京城賄賂上司,是老爺?shù)挠H信。或許,一怒之下打死個衙門的小差役,他也不覺得是太大的事情?但這案子審起來,因西門慶大把使錢,上下打點,方向就變了,成了武松醉酒尋釁,為細故斗毆殺人,西門慶的影子都不在案卷里出現(xiàn)。
縣太爺定案,需要旁證,這當然沒有多少難處;需要口供,也“朦朧取了供招”---這表明武松是認了罪的。你要是受《水滸傳》的影響,難免會驚詫:武松這樣的英雄,怎么可能報仇不成,還低頭認罪?
但這是《金瓶梅》,它不相信正義也不相信英雄。縣太爺?shù)男艞l,叫作“人是苦蟲,不打不招”。這話稍加詮釋,意思是:人遭罪受苦乃是本份,無所謂冤不冤,只要定了罪名用上刑,哪有不招認的?豈不知英雄難過苦刑關(guān)!
后面一番周折,寫得更有意思。
案子提交到上級衙門東平府復(fù)審,而這東平府府尹陳文昭“極是個清廉的官”,他“天生正直,稟性賢明;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這顯然有了轉(zhuǎn)機,給讀者以極大的希望。果然,武松叫起冤來,府尹立刻明白了真相,當下把負責押送武松的司吏錢勞打了二十板,行文到清河縣提取西門慶、潘金蓮等一干人犯。青天在故事需要他的時候及時地出現(xiàn)了。
但青天也有他的難處。西門慶不敢打點陳文昭,星夜派家人去京城走楊提督的門路,提督又轉(zhuǎn)央內(nèi)閣蔡太師,關(guān)系找到中央去了。太師考慮的因素很多,不僅有楊提督的情面,還有清河李知縣的“名節(jié)”。至于賣餅的武大郎,生也罷死也罷,不值得多說。于是連忙發(fā)信給陳府尹,讓他不必節(jié)外生枝。而陳府尹本是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二人份量之重,足以壓倒他的“正直”與“賢明”。認為清官就一定會“清”到底,在《金瓶梅》的作者看來,也是幼稚可笑的念頭。官場本身已經(jīng)污濁不堪,如果有那樣的清官,早就混不下去了!
終了武松得以免死,問了個脊杖四十,臉上刺了兩行金字,發(fā)配二千里充軍。作為“清官”,陳文昭在人情和良心兩方面都做了交代。
“武二充配孟州道,妻妾宴賞芙蓉亭”,這是《金瓶梅》第十回的回目,對比極其鮮明而生動。這以后,西門慶依舊做他的生意做他的官,安享富貴,尋花問柳,直到縱欲身亡。等得武松回過身來再度尋仇,只找到失去依靠的潘金蓮和王婆。沒有了西門慶,他手忙腳亂,對兩個雖說有罪其實孤弱的女人又是斷頭又是剜腹,顯得愚蠢而可笑。說到底,那也只是“張公吃酒李公醉”罷了。
王國維說,中國文學好說詩化的正義,“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罹其罰”,以此給人以虛假的安慰。《金瓶梅》卻是例外,它告訴人們:惡人只要足夠強大,沒有什么想象的正義可以懲罰他,死也只是他自己找死罷了。它倒是有許多“張公吃酒李公醉”式的荒誕,以一種精神上的壓迫使人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