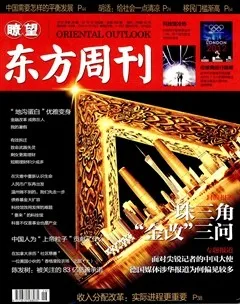“珠三角金改”門徑
“深圳前海將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試點”、“RQFII相關ETF產品和港股ETF產品獲批”等重大消息不斷釋放,顯示國家政策層面力挺廣東“國際金融”戰略。
6月最后兩天,《珠三角金融改革創新綜合試驗區總體方案》獲批的消息,一股腦兒釋放出來。
與兩個月前“溫州金改”放出消息時的情形不同,盤桓在2200點左右的股市沒有應聲上漲,被研究機構精心挑選出來的“金改受益股”也未能享受資金狂熱追捧待遇。
此間的上海陸家嘴金融論壇上,又傳來“金改先行者”溫州的非利好消息。有專家說,由于往深一步不知如何改起,“溫州金改”面臨難題。
這是否讓“珠三角金改”的前途平添一重陰影?
金融第一省“金改”
“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廣東金融學院代院長、聯合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陸磊,參與了廣東省內重要金融規劃,他在今年5月底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就透露“珠三角金改”即將獲批。在他看來,如此量級的“金改”動作,對于珠三角,尤其對于廣東而言,稍顯姍姍來遲。
廣東籌謀全省范圍內金融改革創新,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彼時,“十五”剛剛啟幕,當年6月,正在系統反思金融發展“大而不強”的廣東省,始掛牌成立省金融服務辦公室,“金融強省”隨即上升為政府意志。
進入“十一五”,2007年6月,廣東趁熱打鐵,正式推出“金融強省戰略”。而直到2010年,廣東在布局珠三角產業規劃時,才提出“允許在金融改革與創新方面先行先試,建立金融改革創新綜合試驗區”思路。
此為“珠三角金改”構想首度面世。之后不久,2011年,《廣東省建設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創新綜合試驗區總體方案》上報至國務院。而今年3月底,國務院批復的第一個“金改”試驗區是溫州,“珠三角金改”方案能否獲準批復,一度顯得不太確定。
現在,“珠三角金改”已成定局,陸磊評價其政策力度超過溫州,“這是真正的國家戰略,這里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一站,而人民幣國際化將引至整個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地緣等一系列大的變化,我們將會看到一個全新的世界范圍內的貨幣版圖”。
廣東是中國的實業大省,2011年度GDP突破5萬億元人民幣,金融總資產超過13萬億元,穩居全國第一。與之對比,搶得“金改”頭籌的溫州,無論經濟體量還是金融體量,大致只抵珠三角區域內一個市轄區。
另外,從地緣上看,珠三角毗連香港、澳門,尤其香港,本身具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因此,即便從國家層面考量,置身特殊地緣環境,在一個巨無霸經濟體中力推“金改”,其意義應該比溫州更加“牽一發而動全身”。
與“溫州金改”的不同之處是, “珠三角金改”的起點有自己的特征。“簡而言之,我們在金融改革創新中的一些關鍵問題上,還沒有真正破題,全國性首創要么來自于濱海新區,要么來自于浦東,社區性的面向自然人的金融創新和服務更多來自于江浙。因此,無論(金融)市場、服務、產品、機構,廣東沒有非常突出的亮點,還處于滯后期。”陸磊認為。
這一說法不缺印證。6月26日起連續3天,首屆中國(廣州)國際金融交易博覽會作為“珠三角金改”的預熱節目,在廣州會展中心舉行。本刊記者走訪展區內粵籍小貸公司,發現大多數公司正專注于抵押貸款,而本刊此前在中國西部調查顯示(見《瞭望東方周刊》2012年第16期《小額貸款公司灰幕》),小貸公司抵押貸款業務已經步履維艱,轉而謀求信用貸款技術創新。在融資技術創新上,重慶小貸資產甚至已經推入金融資產交易所上市交易。
“珠三角金改”布局中,廣州是重要一環。6月29日,廣州市金融辦主任周建軍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廣州未來一段時間金融工作抓手時,提及廣州將致力于發展“碳排放權交易所”、“股權交易中心”、“期貨交易所”三大市場交易平臺。
實際上,在廣東以外,從北京、天津、上海一直到大連、成都、重慶,類似交易平臺在三到四年前完成搭建,部分交易平臺經證監會整頓之后已進入二次亮相階段。
“63層”的金融傷痕
“這并非說,廣東金融一直就死氣沉沉,相反,廣東早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拆借市場、融資中心、外匯交易都已經相當活躍。問題是,那時缺乏有效監管和風險認知,因此產生了嚴重的風險和歷史包袱。”
陸磊領銜創辦了中國金融轉型與發展研究中心,對廣東金融流變尤其熟悉。據他介紹,中國城市信用社全行業關閉起源于廣東,國家層面推動的貸款五級分類政策最早也從廣東試點,“1998年,幾乎當時全中國風險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操作者都集中在廣東”。
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廣東確曾在“金改”創新的道路上迅猛突進,既有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奇觀,也曾留下傷痕。而這一切的見證者,當屬至今仍矗立在廣州環市東路上的廣東國際大廈。
廣東國際大廈俗稱“63層”,曾有“南天一柱”的贊譽,在2010年世界第六高的廣州國際金融中心大廈(廣州西塔)崛起之前,老廣東人心目中,“63層”既是廣東改革開放成功的象征,又像是廣東金融的敏感高度。
“63層”主要由原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下稱“廣國投”)于1991年投資建成。在此之前,“廣國投”已被國家主管機關確定為全國對外借款窗口公司,并作為此類窗口公司的領頭羊,在香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到1997年底,“廣國投”一路走到最高點,成為總資產327億人民幣的特大型綜合金融投資實業集團,位居中國信托業第二。
轉眼到第二年,隨著亞洲金融風暴愈演愈烈,“廣國投”于1999年1月正式向法院申請破產。隨后的清算結果令人咋舌,其總資產214.71億元,總負債361.45億元,負債率高達168%。
“破產后,‘63層’成天被債權人圍堵,甚至有人圍攻22樓清算小組。相當一部分又是上年紀的老人,情緒激動,場面混亂,高峰時候人數上千,警察就來了好幾百人。”一位曾專訪過“63層”負責人的記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時這種局面持續了一段時間。
作為“中國第一破產案”的“廣國投”破產,給廣東金融發展留下一道陰影。曾任廣東省財政廳長的劉昆在《金融研究》發表過論文,說:“廣東地方金融機構,是從1980年成立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粵海公司起步,1988年恢復廣東華僑信托投資公司,成立廣東發展銀行,以后市縣政府又陸續以這些公司分支機構名義成立獨立法人的金融企業、城信社。1995年以后,一些地方又組建農金會,到1998年進行清理整頓時,形成了龐大的金融資產和負債。巨額的資產損失,成為廣東經濟生活中的‘定時炸彈’。”
“1997年以后,一直到2007年,廣東在金融工作方面的一個著力點就是化解金融風險。這十年中,廣東面臨非常嚴重的金融歷史包袱,因此不能責怪這些決策者(未能改變廣東金融‘大而不強’的局面)。”陸磊打了一個比方,“假設你面對的是姚明,而且他又生病了,你就不能指望他立即重現賽場神威。但是,廣東金融現在看起來似乎落后,并不意味著將來也會落后。”
政策力挺“國際金融”
此次“珠三角金改”,廣東設定了五條路徑,即國際金融、科技金融、產業金融、農村金融、民生金融。對此,陸磊認為,廣東未來推進“金改”的看點,是國際金融。
在6月26日開始的“金博(交)會”期間,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特意主辦“跨境人民幣業務與企業國際化發展機遇”分論壇。隨后,“深圳前海將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試點”、“RQFII相關ETF產品和港股ETF產品獲批”等重大消息不斷釋放,顯示國家政策層面力挺廣東“國際金融”戰略。
陸磊主持了前述“跨境人民幣業務與企業國際化發展機遇”分論壇,他日前向《瞭望東方周刊》解讀了“珠三角金改”中有關“國際金融”設計的基本邏輯和可能愿景。其邏輯起點仍在廣東實體經濟上面。
廣東所呈現的實體經濟圖景,首先是對外開放窗口。長期以來,“對外”所指,核心是立足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資,同時以香港為中轉站,實現中國商品對外輸出,并由此塑造了中國“世界工廠”形象。而廣東在“世界工廠”當中,向來三分天下有其一。
隨著實體經濟走到現在,廣東積累了豐裕的貨幣資金,區域要素稟賦卻在變化,勞動力更貴,土地更貴,原先的制造業基地優勢可能不再。此情此景,廣東企業家除了面向中國中西部地區,還同時向東南亞國家輸出資本。
廣東的現實是外貿仍然偏大,外資由進變成出。于是貨幣之間的結算,也就是作為一種貿易貨幣和投資結算貨幣,到底以哪些幣種為主,成了一個活生生的金融課題。
人民幣在這期間迅速展現活力。陸磊公布一組數據: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只有35.8億元,2011年即飆升到2.08萬億元。2007年,人民幣在香港存款余額為200億元,去年年底則達到7000億元人民幣。
“貿易項下,中國進口其他國家貨物對外支付人民幣,人民幣就通過貿易流出。第二個,由于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歐元持續升值,跟我們發生貿易關聯的人就將人民幣作為一種資產持有。現在,一些東南亞商人、政府都在公開或不公開增持人民幣。”
由于一種主權貨幣只能用于境內投資,當境外越來越多的人持有數量龐大的人民幣時,他們基于生利愿望,便希望中國開一個口子到境內投資,比如買中國金融資產,或者持有中國商品。
“這樣一來,金融層面的鏈式反應便展開了。需要相應幣種之間交易,這是最早的外匯市場;需要對匯率進行管理,有匯率衍生品市場;需要對企業股權交易,就有產權交易市場和場外交易市場(OTC)。”
陸磊說,廣東目前積極推動國際金融板塊建設,恰好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內在需求,“所以才有珠海橫琴離岸貨幣市場的想法,才有深圳前海能否打通港股和A股的想法,也才有廣州南沙建設跨境總部金融基地的想法。”
陸磊認為,“珠三角金改”籃子中的“國際金融”板塊建設,比指定某地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更接地氣。
“去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中,1/4是廣東貢獻的,廣東有真實的貿易背景和投資背景,有真實的交易量,有內在的交易機理,并且有獲利動機,所以它不同于某些地方向‘一行三會’要政策,廣東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完全基于實體經濟需要。”
廣東省社科院經濟學博士丁力,此前長時間工作在浙江,立足“溫州金改”觀察廣東,他認為,如果“溫州金改”是在探索利率市場化,那么,“珠三角金改”可以探索匯率市場化。
丁力的著眼點在于“地下”。在他看來,以前溫州地下錢莊、民間金融發達,導致利率混亂、風險積聚,故“溫州金改”改堵為疏,給予適當的利率空間將地下金融引入合法軌道,并形成有效監管。
廣東地下錢莊業務偏重外匯交易,事實上也在監管之外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地下外匯市場。因此,丁力認為,“珠三角金改”要直面現實,繞不過匯率市場化這道門檻。
丁力是在今年5月底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提出這一設想,其時,外界對“溫州金改”尺度的議論懸而未決,主張溫州為利率市場化改革探路的呼聲漸高。
而剛進入6月,懸念即告終止。此間周小川在華盛頓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表示,“利率、匯率方面的改革不可能由一個地方試點,要做就大家都做了,否則套利機會太顯著。”
技術派突圍“金改”
6月28日,廣東“金博(交)會”尚未閉幕,上海“2012陸家嘴金融論壇”又告開幕。在這場政、商、學界金融精英薈萃,規格更勝廣東一籌的金融大會上,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面對媒體采訪時說:“‘溫州金改’有可能出現雷聲大、雨點小,走向‘流產’現象。”
在郭田勇看來,溫州金改實驗區準備并不充分,有些倉促上馬,上馬以后便會騎虎難下、進退兩難,“因為不改也不行了,但是往深處改又不知道怎么改,沒有什么實質性的突破口”。
目前,“珠三角金改”實驗區已經獲批。那么,“珠三角金改”到底能改什么,怎么改革,不止被各方猜測,也有人擔憂會不會淪為“溫州金改”后繼。
“首先,金融政策很大一塊都掌握在北京,地方很難在政策上有作為,真正地方‘金改’創新,一是制度創新,就是突破政策管制,同時又在監管方面有所創新。二是金融產品創新,三是金融技術創新。”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綜合開發研究院是接受國務院研究室業務指導的研究機構,發布中國29個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指數,這種全國視野下就金融工作進行經常性比對,使郭萬達建立起一套審視地方“金改”的格式系統。
在郭萬達看來,地方“金改”千頭萬緒,究其實質,都跑不出制度、產品、技術三個層面的創新。而這三者當中,他尤其看重后兩者。
深圳從2007年推動的中小企業集合債,被郭萬達視為金融產品創新活生生的案例,“大企業發債很方便,小企業要發兩三千萬的債,標的太小,誰都不敢買。于是把多個中小企業集合起來,捆綁打包統一發債,這就是創新”。
郭萬達還預判,未來金融技術創新或更多通過IT技術達成。他舉例,深圳某保險公司目前正打算在互聯網上打造金融超市,面向客戶實現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產品的一站式服務。
“客戶眼中,這家保險公司同時做銀行、保險、證券業務,好像它違反監管搞起了混業經營,但實際上它只是通過網絡技術把分業經營的金融業務整合到一個平臺上,既方便了客戶,又在政策規定之內。”
陸磊則對“金改”政策收放尺度不作過多揣測。陸磊于1995年至2003年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政策研究室和研究局工作,諳熟央行面向地方出臺政策的基本原則,“我們搞政策研究的人都有一個基本判斷,并非給你什么政策,你就能做出什么,只有你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已經做得很好了,不給你政策都說不過去”。
陸磊反對把改革創新寄望于頂層設計,為此,不久前他專門發表《讓金融回歸技術》一文,斥責“我們如濫用抗生素一樣濫用‘改革’”。他認為,過于強調金融的體制性,結果是諸多可以在技術層面解決的問題變成了體制改革,他甚至認為“無論是利率市場化還是匯率形成機制,無論是人民幣國際化還是新股發行,均屬于由誰定價、如何定價的技術問題”。
郭萬達、陸磊這樣的技術立場,似在拓展地方“金改”上手的空間。但陸磊接受本刊采訪時又特別強調,“珠三角金改”的全面推開,亟待廣東形成一個掌握現代金融知識的技術官僚集團,方才能抓住“金改”主動權,真正達成改革愿景。
本刊記者此次走訪了“珠三角金改”3個布局點,即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在如火如荼的建設工地背后,從與基層官員交談中不難發現,部分官員談及新區招商引資往往滔滔不絕,涉及金融則顯得力有未逮。
據陸磊說,他已向廣東省政府建議“十百千萬工程”,即5年內引進10名國際頂尖金融人才、100名高級職業經理人,培養1000名金融骨干專業人才、10000名金融中介技術人才。目前,該計劃已被政府采納,并寫進《廣東省金融改革發展“十二五”規劃》。
“廣州價格”
6月28日當天,在具有百年商業、金融源脈的廣州長堤大馬路上,廣州市政府傾力打造的“民間金融街”正式開街,以本土小貸公司為主的32家金融機構一齊入駐。
與其他地方一省(直轄市)之內動輒上百家小貸公司相比,廣州的手筆似乎不夠大。但“民間金融街”街頭同步掛出電子公告牌,及時發布金融街內小貸、擔保、典當利率、費率,由此使這片金融洼地變身為中國民間融資的價格風向標。
這就是技術細節,廣州金融官員了然其技術邏輯。他們對媒體闡述:集中發布駐街機構資金供求信息,逐步建立反映資金供求狀況和監管治理環境的民間金融利率、費率價格形成機制---即“廣州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