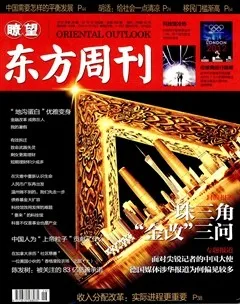中國需要怎樣的平衡發展
夜晚從飛機上俯視地面會看到層次分明的明暗斷層區域:明亮的是城市化進展迅速的區域,農村和無人居住地區呈現出的是“黑暗”區域,并且東部沿海和中、西部內陸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在一系列的戰略構想和摸打滾爬中跨時30余年,兩個大局、摸著石頭過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到今天,取得的成績舉世矚目,而存在的矛盾也無法忽視。協調發展、平衡發展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種經濟發展失衡的現象。
這也為中國經濟失衡向平衡轉變的研究迎來了最好契機。
如何總結經濟快速增長進程中的失衡約束和發展陷阱,為未來經濟實踐提供可以借鑒的政策思路,是值得探討的重大話題。
內部失衡
就內部失衡狀況來看,主要分為城鄉發展和區域失衡。
其中,根源于城市和工業發展的“偏向”政策,30多年來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和近20多年來不夠完整的城鎮化進程致使城鄉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換句話說,農村實體經濟發展的循環血液逐漸被“抽空”。這種發展軌跡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農業產出比重下降趨勢明顯,農業從“基礎”地位逐步下降為國民經濟的“補充”,由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三分天下”轉而成為“十分依靠”;與此同時農產品出口比重逐年快速降低,進口規模增加;
其次,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未來10年農村農業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問題可能將凸顯,農村農業工人“工資”水平快速上升成為趨勢;
第三,對農業和農村資源的過度“挪用”,借助手段主要是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金融資本的城市與工業偏向,農村、農業被迫支援城市和工業發展。
在此過程中,農村內部也出現了兩個失衡格局:農業勞動力供需結構失衡和農村內部產業結構失衡。而這很可能演變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枷鎖。
再加上目前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的不完善,以至于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格局和失衡加劇的風險短期內難以消除。
對于區域失衡,學界的通常做法,是用地區差距度量區域失衡。通過地區生產總值橫向和縱向比較很容易看出:1978年最低的西藏自治區僅為6.65億元,最高的上海為272.81億元,相差約40倍;到2008年西藏增加到395.91億元,而上海達到13698億元,仍相差約34倍。
僅看增長差距確實是在縮小,但從基數和絕對差額倍數來看,差距在擴大。
用“燈光效應理論”可以很好地描摹區域發展失衡重要分塊特征。夜晚從飛機上俯視地面會看到層次分明的明暗斷層區域:明亮的是城市化進展迅速的區域,農村和無人居住地區呈現出的是“黑暗”區域,并且東部沿海和中、西部內陸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
人口地域空間分布不合理是區域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戰略及政策,無疑是中央政府在為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方面做出一系列重大安排。
外部失衡
另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局面是外部失衡。
1978年改革開放,對外經濟發展迅速,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對外開放從局部地區向全國推進,1979年首先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實施特殊政策和優惠措施,1980年開設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對外開放的范圍逐步擴展到其他沿海、沿江、沿邊地區,1992年相繼開放沿江城市和三峽庫區、邊境和沿海地區省會城市、沿邊城市,開放內陸省會城市—— 出現了當時的經濟開發區建設大潮。
隨后又陸續開放大批的內陸縣市,形成從沿海向內地推進的格局;外資、外貿集中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成為創匯的核心區域。而時至今日,這樣的格局并未有所改觀。
值得關注的是,對外直接投資雖然開始于1979年的改革開放,但近年來對外投資規模才快速增加——開始于2005年的外向型經濟模式由“引進來”向“引進來”與“走出去”齊頭并進戰略轉變,到2008年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到559.1億美元。
伴隨著人民幣升值的加快,國民財富蒸發成為政府高度關注的政治和經濟難題,背后的解決之道實際上就是尋找如何消除外部失衡的有力措施。大國經濟發展角逐游戲持續時間越久,波及范圍越大,國民儲蓄的貶值風險就越高。
無論是從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或是從維護寬松的外部經貿環境,還是從規避和控制風險過度積累等方面考慮,都需要加快外部失衡治理步伐。
厘清思路點面齊動
從我們的研究結論來看,基于內外失衡加劇的潛在風險防范,實現可持續的平衡增長和民富國強齊頭并進目標,可有如下的政策思路。
第一,破除城鄉失衡,首要任務應該是發展農村經濟,消除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城鄉消費差距。
目前農村勞動力已經實現了大規模的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結合最新的統計數據做出保守估計是——中國農村勞動力外流規模應該在2.3億~2.5億之間。這無疑為農村經濟發展創造了土地與勞動力的配比大好時機,但前提是有強大的資本支持。所以,需要充分發揮農村正規金融的供養和支持作用,實現金融“反哺”,從根本上化解農村經濟面臨“中空化”危機。
農村居民消費不足并非意愿需求,實際可支配收入穩定增長才是關鍵。近期看最直接的手段是強化反貧困政策和實施調節收入分配政策。一旦收入再分配政策改革得到順利推進,貧富差距得以縮小,城鄉失衡破除則是順理成章之事。
第二,破除區域失衡,根本出路則是推進健康合理的城市化。
區域和城鄉聯動及平衡發展并不一定要以犧牲經濟效率為代價,隨著政府對協調城鄉和區域間發展重要性認識提升,各種為促進內地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政策頻頻出臺。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共同謀劃為實現區域協調、平衡和城鄉融合、統籌發展目標審視“有所為而有所不為”。
第三,破除外部失衡,關鍵是利用好外資和外貿發展平衡工具。
長遠之計是需要從現在開始把握癥結所在和清醒地看到失衡程度,必須做好內外經濟失衡的“摸底”——監測與預警。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和流出)是解決外部失衡矛盾的關鍵變量。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關注國際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關系的重要性認識已經十分明確。
內外經濟失衡是聯動的,區域與城鄉也是聯動的;要實現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平衡發展目標,必須消除失衡,架構起城鄉、區域公平發展框架思路,追尋內外平等格局,提升內部經濟發展質量來推進和實現外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