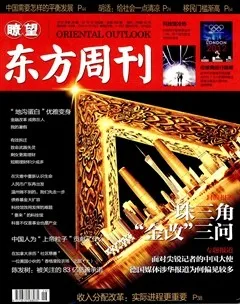科技館效用發揮的難題
社會對科技館的捐助資金幾乎為零,這似乎告訴人們,今天許多事情到了有條件認真思考并加以行動的時候了。
毫無疑問,過去10年是中國科技館“跨越式發展”的10年。
建筑面積13.75萬平方米的廣東科學中心、10.28萬平方米的中國科技館新館、10.07萬平方米的上海科技館,已分別躍居世界規模最大科技館的第一、第三、第四名。
中國科技館“全國科技館現狀與發展趨勢研究”課題組的統計分析說,自2000年中國科協發布《科學技術館建設標準》到2010年底,中國“達標科技館”由11個增加到86個,10年間增加75個。
這個課題組的負責人、中國科技館科研規劃部主任朱幼文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十五”期間,各地先后有將近30多座新建、改建或改造后的“達標科技館”對公眾開放;“十一五”期間,有40多座科技館建成開放;2011年,各地又有湖南省科技館、吉林省科技館等十多座高規格科技館竣工,全國“達標科技館”總數接近100座。
中國的科技館事業,雖然起步比發達國家晚了約50年,卻只用了10年就一躍成為“世界科技館大國”。
新建科技館的確展示著城市的嶄新面貌和“科教興國”、“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的雄心。今天科技館已成為許多城市的地標。巨大、震撼、壯觀??這是媒體對于一座座新科技館的描述。
熱潮之下,是全國新建科技館每年超過15億元人民幣的運行經費需求。
中國科普研究所所長任福君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為了使科技館正常運行并發揮社會效益,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經費投入,一方面應盡快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法規,營造全社會支持科技館發展的良好社會氛圍。
問題也許不止于此。如何讓科技館的效用最大化發揮,已經顯得越來越重要和緊迫。
轉折之后的“喜”與“憂”
2000年以前,由于歷史原因和對于科技館的性質、功能存在模糊認識,各地建設了許多科普展教功能薄弱的科技館。當時,全國以科技館為名的場館達到320多個,但其中以科普展教為主要功能的僅有11個,其他大部分場館稱為會堂、辦公樓或許更為合適。
2000年12月,中國科協召開首次全國科技館建設工作會議,明確了科技館的主要功能是科普展教,發布了中國科協系統的《科學技術館建設標準》。這是中國科技館事業發展中的一次重大轉折。
這一年,鄭州科技館、江蘇科技館、沈陽科技館、正定科技館、中國科技館二期工程相繼建設開放。這之后,“樓、堂、館、所”型的科技館建設勢頭開始被扭轉,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強調科普展教功能的科技館改造和興建。
“11年來,一部分原來不達標的經過改造、擴建或改建,加上這兩年新建開放的科技館,現在‘達標科技館’將近100座。”朱幼文預計,到2015年,全國達標科技館總數將達到130座至160座。
根據國務院2006年發布的《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的要求,到2010年各直轄市和省會城市、自治區首府至少擁有1座大中型科技館,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上的大城市至少擁有1座科技類博物館。
截至目前,尚有9個省會城市、自治區首府未能按《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的要求建成“達標科技館”,其中陜西省和海南省的科技館建設工程尚未立項。
“科技館建設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部分地區建設改造速度太慢,部分科技館規模過小,還有大批‘未達標科技館’有待改造、改建;二是部分地區場館規模過大,部分不適宜建設科技館的地區也建設了科技館,致使其社會效益不能正常發揮。”朱幼文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現在,除了約100座“達標科技館”之外,全國各地還有250多座“未達標科技館”。這些科技館有的實際上是當地科技部門的辦公樓、會堂,乃至招待所,還有一些縣級科技館只有一兩間辦公室和教室。
有些大中城市有能力對科技館進行建設改造,但還未見行動。陜西省科技館建筑面積9700平方米,常設科普展廳面積為1400平方米,屬于“未達標科技館”。據說,該館的改建工程至今尚未立項。
2007年,建設部和國家發改委聯合發布了國家《科學技術館建設標準》。該《標準》規定,為實現科技館的科普展教功能,常設展廳不宜小于3000平方米。而在現有的“達標科技館”中仍有30多座科技館常設展廳不足3000平方米,其中有11座科技館小于1000平方米。“如此小的展廳,很難正常發揮科普展教功能。”朱幼文認為。
“遙遠”的科技館
據國家《科學技術館建設標準》規定,市區人口數量不足50萬的城市不宜建設科技館。“有些地區把轄區農村人口也計算進來,造成科技館建設規模過大,超出了當地的實際需要和經濟承受能力,也造成社會效益低下和政府投資的浪費。在現在的發展階段,是有些不太合理的。”作為參與過中國科協和國家兩個《科學技術館建設標準》起草工作的專家,朱幼文的觀點是,國家有關部門應盡快出臺政策,明確提出市區人口不足50萬的城市不宜建設科技館。
“日本最大的科技館---日本科學未來館在2001年建成開放,它的建筑面積剛過4萬平方米。而在我國西部地區,一個經濟欠發達的地級市卻要建一個將近5萬平方米的科技館,顯然超過了當地的經濟資源和人口承受能力,除非初衷就沒有想當科技館來用。類似情況近年來不止一次地出現。”朱幼文解釋說。
河北省科技館舊館開放于1987年。2006年3月23日,緊鄰河北省博物館和河北省體育館的科技館新館建成開放,投資1.5億元,建筑面積1.27萬平方米,展廳面積8400平方米。
河北省科技館宣傳部王部長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目前這個館每年接待觀眾量近20萬人次。石家莊市區人口為300萬。
目前,河北省科技館正在遠離石家莊城區的滹沱河北岸正定新區籌建近8萬平方米的新館。在正定縣,還有一個展區面積為1萬多平方米的“河北正定科技館”。
位于沈陽市渾河南岸渾南新區的遼寧省科技館新館正在建設,建筑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
為滿足巨大的場館規模,大多數新建科技館都選址較邊遠的城市新區。而按更為合理和有效發揮效用的原則來選址,科技館更應建在城市中心、交通便利的公共文化區。
廣州科學中心建在番禺區的廣州大學城,從市區到科技館開車需兩次經過收費站,公共交通也并不便捷,有些觀眾從科技館出來連出租車也打不到。
交通不便,會制約觀眾流量。相比建筑規模排在它之后的中國科技館和上海科技館年觀眾量超過300萬人次的數字,這座建筑面積世界排名第一的科技館,年觀眾量200萬人次就顯得不太匹配了。
朱幼文認為:科技館規模過大、過小或選址不太合理,都不利于發揮社會效益,還會造成國家投資效能不高的問題。
形成反差的是,在一些地方,科技館以景點形象出現,游客成了主要觀眾。
科技館不能缺什么
2000年底11個“達標科技館”共接待觀眾230萬人次,2010年已升至2100萬人次。“總體而言,中國科技館的社會效益有了明顯提升。”朱幼文在做出十分肯定的概括后也提出,這期間科技館平均觀眾量和單位面積的觀眾量增長不到10%。
后一個數字是需要關注的。換句話說,科技館平均效益的增長還不十分明顯,整體效益的提升主要還是靠科技館數量與規模增長來拉動。
即使是現有的約100座“達標科技館”,也還存在著進一步提升科普展教能力與水平、發揮更大社會效益的巨大空間。
朱幼文根據近年來的調研結果指出:我國科技館在展覽設計、教育活動和網絡傳播三方面,與發達國家先進科技館存在很大差距。
作為科技館最引人注目的科普手段,2001年以來我國科技館常設展覽的規模和展品數量增長了近10倍,但展示內容雷同、創新乏力、單純傳播知識、缺乏科學思想內涵的問題也日益凸顯。
長期以來,中國的科技館大體還是在走模仿的路子:國內大型科技館模仿國外發達國家的科技館,中小型科技館模仿國內大型科技館,從展示內容到展品差別較小。
中國科技館新館內容建設國際顧問、德國著名科技博物館展覽設計專家布雷德伯恩在批評一些歐美科技館時曾說:“科學中心不能像麥當勞一樣,每個地方都是同樣的菜單、同樣的方法、同樣的展品。”“科學中心太拘泥于用展品說明本身的原理和知識,忽視了這些展品背后科技與社會的關系。”朱幼文認為,布雷德伯恩的這兩句話也適用于中國的許多科技館。
他告訴本刊,在考察美國、加拿大的科技館后發現,在展廳中向任何一個方向看去,都能看到工作人員或志愿者在與觀眾交流,或通過開展實驗、表演等活動,幫助觀眾理解展覽和展品。美國、加拿大的科技館還開展了種類繁多、形式多樣的其他科學教育活動。
國內科技館難以望其項背,部分科技館認為:只要把展覽、展品展出了,科技館就完成了科普任務。在2011年對各地科技館的調查中,超過50%的科技館除了展覽外沒有自主開發其他科學教育活動。
在中國科技館2011年進行的全國科技館調查中還發現:各地超過半數的科技館沒有建網站;而現有的科技館網站,大多數局限于開放時間、交通方式、展覽內容和教育活動的簡介,未開辟科普欄目。
而美國“探索館”、芝加哥科學工業博物館等著名科技館,僅科普欄目就達數百個,科普類文章、圖片、視頻的頁面達上萬個,而且內容更新迅速。
除上述缺失,恐怕影響科技館效用發揮的缺失元素,還有志愿者的廣泛參與以及科技館與學校教學之間的緊密聯系。
據2011年數據,中國目前已有43萬個志愿者組織,常年開展活動的志愿者已超過6000萬人,其中注冊的志愿者達2000多萬人。志愿者服務已成為中國全民公益活動的亮點之一。
如果以志愿者群體中具備較高科學和專業知識的志愿者為主體,形成專門服務于科技館的志愿群體,包括院士級、大師級的科學家和各個領域的科技專家,也能常態化地現身于科技館從事志愿活動,其效應或許遠超過會堂式、街頭式的臨時性科普活動。
這一點,在中國是有條件做到的。2011年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知識分子共有1.19億人。如果能夠形成一個并不是靠硬性制度規定的社會公益美德口碑評價機制,讓大專院校的教師、科研院所的專家,將“每年做一天科技館志愿者”成為一種自覺選項,效果會是多重的。
小學生、中學生乃至大學生,是科技館最主要的“顧客”,他們代表著中國科學的未來。目前普遍的景象是,每逢假期科技館會迎來學生潮,而其他時間則冷清不少。
能不能把大中小學開設的相關科學課程,在科技館設下常設課堂呢?一旦科技館成為學校科技教育的“常設課堂”,衡量科技館的“產出效應”就會有一項新的衡量指標。
中國科協在2008年就提出:我國科技館要從以往以數量和規模增長為特征的發展模式,轉變為以提升科普展教能力與水平為特征的發展模式。
如何彌補這些缺失的元素,很重要也很現實。
單靠國家能否為科技館埋單
根據國家《科學技術館建設標準》編制組的調查和測算,科技館的年度運行費用,一般是其建設總費用的8%至10%。“按照‘達標科技館’平均每座造價約1.7億元計算,全國現有‘達標科技館’的年度運行費用需要大約15億元。”朱幼文說,
現實情況是,目前全國科技館中超過70%的場館年度運行經費未能達到其建設費用的8%,近30%的科技館年度運行經費不足其建設費用的5%。
日常資金的缺口,讓許多科技館只能在困難中運行,開發短期展覽和教育活動,缺錢;更新破舊的展品,也缺錢。
按發達國家的經驗,科技館的運營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撥款、社會捐助、自營收入三大渠道。以美國為例,三者各占約三分之一。自營收入包括了門票收入和其他經營性收入。
“國內科技館門票收入在經營性收入中的比重超過90%。”朱幼文估計。他分析說,國內科技館70%的經費需要國家財政撥款,其他約30%的資金來自門票收入。與國外相比,社會捐助幾乎為零。
在中國,科技館作為公益性場館,正在向減免門票方向發展。屆時,科技館的日常支出可能會更加依賴于政府財政。目前,部分地區政府一方面要求科技館免費開放,另一方面并沒有為科技館新增必要的經費投入,日常運行資金的缺口可能拉大。
“科技館作為國家典型的公益性單位的性質不能變,基本運轉經費應當穩定地得到政府支持。”中國自然科學博物館協會理事長徐善衍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科技館的日常支出主要用于展品維護、水電費用、人員工資,以及常設展覽更新改造、開發新的短期展覽和教育活動,其中人員工資占主要部分。另外,互動性展品損壞率和維修率較高,“根據國際經驗,科技館每年更新的展品應該占全部現有展品的5%至10%。”朱幼文說。
他認為,科技館不應該涉及太多商業性活動,現在最缺的是社會捐贈。其原因,一方面是國家現有鼓勵社會力量和個人贊助公益性科普事業的政策還不完善;另一方面,我國還沒有形成較好的社會捐贈氛圍。
河北正定科技館作為目前國內最大的民營科技館,在建館過程中接受了不少捐助。比如,北京電影制片廠捐贈了捷克上世紀50年代生產的“35n/m中西尼風攝影機”,石家莊收藏家徐鳳吉老人贈送了“35n/m先鋒牌攝影機”和一批老式電話機,核工業航測遙感中心高級工程師董庭寬也贈送了包括鐵隕石在內的一批礦石。雖然在展品上得到一些捐助,但正定科技館在資金上還是嚴重匱乏。
同樣是民營科技館的“廣州南沙科學展覽館”,被稱為華南最大的民營科技館。它作為霍英東基金會響應國家“科教興國”號召捐資建立的一個項目,近年來由于運營經費不足,在建成開放十年后的2010年3月停業。
2003年5月和11月,科技部、財政部、國稅總局、海關總署、新聞出版總署先后聯合制定了《關于鼓勵科普事業發展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和《科普稅收優惠政策實施辦法》,規定企事業單位捐贈、贊助科普事業,在財稅方面將得到支持和優惠。
在2006年國務院頒布的《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中,提出了“鼓勵捐贈,廣辟社會資金投入渠道。進一步完善捐贈公益性科普事業個人所得稅減免政策和相關實施辦法,廣泛吸納境內外機構、個人的資金支持公民科學素質建設”。
不過在實踐中,上述優惠政策和意見還未得到切實的貫徹落實。
中國科普研究所所長任福君認為,在《科普法》和《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中,還有類似的很多政策難以具體實施,需要對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修訂,制定相關實施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