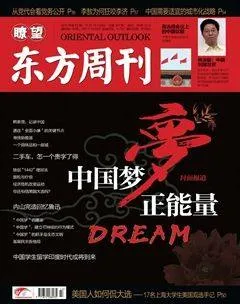內山完造回憶魯迅
2012-12-29 00:00:00內山完造
瞭望東方周刊 2012年43期

我原本也打算加入該同盟,可是魯迅先生說:“你還是莫加入的好,一旦中日關系惡化,你就可能被當作間諜處理,要慎重啊……”于是我便打消了加入的念頭。
相識即朋友
那時聽說先生是偕妻子來到上海的,而他的妻子就是他的秘書許女士,可就在不久前還聽聞先生尚未結婚。他們相識于五四運動之時,當時先生在北平女子師范學校當講師,就在運動掀起一股熱潮的時候,許女士站在了眾多女學生的前面,揮舞著旗幟,英姿颯爽……
先生來到我家,頭一句便說:“老板,我結婚了哦。”
我便問:“怎么會……”
“是和許結的婚,雖然我本無結婚的打算,但大家都撮合我們,最后我也就隨了他們的意。”
“對象不是在北平嗎?”
“哦,那是我母親的媳婦,可不是我的媳婦呢。”先生爽快地答道。
原來中國式的婚姻中男女雙方大多未曾謀過面,所以對于男方來說,更多的像是母親在娶媳婦而并非自己娶媳婦。
在家族制度改革方面,魯迅先生寫了中國白話文運動最早的一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這部小說旨在喚起家族制度的革命,我想他懷揣的這種思想在他那不經意的言語中也有所體現吧。那句話一點兒也不像是刻意說出來的,雖然作為日本人聽上去感覺有點兒不自然,但先生本人確確實實是心如其言的。難怪那位所謂的“母親的媳婦”一次都沒來看望過遠在上海的丈夫。
后來先生一家突然搬出了景云里,這都是因為背后的一種危險,這危險正逐漸逼近他。
那時先生說想要搬家,我就說那我幫他找找看有什么好的居所。
“形勢緊急,沒那么多時間慢慢找了。”他一臉嚴肅地說。
我提議道:“那搬到我家來吧。”
“你住的地方有很多中國人出入,不妥。”
剛好我一個朋友住在現興亞院前的拉摩斯公寓,他由于工作調動去了青島,把房間空了下來。我給先生提議這個地方,他說很好,于是就以我的名義租下了房子,并于當天搬了進去。當時他什么行李都沒帶。
……
諸如此類事情,之后也常有發生,迫于形勢,最后只好委屈先生暫住我家三樓那狹窄的地方,就像被軟禁監視一樣。
風暴來襲
那時,中央黨部大肆屠殺學生,就像斬蘿卜似的毫不留情。為反抗黨部的此種行為,蔡元培、宋慶齡、楊杏佛和林語堂(那時林語堂還不算知名人士)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開展了諸多活動,在社會上頗為活躍。同盟的宗旨在于維護人類的生存權,其立場非常單純,頗具人道主義精神。
其實我原本也打算加入該同盟,可是魯迅先生說:“你還是莫加入的好,一旦中日關系惡化,你就可能被當作間諜處理,要慎重啊……”于是我便打消了加入的念頭。
時值中央黨部無故屠殺中國人的事件在世界各國被相繼報道,由于林語堂擅長英文,先生又懂德文,加之宋慶齡、蔡元培大量撰寫文章,所以短時間內民權保障同盟的名字已為世人所知曉。
中央黨部為打壓同盟的活動不惜使出暗招,想暗殺同盟成員來殺一儆百。可就在暗殺對象的選擇上頗費了一番腦子。
從地位上來看楊杏佛可能要高于魯迅,但其影響卻很小,在青年人中沒什么影響力。當時我接到一個電話,說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黨部遂決定選擇楊為暗殺對象。
我把這些信息轉告給魯迅先生,他聽完后馬上動身去了同盟。考慮到危險性,我勸他在我家暫避,可他說“在哪都一樣,該來的總會來的”,最后執意去了同盟。許夫人急忙趕來問先生的去處,由于形勢緊迫,未能同去。那時候局勢相當嚴峻,但先生得以安全渡過此次劫難。
之后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他依舊說“該來的總會來的”,然后坦然地出門。
迫于當時的形勢,再加上他身體有病痛,于是我把他們一家三口藏在了家里。他們終日不出門,像是被“軟禁”了一般。后來事情慢慢平息下來,先生一家也平安無事,而民權保障同盟不知何時解散了。
離開廣東中山大學的時候,魯迅先生就已經明確了自己與蔣介石的相反立場。蔣介石秉承了孫中山的容共政策,鼓勵學生留學俄國,給學生以最高待遇,可是后來卻推行清黨運動,大肆殺害學生。
有段時間人們大力聲討蔣介石的這一欺騙性政治活動的諸多弊病,說如果國民黨內部容許這樣的政治活動,那黨本身也在進行一場欺騙性的政治活動。
蔣介石是浙江人,魯迅先生也是浙江人,但這不能阻擋兩位同鄉立場上的對立,他至死都在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這一立場堅定不可動搖。
他從廣東來到上海不久,當局就發放了逮捕令。那時我不無擔憂地說:“逮捕令都出來了,這下可危險了。”可他卻毫不在意地說:“不用擔心,沒事的,發逮捕令也就是想讓我老實安靜點兒罷了,如果真想逮捕我的話,應該是一言不發直接過來解決掉我。”
那時先生用筆名在《申報》的自由專欄里發文章,一般不出三天,就被人發現了,于是又改筆名。那個時候是他筆名用得最多的時候,估計有五十七八個。
原稿是絕不能直接發出的,而是經由先生的妻子修改之后再發出。當時論戰也相當激烈,其中尤以與創造社、太陽社間的論戰為多,而論戰的對象有國民黨及其他各色人等。每當疲于論戰時,先生就會到我那里與我暢談。
各派人士聚在一起漫談時也是在我家,這時我定會邀請先生。如果我的注意力、觀察力再高那么一點兒的話,就能抓住更多他在漫談中所說的事情,可現如今,他說過的話大體已模糊了,我亦無法從中汲取什么了。
可以說,有十年時間我都過著與先生同吃一鍋飯的生活,可現在卻無法捕捉更多他當年的話語,實屬遺憾!
文學家之魂
倘若以一言來形容魯迅,我只能說他有著古武士之氣概和中國式的血肉之軀,該強硬的時候他絕不妥協。這與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我與郭有相當深的交情,他主要偏向于政治,所以渾身上下散發著一種政治家的氣質。而魯迅則是純粹徹底的文學家,文章犀利伸展到一切可能的地方,至死都在拼命伸展抵抗。
先生臥病在床的時候,托我找他時任南京憲兵隊長的一名學生來見他。先生說:“帶他來見我。”那名學生去見了先生,“我來看老師了。”學生沒說上幾句話就回去了。
不久后先生收到從南京來的一封信,信中言辭懇切委婉,大意如下:
前幾日得見老師,激動欣喜之情不勝言表。老師現在臥病在床,而針對老師的逮捕令已發出十年,至今未撤,作為您的學生,我的立場也很尷尬,所以一直想撤銷對您的逮捕令,可是如果我現在自行撤銷的話,只怕日后您會有所不滿,所以特詢問您的意思。
那天魯迅先生又晃悠到我家,說道:“老板,今天我可遇上了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哦。上次從南京來看我的那家伙居然給我來了封信,言辭懇切委婉至極呀,說是想要撤銷對我的逮捕令呢。我可不同意,所以這就來給那家伙回信了。”
“好不容易撤銷了,那不是很好嗎?”我問他。
他回答說:“我的日子也不長了,突然撤銷跟了我十年的逮捕令會讓我感到寂寞冷清的,所以信中已說明讓那家伙不要撤銷對我的逮捕令了。”
……
每次說到“藤野先生”的事,先生總是眉飛色舞,饒有興致,仿佛那些事情已經根深蒂固了一般,而《藤野先生》一文現已收入“巖波文庫”的翻譯集里。據說先生在北平的時候,書桌前掛有藤野先生的照片,每天在這張照片面前學習,當困意來襲想偷懶的時候看到這張照片就又奮發起來繼續學習。每次談到翻譯的事情時他定會強調要把《藤野先生》一文譯出來。
對于在日本的諸多事情,贊成的贊成,反對的反對,他從來都是態度分明,可是對于藤野先生,總是毫無條件地一并說好,報以百分百的敬慕之情。
對于中國,特別是中國人,他總是毫無掩飾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我在《活中國的姿態》這本漫談書中寫到中國的優點,可對此先生卻批評道:“老板,這可不行啊。過度的夸獎會讓孩子們得意忘形的。書總要起點教育作用,所以還是得從頭到尾地多加批評才是。”我回答說:“可是,這確確實實是中國人的一個優點啊。”先生遂又回道:“要是我就不會這么寫,但因為是老板寫的,我也不多說什么了,要換成我,是斷然不會這么寫的。”語氣依然強硬,堅決批判中國人的缺點。
但是先生并不是為了揭露而揭露,實際上他真的在擔心著中國的命運,記得他臨終前說過這樣的話:“中國的未來如同阿拉伯沙漠,國內由于戰爭在不斷地沙漠化,而國外又在不斷地加速擴大沙漠化,兩個方向都在不斷地沙漠化。如果照這樣下去的話,中國的四萬萬民眾將被逼到饑餓的戰線上,到這時,就不僅僅是中國的不幸了,而是中國全體國民的不幸了。”
說出這些話的時候,先生把中國的未來清晰地擺到了自己的眼前,這番話也表明了他的意思,即:中國必須得改變當下的行進方式,這也是對中國的一個全面清晰的剖析。
理所當然的事
中國人對比自己生活水平低的人,總是毫無理由地認為應該幫一把。也不光是對比自己生活水平低的人,對一些自己有而別人沒有的東西,也總想著從自己的一份里拿出一部分分給沒有的人。如果不這樣做,他就會心里不安。同理,接受的一方也不應該拒絕,好像拒絕了心里也會不踏實(可能有一些夸大)。這種時候,就根本不是什么面子之類的原因了,而只是出于一種非這樣做不可的不成文的規定,覺得必須得幫對方一把。
有人給魯迅先生寄來了一百塊稿費。正好趕上先生來我店里,我就把稿費的事情對他說了。先生聽后對我說道:“那今天就把那一百塊給我吧,正好我有點兒用。”我聽后馬上把錢給他了。
我倆剛閑聊了一會兒,有個女人過來找先生。先生轉過去聽了會那個女人說話,就把我剛給他的一百塊錢給了那個女人。那女人只說了一聲謝謝,拿著一百塊錢就匆匆回家去了。
要知道,在魯迅先生的生活里,一百塊錢絕不是一筆小數目。我忍不住問先生:“怎么了?發生什么事情了?”先生說道:“那個女人的丈夫,因為一個朋友的讒言,前段時間被關進蘇州監獄了。這個女人正好從事解放運動。幾天前從監獄方面傳來消息,說是只要帶三百塊錢過去就把人給放了。她自己和朋友只拿得出兩百塊,另外一百塊怎么也拿不出來,所以讓我借一百塊錢給她,于是我就把錢給她了。”
那個女人可能被騙了,我想要不要提醒先生一下呢?最后我還是忍不住問了先生那人到底和他是什么關系。
先生對我說道:“那個女人和她丈夫都是我在北平時候的學生。我也知道她是被人騙了,中國監獄的那些獄警很多都不是好東西,編編謊話欺騙這些可憐人的不在少數。這個女人應該也是被這些流氓給騙了,但是這會兒我不能告訴她這些。她拿錢走的時候應該心里充滿了希望吧,算啦。”
我一時還真的體會不到先生說的這些,不過要是換了我站在先生的立場上的話,我是絕對不會拿錢出來的。而且我會明明白白告訴那個女人她被騙了,勸她別去。
聽了我的想法,先生說道:“老板,你可以把立場再換一換呢。如果你是那個女人,而我像你剛才說的那樣勸你不要去,你肯定會迫于無奈答應下來,但是心里邊一定很絕望吧?”
先生的話讓我臉紅起來。緊接著他又說:“按照中國人的習慣,是不應該拒絕的。這種時候,如果你手上有,不論出于什么原因都要借給她。這是一種習慣。”
我問先生這種只要有就不會拒絕,是不是為了“面子”?先生笑道:“不不,不是為了面子什么的。這樣做并沒有什么條件,對于有的人來說,只要一無所有、生活困難的人有需求,能幫忙的話幫一把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哈哈哈。”我聽后,再一次感覺慚愧起來。
……
就憑這一件事,我也不會淺薄地賣弄自己是個中國通。
一次文物鑒定
很多人都對我說:“吶,內山先生,魯迅現在是不是被神化了啊?”
……若我只說“雖然中國人把魯迅當成圣人,卻絕不會將他神化,因此不必擔心”,可能還是會有人不放心。所以,我再來跟大家說說魯迅先生本人的態度吧。
“看到日本寺廟里的四天王還有仁王等國寶級木像,我發現它們真是毫無瑕疵,完全是超乎人力的雕像。中國類似的佛像呀五百羅漢呀就總感覺做得不夠精細,稍微挑剔一點就會發現貽笑大方之處。”我如此對先生說道。
他則回答:“是啊。日本人太認真,于是做出了超乎人力的東西。中國人無論怎么認真,做出來的東西總還是有人氣的,故而做出來的佛像也是跟人差不多的。”至今我還記得他的話。
有一次,一位S博士對我說:“我帶了一幅杜甫的掛軸過來,想找人幫我鑒定一下真偽。”我便問先生:“您認識什么鑒定家嗎?”他回答說:“這可真有趣。中國都沒有杜甫的真跡,日本時不時就會冒出一些在中國已經消失的東西。那個掛軸還請讓我拜見拜見。”于是我向S博士轉達了先生的要求,讓他把掛軸帶了過來。
那是一幅很大的掛軸。先生將掛軸鋪在一張很大的桌子上,展開來一看,喟嘆道:“我不知道這是誰寫的,不過字寫得還真是好。可惜的是,上面題的詩卻是比杜甫晚了很多朝代的人做的。”
之后先生又仔細看了旁邊許多名家確認真跡的落款,還一邊看落款印章上的字一邊用手指比畫。似乎是看到鄭板橋的印章時,先生用手指比畫上面的字,說道:“啊……這個字錯了。若是鄭板橋落款,按理來說是不應該出現錯字的。”先生一邊說著,一邊抬起身子望著整幅掛軸。
“康熙、乾隆以及其他多數鑒定者的印章都是肉色的,跟杜甫落款的顏色一模一樣——這張紙是染過的—— 果然是贗品。”
先生這么說道,我大吃一驚,既是因為此前我從不知道先生竟能鑒定文物,也因為他一開始就憑上面的詩作是比杜甫晚了許多時代的人做的而判定這是贗品。我不知道日本是否有鑒定家是這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