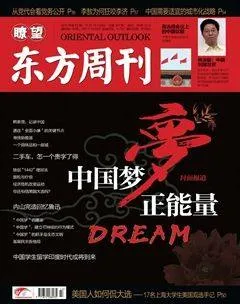中國需要適宜的城市化戰(zhàn)略
我們?nèi)菀讓⒌貐^(qū)間經(jīng)濟(jì)總量或規(guī)模的差異視作發(fā)展上的失衡,這種認(rèn)識需要糾正。真正的平衡發(fā)展應(yīng)以人均指標(biāo)而非總量指標(biāo)來衡量。東部地區(qū)經(jīng)濟(jì)的總量規(guī)模很大,中西部地區(qū)的總量規(guī)模較小,這并不必然導(dǎo)致地區(qū)發(fā)展的失衡
城市化是中國未來經(jīng)濟(jì)增長與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動力,借用時(shí)下比較熱門的“中等收入陷阱”來說,城市化也將成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動力之一。而其前提是,我們需要有新的戰(zhàn)略和思路來引領(lǐng)中國未來的城市化道路。
中國的大城市是不是太大了?
現(xiàn)行的城市化戰(zhàn)略有些傾向于限制大城市人口規(guī)模。
在城市化速度方面,“十二五”規(guī)劃提出,到2015年城鎮(zhèn)化率由現(xiàn)在的47. 5%提高到51. 5%,5年提高4個百分點(diǎn),低于當(dāng)前大約每年1個百分點(diǎn)的速度。國際經(jīng)驗(yàn)是,在城市人口比重達(dá)到50%左右的時(shí)候,應(yīng)該是城市化進(jìn)程加快的時(shí)期。
在城市體系的調(diào)整方面,政策導(dǎo)向是重點(diǎn)推進(jìn)中小城鎮(zhèn)的發(fā)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發(fā)展,具體體現(xiàn)在城市人口規(guī)模和戶籍制度方面。“十二五”規(guī)劃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規(guī)模,大中城市要加強(qiáng)和改進(jìn)人口管理……”
對人口流入的限制借助戶籍制度而實(shí)現(xiàn),對大城市發(fā)展的制約則與現(xiàn)行的土地制度相聯(lián)。每年中央政府劃撥的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決定了各個省有多少農(nóng)業(yè)用地可以轉(zhuǎn)化非農(nóng)用地,則該指標(biāo)是不允許跨省交易或調(diào)劑的。由于集聚了更多特大城市的東部沿海地區(qū)土地指標(biāo)相對不足,因而這一制度的結(jié)果便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發(fā)展受到空間上的限制。
那么中國的大城市真的太多太大了嗎?數(shù)據(jù)對比也許不是這樣。如果把人口在300萬以上的大城市與人口在100萬到300萬之間中等城市的數(shù)量做一個比值,那么2000年全球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比率為0. 29,中國則是0. 12;即使到了2009年,中國的這個比率也只是0. 17,也就是說,中國的大城市比值低于全球水平。
那中國的那些大城市,是不是太大了呢?城市人口的空間基尼系數(shù)可以反映城市間的規(guī)模差異。該基尼系數(shù)全球是0. 56,日本是0. 66,中國為0. 42。也就是說中國的大城市還不夠大,城市間的規(guī)模差異小于全球平均水平。
我們自己的研究曾把中國、東京(圈)、紐約進(jìn)行過單位面積人口密度的比較。以面積相當(dāng)?shù)摹吧虾<犹K州”與東京圈為例,兩者的單位面積人口密度較為接近。
著眼于未來的話,我們知道,決定一個城市未來發(fā)展空間的還有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基礎(chǔ)設(shè)施、治理能力等因素,而在這些方面,我們有理由相信,上海要比東京(圈)更有潛力。所以,諸如長三角、珠三角這樣的大都市圈的發(fā)展不應(yīng)過于人為限制。
或許寄希望于通過中小城市的發(fā)展來取代大城市的功能,這恐怕不太現(xiàn)實(shí)。事實(shí)上,我們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中小城市的發(fā)展并不能獨(dú)立于大城市。我們選取了在1990年人口超過150萬的14個區(qū)域性大城市,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越接近這些區(qū)域性大城市的中小城市,便能取得更快的增長速度。也就是說,中小城市的發(fā)展得益于大城市的發(fā)展。
用戶籍門檻來提高本地的勞動力素質(zhì),適得其反
也有一些大城市試圖通過提高戶籍門檻來限制人口流入,提高本地的勞動力素質(zhì)。事實(shí)可能并不會完全實(shí)現(xiàn)政策制訂者們的初衷。通過比較城市初始年份的大學(xué)生比例與該比例的增加速度,我們發(fā)現(xiàn),兩者呈現(xiàn)明顯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也就是說,大學(xué)生傾向于流向大學(xué)生比例更高的地方,通俗地說,就是人往高處流。
而在上海和北京這兩個特大城市,大學(xué)生比例的增長速度卻與其初始的大學(xué)生比例并不相稱。這表明,戶籍制度限制了高素質(zhì)勞動力在大城市的集聚。這一結(jié)果并不難理解,因?yàn)槊窆さ侥睦锒家粯樱唤o戶口他也流入城市了,而大學(xué)生不給戶口的話,很可能就選擇流往他處了。
一系列的實(shí)證研究都提示戶籍和土地控制所帶來的后果。大城市中沒有戶籍的人幸福感會降低,戶籍對外來人口中高教育程度者幸福感的不利影響尤甚,因?yàn)樗麄冊诔鞘兄械臋C(jī)會獲得時(shí)常會受限于戶籍身份。
在大城市,還出現(xiàn)了基于戶籍的居住區(qū)分割的情況,即沒有戶籍的人傾向于居住在一起。我們在信任水平的研究中,還發(fā)現(xiàn)了個人的信任水平會受周圍其他人的影響,聯(lián)系到基于戶籍的居住區(qū)分割,其結(jié)果可能是,城市中信任水平更低的非戶籍人口傾向于居住在同一社區(qū),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又會進(jìn)一步降低各自的信任水平。這些對于城市的和諧發(fā)展與公共管理都是不利的。
新導(dǎo)向的城市化戰(zhàn)略
在筆者看來,我們需要一個新導(dǎo)向的城市化戰(zhàn)略,不妨將其簡單地總結(jié)為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強(qiáng)調(diào)以市場化的方式而非通過戶籍與土地指標(biāo)來人為控制城市化的趨勢。市場效率導(dǎo)向的城市化戰(zhàn)略的目標(biāo)是,人口、土地按市場規(guī)律在空間上的再配置。最近我們的一項(xiàng)實(shí)證研究顯示,東部沿海地區(qū)的市場潛力仍是吸引企業(yè)集聚的最為重要的力量。
其次,應(yīng)充分發(fā)揮大城市的引領(lǐng)作用,其目標(biāo)是讓大城市帶領(lǐng)中小城市,形成一個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城市體系。目前的現(xiàn)狀是,城市規(guī)模的差異不夠大,城市體系在空間上是扭曲的。
最后,應(yīng)當(dāng)是一個由集聚走向平衡的過程。也就是借助市場機(jī)制下東部沿海地區(qū)集聚效應(yīng)的充分發(fā)揮,走向地區(qū)間發(fā)展的平衡。我們?nèi)菀讓⒌貐^(qū)間經(jīng)濟(jì)總量或規(guī)模的差異視作發(fā)展上的失衡,這種認(rèn)識似乎也是不全面的。真正的平衡發(fā)展應(yīng)以人均指標(biāo)而非總量指標(biāo)來衡量。東部地區(qū)經(jīng)濟(jì)的總量規(guī)模很大,中西部地區(qū)的總量規(guī)模較小,這并不必然導(dǎo)致地區(qū)發(fā)展的失衡。
只有勞動力充分釋放出來以后,中西部地區(qū)的人均土地稟賦、資源稟賦才可能提高,中西部地區(qū)農(nóng)業(yè)的現(xiàn)代化才能真正體現(xiàn)。此時(shí),伴隨要素的自由流動,在總量“失衡”的同時(shí),人均意義上地區(qū)間可能是走向平衡的。現(xiàn)在東部地區(qū)的集聚仍在發(fā)生,而戶籍制度可能限制了中西部地區(qū)勞動力對東部地區(qū)集聚效應(yīng)的分享。
所以,我們要轉(zhuǎn)變思路,要選擇一個新導(dǎo)向的城市化戰(zhàn)略。當(dāng)然,這樣的城市化戰(zhàn)略需要多方面的配套性措施,例如,這其中需要政府在公共服務(wù),特別是教育投入上做到地區(qū)間的適度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