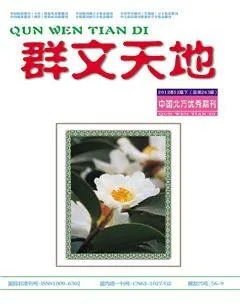唐代山南東道節度使略論
摘要:山南東道節度使于至德元載設立,一直存在至唐朝滅亡。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唐廷極為重視。雖然在有些時期內山南東道發生叛亂,但在大多數時期還是遵守皇帝詔令,受中央控制。文章從山南東道節度使的設立以及地位,所領州數的變動及其原因等方面對其進行了研究,以此來看山南東道節度使對唐朝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和對政局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關鍵詞:唐代;山南東道節度使;戰亂
唐睿宗景云年間,節度使始設。自后天下分設四十余鎮,節帥擁兵自重,割據稱雄,唐廷所控之地僅東南幾鎮!魏博、淮西、淄青等藩鎮已有很多人關注,而山南東道卻缺少專門系統的研究。山南東道除了具有唐代藩鎮的共性外,還有其自身的特點。研究山南東道,對了解唐中后期的政治軍事狀況,以及對節度使制度的研究都是有所裨益的。文章擬從以下兩個方面對山南東道的情況作一考察。
一、山南東道節度使的設立及其重要地位
山南東道為山南道析分而來。貞觀元年(公元624年),唐太宗根據地形地勢劃分軍事區域統一部署,共有10道,山南道為其一。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山南道所轄甚闊,分為山南東西二道。唐玄宗時分天下為15道,山南東道轄1府17州。此時的山南東道尚為監察區,真正成為藩鎮設節度使在唐肅宗的至德元年(756年)。
關于山南東道節度使的設立時間,《新唐書·方鎮表》記載:至德二載,“廢南陽節度使,升襄陽防御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鄧、隋、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南陽郡即鄧州。而《資治通鑒》記載的時間與之不同:至德元載,“七月,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吳廷燮《唐方鎮年表》所持觀點與《資治通鑒》略同。筆者認為,山南東道設立的時間應于至德元載。與大多數藩鎮設立的原因一樣,山南東道節度使設立于安史之亂時,設立的原因就是平叛。從至德元年于襄陽、南陽皆設防御守捉使可以看出其目的。
關于山南東道節度使的地位問題,曾有學者對唐前期的山南東道的地位做了研究。如周尚兵《唐代前期的山南東道——兼論唐前期漢水中游的戰略地位》,任大熙《唐朝前期政治中的山南、劍南地區》一文對整個山南地區的重要地位,特別是經濟交通上的地位做了論述。唐朝前期的山南東道與山南東道節度使的管轄范圍是大不相同的,唐前期的山南東道其實還包括后來的荊南節度使。但山南東道節度使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
(一)軍事地位。山南東道節度使地處中原,本不應有防御河朔藩鎮的責任,但一則地理位置重要,是連接各地的交通要道,二則與淄青鎮相接,與河朔藩鎮也相去不遠,所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就具有了防御河朔藩鎮的責任。其治所襄陽的軍事地位更是自古便受到重視,“荊襄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竊以為荊、襄者,天下之吭;……荊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關、洛……無荊襄不可以立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山南東道節度使的重要軍事地位。
(二)經濟地位。山南東道節度使所轄地區除了土地肥沃,擁有較發達的農業外,其交通樞紐的地理位置是提高其經濟地位的重要原因。作為交通要道,不僅水路交通運輸便利,朝廷調運東南財富要通過此地,而且促使了該地的商業貿易的發展,使其商品經濟獲得了發展的機會。
由于山南東道節度使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自設立以來,朝廷就極力加以控制,派很多的重臣任節度使,雖然大多數時候山南東道節度使都是受朝廷節制,很少對抗朝廷。但比起其它朝廷控制的藩鎮來說,山南東道節度使存在較多的兵變和叛亂,像梁崇義割據參加的四鎮之亂等等。所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擁有許多與其它藩鎮不同的特點。
二 山南東道節度使所領州數的變動及其原因
據《新唐書·方鎮表》:至德二載“廢南陽節度使,升襄陽防御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鄧、隋、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資治通鑒》:至德元載七月“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兩書雖時間記載不一致,但州數相通。而同在《新唐書》的《魯炅傳》中記載:“至德二載五月,乃率眾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炅殊死戰二日,斬獲甚眾,賊引去。俄拜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這就與上面相抵觸,筆者以為《新唐書·方鎮表》、《資治通鑒》所記載的“九州”較之《魯炅傳》更為可信。《資治通鑒》采納“九州”之說必有其道理。
《資治通鑒》:寶應元年“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之,乃諷所部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荊南節度使呂諲、淮西節度使王仲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眾心,恐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從記載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來瑱為了留在山南東道,慫恿屬下上表留己。朝廷雖然答應其請求,但是怕他以后勢大難平,便削其四州(金、商、均、房四州)。關于這四州的歸屬,上面提到《新唐書·方鎮表》記載“金、商二州隸京畿。”均、房二州沒有提及。《資治通鑒》有明確記載:“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事實是怎么樣,因文獻記載太少,筆者不敢妄下結論,有待以后加以考證。
《新唐書·方鎮表》:元和十年(815年)“置唐隋鄧三州節度使,治唐州。”元和十一年“廢唐隋鄧節度使,是年復置,徙治隨州。”元和十二年“廢唐隋鄧節度使,以唐、隋、鄧三州還隸山南東道。”從元和十年至十二年這三年間,唐、隋、鄧三州別置一節度,其原因源于當時的淮西吳元濟之亂。《舊唐書·地理志》也記載:“……元和中,淮蔡用兵,析鄧唐二州別立一節度。”
《新唐書·方鎮表》:光啟元年(885年)“升金商都防御使為節度,兼京畿制置萬勝軍等使。是年,罷節度,置昭信軍防御使,治金州。”在光啟元年的上一年,也就是中和四年,秦宗權將趙德諲攻陷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秦宗權以其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后,而趙德諲當時并未控制金、商二州,所以朝廷在此置昭信軍,以抵御趙德諲。
《新唐書·方鎮表》:天祐二年(905年)“賜昭信軍節度號戎昭軍節度,增領均、房二州。是年,更戎昭軍曰武定軍,徙治均州。”天祐三年“忠義軍節度復為山南東道節度。廢武定軍節度,復以均、房二州隸山南東道節度。”天祐二年,西川王建遣將攻昭信軍節度馮行襲,破金州,朱全忠遂加強了金州防務,更名武定軍,并增領兩州,將治所遷至均州。天祐二年八月,朱全忠遣武寧節度使楊師厚攻趙匡凝,九月趙匡凝逃到淮南,接著又攻占荊南。因山南東道與荊南得以平定,更為了賞賜楊師厚,朱全忠便將武定軍廢除,將均、房二州隸山南東道節度,以楊師厚為節度使。武定軍節度使馮行襲也改任為匡國節度使。
三、余論
山南東道節度使自至德元載設立,直到唐朝滅亡朱全忠建后梁。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故山南東道地區經常遭受戰禍,雖不像河北等藩鎮常發生叛亂和兵變,但也不如東南藩鎮安寧,在有一些時期十分的混亂。總的來說,山南東道節度使基本還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為維持唐政權做了努力,從多個方面影響著唐朝的政局。
參考文獻:
[1]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9.
[2]司馬光.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2001.
[3]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4]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5]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2000.
(作者簡介:楊金寶,男,甘肅平涼人,甘肅省平涼市莊浪縣陽川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