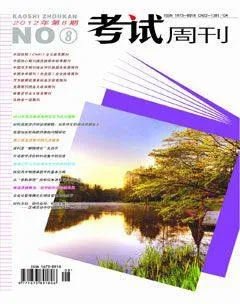葡萄傳入內(nèi)地考
摘 要: 葡萄作為一種外來作物,是早期中西交流的重要代表之一。一直以來,普遍認(rèn)為葡萄是張騫出使西域時引入葡萄的。實際上,葡萄的引入存在多方面的爭議。本文通過對《史記》、《漢書》等文獻的考察推證、借鑒,并利用前人經(jīng)驗等相關(guān)材料,證明葡萄的引入并非張騫第一人所為。
關(guān)鍵詞: 葡萄 張騫 引入內(nèi)地
一、引言
葡萄,《史記》《漢書》都作“蒲陶”,后來又有“蒲桃”、“蒲萄”、“葡萄”等寫法。可見它是外來語的記音字,并不是中國原產(chǎn)。據(jù)考古資料,最早栽培葡萄的地區(qū)是小亞細(xì)亞里海和黑海之間及其南岸地區(qū)。中國栽培葡萄已有2000多年歷史,相傳為漢代人張騫引入。張騫將葡萄引入內(nèi)地這一事件,第一次見于文獻記載的是《齊民要術(shù)》①卷二“種蒜”引王逸曰:“張騫周流絕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酉陽雜俎》也有載:“庾信謂魏使尉瑾,……瑾曰:‘此物實出于大宛,張騫所致。’”②這些記載很顯然都把葡萄從西域的引入歸功于張騫。直到今天,普遍的觀點還是認(rèn)為,葡萄最早是由張騫引入內(nèi)地的。
張騫真的是引葡萄入內(nèi)地的第一人嗎?事實上,葡萄是否由張騫引入內(nèi)地還存在多方面的疑惑。本文利用文獻記載針對各方面進行考證。
二、葡萄非張騫所引
據(jù)《史記·大宛列傳》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shù)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中葡萄、苜蓿極望。”③通常從其中的關(guān)鍵詞“始”理解,認(rèn)為葡萄就是由張騫出使西域引進中國內(nèi)地的。而《漢書·西域傳》對此的說法也是大同小異:“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至數(shù)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苜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苜蓿離宮館旁,極望焉。”④通常也理解為,自西域之路開通后,漢朝統(tǒng)治者便讓使者帶回葡萄種子,引入內(nèi)地。
實際上,長期以來,后人對《史記》、《漢書》等材料對此問題論述的理解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史記》、《漢書》原文只是講到張騫經(jīng)過大宛,知其地盛產(chǎn)蒲陶。“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⑤,“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⑥。不過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寫在西域之路通行后。雖然到過大宛的使者不少,但論最出名的使者,當(dāng)屬張騫,也無怪乎后世將葡萄的引入歸于張騫的功績之一。這是后人對史料的理解存在“想當(dāng)然”的態(tài)度。但是所提供的史料并沒有明確地表示葡萄就是由張騫從西域引入內(nèi)地的。
根據(jù)歷史事實了解,張騫一共兩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39年。“……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逃遁而常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yīng)募,使月氏”⑦,于是張騫就從長安出發(fā)前往月氏了。然而,途中經(jīng)過匈奴時,被單于扣留。“經(jīng)匈奴,匈奴得之,傳旨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余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jié)不失”⑧。從中可以得知張騫在前往月氏的過程中被單于扣押了十多年,還娶妻生子了。后來張騫率部下逃出匈奴的看管,順利來到大宛,“大宛……遣騫,為發(fā)導(dǎo)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復(fù)為匈奴所得。留歲余……”⑨。張騫從大宛返國途中又被匈奴所阻,到了次年才脫險逃歸。這一路一共經(jīng)歷了十幾年,還歷經(jīng)兩次匈奴人的扣押,相當(dāng)坎坷艱辛,所以這次張騫是極少可能帶回葡萄種子的。事實是,張騫回朝后,他所做的,只是“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⑩,將一路的見聞向漢武帝做了介紹,是否因此引入種子,并沒有明確說明。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在前115年。武帝詢問剿滅匈奴之計的時候,張騫“因言曰:‘……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11}。可見這次出使西域是為了加強與烏孫的聯(lián)合,壯大漢朝的實力。張騫本人只到過烏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礬及諸旁國。烏孫發(fā)導(dǎo)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shù)十人,馬數(shù)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12}。“歲余,騫卒。后歲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13}。張騫在烏孫國出使一結(jié)束,便偕同烏孫使者數(shù)十人返抵長安,一年多之后就過世了。而此時漢朝與西域之間的交流開始日益頻繁,由此引發(fā)的經(jīng)濟交往也更加密切,不排除葡萄種子引入的可能。但是并沒有明確說明是由張騫帶回來的。由材料可以猜測,當(dāng)時忙于向烏孫國展示大漢王朝的張騫使團,也并沒有引入葡萄。
可見,無論是史書記載還是根據(jù)歷史事實的推測,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將葡萄種子引入中國內(nèi)地的可能性都極小。
三、葡萄在張騫之前已經(jīng)傳入
葡萄具體是在什么時候傳入內(nèi)地的呢?《史記·大宛列傳》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shù)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中葡萄、苜蓿極望。”{14}此部分載于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部分。據(jù)前人對這部分的研究,其認(rèn)為《史記》的觀點是:葡萄引入于公元前115年。
而在《漢書·西域傳》中載:“(王)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于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后十余萬人伐宛,連四年……又發(fā)使十余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官館旁,極望焉。”{15}上引文記載“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的時間是李廣利將軍攻克大宛之后。同樣據(jù)前人之言,認(rèn)為《漢書》的觀點是:葡萄引入于公元前101年。
因此,絕大多數(shù)人認(rèn)為,葡萄是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后才引入中國內(nèi)地的。除了前文已經(jīng)排除的張騫外,不少人還持有“葡萄可能由漢使團中其他人引入”的觀點。然而,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卻出現(xiàn)了葡萄在張騫之前在內(nèi)地已有種植的證據(jù)。
司馬相如是漢代的辭賦作家。《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引入了他的作品《上林賦》,其中有言:“于是乎盧橘夏孰,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樸,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郁棣,榙盤荔枝,羅乎后宮,列乎北園。”{16}此處描寫的是位于荊楚之地的上林苑宏大的規(guī)模。這里可以很明顯地發(fā)現(xiàn),“蒲陶”作為水果之一,與盧橘、柑橙、枇杷、柿子、楊梅、櫻桃、荔枝等一起被羅列出來了。可見當(dāng)時,葡萄已經(jīng)傳入內(nèi)地。雖不敢確認(rèn)它已經(jīng)成為普通的日常水果,但是能夠證明它起碼在帝王之家有存在。
《上林賦》具體的寫作年代沒有明確記載。據(jù)《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是時梁孝王來朝……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生游士居數(shù)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17}由以上材料可知,司馬相如于漢景帝時跟隨梁孝王由家鄉(xiāng)蜀到長安,幾年之后完成了《子虛賦》。公元前144年,梁孝王死后,司馬相如回到蜀地。受到當(dāng)朝天子,也就是漢武帝的賞識,請求為天子游獵作賦。之后便完成了《上林賦》,被封為中郎將。司馬相如“為郎數(shù)歲”,被派回蜀處理事情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相如)乃著書,藉以蜀父老為辭……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18}由其時間可以推知,《上林賦》大約完成于漢武帝即位之初。而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也大約在此時,只是中間經(jīng)歷了十幾年才輾轉(zhuǎn)回朝。也就是說,《上林賦》完成于張騫回到長安之前的若干年。假若張騫在第一次出使西域便能引入葡萄,也比《上林賦》所述的時間晚得多,更何況在當(dāng)時引入的幾率小之又小。既然如此,那么上林苑的葡萄,就不是由張騫出使西域后引入內(nèi)地的。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葡萄的引入不僅不是張騫親歷所為,反而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葡萄就已經(jīng)在內(nèi)地種植了。
四、張騫之前的中西交流
實際上,內(nèi)地與西域的交流,在張騫通之前已經(jīng)存在了。《史記·匈奴列傳》中多次記載了內(nèi)地與西域的交流,“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jié)和親之約……于是高后乃止,復(fù)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fù)修和親之事……”,“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19}。而《史記·西南夷列傳》更是明確指出:“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史焉……”“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馀縣,屬蜀。”{20}種種跡象表明,張騫以前,中國內(nèi)地與包括匈奴、西南夷等地區(qū)都有使者、和親等類似的較為頻繁的交流,當(dāng)然少不了與西域地區(qū)的交流。這些交流的同時,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將葡萄引入內(nèi)地的可能性。
關(guān)于中西開始交流的最早時間,史學(xué)界頗有爭議。在《早期中西交通與交流史稿》一書中,作者認(rèn)為:“自西周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條道路上已經(jīng)有中國的絲綢、銅器大量地運往中亞,傳去的還有中國的天文、歷法。絲綢更通過那些游牧民族間接地傳到更加遠的地方,甚至歐洲。”{21}這種說法認(rèn)為絲綢之路開始于春秋戰(zhàn)國時。考古學(xué)家王炳華先生指出:“包括吐魯番在內(nèi)的新疆大地,作為歐亞大陸交通往來的重要通道,遠遠要早于公元前2世紀(jì)。”{22}因此,我們得知,在張騫之前中國很早就與西域有交流了。葡萄完全有可能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就在內(nèi)地種植了。只是相對而言,張騫出使西域更為人所知,其宣傳和介紹使得葡萄大量引入,并在內(nèi)地更廣泛種植,因此在漢代逐漸普及開來。
五、結(jié)語
綜上所述,葡萄已經(jīng)被證明了不僅不是張騫出使西域時引入的,反而是在通西域之前在內(nèi)地已有種植;史料也證明,推動西域與中國內(nèi)地的交流,在張騫之前已有人為。所以,傳統(tǒng)觀點認(rèn)為的張騫通西域,并將葡萄引入內(nèi)地,并不真實可靠。
后世之所以把這一事跡歸功于張騫,也許是因為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后,較為大力地推薦葡萄這種作物,使得葡萄開始在內(nèi)地廣泛種植。且由于記載的可供研究的資料較少,《史記》、《漢書》的記述則讓后人產(chǎn)生了誤解。
不可否認(rèn),張騫的確在推動中西交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見于《史記》《漢書》等文獻中,他只是對西域的葡萄做了較為廣泛的宣傳介紹,確實推動了葡萄在內(nèi)地的廣泛種植。也許是因為較之其他使者來說,張騫的貢獻更為巨大,所以后人把葡萄的引入這一功績也歸于張騫。雖然張騫的功績彪炳千古,我們不能抹殺,但是也要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chǔ)上進行辨析。
注釋:
①轉(zhuǎn)引自:石聲漢校定,《齊民要術(shù)今釋》1—4分冊,1958年科學(xué)出版社。
②轉(zhuǎn)引自:涵芬樓,《四部叢刊》,影印明趙氏脈望館本,卷18。
③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2420頁。
④班固,《漢書·西域傳》,中華書局,968頁。
⑤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2404頁。
⑥班固,《漢書·西域傳》,中華書局,968頁。
⑦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2402頁。
⑧同上。
⑨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2402—2404頁。
⑩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2404頁。
{11}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2410頁。
{12}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2412頁。
{13}班固,《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中華書局,968頁。
{14}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2420頁。
{15}班固,《漢書·西域傳》,中華書局,968頁。
{16}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華書局,2261頁。
{17}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華書局,2246—2250頁。
{18}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華書局,2272頁。
{19}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中華書局,2128—2132頁。
{20}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2236—2238頁。
{21}轉(zhuǎn)引自:石云濤,《早期中西交通與交流史稿》,學(xué)苑出版社,2003年版。
{22}轉(zhuǎn)引自:王炳華,《訪古吐魯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中華書局,2008.
[2]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華書局,2008.
[3]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中華書局,2008.
[4]司馬遷.史記·南越列傳.中華書局,2008.
[5]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2008.
[6]班固.漢書·西域傳.中華書局,2007.
[7]班固.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中華書局,2007.
[8]徐朔方.史漢論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
[9]石聲漢.試論我國從西域引入的植物與張騫的關(guān)系.2008.
[10]李嬋娜.張騫得安石國榴種入漢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