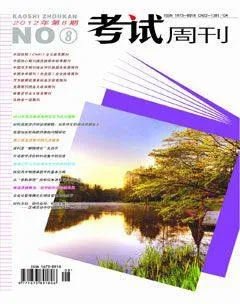語文課到底該教什么?
一
近日,拜讀了朱良才老師的《教育三十七度二》這本書,其中有一則《語文老師放牛》的小故事。故事情節是這樣的:
如果讓一位語文教師去放牛,他會拔起一根青草,向著牛群不停地發話:“這是什么草?注意,不要亂說——舉手回答。”
“你們以前吃過這種草嗎?想不想吃?”
“快速地嗅一嗅,告訴我它的氣味。”
“仔細觀察它的樣子,看看能分幾段,每段的作用是什么?”
“在這種感受的基礎上,你決定將來怎么辦?比如,更加熱愛——大自然,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和血。”
結果,牛餓死了。語文教師還在感嘆:真是對牛彈琴!
教育哲學家喬治·奈勒說:“不應用哲學去思考問題的教育者,必然是膚淺的。”這則故事看似可笑,實則辛辣,耐人尋味。
“放牛”與“語文教學”原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卻被用來作形象的對比。看語文老師“放牛”的步驟,窺探有些語文教學猶如“十萬個‘為什么’”,寶貴的課堂時間在這無效的一問一答中消耗掉,教師將精美的文章分解得支離破碎,學生學習索然無味。
要想讓牛兒吃飽喝足,必須讓牛兒自己去吃、去喝。學習語文也是如此,語文老師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是找到一個既讓學生樂學,又讓我們樂教,既好看又實用的教學方法。但有一點是需要我們經常思考的,那就是:“語文課到底應該教什么?”
文學家、語文教育家葉圣陶晚年曾提出這個纏繞語文教學百年的問題:“語文教學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認為,語文教學之所以“少慢差費”,幾十年無大的改觀,根源在于對此問題沒有很好的解答。已屆耄耋之齡的葉老對此心急如焚,呼吁語文教育對這一問題加緊研究,并期待自己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答案。
遺憾的是葉老沒能如愿以償。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對這一問題語文教育界仍然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特別是現在進入了新課程時代,對語文老師提出了更高的專業要求,如小組學習,主題閱讀,關注課堂效益,等等。但是有時候我們也很迷茫“不知道語文到底該教什么”,甚至發出“越來越不會教書了”的感嘆。
二
語文課到底該教什么?當然教語文。在教師的潛意識中,這個問題被認為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可是問題就出現在這里。諸多現象,我將其分為幾類。
一是把語文課上成了思想道德說教課。現在我們聽到的種種語文課,大多進行的是語文中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剖析、評價,教師也往往是由課文的思想內容引申開去,旁逸斜出地聯系學生的學習和生活。一講《氓》就大談特談古代封建婦女地位問題,一講《奧斯威辛沒有什么新聞》就把重點放在介紹二戰集中營的種種酷刑,卻忽略了引導學生學習篇章結構、表現手法、語言風格等。朱自清先生1934年就從自己“在中學教過五年國中”的實踐中得出結論:“讀的方面,往往只注重思想的獲得而忽略語匯的擴展,字句的修飾……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訓練,所獲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為思想也就存在語匯,字句,篇章,聲調里;中學生讀書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將書里的話用他們自己原有的語匯等等重記下來,一定是相去甚遠的變形。這種變形必失去原來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輪廓,沒有什么用處。”(《文心序》)朱先生的批評真可謂一針見血。
二是把語文課上成了科學課、政治課。一說加強與其他科目的溝聯,許多老師就種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上《動物游戲之謎》就著力解決“動物是如何通過游戲傳遞信息的”諸如此類的問題,上成了科學知識課,忽略了語文學科方面的學習。合作是合作了,探究是探究了,可這是語文課該管的事嗎?
三是小組學習缺乏時效性。一說自主互助學習,就嘩啦啦圍成小組,不管問題是否有必要討論,就讓學生七嘴八舌地說個沒完,使得“合作”教學在課堂上僅僅是讓學生討論討論,走走過場而已,“自主”變成了放羊式的學習,全然沒有了教師的指導。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包括各方面的因素,學習形式應該也必須是多種多樣的,而自主合作探究作為一種新的學習方式,僅僅是眾多方式中的一種,它還需要在實踐中得以進一步的檢驗和修正。萬萬不可以把它作為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應該先領會其精神實質,精心設計實踐,與其他學習方式配合,且不可濫用。
四是老師在課堂上沒有準確的定位。一說“自主互助學習型課堂”,有的老師就真的把“學習的時間和空間”完全放給了學生。一提“講不過十分鐘”,有些老師就不敢講了。前幾天讀到著名特級教師吳心田的文章,心有戚戚焉。他說:“語文教學的過程應該是師生互動,教學相長,這是一條規律。只靠教師單一性的講析是難以奏效的,必須通過學生的大量實踐和訓練才能達到,而這種實踐和訓練又離不開教師的科學指導。”然而近幾年來,有些語文老師卻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過分地強調學生的自主性,而忽視了教師的指導作用。有的語文課一味地讓學生自讀或自學,缺乏老師必要的指導,使得學生的自學和討論不得要領,帶有一定的盲目性,甚至有些學生難以理解的問題未得到解決即下課。
三
福建省莆田市特級教師許更生一直積極倡導“構建以詞語為核心的語文教學”。他的課上得很樸實,先是讓學生劃詞語,然后是抄寫詞語,再就是背誦優美的段落,最后就是用上劃出的詞語仿寫句子。教學過程很簡單,沒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東西,卻遵循了語文教學的本質規律,那就是品味語言、積累語言、模仿語言、創造語言。回想起自己上小學的時候語文老師上課總是要劃生字生詞,現在想起來,這不失為積累語言的一種好辦法。只是我們太習慣于跟風了,我們總為自己的東西貼上“新”的標簽,如“新課程”、“新課標”、“新教育”、“新語文”,總之是越“新”越好。不過,靜下心想,這些“新”的東西還是從傳統中來的,現在大家都在學習杜郎口經驗,他們的教學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叫“展示”,就是讓學生到黑板上展示自己的學習成果,因為只有展示才能暴露問題,才能使教學做到有的放矢。說白了就是爬黑板。可是如果換了我們,誰要是在公開課上用大量的時間讓學生爬黑板,肯定會讓人恥笑:“都新課程了,都自主互助學習型課堂了,還用這種老掉牙的東西!”
可是多年來,我們就是這樣過來的。“語文老師放牛”看似是一個笑話,實則是一個警示, 警示著語文教師如何才能“讓學生帶著問題走進教室,帶著更多的問題走出教室”。 “語文課到底該教什么?”從根本上講就是要關注語文的學科特點,遵循語文的教學規律。語文教師應不斷反思,繼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