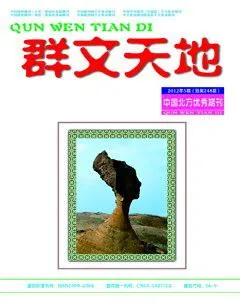關于“花兒”的早期記載與研究活動
西北“花兒”,以其五彩繽紛的靚麗,引起世人的關注。可惜在它早期的萌芽階段和產生初期,限于歷史的社會的世俗的多種因素的限制,很少留下文字記載。
據甘肅學者王沛在《中國花兒曲令全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說,明代成化年間(公元1465——1487年)兵部尚書王竑辭官回家后,在家鄉大夏河畔留下的詩作《柳岸薰風》中贊頌“花兒“音樂:“堤邊楊柳郁如林,日日南風送好音。長養屢消三伏暑,詠歌曾入五弦琴。”王沛認為,“南風送”來的“好音”,正是優美的“花兒”旋律。如此說成立,則比明代萬歷年間(1573——1619)高洪的詩作《古鄯行吟》中所提及的“花兒”早了100多年。
不少傳統“花兒”中提及明代“十三省”。甘肅學者柯揚在論著《詩與歌的狂歡節》(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說:“洮岷‘花兒’中唱到:‘松樹林里虎丟盹,看見尕妹擔的桶,人品壓了十三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明初沿用元代的行省制,將元代的十一省增加為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包括現在的甘肅)、四川、廣東、廣西、云南、貴州等十三省。后又改稱‘十三承宣布政司’,清康熙以后增為十八省,光緒時增至二十三省、四藩部。所以說,‘十三省’是明初的概念,是指的全國。說這首花兒產生于明代,看來是恰當的。”寧夏學者武宇林在《中國花兒通論》中認為,青海民研會1982年編印的《“少年”(花兒)論集》以及羅耀南《花兒詞話》中搜集舉例的 “十三省”花兒,皆屬于此類。如此,“花兒”在明初,實際上就已唱紅。
趙宗福《花兒通論》:高洪,明代西北名士,山西籍名宦、詩人。明神宗萬歷年間曾任職河州,尊嚴有度,博學善吟,重視地方人才培養,頗有政績,去后曾入祀名宦祀(王世臣《河州志·名宦》)。任職期間曾西游湟水流域,寫下了《古鄯行吟》之二:“青柳垂絲夾野塘,農夫村女鋤田忙。輕鞭一揮芳徑去,漫聞花兒斷續長。”(鈔本《秦塞草》)明確地記載了“花兒”當時已在河湟地區唱紅的勝景,這是迄今為止,最早確切記載“花兒”演唱的文獻,比吳鎮有關“花兒”的詩句推早了將近200年。
馬志勇《河州志校刊》(甘肅文化出版社2004年):據明代吳禎著《河州志》載,高弘(誤為高洪),山西大同府朔州人,舉人,成化庚寅年任。
魏泉鳴《中國花兒學術史論稿》(西北民族大學編2011年):《河州志》人物志名宦對高弘有“在任尊嚴守正,篤學善吟,人材多有成就”的評價。明代成化年間乃憲宗皇帝朱見深在位,1465—1478年凡23年。明代萬歷年間乃神宗皇帝朱翊鈞在位,1573—1620年,凡48年。萬歷年間以最后一年計距今為384年,成化年間以最后一年計距今已517年,兩者之間相差133年。明憲宗成化六年為庚寅年,公歷對應為1470年,高弘在任期間,至今已534年,“花兒”一詞出現距今已530年左右了。
《我憶臨洮好》,甘肅臨洮人吳鎮(1721—1797年)作,共10首,其中第9首“我憶臨洮好,靈蹤足勝游。石船藏水面,玉井瀉峰頭。多雨山皆潤,長豐歲不愁。花兒饒比興,番女亦風流。”此為甘肅張亞雄、慕少堂1936年12月3日在《松花道人賞識花兒》中所引。吳鎮與詩人袁子才、蔣心余、趙甌北同時,隨784f03e0946873bba132de7abdea5011e182cc5ae6d654fc77ae2306d4983d97園詩話亦盛稱其作品。憶臨洮10首,大概是游宦瀟湘時所作。
《甘肅竹枝詞》,清代道光初年安徽桐城人葉禮漫游甘肅、青海一帶時,作竹枝詞8首,其中一首寫道:“男捻羊毛女耕田,邀同姊妹手相牽。高聲各唱花兒曲,個個新花美少年。”見趙宗福《花兒通論》,此為“花兒”與“少年”稱謂同時記載的最早詩作。
《循化志》,清乾隆年間(公元1736—1795年)編修。據青海學者董紹宣和甘肅學者王沛分別查考,該志書記載了當時流行的花兒:“大力加牙壑里過來了,撒拉的艷姑哈見了;撒拉的艷姑是好艷姑,艷姑的腳大者壞了;腳大手大的不談閑,走兩步大路是干散。”
《游松鳴巖》,近代隴右詩人張建作,“松鳴佳景出塵埃,一度登臨一快哉。石磴疑從云際上,天橋渾向畫中排。林藏虎豹深山古,路接羌戎絕徑開。我亦龍華游勝會,牡丹聽罷獨徘徊。”這是甘肅學者柯揚從清黃陶庵纂《導河縣志》中所查,柯揚在《花兒溯源》一文中認為“詩中‘牡丹聽罷獨徘徊’一句,明確指出所唱的是花兒。‘牡丹’一詞,或是指‘白牡丹令’之類的令名,或是用牡丹作比喻,或是指《十二月牡丹》一類的專唱牡丹的花兒,三者必居其一。”
《松鳴巖古風》,近代隴右詩人祁奎元作,其中“老僧新開浴佛會,八千游女唱牡丹”句,甘肅學者王沛《河州花兒》中引用并認為“唱牡丹也可能指唱花兒。”
《花兒集抄》、《花兒探索》,分別是十九世紀末鄧華堂先生記錄過的手抄本,是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花兒”研究,標志著“花兒”理論研究的興起。可惜未出版就全部佚失了。
《田家雜詠》,青海近代詩人基生蘭作,其二“聞到田歌四起,清聲雅韻悠揚。此是農家樂處,外人莫笑輕狂。”趙宗福《花兒通論》中說,詩中“田歌”即指“花兒”,根據詩人當時活動的地域范圍,還可知指的是河湟“花兒”。
《西寧道中》,隴右近代史志學家慕少堂作,其著作頗豐,尤以《甘青寧史略》著名。其中之一“荊布田家婦,含羞薄面皮。風流曲成調,一路唱花兒。”此是他于二十世紀20年代來西寧途中所作。
《甘肅的歌謠·話兒》,地質學家袁復禮20年代初所寫文章,連同他在地質勘查工余所搜集的“花兒”30首,發表于北京大學《歌謠》周刊1925年第83期。這篇文章,由于搜集較早,當時把“花兒”誤寫成了“話兒”。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后,第一個向全國介紹“花兒”的人。
《甘肅大通縣風土調查錄》(手抄本,存北京圖書館),1926年大通縣知事聶守仁所撰。甘肅柯揚《花兒溯源》披露,其中記載了當地“俗尚簡樸,山歌野曲,番漢相雜。”
《中國歌謠》,朱自清1929年著。他是第一個把花兒寫入專著,第一個把“花兒”引入大學課堂的人。朱自清在北京大學講授“歌謠”時引用過袁復禮搜集的一首花兒:“焦贊孟良火葫蘆,火化了穆柯寨了;錯是我倆都錯了,不是再不要怪了。”
《花兒集》,甘肅榆中學者張亞雄(1908——)著,15.3萬字, 1931年北平平民大學新聞系畢業,早年從事新聞和報業工作,解放后在甘肅省政協文史資料室工作,現為甘肅省民研會理事。他早在20年代就開始了對西北“花兒”的采集研究,1940年于重慶出版我國第一本“花兒”的專著《花兒集》,1948年、1986年分別在蘭州、北京增訂再版。分上、下兩編,上編系統歸納了“花兒”的研究過程,涉及了“花兒”的源流、民風民俗、流傳演變、文學與音樂、流派及結構等,下編分30個類別,精選了“花兒”627首,包括河湟“花兒”、洮岷“花兒”,大多為河湟“花兒”。他是第一個認為西北花兒分河湟“花兒”、洮岷“花兒”兩大流派的人,也是第一個明確指出青海花兒“令”、“調”特殊,青海是“花兒”的家鄉的人。據張亞雄回憶,他編著《花兒集》時,就求教于青海學者李文實和魏明章,兩位青海學者為他提供了不少“花兒”唱詞。其出版奠定了“花兒”理論系統研究的基礎,標志著“花兒”研究時期的開始。
《花兒集·校補敘言》,謝潤甫(甘肅臨洮人)為張亞雄校補其《花兒集》時所作,提出了《花兒集》在研究民情、民風、歷史、方言文學等好多學術方面有一定作用;內容真切無文人修飾;“花兒”是活詩經;準確注釋洮岷“花兒”等。業內學者認為,其價值超過文字本身。
《甘寧青史略》, 1936年蘭州俊華印書館印行,編纂者慕少堂首次將“花兒”編入其中。甘肅魏泉鳴《中國花兒學史綱》說,其中的《歌謠匯選》收入近百首民歌,內有“花兒”6首,他是第一個把“花兒”編入西北地方史的人。慕少堂,名壽祺,字子介,甘肅鎮原人,民國元年任甘肅臨時議會副議長,曾為甘肅省通志局副總纂、甘肅文史學院教授,著述頗多。
《評論花兒的價值》,見慕少堂《甘青寧史略》副編《歌謠匯選》。序曰:“時有不速之客在寓頑小牌正在算胡,鄰家做土工者又在房上漫花兒,一唱一和,音調酸楚動聽,有時用比體以發端。余聞之喜曰:此好資料也!湊成四韻,聊以代評。”其詩:“世情大抵愛新奇,譜續霓裳更有誰?作戲逢場頑葉子,聽人隔院唱花兒。來源遠矣伊涼調,淫曲居然鄭衛詩。畢竟其中多比興,松崖評語正相宜。”趙宗福《花兒通論》認為,其文字介紹了收錄“花兒”的原則標準,又敘述了寫詩的背景,詩中推測“花兒”源于唐代伊涼曲、涼州曲等曲名,花兒和《詩經》中的“鄭風”、“衛風”類似,正如吳鎮“花兒饒比興”之說。這些比一般演唱情景的描寫,更深了一層,帶有濃厚的理論色彩。
1938年4月,王洛賓曾在六盤山下一個車馬大店向循化撒拉族“花兒”歌手五朵梅搜集花兒,成為第一個用樂譜記錄六盤山“花兒”的人。5月,王洛賓先后在蘭州、西寧搜集、整理“花兒”曲令多達30多種,是當時記錄“花兒”曲令樂譜最多的一個人。此外,他還在舞臺上演唱“花兒”,成為當時第一個登上舞臺演唱花兒的文人。他在“中國花兒學科史上創下了三個第一”(魏泉鳴《中國花兒學史綱》)。
1939年9月,著名電影導演鄭君里導演的電影《民族萬歲》在海晏縣三角城金銀灘拍攝。1938年11月到西寧回民中學任音樂教師的王洛賓(1913—1996年)與藏族千戶同曲乎的養女薩耶卓瑪姑娘同時應邀在《民族萬歲》影片中扮演牧羊姑娘和其幫工的角色。在愉快的相處中,兩人產生愛情,歌王王洛賓激情創作了后來被譽為東方音樂經典的著名歌曲《在那遙遠的地方》。之后,王洛賓又來到千戶家達三月之久,和薩耶卓瑪在一起,不僅創作了《半個月亮爬上來》等許多青海名曲,而且搜集了大量青海“花兒”,吸取了藝術營養,大大豐富了民歌素養。
《青海民間的情歌》一文,1939年西北晨鐘社匯輯和介紹包括青海“花兒”在內的民間情歌,刊登在《西北晨鐘》第1期。
《青海民歌》,1940年王洛賓在《新西北》5-6期上連載,介紹了當時流行的包括“花兒”在內的青海民歌。
《青海民歌的一斑》,鐘世隆在《新西北》上發表的介紹文章。
《四季歌》和《花兒與少年》。1942年3月,音樂家王云階與夫人李青蕙從重慶來青從事音樂教育,王云階被安排到昆侖中學教音樂,李青蕙在青海女子師范教音樂。在西寧聽到王洛賓努力發掘青海民歌的事跡,深受感動。于是抓緊學習和記錄青海民歌。并編輯《青海民國日報》的副刊《樂藝》,將廣泛搜集的青海“花兒”和其他民歌,開辟“青海民歌專號”發表,主要有“尕馬兒”、“山丹花開”、“白牡丹”、“水紅花”、《四季歌》、《菜籽花兒黃》等。據王云階在《生命狂想曲樂章之一山丹花》中說,“《四季歌》原是青海民歌《再等上一等我》的曲調,由當時在昆侖中學教國文的老師石蓉久(石殿峰)先生配詞的。”“在《樂藝》副刊發表后,很快流傳了。”《四季歌》流傳開的當年,在西寧樂家灣兵營輔導春節社火演出節目的王洛賓、周宜逵等人,改編了一出民間社火歌舞節目,名叫《八大光棍》,伴唱以《四季歌》為主。《八大光棍》也推動了《四季歌》的流傳(謝承華《青海民間文化風情》)。二十世紀40年代,《八大光棍》的確已成為青海社火的傳統節目,得到當時親自參加過該節目排練的人們的確認(羅耀南《莫把“花兒與少年”歌舞劇當做青海民歌》)。1956年冬天,為參加全國專業舞蹈匯演,陜西歌舞劇院組織當時在該劇院工作的朱仲祿,及作曲家呂冰、編舞家章新民,以青海民間小調和“花兒”旋律為素材,共同創作出了抒情歌舞《花兒與少年》。期間,由朱仲祿提供了青海民間小調《藍玉蓮》、《四季歌》、《五更鼓》等原始素材,并根據需要,對歌詞作了部分改動。定稿時,由朱仲祿建議給抒情歌舞起名《花兒與少年》(見2007年11月9日《西海都市報》羅成專訪朱仲祿稿)。據《西海都市報》記者采訪當時參與設計服裝的國家一級美術師趙翔,他說:“當時朱仲祿負責唱腔和表演,我負責演員服飾。”在陜西及全國專業團體音樂舞蹈匯演中取得成功。在莫斯科第10屆世界青年聯歡節獲金獎。
《青海的花兒》,長弓于1942年在《西北日報》發表,后有刻印本散見于民間。
《山丹花》,青海花兒曲集,王云階編著,1944年出版。1943—1944年,王云階夫婦由重慶國立音樂學院教務主任李抱忱介紹給青海省政府,在西寧學校教音樂。同時,搜集“花兒”及其曲譜,并在《青海民國日報》主編《樂藝》副刊,刊登他的中國音樂史稿及“花兒”曲譜,后匯集成冊。
《臨潭民歌》,陸泰安記錄,刊登在1941年8月《新西北月刊》4卷6期。
《青海情歌》,寄鴻編輯,刊登在1941年《邊事研究》13卷1、2期。
《青海民俗和民歌》,江源編著,刊登在1942年《西北論衡》10卷4期民俗專號。
《窯街花兒》,岳劍寒編著,刊登在1944年《旅行雜志》第18期上卷5。
《河洮紀行》,安徽六安人、近代著名學者高一涵作于1945年,趙宗福《花兒通論》錄其九:“少年個個美髯髭,黑白平冠老將師。渡過康家崖畔水,野田處處唱花兒。”
《青海花兒新論》,萌竹(原名逯登泰,青海樂都人)著,刊登在1947年10月15日《西北通訊》第8期。1948年9月2日《和平日報》刊出《青海的山歌》,后有郝忠等手抄本遺存。他還寫了敘事花兒《腳戶哥》。
《關于西北民間文藝》,刊登在《新西北月刊》3卷5、6期合刊。
《民歌選》,1947年北方大學文藝研究室編印,收入“花兒”。
《西北民歌》,于試玉、王文華合編,1949年華西大學華西邊疆研究所出版,收入“花兒”。
迄今為止發現早期在詩文中記載“花兒”的詩句,客觀反映了明清以來“花兒”在西北傳唱的盛況,可窺見“花兒”傳承的歷史軌跡和真實面貌。出現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的第一次“花兒”研究熱,是甘寧青1929年分省前后青海“花兒”研究的初始期。其特點是,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文人們對傳承了500多年的西北“花兒”,逐漸改變了傳統的不屑觀念,開始了空前的關注,先后出現了積極倡導、搜集、介紹和研究“花兒”的先驅,有張一悟、牙含章、張亞雄、謝潤甫、李文實、魏明章、萌竹、王亞森、王洛賓、丑輝瑛、羅麟、王云階、馬濟華、羅偉、范長江、李洽、楊質夫、于立亭、王俊卿、尹伯萊、陸泰安、寄鴻、江源、岳劍寒、王玉民、于式玉、王文華等。不僅通過各種渠道,搜集、整理、發表“花兒”,而且逐步談到了“花兒”的曲調、流傳、地域、唱家和風格;不僅有了零散的“花兒”傳抄本,而且出現了張亞雄的第一部“花兒”研究專著。標志著早期 “花兒”研究熱潮的出現,并為逐步走向系統化、理論化,做了開創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