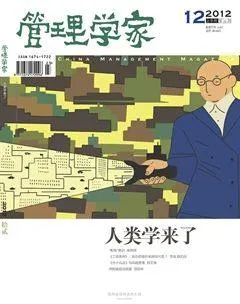人類學改變企業思維習慣




開始的話
有人問我,你經常在講,管理者要有人文思想,管理實踐要注重人文關懷,管理學院要研究和傳播人文精神,請問,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請關心下人類學的思想方法論和研究成果吧。結果又引出新問題:什么是人類學?人類學家是干什么的?人類學知識有何用處?
對國人來說,這真是一個非常陌生和難以理解的問題。
迄今為止,在中國,略知一點人類學的“知性”人士的理解是:人類學是歐美人的獵奇心態和閑情逸致的玩物。這些白種人怎么會對其占領的殖民地尤其是大洋島嶼中的部落人群的“奇怪”行為感興趣呢?他們為什么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去觀察和解釋部落的儀式?比如,部落人圍聚在一起,對著火堆跳著莫名的舞蹈,嘴里還嘟嘟囔囔地念念有詞。這有啥好研究的?不是“吃飽飯撐得慌”吧?人家的規矩就是規矩,知道了就行了,用得著去探究嗎?有啥用處?
這里,存在著兩個問題:
一是什么樣的知識是有用的?對于目前仍在、正在或即將開始工作階段的國人來說,兒時開蒙的家教及以后的學校傳導給他們的是,從“知識就是力量”、“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今天的“就業導向”的大學教育以及流傳民間的“拼爹”等。這大抵表明國人對于知識的態度和取向:有用才是硬道理。
二是什么樣的外部世界值得去了解?在“有用就是硬道理”的前提下,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在于,自然和工程知識的精美奇幻、科學技術的先進發達、社會管理的井然有序、政治經濟體制的開放透明、工作生活環境的舒適宜人、品牌世界的有型有款和令人感嘆的美麗生態和自然風光。在這些方面,人人會說,雖然我們已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還不夠發達,還要繼續努力。但對于那些比中國落后很多的島國和部落,幾乎人人又會懷疑有何價值又有何意義值得去觀察和研究?
這實際上是漢族人的歷史傳承使然:一個有著龐大人口和居住空間的民族,在其數千年的生存發展史上,“功名情節”和士大夫風范至今仍在深刻地影響著知識分子,尊重威權和風險規避意識導致實用主義盛行,很少會對研究外族人的文化差異和生活習俗的人類學發生興趣。在漢族的歷史傳承中,一直缺乏類似西方人關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要不是鴉片戰爭后帶來的百年屈辱,國人是用不著“眼睛朝外”的。即便如此,要“看外面的世界”就看那些用洋槍洋炮欺負中國列強的強盛奧秘——這便是為了應對“落后就要挨打”、六十年來中國始終堅持的“趕超戰略”理念產生的根源。
對于知識學習和外部世界,國人如此的實用主義取向,反映在對本國文化及其行為特征的了解也是不甚了了。不信,不妨隨便找個國內非人類學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他可以很清楚諾貝爾經濟學獎某個名人的身世和學問,侃侃而談其艱澀大作的內容和意義,但若問及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這本薄薄的書中說了些什么,恐怕只能顧左右而言他。
問題的根源在于,雖然林毅夫先生論證了中國作為一個極度后發國家獲取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的來源——技術領先和政府干預,但唯技術至上的發展導向,使國人缺乏自我認知的思想危機,嚴重地阻礙著國民的自信自強和國際的理解認可,反而國人的自傲自滿情緒卻日漸增長。由此看來,“我是誰”的自我觀念命題極需要予以展開討論和厘清。
難怪20多年來,中國思想知識界終于明白了一個道理:光講現代化是不夠的,還需要補上體現“現代性”的“文明課”。即,不僅要尊重世界各地的文明傳統,而且要讓世界了解和理解中國的文明。這里所指的“文明課”,就包括了人類學在內。
因此,管理實踐、管理者和管理學,也要補上這門“文明課”。
那么,如何補呢?
將“負值”變為“正值”:人類學家的立場和態度
二戰末期,圍繞著戰后的接管和改造日本問題,美國政府需要考慮:日本政府是否會投降?是否要保存日本政府機構以及天皇制?當時政府委托了一些專家做專題研究。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結論是:日本會投降,要保存和利用日本的政府機構。最終,如世人所見,美國政府的決策和該結論一致。
兩年之后,魯思·本尼迪克特將報告整理成書,發表了著名的傳世之作——《菊花與刀》。她寫道:“現在,無人不感到美國與日本在文化上的根深蒂固的差異。我們甚至出現這種關于日本的說法:凡是我們干的,他們就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個研究者如果相信這種說法,而簡單地認為,根本不可能了解那種民族,這當然是危險的。”
對照上述言論,聯系到66年后的今天,世界上對中國國力強盛后果的猜疑、對“中國制造”的態度,以及我國企業的國際化歷程中所遇到的種種障礙,真是何其相似爾,也令人頗為感慨。
在該書中,本尼迪克特還指出:“人類學者根據自己的經驗充分證明,即使最離奇的差異也不會妨礙研究者對它的理解。人類學家比其他社會科學家能夠更好地把差異作為一種‘正值’即有用的資料來利用,而不是看作‘負值’。對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任何東西他都不會視為當然......”
這句話可以說是恰如其分地表明了人類學家的立場和態度:如果將“差異”作為“正值”而非“謬誤”來考察的話,那么尊重“差異”并試圖從中找出相應的對策,很多問題當會迎刃而解。
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反思我們向來認為是自得自豪的驕人成就,讓國人捫心自問:“中國制造”使全世界許多國民失去了工作機會,從而遭致諸如反傾銷和進入壁壘之類的報復行為。可否將這種報復行為作為“正值”來看待?同理,中國企業在全世界的資源和產業并購活動也遭到了抵制,可否也可以作為“正值”來看待?進一步地,中國國力的強盛,更遭致世人的質疑:中國已經很強大了,還這么努力,將來它更強大了,有最先進的技術和裝備,有強大的軍事科技力量,它準備以何種姿態面向世界?這也能作為一種“正值”看待嗎?
這里,所謂的“正值”不可能沒有來由。剛結束的美國總統大選,第一輪辯論中,兩位競爭者開始圍繞著“中國制造危及美國人就業”互相攻擊;到了第二輪辯論,他們不得不回到現實中——中國變成了美國的“利益攸關者”。即,辯論雙方都意識到,美國離不開中國,但要讓中國按照所謂的“游戲規則”和美國做生意——當然,這兩位候選人實際上并無一個能明確和中國生意往來的“游戲規則”。既然中美彼此間的利益界定是含混不清的,則中美之間存在著許許多多個犬牙交錯且有利于討價還價的空間。
應當指出的是,將“負值”變為“正值”的視角轉換,非人類學家也能做出杰出的貢獻。但人類學家依靠觀察、田野研究等方法和技術,非常注重其他學科的學者所很少關注的日常瑣事,即人們工作和生活的細節。他們能發現其他學者所不能察覺到的支端末節,并可進一步考察產生這些細節的當事人的感覺。
但是,憑著細致入微的觀察就能解決其他學者所不能回答的問題?非也。這樣的感覺只能代表特定情境下當事人的即時反應,并不能對任何有特殊意義的言論行為進行合理解釋。比如,可口可樂新配方的市場調研取樣有21萬份之多,結果大多呈正向反應,但正式應用后卻遭致反對。如何解釋這種現象?有點常識的人會說,街頭攔截往往并不代表消費者真實的內心選擇,但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論斷,絕非問題的根源所在。問題實質是,在百事可樂大肆進攻下,可口可樂決策層忘記了自己所擁有的不是一個簡單的暢銷商品,而是一個極為珍貴的品牌——它是美國的一個文化象征。換言之,沒有可口可樂,哪里會有百事可樂?所以說,可口可樂的錯誤在于,離開了其安身立命的本源——文化,所謂按照統計規律的推算結果自然會出錯。
人類學家認為,人之所以是具體的人,在于每一個具體的他或她總是生活在特定的國度之中。他或她之所以贊同或反對或含混地對待某種信號,根據本尼迪克特的說法,“一個人類社會總必須為它自身的社會進行某種設計。它對某些情況的處理方式及評價方式表示贊可,那個社會中的人就把這些結論視為全世界的基本結論。……人們既然接受了賴以生活的價值體系,就不可能同時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價值體系來思考和行動,否則就勢必陷于混亂和不便”。
據此,可以用簡潔的語言來表述人類學和人類學家的工作價值:細節來自習慣,習慣來自文化,文化使習慣和細節具有意義。
要強調的是,承認并研究的種族、國別或區域間行為差異,必須建立起兩種取向,首先是寬容,即人類學不以世俗觀念為轉移,“差異”必定有其存在的道理;其次是耐心,即人類學研究要沉下心去,認真觀察,逐步深入,方能有效地解釋為什么會有“差異”以及如何應對這種“差異”。
人類學為何可成功運用到
企業管理中?
人類學和人類學家如何將所學所知用到企業管理中?那些白人對“夷族”及“野蠻人”的研究方式和方法適用于現代化程度很高的企業管理實踐嗎?
大量的文獻和成功實例已經證明,人類學本著文化導向的立場,在諸多細枝末節與所在國度的文化之間構造了內在的聯系,從而賦予企業管理實踐以人文意義,所提的改進方案往往具有出人意料的療效。相對而言,強調效率導向的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成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反而不及人類學的研究成果。
自著名的霍桑實驗開始,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陸續在企業文化、知識管理、文化審核、組織變革、產品設計與開發、市場營銷、消費者行為、品牌化、企業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創業和創新管理、企業國際化經營、國際商務和商務溝通以及本土化的組織管理知識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果,許多跨國企業專門聘請人類學家研判企業的戰略和運作方面的問題。許多知名的商標設計也飽含了人類學家的辛勤工作,諸如舉世聞名的“Intel Inside”就來自兩個人類學家的研究所得。
為何人類學具有如此的效用?
因為人類學所注重的文化,不是抽象的文化,而是普通人都可理解的常識。但與普通人不同之處在于,普通人的言談處事習慣來自于他們日常生活的養成——所謂理所當然而不用思考的反應,人類學家卻善于從此之中找到“解決問題之道”。
這里會引發的一個問題是,既然是企業自己理所當然的反應,為何企業自己不能解決已意識到的錯誤,而要花錢雇傭人類學家來觀察和提煉?這與企業請咨詢公司來解決自己不便處置的自身難題的做法是一回事嗎?
這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去對待的問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相信,有著較為豐富經驗的企業領導和經理人大概應該認可以下所述——這也是在企業中時時處處可以感受得到的事實:
在企業管理的實踐中,最常見的問題同時也是永久存在的問題體現在:
“責任不在我”。在企業和顧客之間,總是缺乏有效交流的橋梁和窗口。原因是,產品或服務的創意、設計、開發、生產、銷售和服務者有著很好的科學技術、工程制造和市場銷售水平,但最為缺乏的是良好的人文意識。他們總是認為,相對顧客而言,他們更明了產品或服務的原理、功能、用途和特性,是他們在制造產品或服務,顧客只是在消費或者使用。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意見如何,他們不了解也不愿意為此去花時間和精力。
“官兵捉強盜”。在企業內部的上下關系或者平行關系之間,也總是缺乏有效交流的橋梁和窗口。原因是,企業內上一級的主管會認為,下級缺乏他們所有的責任感和全局觀。他們認為,下級不可能了解他們所知曉的情況,不可能也不愿意知曉所發生問題的緊急和重要程度,而只會過多地考慮各自的工作的便利和利益。如果讓這些主管們從下級角度和立場去考慮,那么他們如何去面對更上一級的主管呢?同樣地,所謂“屁股決定立場”,平行的機構相互間也常常存在著推諉拖延現象。結果自然是兩種:第一是以 “殺雞給猴看”的方式去處置“刁民”,第二是以“擺擺平”方式去處置上下級或同級之間的關系,搞個皆大歡喜了事,結果是“問題永遠是問題”,矛盾越積越深,誰都不愿意去觸碰這個“亂成一團”的毛線團。因此,經常是今天的官兵可能就是明天的強盜。
“宮心計”。除上述兩個之外,企業最常見的毛病存在于政府和企業、社會與企業以及董事會和執行層的關系中,這些關系好像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企業的聲譽和公關問題、企業的老板和金領的問題,實際上都是企業制度的治理問題。如果以中國人熟悉的歷朝歷代故事來比喻的話,其中有皇帝和臣子的關系,皇帝和后宮的關系,皇帝和至親兄弟的關系,皇帝和外戚的關系,皇帝和大內的關系以及這些人群相互間的關系。比如,借助中國“人口紅利”所獨有的“天時地利”和企業家和員工們的堅韌勤奮,中國民營企業雖然可以做大,但僅僅可能由于在“傳內(兒子)還是傳外(駙馬爺)”上糾結不清,做強就很難。因此,這部分通常是“道不清理還亂”,“宮心計”輪番上演。
這里,關鍵在于,企業不是一個“排排坐,吃果果”的禮儀團體或者慈善組織,其法律和經濟性質決定了它就是一個以利潤為導向的經濟組織。在謀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企業組織成員及其利益攸關者的心態和價值取向不可能是一致的,相互間的摩擦在所難免。尤其是當組織一旦取得了生存資格并達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站穩腳跟后,自然會演化出其特有的習俗、傳統和惰性,其個中因素可以說是“魚龍混雜”,良莠難辨。這樣,組織中的人性弱點會對組織的生存和發展造成錯誤的引導。這便是人類學所關注的文化現象,也是我們經常在議論的管理的人文現象。
也正因如此,人類學家所保持的中立和客觀立場,使其比企業決策層和管理層更容易發現問題的癥結所在。換言之,“身在此山中”的領導和經理人已處于“想當然”的思維定勢狀態,要走出他們為自己設置的“圈圈框框”已經很難,這就需要外人出來加以點撥。況且人類學家的文化觀決定了,他們的確可以客觀地為企業找到“問題解決之道”。
本土管理“人類學智慧”開發的困境和對策
了解了人類學的文化意義后,我們這些非人類學家們,應該有怎樣的收獲呢?
諸位大概會想起流傳至今的一句古話:“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你們可能會說,這沒什么新奇,我也會。
錯矣。只懂得這個道理,還遠遠不夠。這句古話自然有其生活哲理,但也會阻礙我們去學習新知識,去了解許多我們并不知曉但一直認為是落后的外部世界。
讓我們回到本文的開頭部分,要重視企業管理中的人文因素,就要克服我們民族和企業管理實踐中的二個不足,一是“有用的才是知識”,二是“先進的外部世界才是要關心的”。其中的關鍵是尊重和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差異”,我們雖不能像人類學家那樣,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觀察和提煉,但至少要對現實社會和組織中的人性因素對企業管理的錯誤影響作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這里的關鍵是,中國的企業管理實踐和研究應當積極吸取人類學的“人文關懷”思想,構造中國管理的“人類學智慧”。
這里要說的是,中國并不缺乏具有人文情懷的大智若愚的文化智者,也不缺乏具備“活在當下”意識的成功實踐者。即,我們也有著我們自己的“人類學思想”。只是在鴉片戰爭之后,由于上述的“兩個不足”,國人有可能將自己民族文化的精華當洗腳水“潑”掉,卻留下了糟粕,以至于時至今日,社會上流傳最多的是對“潛規則”的好奇——不要和我說什么“高尚純潔”,骨子里還不是“男盜女娼”那一套。當今中國社會人們思想之混亂,可見一斑。這是否說明,對自己民族的文化不可以簡單地按照個人偏好來隨意劃分“精華和糟粕”并加以處置?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圍繞著這個有著憨憨農民情結的小說家,為何可以擁有如此國際聲譽的問題,國內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但是至今為止,似乎并無激發出能點撥蕓蕓大眾的人生啟示。這使我想起了20年來國人對于外界有關中國評價的反應:首先是反感,這可由張藝謀改編莫言小說所攝制的“紅高粱”電影獲獎引起——原來外國人贊賞中國人的“高粱地里的情愛故事”。這只能說明,老謀子滿足了老外的“獵奇”心理,他們對中國落后的感興趣,表明了對中國之崛起的“陰暗心理”;其次是不解,中國六十年的艱難曲折奮斗,目的是擺脫國家之“落后”,老外為什么不看到“兩彈衛星奧運世博”以及“中國制造普及全球”的宏偉大業,卻喜歡“土坷垃傳說”?
誠然,中國是向全球展示了其在科學技術、生產制造和城市現代化領域中的種種不凡,而且中國的國力強盛已經在影響著世界的進程,然而,世界并未否認中國之種種成就,但所要迫切了解和知曉的是,中國人的所思所為是否能和普世價值相融合,中國人在全球“悶頭做事”的風格能否有利于全人類社會的和諧和持續發展。即,中國人能否擔當起對全世界負責的大任,中國人又會怎樣擔當起此種大任?
在此意義上,人類學所要考察的,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的差異和融合便是重要事項。在國際工商管理領域,則可體現為中國管理文明與國際管理文明的差異及其融合問題。
要在中國的管理學領域,尋找中國管理所包含的人類學思想,應該圍繞著“在中國,企業如何才能夠獲得事業及其持續性成功”這個命題展開。原因在于,中國企業及其經營者的所思和所為,莫不是來源于自幼所受到的生活體驗的浸潤。離開了這個安身立命的根基,一切均無從談起。可惜的是,在中國的管理學領域,過去的一個相當長時期內,此題并不在可討論和可傳授之列。
近來,中國管理學界注意到這種趨勢的變化,但限于前文所述的“兩個不足——對知識的理解和對外部世界的關注”以及中國社會數千年以來的傳統習慣所制約,本國管理學界不善于在“地方性組織與管理知識的生產及制造系統”有所作為和發展,即便是在林毅夫所述的技術領先和政府干預下的企業戰略和組織管理,也缺乏相應的知識開發思路和途徑。對此,只要注意到各種有關“中國管理”的文獻,就會發現,相關研究及其成果的貧乏和無知到了何等的地步。面對這一困境,有兩點需要引起重視:
本土管理知識的創造和開發需要有“莫言精神”
如前所述,中國企業經營者并不缺乏“人類學智慧”,這些來自中國企業的“莫言”們天天在創造各自行之有效的“土坷垃經驗”。問題是,學術界是否鼓勵學術界同仁走出“象牙塔”,像人類學家那樣沉下去觀察和做田野研究?
這里,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本土學者力求要有“莫言精神”,即腳下有地,頭頂有天,眼中有人,心中有情。做到了這一點,自然會開發出具有啟迪作用的“地方性組織與管理的知識系統”。
但是,攔在本土管理學者面前的最大障礙,莫過于所開發出來的知識的科學性和精確性,有沒有一個被認可并符合現行業績考核制度的陣地和平臺去發表和傳播這些知識?
這在全球管理學界,仍舊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也正因如此,人類學的思想及其研究方式在國際管理學界所取得的驕人成就,對于處于“糾結”狀態中的本土管理學者來說,意義重大。
顯然,目前國內管理學界某些人借“國情特殊”名義,排斥國際管理學的思潮和方法,不能解決也不能有效地解答,中國管理文明與世界管理文明的差異及其融合問題。即,在頂天立地和腳踏實地之間,并不存在絕然的對立關系。
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將現實中的“人文關懷”對企業進步和發展的作用轉換為對企業進步和發展具有啟迪意義的“管理智慧”。換言之,人類學對管理學的知識貢獻與其他學科對管理學的知識貢獻是相互影響和相互融合的關系。
這恰恰是,中國管理者和管理學者今天要去了解、知曉和重視人類學在管理學研究和應用中已有貢獻和特點的緣由。
與其去鉆研“陽明學說”,不如沉下去觀察和提煉
近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分析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晚清時代人士的“救國之道”之后,注意到陽明學說對他們以及對蔣介石、毛澤東的影響。這些學者注意到,在內憂外患的情形下,這些名人均為知識分子出身,均經歷了由“格物致知”到“知行合一”的轉換。學者們發現,那些相對他人而言較為高明的名人言行,來自他們對極具高度情境依賴和低度風險規避特色的中國社會生存之道的認知。而這些名人轉換的關鍵,又在于陽明學說給予他們巨大的影響。
由此,這些學者認識到,“活在當下”意識可能是中國歷朝歷代成功者的生存和發展理念,也是當今中國面對全球化挑戰和機遇選擇的考慮,更是中國企業家做大做強其組織的訣竅所在。
最近,柳傳志在回答《財經》雜志問題時直言:不要對企業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決于政治環境,政治環境好,我們就會更努力,在經濟方面發揮作用;當環境不好的時候,我們就少說話,或者是少經營業務。作為一個企業家,我從來軟弱,但是我不搖擺。此番言論明確地告訴大家:企業和企業家是特定社會的產物,辨勢而動,動在道上,這樣才能有所“折騰”,有所收獲,才是企業和企業家的行動原則。
柳傳志所言,實際上就是一種極具世俗性的“人類學智慧”,也是值得中國管理學者去深思和開發的“地方性組織與管理知識”。
既如此,中國管理學者為什么直到現在才能察覺到其中奧妙呢?
原因在于,20多年來,在“知識必須有用”的導向下,中國管理學者只是在被動地接受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而并未接受西方管理思想所蘊含的情境——文化——管理的理性思維。當面對本國管理實踐中的種種問題時,便不能給予有效的解釋和判斷。于是,回頭去再看中國的管理思想時,才發現自己是多么的蒼白和無力。
由此,不妨給自己提出點具體的任務,與其花時間再去鉆研“陽明學說”不如沉下去看看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的所思所為,通過觀察和提煉,發現文化給企業行為的影響和作用,從而構建起“地方性的組織與管理知識系統”。
毋庸置疑,這樣的研究,完全符合管理知識的科學建構要求。
可以相信,中國管理學者在吸取了人類學的思想和研究方式后,一定會在組織行為、消費者行為、品牌化、產品開發和設計、戰略變革、創業創新、企業國際化經營、國際商務和跨國溝通交流等諸多方面有所作為。
所以說,困境的突破,就在于“事在人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