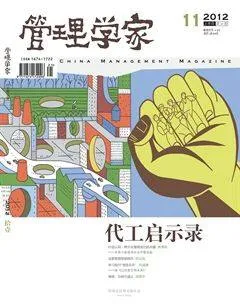1995,生死劫
2012-12-31 00:00:00杜博奇
管理學家 2012年11期


人們常說“向管理要效益”,為什么向管理能要到效益呢?說到底,就是因為它也是生產力。
——魯冠球 《我的管理觀》
進入1990年代,隨著中國本土企業的迅猛成長,急于分食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遭到頑強抵抗。中外企業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終于在1995年爆發了第一次大規模沖突。商戰之中,中國企業的領導者真切地感受到技術、品牌、營銷、管理各個層面的懸殊落差,危急關頭,能夠用以抵御外強的,似乎只有價格這一個武器了。
施耐德狀告正泰
跨國企業雷厲風行地布局中國市場,大肆收編中國企業,讓人感到陣陣寒意。1994年重慶天府可樂與百事可樂組建合資公司,天府可樂以廠房、設備占股40%,百事可樂居于控股地位。至此,通過合資、購并等方式,可口可樂、百事可樂收編了中國八大飲料廠中的七家,時稱“兩樂水淹七軍”,輿論驚呼“中國軟飲料業的半壁江山被洋人占去了”。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家電領域。1994年,博世-西門子與無錫小天鵝組建合資企業,持有60%股權,第二年又以同樣的方式與安徽楊子集團展開合作,在合資企業中持股高達70%。與此同時,美國白家電巨頭惠而浦擊敗眾多強敵,相繼與北京雪花冰箱廠、上海水仙洗衣機廠合資建廠,并分別占有60%、55%的股權,全面負責合資企業經營管理。
施耐德電氣更為激進,1994年直接向溫州民營企業正泰集團提出收購請求,意圖以現金收購其80%股權。施耐德是收購領域的老手,1992年通過兼并在中國開有多家合資企業的梅蘭日蘭進入中國市場,隨即與正泰、德力西等溫州低壓電器企業兵戎相見。施耐德面向高端市場,正泰、德力西面向低端,后兩者是由樂清求精開關廠一分為二而來,它們的迅速成長讓施耐德如芒刺在背,試圖用充滿誘惑的“金錢+技術”的收購消滅潛在的競爭對手。
1994年的正泰營業收入不足1億人民幣,面對施耐德伸過來的橄欖枝,南存輝感到難以置信,但他很快恢復理智,堅持自主權和控制權,拒絕了施耐德的控股性收購。正泰由此幸運地躲過了一劫——那些被跨國巨頭收編的本土企業大多淪為外資品牌的生產基地,凝聚無數人心血的本土品牌被雪藏,逐漸湮沒無聞,更有甚者如惠而浦,因不了解中國市場而盲目地套用既有的管理模式,致使合資企業陷入持續虧損,本土企業合資失敗,反受拖累。
1995年,收購談判破裂后,施耐德以“產品侵權”為由,將正泰集團告上法庭,雖然最終以和解告終,卻給南存輝留下了深刻的教訓:“這才知道知識產權是受保護要尊重的”。
此后多年,對正泰情有獨鐘的施耐德一面提起收購要約,一面揮舞訴訟大棒,分別在1998、2005年收購失敗后起訴正泰侵權。而南存輝始終不為所動,在施耐德重重阻擊下專注于低壓電器主業,堅持自主研發,終于在全球市場贏得一席之地。期間施耐德在世界多個國家對正泰發動20余次專利訴訟。2006年施耐德退而求其次,與正泰宿敵、多元化擴張不利的德力西結成聯盟;一年后,正泰轉守為攻,以施耐德擅長的專利訴訟將其告倒,獲償3.3億人民幣。
打贏官司后,南存輝說過這么一番話:“中國企業要樹立自信,不要迷信大公司,它們也是從小企業起來的。沒有一家大公司不被人告,也沒有一家不告人。”而在1995年,面對洶涌而至的跨國公司,南存輝和多數中國企業家尚不具備這樣充滿見地的自信。那時他們還年輕,更多地是被家國情懷所激發的莫名的悲壯豪邁驅動,他們掌握的技術和他們的能力一樣有限,但殘酷的現實擺在眼前,如果不低端模仿、低價競爭,他們的企業也許早已不復存在。
李東生發動價格戰
不同于南存輝的忍辱負重,李東生拉開陣勢,決心正面迎擊跨國企業的進犯,他不無悲壯地說:“外國兵團已經沖到我們院里來了,此時不戰,更待何時?與外國兵團較量,TCL集團公司要做產業報國的敢死隊,我李東生就是敢死隊長。”
相比低壓電器行業,家電領域的競爭尤為激烈,生態也更為復雜。全國各省存在大量地方性家電企業,改革開放初期引入日本生產線,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涌現出TCL、長虹、康佳等一批出類拔萃的國產品牌,但它們的知名度大多局限于本地,尚未形成氣候。品牌化不足的短板,加上核心技術匱乏,使其在與洋巨頭的競爭中處于下風,與此同時,日益猖獗的走私也在壓縮國內市場空間,致使本土企業產品嚴重積壓。而政府決定進一步開放家電市場,將彩電的進口關稅從35.9%降到23%,跨國品牌聞之大喜,日本松下公司磨刀霍霍,放言“不惜30億美元占據中國彩電市場的絕對份額”。這就是李東生上述講話的背景。
1995年,38歲的李東生還只是TCL集團分管電子業務的二把手。生產磁帶起家的TCL在1992年組建為集團公司,那一年,李東生主持上馬彩電項目,推出了“TCL王牌”系列產品,但此后兩年辛勤耕耘卻業績平平,令他十分失落。市場開拓成為問題關鍵。李東生三思之后決定進軍北京市場。打下北京市場,就等于建立起全國知名度。
然而,北京市場并不容易進入。日系品牌幾乎霸占了整個北京市場,國產彩電幾無立錐之地。李東生只有一個辦法——以極低的出貨價為條件,與商場簽訂“保底協議”搶占有利位置,承諾每平方米柜臺每月銷售不低于5萬元,之后公然發動“價格戰”。當時北京市場29英寸彩電幾乎全是日本原裝進口,標價都在萬元以上,李東生將29英寸TCL王牌彩電調價至4000元,并花費巨資聘請當紅演員劉曉慶代言。借助劉曉慶的人氣,TCL的低價策略收獲奇效,知名度迅速抬升,極大帶動了銷量,數月時間,TCL以壓倒性優勢占據北京市場最大份額。
相比北京、上海、廣州等競爭殘酷的一線城市,二三線城市異常平靜,市場競爭也相對溫和。TCL要把北京市場建立的品牌優勢推而廣之,一個明智的選擇是,搶先在二三線城市布局。李東生正是這么做的。1995年結束的時候,一個密密麻麻的全國性銷售網絡已經初具雛形了,囊括7大區域、32家分公司、180個經營部,它的觸角甚至能夠延伸到縣級市場。
然而這種生產商自建銷售渠道的做法引來業內熱烈爭議。當時流行的做法是,生產商專注于生產,銷售環節交給批發商、零售商,這樣做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是通過削減流程降低管理難度,生產商、渠道商密切協作、各司其職、互助雙贏,春蘭與蘇寧、長虹與鄭百文就是此類典型。不過一個同樣顯著的弊端是,強勢的渠道商難免制約生產商,1990年代中期爆發的“砍大戶”風波就是生產商對渠道商的反抗。而在李東生看來,與其授人以柄,不如自建渠道。
可是,當TCL的銷售網絡鋪到河南鄭州的時候,卻遭致當地“渠道大戶”鄭百文的百般刁難。鄭百文全稱鄭州百貨文化用品公司,1990年代初幫助長虹打下半壁江山,同時也建立了自身在彩電經銷領域的優勢。鄭百文憑借強大的渠道話語權享有低價進貨、延期付款等便利,令上游生產商苦不堪言,熊貓、北京等老牌家電企業就樣被其拖垮。鄭百文希望TCL效仿長虹,將代理權交給它,李東生對此不屑一顧,幾次談判無果,終致掀起價格戰。
倪潤峰:“不降價不行!”
正當TCL與鄭百文爭執不休的時候,四川綿陽,長虹老總倪潤峰開始謀劃“價格洗牌”。
倪潤峰締造了長虹。長虹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的軍工企業長虹機器廠,1985年倪潤峰被任命為廠長。上任第一年,倪潤峰斥資2900萬人民幣從松下引入一條彩電生產線,讓長虹趕上了“政策末班車”,進入彩電生產領域。1989年,長虹產品全線積壓,倪潤峰宣布讓利銷售,20萬臺彩電一夜告罄。有人將其告到上級,以擾亂物價之名要求嚴懲。政府卻網開一面,出臺政策允許彩電調價,長虹開價格戰先河,也由此奠定了在國產彩電行業中的地位。
幾乎與TCL同一時刻,長虹涉足利潤更為豐厚的大屏幕彩電業務,但是由于品牌影響力有限,產品銷售并不理想,1995年長虹庫存一度高達100萬臺,甚至“每個月建倉庫都來不及堆放”。
1995年,倪潤峰敏銳地抓住了“民族工業告急”的大眾心理,將長虹的使命重新厘定為“以產業報國,民族昌盛為己任”,廣告詞也順應時勢,改為“長虹以民族昌盛為己任,獻給你——長虹紅太陽”,配上一句煽動性標語:“用我們的品牌筑起我們新的長城”,為即將發動的價格戰制造聲勢。
倪潤峰生性豪爽,但并非有勇無謀之輩。一次公司會議上,他說,“急癥必須用急藥來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用自己的價格優勢去拼掉對方的品牌優勢。”倪潤峰推敲一番,認為長虹要“拼掉”進口彩電的品牌優勢,起碼應該便宜30%。然而長虹的毛利只有25%,降價30%,不僅無利可圖,還會賠錢。難道要“賠本賺吆喝”?“考慮來,考慮去,算過來,算過去,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不降價不行!”從1995年秋天開始謀劃,直到1996年春天才下定決心打價格戰。
1996年3月26日,全國61個城市150多家商場的長虹彩電全線降價。這場全國性降價促銷徹底點燃了價格戰的導火索。在長虹影響下,本土彩電企業紛紛跟進,進一步加劇了行業洗牌力度。到1996年末,洋品牌已被擠出市場前列,近百家經營不善的本土地方性品牌走向沒落,長虹以35%的市場占有率穩居行業第一,康佳和TCL緊隨其后。
慘烈的價格戰過后,中國彩電市場由亂到治,從外敵林立、草莽混戰的格局進入寡頭紛爭的時代。作為市場化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家電業此后還將爆發無數次價格戰,乃至成為市場常態。
應當意識到,價格戰不應流于惡性競爭,在價格競爭的背后,還有對企業管理水平的考驗和錘煉。長虹降價30%仍有利可圖,是因為倪潤峰找到了精細化管理這個法寶:通過提升管理水平,精簡流程來削減成本。長虹并沒有圍繞30%這個目標盲目地降價,而是進行了巧妙的產品組合,一個簡單的例子是:降價幅度最大的產品,恰恰是那些嚴重滯銷的積壓貨。
價格戰只是市場開拓的一種手段,如果沒有磨練出核心競爭力,以價格戰打下的江山也會輕易被攻克。在這方面,海爾值得一提。1995年,海爾在參與家電價格戰的同時,積極籌建遍布全國的服務網點,并率先推出“星級服務管理”。通過一套標準化的服務管理體系對售前、售中、售后三個環節進行服務流程管理,還別開生面地提出免費送貨、免費安裝以及24小時維修等服務項目。此舉不僅助其在價格戰中擴大戰果,更奠定了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光輝形象。
劉氏兄弟“二次分家”
1995年,美國《福布斯》雜志推出的“全球400富豪榜”上,17位中國企業家的名字赫然在列,排在首位的是44歲的四川人劉永好,他以6億人民幣身價當選“中國首富”。就在一年前,他被授予“中國十佳民營企業家”、“中國改革風云人物”等稱號,并獲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工商聯副主席。聚光燈下,劉永好名利雙收,但這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四兄弟聯手創業之功。
劉氏四兄弟按照長幼排序分別是劉永言、劉永行、劉永美、劉永好,最后一個字合起來便是“言行美好”。四人性格鮮明,各有所長。老大內向憨厚,是一名科研能手;老二嚴謹認真,與精明細致的老三一樣擅長經營管理;老四劉永好性格開朗,能言善辯,具有優秀的推銷才能。不同的專長恰恰為他們的創業提供了便利。1982年四兄弟辭去公職,變賣家當籌集到1000元,回到新津老家養鵪鶉,6年后他們積累了1000萬元,由于當地的鵪鶉養殖日趨飽和,競爭加劇,利潤稀薄,他們便創辦“希望飼料公司”,轉向豬飼料生產領域。
1989年,劉氏兄弟成功研制出質優價廉的“希望1號”乳豬飼料,在市場上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那時泰國“正大”壟斷著中國飼料市場,靠著成本低廉的“希望1號”,劉氏兄弟大打價格戰,把“正大”趕出大西南市場。1992年,他們在“希望飼料公司”基礎上組建希望集團,成為國內第一家經工商局批準設立的民營企業集團,隨后進行了創業以來第一次“分家”,并對管理工作進行了明確分工:四兄弟均分股權,各持股25%,老大轉向高科技領域,老三在負責現有主業的同時開拓房地產業務,老二劉永行和老四劉永好到各地發展分公司。
隨后三年,希望集團發展一日千里。1993年,劉永行、劉永好橫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建立起10家分公司;1994年,分公司數量增加到27家;1995年,希望集團成為國內飼料行業領頭羊,并成為規模最大的民營企業。也是在這一年,老二劉永行提出了“分家”。
劉永好并不贊同分家的說法,他更樂于用“規范產權制度”來評價這次分拆。起初劉永行的提議招致家族成員強烈反對,一度陷入僵持,后來其余三兄弟逐漸意識到建立現代化企業管理制度的必要,“企業發展壯大了,面對著金錢、榮譽和掌聲,看法就會不一致”,而分家則是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后一種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劉永好從長遠考慮也同意分家:“因為我們是家族企業,產權這么大的問題一定要分清,否則以后會很麻煩。我們這代還好,四個人一塊創業,大家又都是親兄弟,很多事情都能說得明白。但下一代,再下一代呢,恐怕問題就多了”。
1995年,希望集團分拆重組為四大集團——大陸希望集團、東方希望集團、華西希望集團、南方希望集團,劉氏四兄弟分別執掌一個集團公司。劉永行、劉永好對打下的江山進行分割,一人分到13家工廠,然后以長江為界,劃江而治。劉永行的東方希望開拓東北市場,劉永好則負責南方市場,不久他就把南方希望更名為新希望。多年后,劉永好這樣評價這次調整,“有分有合,大家都發展得很好。合的部分是希望集團,作為存量一直都沒有變。……實際上,我們分的只是產業發展方向和地域。”
褚時健“煙王末路”
1995年7月,67歲的褚時健接到通知,上級考慮讓他退休,已經開始物色他的接任者了。
褚時健內心失衡了。從1979年出任玉溪卷煙廠廠長,16年兢兢業業,將這家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小廠發展為亞洲首屈一指的現代化煙草企業集團,作為創業功臣,褚時健得到了“明星企業家”的種種待遇,1994年還被評為“十大改革風云人物”,云南省每年也給他一定的獎金,1995年甚至高達200萬元。但這些都彌補不了退休帶給他的巨大失落感。
接到上級通知后,褚時健思量了許久,考慮到“新總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苦了一輩子,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于是便和副廠長、總會計等人私分了300多萬美元。他心想,“夠了,這輩子都吃不完了”。
褚時健不知道的是,這時候中紀委已經對他展開了秘密調查。1995年2月,中紀委接到一封匿名舉報信,聲稱三門峽煙草公司、洛陽水泥廠工作人員用送禮、行賄等方式,從玉溪卷煙廠購進8000余件卷煙,獲利800多萬。紀檢、司法部門發現,褚時健利用職務之便多次“批煙倒煙”,他的親屬從中收受大量金錢,存在嚴重經濟犯罪行為。
褚時健在企業內建立了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身兼廠長、書記二職,下屬尊稱他“老爺子”。看似民主科學的監督制度,對褚時健來說均形同虛設,他念念不忘的“簽字權”,其實就是審批權力,全憑他一人做主。利用這一特權,褚時健從1990年代初開始,大量謀取私利,聚集數千萬資產。
1990年代初,上級批準玉溪卷煙廠完成計劃任務外,可以生產部分卷煙交換鋼筋、水泥等生產性資料。但這批計劃外產品并未用于上述交易,而是流向東部沿海地區,收入也未記賬在冊,而是打到另外幾個賬戶上,幾年下來,“小金庫”賬上資金高達10多億元。這是褚時健留下的退路,只有他和副廠長、總會計等少數幾人知道,他們私分的300萬美金就是出自這里。
一年之后,1996年12月28日,調查即將水落石出時,褚時健驚慌失措地從云南邊境出逃,被邊防站截獲。面對人證物證,褚時健供認了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事實,最終被判無期徒刑。一代“風云人物”就這樣淪為階下囚。褚時健一案引發社會熱切關注,“國企管理者責權”走向公眾視野,成為經久不衰的話題,在日后更引發“59歲現象”大討論。
1995年,曾經名噪一時的國企廠長、“改革明星”紛紛墜落。褚時健之外,77歲的周冠五因經濟問題被撤職,黯然離開奮斗了44年的首鋼;“馬勝利紙業集團”解體,馬勝利因效益滑坡被免職。
一派蕭瑟之中,互聯網經濟放射出朦朧而迷人的曙光。摩根士丹利分析師瑪麗 · 米克爾寫就了300頁的《互聯網報告》,預言互聯網經濟的到來。英特爾總裁安迪 · 格羅夫在飛機上讀完這篇報告激動不已,下決心將公司帶入互聯網時代。瑪麗 · 米克爾將網景公司推入股票市場,一夜之間成為華爾街上炙手可熱的人物,她還帶來了一個新興職業:互聯網分析師。
田溯寧、馬云、張樹新成為中國互聯網第一批弄潮兒。田溯寧將他在美國成立的亞信公司搬入中國大陸。馬云創辦“中國黃頁”。張樹新在北京中關村白頤路上打出一個條幅宣傳她的瀛海威,“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有多遠——向北1500米”。寧波電信局員工丁磊辭去公職,獨自前往廣州,那里,將成為夢開始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