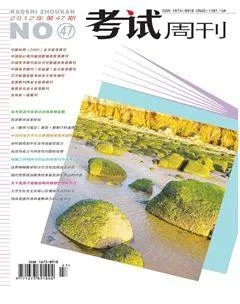從《傲慢與偏見》看簡·奧斯汀的道德關懷
摘 要: 簡·奧斯汀是英國18-19世紀著名的現實主義女作家,她家喻戶曉的作品《傲慢與偏見》以清新睿智的文字,描繪出英國的人情世故,表達了特殊的道德關懷。本文通過分析在《傲慢與偏見》中頻繁出現的兩個詞語——“教養”與“禮儀”,結合英國18—19世紀的社會語境,說明奧斯汀呼喚理性與道德的約束,認為良好教養來自內心的良善,而非出身與地位的高貴。
關鍵詞: 簡·奧斯汀 小說《傲慢與偏見》 道德關懷 教養 禮儀
一、引言
著名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曾經這樣評價簡·奧斯汀:“在所有偉大的作家當中,簡·奧斯汀是最難在偉大的那一瞬間捉住的。”[1]奧斯汀及其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漸崇高,她甚至被譽為可以與莎士比亞平起平坐的經久不衰的作家。
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英國文壇盛行具有戲劇性的“感傷小說”和“哥特小說”,借此“浪漫主義”之風,文學作品的題材已經逐漸駛離現實生活。而此時奧斯汀的小說打破常規,展現了英國鄉村貴族及中產階級的日常生活和田園風光,開啟了樸實清新的現實主義之風。《傲慢與偏見》便是這樣一部與社會現實緊緊契合的作品,它圍繞浪博恩村中班納特一家的生活展開,描寫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生動的社交場合,擁有不同教養(manners)的人物之間的沖突,以及社會禮儀(propriety)規范對人物言行的約束。不僅如此,敏感的奧斯汀還捕捉到了當時處于轉型期的英國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在描繪人物時加以適當的同情與諷刺,并寄予道德的關懷。因此,《傲慢與偏見》這部現實主義著作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教養與禮儀的重要性,傳遞了作者細致的觀察與道德關懷,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值得進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二、《傲慢與偏見》的社會語境
簡·奧斯汀的一生經歷了英國的攝政時代(1795—1830),她生長于英國南部漢普郡斯蒂文頓鎮的一個中產階級牧師家庭,目睹了英國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社交場合和各種細致瑣碎的家長里短。這樣的經歷成為她進行創作的基本素材,題材雖小,卻洞悉了英國社會獨特的經濟、階級和人際關系。
當時,不論是貴族還是中產階級都比任何時候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經濟能力的重要性。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根深蒂固的長子繼承制傳統(primogeniture),即只有家中的長子才有權繼承家族中所有的財產,而其他子女則分文不得。面對這樣的尷尬局面,分不到財產的子女不得不另謀生路,這樣就產生兩種后果:除了大兒子以外的男子必須自食其力養活未來的家庭,他們有的尋求贊助人謀求工作,如柯林斯先生,抑或是投身軍旅生活,如韋翰先生;女性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由于女性角色在當時受到強烈的局限性,體面家庭的女子幾乎不能通過工作來改變命運,她們因此轉而尋求婚姻的庇護。這樣的兩種情境滋生了許多社會問題。
奧斯汀所刻畫的小兒子們,要么像柯林斯先生一樣,以一種扭曲的姿態阿諛逢迎,循著上層社會的階梯向上爬;要么像韋翰一樣,用英俊的外表來掩藏自己的謊言,用坑蒙拐騙謀取錢財。金錢對無繼承權的男性們的控制力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奧斯汀擔心人們對金錢的盲目崇拜會戰勝道德的良知,產生不堪設想的后果。奧斯汀塑造這樣兩種形象無疑是要告誡人們:切勿在對金錢的追求中迷失自我,而應當重塑理性與道德正確的方向。
與此同時,女性則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當時,女性的職業范圍極其有限,多是女仆和女工這些被貴族和中產階級女性認為不體面的下層婦女職業。雖然有少數女性像奧斯汀一樣通過寫作維持生計,但她們時時面臨著來自出版商的壓榨和男性社會的冷落,因此,寫作對于大多數有文學素養和寫作能力的女性來說,更多的是自我滿足和欣賞的需要,很難作為謀生的長久之計。她們被迫或自愿局限于家庭,想方設法通過一場有利可圖的婚姻為未來尋求保障。
在當時,婚姻幾乎不可以解除。英國議會法律規定,上層社會可以離婚,丈夫可以休不忠的妻子,而妻子無權提出與不忠或暴戾的丈夫離婚。然而,對于不能從事任何職業自謀生路的女子來說,“危險的婚姻也被視為比獨身好”。從而,絕大多數女人選擇了為生活、為錢、為財產而結婚。[2]實際的情形是,中產階級未婚女子總是成為婚姻市場昂貴的滯銷品。考慮金錢和門第,她們不會嫁給下層男子,而同階層未婚男子面臨著經濟壓力,除了長子,都得自謀生路,經過漫長個人奮斗獲得穩定經濟來源后,才娶妻生子,而這時往往年過而立。[3]
女性可以進入初級學校學習,但這種教育更多旨在培養多才多藝、蕙質蘭心、溫柔賢惠的女兒、妻子和母親,而不是培養自食其力的工作者。女性的修養還來自閱讀當時廣泛使用的行為書籍(conduct books),這些書籍大多由神職人員編寫,通過道德的教條約束并教導女性。這些書籍灌輸諸如禮貌、良善、謙遜、忠誠等美德,幫助女性扮演其固定的社會角色。大學只對貴族和中產階級的男性開放,女性只能通過家庭教師和私立學校獲得有限的教育。[4]因此,有身份的女性僅靠自己很難維持生活,而美好的婚姻又可遇不可求,一些中產階級婦女的婚姻因此被耽擱,而奧斯汀便是其中之一。奧斯汀對愛情和婚姻曾抱有轟轟烈烈的幻想,但深深體會到現實殘酷的境況,她用冷靜和清醒的筆觸細細描繪著生活的平凡與瑣碎。司各特曾經這樣說:“又讀了一遍,我讀奧斯汀小姐的杰作《傲慢與偏見》至少已是第三遍,這位年輕女士有描寫普通人物的情感,性格及錯綜復雜的生活的天賦,對我來說,她的天賦是我所知最出色的。我雖然能寫出幾個優美的句子,但卻沒有她那種細膩的風格——把普通的人和事描寫得栩栩如生,引人入勝。”[5]
《傲慢與偏見》的內容讀起來全是世俗百態,卻處處充滿了道德關懷,這種道德關懷便呈現在對人物教養和社會禮節的描述之中。“教養”(manners)和“禮儀”(propriety)兩個詞出現頻率之高,足以說明教養和禮儀在攝政時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在奧斯汀思想中的崇高地位。以下便是對這兩個詞語在全文中特殊意義的分析。
三、教養(manners)
在英國文化中,禮貌語言及與其緊密相關的行為方式是一個明顯的特點,而《傲慢與偏見》反映的那個時期里這個特點又是尤其突出。[6]縱觀整篇小說,“manners”出現的次數竟有一百一十三次之多。在英文中,“manners”一詞包含了很多意義——舉止、談吐、禮貌、修養等,大致可以用“教養”一詞來概括。教養能夠體現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文化素養和教育程度等。在18世紀末,“manners”一詞的意義涵蓋范圍廣泛。根據塞繆爾·約翰遜在1755年完成編纂的《英文字典》記載:“manners”的意思包含人們的思想品格,生活態度,道德水準和禮儀規范。[7]
在《傲慢與偏見》中,只要有新人物出現,隨之而來的便是人們對其教養的評價。教養完全決定人們的第一印象。當彬格萊先生第一次出現在浪博恩的舞會上時,便是一個“儀表堂堂”“大有紳士風度”的年輕人,他的教養被評價為“沒有拘泥做作的習氣”,這為他贏得了全場來賓的青睞。與之相反的是,達西先生被認為具有“一副討人嫌的神氣”,即便他在德比郡擁有令人瞠目結舌的財產,并因此在舞會上掀起波瀾,成為眾人的焦點,但仍然抵擋不住人們“對他起了厭倦的感覺”,使得“他那眾望所歸的場面黯然失色”。[8]由此可見,個人教養會給他人帶來難以改變的印象,甚至是偏見。
教養的評價標準并不僅僅是禮節或禮貌,雖然如今大多如此。但在《傲慢與偏見》中,它也反映出人物的真實性情和思想狀態。科林斯先生作為全文中唯一從事宗教傳播事業的人物,被刻畫為具有典型“拘泥禮節”[9]的言行舉止,但時不時流露出滑稽可笑的特質來。一方面,他的教養雖然正式而規范,但卻難掩其矯揉造作和生硬刻板,偶爾又顯現出自我膨脹的趨勢,可以說他出身并不高貴,也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另一方面,科林斯先生阿諛奉承的行為也暴露出他不顧一切渴望擠入上流社會的野心,假裝出的紳士態度又不免讓人發笑。就這個自相矛盾的人物來說,簡·奧斯汀將他的個人特質與其談吐舉止結合起來,成功塑造了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科林斯先生。
奧斯汀刻畫的人物基本可以依據教養好壞分為兩種,好的教養必須具備禮貌、友好而且幽默的品質。其中,有一部分人物在剛剛登場時就已經被宣布是具有良好教養的人,其后來的言行舉止不過是對這種教養的具體闡釋,這樣的人物就是后來許多學者所認為的“扁平人物”。另外的一些人物的教養則是不斷豐富,其形象也是不斷具體的,被稱為“立體人物”。例如韋翰先生,他熱衷于社交場合,熟稔和陌生人打交道,并給人留下溫文爾雅的討喜印象,也因此贏得了伊麗莎白的好感。在其后的情節中,他唯利是圖的小人形象才逐漸顯露出來,讓人大跌眼鏡。達西先生則恰恰相反,起初印象中冷漠高傲的貴族子弟其實是一位忠實的朋友和伴侶。伊麗莎白作為中產階級女性的代表,其教養并不符合上流社會的標準,卻以“落落大方的愛打趣的作風”[10]吸引了達西先生的目光。相反,對于真正上流社會的女性,如彬格萊小姐、咖苔琳夫人等,奧斯汀卻并未賦予她們令人稱羨的教養,而是凸顯她們自持的優越感和紆尊降貴的姿態。簡·奧斯汀特意將來自上流社會人物的言行舉止描繪得令人厭惡,卻塑造了一批出身中產階級擁有良好教養的女性們。這固然可能與奧斯汀來自中產階級有關,但更多的是出于要表達這樣的思想:良好的教養并非來自于優越高貴的出身背景和社會地位,后天的家庭教育和個人修養才更為重要。[11]
四、禮儀(propriety)
“禮儀”(propriety)一詞在《傲慢與偏見》中更多是作為對言行得體與否的判斷。小說中的人物常常以謹言慎行來遵從這種不成文的社會公認的體統,雖然不涉及道德的評價判斷,但由此可見個人教養的水平。《傲慢與偏見》中禮儀規范涉及的范圍十分廣泛,幾乎包括了各種社會活動。
全文中形形色色的婚姻引人注意,這幾樁婚事也或多或少折射出社會對于得體與否的價值判斷。達西先生對伊麗莎白的求婚可以稱得上是整部小說的高潮。期間達西袒露心跡稱自己深知這樣的婚姻有諸多不成體統之處:伊麗莎白與自己的身份地位、財富水平相去甚遠;班納特一家的言行舉止多顯缺乏教養之處;班納特家的親戚朋友也來自社會中低層。這都與達西個人及家庭情況相差甚遠。另外,達西的婚事也遭到了家庭成員的反對,例如后來咖苔琳夫人的插手。門當戶對的婚姻才是當時社會認可的得體的婚姻,雖然這場求婚因為兩人的爭吵不歡而散,但這些阻撓像達西和伊麗莎白這樣的兩人相結合的社會因素,也顯示出這種社會默認的婚姻觀念的強大力量。
在此之前,科林斯先生的求婚也以失敗告終。科林斯起初不理會伊麗莎白的拒絕,以為這只是有身份的女性表現優雅與矜持的方式。這一點十分有趣,因為在當時的男女交往中,女性被認為應當保持保守與被動的地位,真正的淑女從不過分顯露自己的情感,更不會主動示好。這與后來伊麗莎白的行為也是相符合的。伊麗莎白經過彭伯里莊園一游后改變了對達西先生的印象,也并未主動和達西先生交流,而是被動地等待達西再次前來表白。
相反,班納特家的兩個小女兒則顯得十分外向主動,積極結交麥里屯的軍官們。這也讓班納特先生斷言她們同她們的母親一樣愚蠢。情況也確實如此,小女兒麗迪雅做出了整部小說中最不成體統的事情——和韋翰先生私奔。作為一個年輕的未婚女性,沒有任何財產,和一個也幾乎沒有財產又居心叵測的軍官私奔,無疑是一件頭腦發熱的愚蠢決定。這不僅會使麗迪雅名聲掃地,而且會讓整個家庭蒙羞。連班納特太太都意識到,這樣的行為對于班納特家其他待字閨中的女兒們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簡·奧斯汀對于社會行為得體與否也有自己的見解。人們認為夏綠蒂和柯林斯這一對看起來天造地設,盧卡斯一家為嫁出了長期待字閨中的女兒而歡欣雀躍,柯林斯也達到了咖苔琳夫人對他的要求,然而作者之前鋪陳描寫柯林斯先生的愚蠢使這段姻緣并不被看好。與此同時,奧斯汀花了大量的筆墨來為達西和伊麗莎白這樁不被人看好的婚姻作鋪陳,達西由傲慢轉為尊重,伊麗莎白由偏見化為理解,那么不成體統的因素也漸漸被弱化了。再加上咖苔琳夫人胡攪蠻纏的干預,更激發了兩人打破社會評判標準的勇氣。當簡·奧斯汀以女性視角來看這樁婚事時,束縛女性發展的社會傳統也要屈服于追求幸福的愿望,此時禮儀規范便不再是一成不變的了。但是,私奔仍被認為是嚴重不成體統的行為,甚至會牽扯上道德的批判。
同時,書中還涉及女性何時涉足社交圈的問題。班納特家的五個女兒,無論年齡大小和婚否,都已經進入了社交場合。咖苔琳夫人得知此事時頗為震驚,認為這是極其不成體統的行為。她認為,按照社會傳統,妹妹必須在姐姐出嫁之后才能外出在社交場合拋頭露面。對此,伊麗莎白反駁道:“要是因為姐姐無法早嫁,或者是不想嫁,做妹妹的就不能有社交和娛樂,那實在太苦了她們。最大的和最小的同樣有享受青春的權力。怎么能為了這樣的緣由,就叫她們死守在家里!”[12]
另外,關于女性外出陪護的社會傳統也有具體的規范。一位未婚的年輕女性是不能在無人陪護的情況下獨自旅行的,或者由一名非家庭成員的男性作為陪護也是極為不妥當的。[13]這作為一種默認的社會習俗,在《傲慢與偏見》中也被伊麗莎白打破。她顧不上考慮是否得體的問題,堅持只身穿越荒郊野外前去尼日斐探望生病的姐姐吉英。對此,彬格萊小姐表現得傲慢又鄙夷,她試圖以“無聊透頂”來詆毀伊麗莎白的形象:“頭發弄得那么蓬亂,那么邋遢!”[14]一連串感嘆句足以表現她的驚詫與嫌惡,并滿心以為彬格萊和達西會附和她的意見,然而兩位紳士的反應讓她大失所望,彬格萊先生認為這是伊麗莎白對姐姐急切的關心之情,而達西先生則表示伊麗莎白美麗的眼睛在經過長途步行之后顯得更加明亮動人。簡·奧斯汀借上層紳士之口,流露出對伊麗莎白獨立精神的贊賞,而是否得體的問題在這樣的情形下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對于禮儀規范合理性的判斷固然重要,但約定俗成的禮節和習慣不是判斷社會行為正確與否的唯一尺度,應當追求其目的是否發自于內心的良善和理性。不難發現,很多此類的得體性標準都關注于女性的行為標準,因此,女性的行為受到更多的限制與約束。上層社會的女性往往熱衷于追求完美的言行標準,漸漸失去自己的性情,優越感促使她們端起架子,擺出傲慢的姿態。因此,奧斯汀通過伊麗莎白這個極具性格的中產階級女性來表明自己對于社會禮儀標準的獨特認識。
可以說,奧斯汀真正反感的是過于儀式化的行為與矯揉造作的禮貌,她無時無刻不在嘲弄和諷刺這樣的人物,并使他們讓人發笑,或是受到懲罰。前文提到的柯林斯先生便是這樣的典型代表。另外,奧斯汀也提醒我們,良好的出身和教育并不代表擁有良好的教養,他們其中的很多人惺惺作態,缺乏應有的真誠和開朗:備受柯林斯一家敬畏的咖苔琳夫人是個無比傲慢和強勢的女人,她口口聲聲強調自己擁有的高貴出身和品位,卻時時表露出粗魯的言行。就連達西先生,這個作者著力打造的黃金單身漢,給人的印象也僅僅差強人意。他雖然受過良好的教育,但缺乏親和力,顯得過于保守和挑剔,這在社交場合中是令人厭惡的。彬格萊小姐自恃出身高貴便自命不凡,費盡心思想要討好達西卻落得兩手空空。
奧斯汀相信良好的教養來自于內心的善良,而非地位的高貴,因此她的譏諷與嘲弄并非空穴來風。她并沒有無止境地說教,而是擺出現實,讓讀者看得更加真切。理智的父母的悉心教導,加上充分的教育,內心善良的人便會擁有良好的教養,而高貴的出身和地位并不一定能培養出真正有教養的人。當我們看到伊麗莎白這位中產階級紳士的女兒,在良好的教育和自身修養之下,以自己獨立的思想和獨特的魅力贏得人們的欣賞,我們仿佛看到簡·奧斯汀的身影。這樣一位同樣擁有敏銳思維和幽默風格的中產階級女性,用她清麗端莊的文筆娓娓道來,回味無窮。
五、結語
兩百多年前,英國著名女作家簡·奧斯汀通過《傲慢與偏見》這部至今仍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小說,還原了英國攝政時代的社會風情,尤其是中產階級的社會生活。她所描繪的人物形象性格各異,言行舉止和個人素養也各有不同。人物之間的對比使讀者更加清晰地認識到良好的素養并非來自于家庭背景,而是植根于教育和品德。簡·奧斯汀對教養及禮儀的強調,其實質在于對當時社會生活中人際交往的道德關懷。攝政時代的金錢崇拜極大地影響了人際關系,尤其是婚姻關系,但言談舉止,待人接物的教養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它是社會地位的象征,也是家庭教育、個人素養的綜合體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簡·奧斯汀作為一位女性作家,更多地注意到社會禮儀對女性自由和發展的限制。她塑造的女主人公伊麗莎白不同于傳統的女性形象,在社會禮節和個人言行中有一些大膽的標新立異之舉,但就整體而言,她還是一個處在社會禮儀條框中依靠婚姻來改變命運的女性,未能完全擺脫禮儀和教養的規范要求。
參考文獻:
[1]伊揚·瓦特.奧斯丁:批評文選[M],1963:15.
[2]李燕姝.簡·奧斯汀的真實故事——評介英國作家邁爾的奧斯汀傳記《倔強的心》[A].外國文學,1998.06.
[3]Harvey J,Graff.the Legacies of Literacy[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320.
[4]Janet Todd.Jane Austen in Context[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304.
[5]凱倫·喬伊·富勒.簡·奧斯汀書友會[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49.
[6]夏侯富生.《傲慢與偏見》中的禮貌言語行為與交際世態[A].外語研究,2009.04.
[7]Samuel Johnson.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London:J.F.and C.Rivington[etc.],1785.Vol Ⅱ:90.
[8][9][10][12][14]簡·奧斯汀.傲慢與偏見[M].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10,77,26,188,44.
[13]Janet Todd.Jane Austen in Context[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