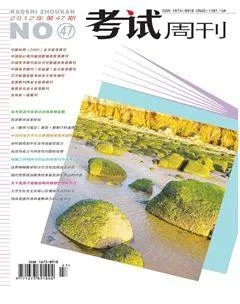《五號屠場》人物形象的不確定性
摘 要: 《五號屠場》在主題、人物形象、語言和情節等方面都充分地體現了后現代主義的不確定性寫作原則。本文從模糊性、多重性和零散性三個方面對《五號屠場》人物形象的不確定性進行文本分析。
關鍵詞: 小說《五號屠場》 不確定性 模糊性 多重性 零散性
《五號屠場》是美國后現代派作家馮內古特的代表作,也是典型的后現代主義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品之一。《五號屠場》在主題、人物形象、語言和情節等方面都充分地體現了后現代主義的不確定性寫作原則。筆者擬從模糊性、多重性和零散性三個方面對《五號屠場》人物形象的不確定性進行文本分析。
一、模糊性
作者在小說中明確表示:“這本故事中幾乎沒有真正的人物,也幾乎沒有戲劇性的沖突,因為書中的大多數人病弱無助,成了被難以抗拒的勢力拋上拋下的玩物。畢竟,戰爭的一個主要后果是人們不想成為真正的人物。”小說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扁平性的,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讀者很難辨認他們的實際身份。
比利是小說的主人公,作者對他的外表描述著墨不多,只有寥寥數語。“他是個長相滑稽的孩子,長大了變成了長相滑稽的青年——高挑羸弱,身材像可口可樂的瓶子”。“比利的樣子愚蠢滑稽——六英尺三英寸高的個子,肩和胸就像一盒廚房用的火柴”。讀者只知道比利又高又瘦,而他究竟長什么樣子卻不得而知,因為作者自始至終沒有對比利的五官進行描述。像比利這種瘦弱不堪的人怎么能去參加戰爭,又如何能在戰爭中得以幸存等,作者在文中沒有交代。戰后,比利與相貌丑陋的瓦倫西亞結了婚,最后在岳父的幫助下做驗光配鏡生意發了財,但是作者對他的婚姻生活和工作的具體情況卻較少提及。因此,比利的形象貌似清晰,實際上只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影子,作者留下的大量的文本空白給讀者提供了無限的想象空間,讓讀者對作品進行再創造,創造出自己心目中的人物形象。
除了比利,小說中其他人物的形象也是模糊不清的。十八歲的韋利是個不討人喜歡的孩子,這是因為他又笨又胖,而且身上總有一股咸肉的臭味。他包裹嚴實,渾身發熱,他從家中帶來的五層厚的圍巾從鼻梁向下遮住了他的整張臉。就連比利也從來沒有見過他的面孔,當比利曾經想象這張臉長得怎么樣時,想到的竟然是魚缸里的一只蛤蟆。處在童年末端的韋利是如何參軍入伍的,為什么他身上總是有一股咸肉味,他渾身發熱,卻又為何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所有的這一切不僅僅使讀者,更使故事中人物對其充滿了遐想。
流浪漢的形象更為模糊,他在小說的第三章里以美軍戰俘的身份出現在德軍運送戰俘的火車車廂里,在第四章里就默默無聞地死了。人們始終不知道四十歲的流浪漢姓什名誰,何等模樣,來自何方,為什么流浪,又是怎樣參軍入伍而成為戰俘的。他在這節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的污穢不堪的車廂里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九天。面對這種惡劣至極的生存狀況他卻一直說著“情況還不算太壞”。流浪漢的話語讓人對他過去的悲慘經歷產生種種猜想,他從前究竟過著怎樣的非人生活而使得他在如此境況下泰然自若。除此之外,四十四歲的中學教師德比、偷車賊拉扎羅、比利的妻子瓦倫西亞、二十歲的電影明星蒙塔娜等人物的形象也都十分模糊,筆者在此不再一一贅述。
二、多重性
小說主人公比利作為隨軍牧師助理在戰爭中得以幸存,被俘后送至戰俘營,后又被送到德累斯頓的屠宰場當勞工,見證了德累斯頓大轟炸。這場“歐洲歷史上最大的殺戮”給他造成了不可磨滅的精神創傷——他患了精神分裂癥,幻想著自己被飛碟綁架,被送到特拉法瑪多星球的動物園中進行展出。比利常常在斷裂的時空環境中幽靈般地穿梭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層面和地球及特拉法瑪多星球之間的空間層面。比利的形象具有明顯的多重性,這種多重性使得他的形象充滿了不確定性:時而滑稽可笑、呆呆傻傻,時而以德報怨、濟世救人,時而又唯利是圖、金錢至上。
1.滑稽可笑、呆呆傻傻。
比利作為一名戰士,沒有傳統作品中的英雄形象,給讀者的印象卻是反英雄形象。戰爭中的比利是一名隨軍牧師助理。他既沒有打擊敵人的實力,又沒有幫助朋友的能量,只是一個受人欺凌的無能之輩。在戰爭中得以幸存之后,他成了一名被打散的游兵,與另外三個游兵一同行進在敵人的后方。“拖在最后面的是比利·皮爾格林,空著兩手,沮喪地做好了送死的準備。比利的樣子愚蠢滑稽……他沒有頭盔,沒有大衣,沒有武器,沒有靴子。他腳上穿的是參加父親葬禮時買的便宜的低幫便鞋,丟失了一只鞋跟,走起路來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地顛簸”。“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個當兵的。他看上去像一只臟兮兮的火烈鳥”。在行進過程中,他不會做出任何反應來拯救自己的性命,必須在韋利的拳打腳踢之下才能勉強前進。被俘之后,他又是受人欺凌和嘲弄的對象,在戰俘車廂里,比利成了倒糞人,可當他想躺下睡覺的時候,每個人都叫他滾遠點,好像他對所有人都犯下了滔天罪行。于是可憐巴巴的比利不得不站著睡覺,要么根本不睡。在俘虜營分發衣服時,比利是唯一拿到死去平民衣服的人。衣服太小,根本不適合他穿。因此,當他穿上它時,衣服后背和肩部撕裂開來,兩只袖子完全脫落,外衣變成了一件毛領子的馬夾。“德國人在他身上看到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可笑滑稽的一幕。他們笑了又笑”。“他現在穿著銀靴子,裹著皮手筒,像寬大的長袍一樣披著一塊天藍色的簾子”。路上的很多人發現比利特別搞笑,一名外科醫生甚至以為他在故意扮小丑搞笑,而比利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只想極力地表現得友好。戰后,由于德累斯頓慘絕人寰的大轟炸給比利留下了難以愈合的精神創傷,他仍然處處顯得傻里傻氣。比利呆呆傻傻、滑稽可笑、任人欺凌的形象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引人捧腹之余,也使讀者對他寄予了更為深切的同情,同時充分地暴露了戰爭的荒謬性和殘酷性。
2.以德報怨、濟世救人。
處處顯得滑稽可笑、呆呆傻傻的比利有時候卻又像是寬恕一切、挽救蒼生的救世主。在小說中,作者曾多次把比利與耶穌聯系在一起。沒有頭盔、沒有武器、根本不像一個兵的比利是伴隨著掛在他墻上的耶穌受難的十字架長大的,他對耶穌抱著馴順的信仰。作者在小說的篇首題詞引用了一首著名圣誕歌的四行詩:“牛群哞哞叫,/圣嬰驚醒了。/小主啊耶穌,/不哭也不鬧。”在第九章,當比利看到他的交通工具——馬的慘狀時,眼里冒出了淚水。而在戰爭中,他從來沒有為別的任何事物哭泣過。而且后來人到中年,有時他也會獨自靜靜地哭泣,但從來不會號啕大哭。此時作者再次提到了這首詩,很顯然作者有意把比利的形象和濟世救人的耶穌聯系在一起。比利像耶穌一樣,對一切人類的苦難都淡然處之。被俘前的比利被韋利拳打腳踢而毫無反抗之意。被俘之后的他受盡欺凌,卻對欺凌他的人毫無仇恨和怨言,這一點與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有相似之處。但是同時,比利也非常關注人類的生存,試圖像耶穌一樣在地球上傳播拯救人類的新福音,他借助時間旅行到特拉法瑪多星球去尋求世界和平的秘訣:“我來的星球上,有史以來一直糾纏在瘋狂的屠殺中。……所以把和平秘訣告訴我,讓我帶回地球,拯救我們所有人:一個星球上怎樣才能和平相處?”由此,我們看到了比利想要挽救蒼生的救世主形象。這也表達了作者對戰爭的控訴和對和平的渴望。
3.唯利是圖、金錢至上。
盡管比利飽受戰爭的戕害,但他從戰場歸來時卻還不忘帶回一顆碩大的鉆石作為戰利品。可見,比利是庸俗的,他和大多數人一樣,擺脫不了對金錢的狂熱。戰后的比利與因不停地吃東西而身體龐大得像一座房子的瓦倫西亞結了婚。他之所以跟相貌丑陋、任何頭腦正常的人都不會娶的瓦倫西亞結婚是因為她是一位有錢人的女兒。他婚后得到了報償:他的岳父送給他一輛新的別克,一套全電器的住所,讓他當生意最興隆的伊利昂分店的經理,這使得他每年至少可掙得三萬美元的收入。而比利的父親曾經只不過是個理發的。正如他母親所言:皮爾格林家的社會地位提高了。由此可見,比利的婚姻跟愛情毫無關系,是完全建立在金錢之上的。這不僅折射出了比利唯利是圖、金錢至上的一面,而且表達了作者對拜金主義盛行、精神道德荒蕪的美國社會的嘲諷。
三、零散性
在后現代派小說中,作為主體的人喪失了中心地位,已經零散化,沒有一個自我的存在。《五號屠場》中人物的形象呈現出強烈的零散化特點,主要表現為主體之死和情感的消失。
小說主人公比利被俘前被韋利踢打而絲毫不反抗,被俘后的他飽受欺凌和嘲弄而毫無怨言,戰后的他為了金錢而跟丑陋的瓦倫西亞結了婚。他和妻子之間沒有愛情可言,就連妻子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時,他也沒有作出強烈的反應。對兒女他也表現得漠不關心,作者在小說中多次提到比利的兒子羅伯特曾經是個問題少年,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不是一位盡職的父親。他也不是一位孝順的兒子,當他的父親在狩獵意外身亡時,他沒有表現出特別的悲哀。比利對母親的感情很奇特,當他的母親來精神病房看他時,他一直用毯子蒙住自己的臉,不愿直面自己的母親,他覺得她讓他感到愧疚,感到自己忘恩負義,軟弱無能,因為她千辛萬苦給了他生命,讓這個生命活在世上,而他卻在見證了德累斯頓大屠殺之后,覺得生活沒有意義,根本就不喜歡活在世上。可見,比利的自我早已經被戰爭消耗殆盡,到了和平年代依然沒有恢復過來,并且日益嚴重。為了逃避現實,他不斷地在時空旅行中穿梭,情感的表達越來越少,與現實世界的隔閡越來越大。因此,畢利的形象非常突出地體現了主體之死和情感消失的零散化特點。
十八歲的韋利也強烈地呈現出主體之死和情感消失的零散化特征。他由于呆笨、肥胖,而且身上總有一股咸肉的臭味而不討人喜歡。在家鄉,他總是被不喜歡與之為伍的人撂在一邊。“每當韋利被人撂在一邊時,他就去找一個比他自己更不討人喜歡的人,與那個人一起胡鬧一陣子,假裝兩人是朋友。然后他就找一個借口,把那人狠狠揍一頓”。被排斥的孤獨感使韋銳的心理產生了嚴重的畸變,正是出于這種畸形的報復心理,他由想要挽救比利的性命而轉為瘋狂地要置其于死地。“韋利將他的右腳戰靴向后收,瞄準脊椎,準備一腳踢向這條裹藏著比利無數重要線路的管道。他要砸碎這條管道”。
除此之外,七十歲高齡的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朗福德身上也體現出明顯的零散化特點。他娶了她的第五任妻子、二十三歲的莉莉不是出于愛情,因為他對她根本不怎么了解,他只是想在公眾面前證明他是個超人。住院期間,他常常用各種方式對醫務員工說,那些體弱多病的人就應該去死。因此,大家都覺得他是個充滿仇恨、自負而又心狠的老人。可見,朗福德的情感也已經消失,他成了一個冷酷無情的人。另外,拉扎羅、瓦倫西亞、莉莉等人物形象也具有明顯的零散化特點,而且主要表現為主體之死或情感的消失。在后現代世界里,主體已經喪失了中心地位,自我沒有立身之地,剩下的只是身心肢解式的零散化。
參考文獻:
[1]陳世丹.美國后現代主義小說詳解[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1.
[2]馮內古特著.虞建華譯.五號屠場[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8.
[3]郭紅.《五號屠場》中荒誕的人物形象[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4,(6).
[4]楊仁敬等.美國后現代派小說論[M].青島:青島出版社,2004.5.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1年度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委托項目(2011GWX029)“《五號屠場》:走向不確定的后現代世界”的階段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