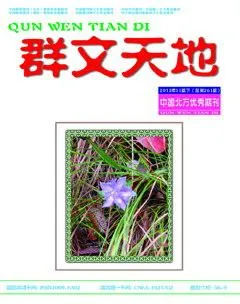愛(ài)的變味
摘要:通過(guò)對(duì)川端康成微型小說(shuō)《玻璃》的層層解讀分析,討論“一條主線(xiàn)、兩個(gè)主體、三個(gè)人物”,尤其是對(duì)愛(ài)的傳遞與回復(fù),從心理角度掃清作者表述迷霧,抓住文本實(shí)質(zhì)。
關(guān)鍵詞:川端康成;玻璃;施恩;心理防御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以其作品《雪國(guó)》、《千羽鶴》及《古都》等,于1968年榮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是歷史上第一個(gè)獲得此獎(jiǎng)項(xiàng)的日本人,也是繼泰戈?duì)栔蟮诙猾@此獎(jiǎng)項(xiàng)的東方人。他“被迫對(duì)日本文化不斷地進(jìn)行批判,從東西方文化的混淆中清理出真正屬于自己風(fēng)土和本能的東西”(三島由紀(jì)夫),并一直堅(jiān)持反戰(zhàn),倡導(dǎo)和平,對(duì)世界文學(xué)形成巨大影響。
《玻璃》是川端康成的微型小說(shuō),在其浩瀚的煌煌巨著中并沒(méi)有突出的地位,但這篇小而精的小說(shuō),不但具備的可讀性,更包含了無(wú)數(shù)的信息,讓人讀后總會(huì)掩卷長(zhǎng)思,并會(huì)讀出不同的意思來(lái)。
《玻璃》一文講述的是未婚妻子蓉子在玻璃廠(chǎng)目睹了一件慘事,一個(gè)童工在工作中嚴(yán)重受傷,于是她向未婚夫提出要去看望這個(gè)孩子,未婚夫同意了。童工痊愈后來(lái)家里致謝。十年后,這位童工成為了小說(shuō)家,丈夫讀到了他的小說(shuō)《玻璃》,并讓蓉子看。小說(shuō)中描述了童工后來(lái)設(shè)計(jì)了最美的花瓶獻(xiàn)給了這位恩人,但是卻深度自責(zé),認(rèn)為作為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自己接受了資產(chǎn)階級(jí)小姐的恩惠是很羞恥的事情。這讓施恩的夫妻兩人陷入沉思。
對(duì)于初讀該文的人來(lái)說(shuō),往往是一頭霧水,巨大的情節(jié)跳躍反轉(zhuǎn),奇怪突兀的用語(yǔ),讓人無(wú)法完全把握住文章意義。 本文試圖以“一條主線(xiàn)、兩個(gè)主體、三個(gè)人物”層疊展開(kāi)分析,賞析該文的精妙所在。
一、一條主線(xiàn):愛(ài)的傳遞與回復(fù)
“資產(chǎn)階級(jí)小姐”蓉子的愛(ài)的付出是真誠(chéng)的,單純的,不求回報(bào)的。也正因?yàn)檫@段愛(ài)是那么的真誠(chéng),所以無(wú)法重現(xiàn)和復(fù)制,在少年痊愈后登門(mén)感謝時(shí),蓉子不愿意接受這樣的尊崇,“逃進(jìn)屋來(lái)”,也不愿意再次當(dāng)面把錢(qián)送給少年,而是讓女傭人轉(zhuǎn)交。正如十年后她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行為解釋是,“我那時(shí)還是個(gè)孩子啊!”
對(duì)于童工而言,她的關(guān)懷不啻雪中送炭,不僅在身體康復(fù)上給予幫助,而且在精神上也是一次重生,讓他逃離了底層的勞苦危險(xiǎn)的工作,在花瓶設(shè)計(jì)上顯示出杰出的才能。
但是,在對(duì)愛(ài)的回復(fù)上,少年表現(xiàn)出了跳躍和修飾,讓愛(ài)變成為一個(gè)很復(fù)雜的東西。首先看痊愈后少年登門(mén)致謝的表現(xiàn):“是你,已經(jīng)痊愈了嗎?”“嗯。”少年蒼白的臉上現(xiàn)出驚恐的神色,蓉子心頭一酸。“你燒傷的地方不要緊了吧?”“嗯。”說(shuō)著,少年便解自己的衣扣。“不用,不必了……”
在這段少年與蓉子的對(duì)話(huà)中,我們感受到的是少年的質(zhì)樸,但內(nèi)心的心思卻洶涌澎湃,“驚恐”一詞看似突兀,卻呈現(xiàn)出他內(nèi)心復(fù)雜的心態(tài)。為何會(huì)驚恐?既是這位資產(chǎn)階級(jí)小姐的關(guān)懷讓他“受寵若驚”,也是痊愈就意味著將失去這樣美好的愛(ài)了。一個(gè)在危險(xiǎn)的玻璃廠(chǎng)工作的童工,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還能有其他的愛(ài)嗎?肯定沒(méi)有。所以失去被關(guān)懷的機(jī)會(huì),不比身體的受傷輕松。
這段愛(ài)對(duì)他的影響足夠深遠(yuǎn),他采取了多種措辭來(lái)應(yīng)對(duì)這份愛(ài)。在心理層面,他先是試圖保留、挽回或重現(xiàn)它,所以他才會(huì)努力創(chuàng)造,“把自己設(shè)計(jì)的最美的花瓶獻(xiàn)給那位少女”。其次,他得不到任何回應(yīng)(其實(shí)對(duì)蓉子而言,這位少年沒(méi)有任何行動(dòng)讓她重拾記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單相思”,心理防御機(jī)制“否定”強(qiáng)勢(shì)登場(chǎng)。他要以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身份去戰(zhàn)斗,要拋棄掉對(duì)資產(chǎn)階級(jí)的幻想,“先讓敵人把我們背上的‘玻璃’打碎就好了,哪怕與‘玻璃’同歸于盡。倘若能卸脫包袱,身輕體便,我就可以精神抖擻地繼續(xù)戰(zhàn)斗。”但是,在“否定”的更深處,他仍然渴望得到愛(ài),他變換著方式來(lái)表達(dá),成為小說(shuō)家何嘗不是他表達(dá)的方式。但除非他明白了自己真正渴求的是什么,否則他永遠(yuǎn)無(wú)法得到愛(ài)。
二、兩個(gè)主體:施恩者與受恩者
施恩者與受恩者處在兩個(gè)截然不同的環(huán)境中,施恩者高高在上,在女子中學(xué)讀書(shū),養(yǎng)尊處優(yōu),衣食無(wú)憂(yōu),聽(tīng)從感情的召喚,真誠(chéng)而單純。受恩者處于社會(huì)底層,干著危險(xiǎn)的工作,無(wú)人關(guān)心他的死活,缺乏關(guān)愛(ài)。兩者幾乎沒(méi)有任何交集,除了她對(duì)他的一次施恩。
施恩者并沒(méi)有想過(guò)要回報(bào),但是她的一次舉動(dòng),卻足以改變了這個(gè)少年的一生。雖然她已經(jīng)是個(gè)“佝僂著腰,臉色蒼白的瘦弱病人”了,但并不影響她當(dāng)年對(duì)少年的巨大影響力。少年對(duì)她有著無(wú)比美好的遐想,一直保持著“少女那種可愛(ài)和清新”的印象,這是對(duì)她無(wú)上的褒獎(jiǎng)。
但是,施恩者隔斷了受恩者的回報(bào)之心,讓一段感激之情一直懸空,成為受恩者最重的包袱,最終,他將此轉(zhuǎn)化為階級(jí)斗爭(zhēng)的包袱試圖將其清理掉,把自己推向了另一個(gè)極端:戰(zhàn)斗。
三、三個(gè)人物:童工、蓉子和表述者
該小說(shuō)共有三個(gè)人物,童工,也就是后來(lái)的小說(shuō)家,他在為生存而奮斗,感受著最?lèi)毫拥沫h(huán)境,忍受著無(wú)人關(guān)愛(ài)的孤寂。蓉子是施恩者,對(duì)童工有著巨大的心理影響力,當(dāng)然,僅僅是少年心目中的那個(gè)女神一樣的幻想,與現(xiàn)實(shí)中的蓉子其實(shí)已經(jīng)大相徑庭。
作者為什么要加入一個(gè)表述者,即蓉子的丈夫?除了在行文上略微方便外,他還有什么作用呢?
縱觀全文,川端康成一直刻意在描繪著故事最外層的東西,他故意避開(kāi)了深處洶涌的暗流,如同冰山一角,他只呈現(xiàn)著大海表面的小風(fēng)小浪,留著大量的想象和揣摩的空間留給讀者。在他看來(lái),用全能全知的第三只眼來(lái)直接描寫(xiě)這段故事仍然太過(guò)接近本質(zhì),他于是在讀者和小說(shuō)主人公之間再增加了一層“磨砂玻璃”,讓人看到影影綽綽的表演,產(chǎn)生更多的遐想,而不是一覽無(wú)余,太過(guò)實(shí)在。
所以,玻璃不僅是題目,是道具,也是呈現(xiàn)小說(shuō)的方式,即表述者。
(作者單位:四川財(cái)經(jīng)職業(yè)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