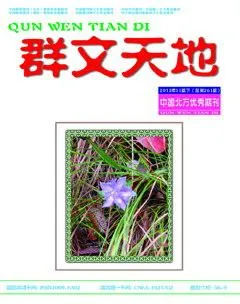東漢私學(xué)與豪強(qiáng)世族化
摘要:私學(xué)教育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一直是中國古代教育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東漢私學(xué)更是空前繁榮,并一度超越官學(xué),成為重要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私學(xué)的繁盛對東漢社會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而最為重要的影響就是豪強(qiáng)地主通過私學(xué)不斷接受經(jīng)學(xué)并最終完成世族化。文章擬從東漢私學(xué)繁榮與豪強(qiáng)熱衷經(jīng)學(xué)的原因,私學(xué)繁榮情況,豪強(qiáng)世族化過程三個(gè)部分來探討東漢私學(xué)與豪強(qiáng)世族化之間的關(guān)系。
關(guān)鍵詞:私學(xué);經(jīng)學(xué);豪強(qiáng)地主;世家大族
一、東漢私學(xué)繁榮及豪強(qiáng)世族化的原因
東漢時(shí)期,私學(xué)達(dá)到了一個(gè)繁盛期,而且在它的影響下,豪強(qiáng)地主逐漸向世族化過度。文章擬從以下幾個(gè)原因來對這一現(xiàn)象做一個(gè)說明。
(一)經(jīng)學(xué)復(fù)興和以經(jīng)致仕為私學(xué)發(fā)展提供了前提
東漢時(shí),劉秀為培養(yǎng)忠君人才,限制軍功豪強(qiáng),采取“退功臣而進(jìn)文吏”, [1] “光武中興,愛好經(jīng)術(shù),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bǔ)綴漏逸。”[2]東漢一朝讀經(jīng)成為風(fēng)氣,使經(jīng)學(xué)但得極大的發(fā)展。同時(shí)自漢武以后,朝廷選拔官吏的標(biāo)準(zhǔn)以明經(jīng)為主,儒生只要通經(jīng),便可以入仕做官,甚至封侯拜相。“士病不明經(jīng)術(shù)。經(jīng)術(shù)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經(jīng)學(xué)不明,不如歸耕。”[3]兩漢時(shí)期,如要進(jìn)入仕途,不管采用哪種形式,經(jīng)學(xué)始終是最核心的選官標(biāo)準(zhǔn)。正是經(jīng)學(xué)的復(fù)興和以經(jīng)致仕,才為東漢私學(xué)的繁榮提供了良好的環(huán)境和前提。
(二)今古文之爭,為私學(xué)發(fā)展提供了學(xué)術(shù)需要
自西漢末年劉歆提出設(shè)立古文經(jīng)學(xué)博士開始,今古文由于在經(jīng)義上和治學(xué)上的風(fēng)格和方式有明顯的不同,今古文之爭變得日益公開化和激烈化。到了東漢時(shí)期,今文經(jīng)學(xué)獨(dú)占了官方教育,但古文經(jīng)學(xué)并未因此而退出。為了宣傳自己的學(xué)術(shù)思想,進(jìn)而獲得官方的認(rèn)可,便堅(jiān)持在私學(xué)中傳授,從而促進(jìn)了私學(xué)的發(fā)展。在今古文兩派長期的論爭過程中,兩派除了希望通過官學(xué)途徑發(fā)展外,“而更多地是借助私家傳播的形式,聚眾授徒,以至使得東漢私學(xué)的發(fā)展規(guī)模極大,盛況空前。”[4]
(三)東漢經(jīng)學(xué)發(fā)展與官學(xué)不足的矛盾為私學(xué)發(fā)展提供了社會需求
東漢時(shí)期,由于經(jīng)學(xué)的發(fā)展和選官的更加注重經(jīng)學(xué)標(biāo)準(zhǔn),使社會上讀經(jīng)蔚然成風(fēng),然而東漢當(dāng)時(shí)的官學(xué)仍然承襲西漢的官學(xué)系統(tǒng),主要分為中央官學(xué)和地方官學(xué)兩種,而且“東漢時(shí)期中央太學(xué)時(shí)興時(shí)廢,而地方雖有官學(xué)之名卻無官學(xué)之實(shí),許多郡縣學(xué)校都久廢不修”。[5]即使官學(xué)最為繁盛時(shí),其規(guī)be6f841fe9971bac7ec5153e143e7fbf模數(shù)量,入學(xué)名額也遠(yuǎn)遠(yuǎn)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相對于官學(xué)的弊端,私學(xué)以其靈活性、廣泛性,特別是儒學(xué)大師的加入而得以空前發(fā)展。因而,傳經(jīng)的重任慢慢向私學(xué)轉(zhuǎn)移,私學(xué)教育成為傳經(jīng)的中流砥柱。
(四)東漢對豪強(qiáng)地主的壓制與籠絡(luò)使其尋求新的出路
東漢政權(quán)本身就是在南陽豪強(qiáng)地主力量的扶持下建立起來的。因而在東漢建立后,豪強(qiáng)地主在經(jīng)濟(jì)上、政治上都有了空前的發(fā)展。豪強(qiáng)實(shí)力的增加,勢必會影響到東漢社會的穩(wěn)定,故而東漢政府對豪強(qiáng)地主即利用籠絡(luò)又壓制其發(fā)展。豪強(qiáng)地主為了維持其家族利益的發(fā)展,不得不尋找一條更加穩(wěn)定的道路進(jìn)入東漢政權(quán)。東漢入仕以通曉經(jīng)義為主要標(biāo)準(zhǔn),故而當(dāng)時(shí)豪強(qiáng)地主紛紛“通過演習(xí)儒術(shù)來改變家族的生存境遇,從明經(jīng)入仕的途徑以一種更被皇權(quán)接受的方式進(jìn)入皇朝政治”。[6]
二、東漢私學(xué)繁榮的突出表現(xiàn)
東漢時(shí)期,私學(xué)在上述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盛極一時(shí),突出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一)私學(xué)的數(shù)量多,規(guī)模大
東漢時(shí)私學(xué)繁榮的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數(shù)量眾多,而且規(guī)模龐大。“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jīng)生所處,不遠(yuǎn)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7]而且,“據(jù)學(xué)者統(tǒng)計(jì),《后漢書·儒林列傳》及其他傳記所記載較大規(guī)模的私學(xué)共38家,受業(yè)弟子千人以上者15家,萬人以上者兩家,尚未計(jì)官僚士大夫之私學(xué)及家學(xué)。”[8]
(二)形成較為完善的結(jié)構(gòu)體系
東漢私學(xué)自下到上已經(jīng)形成較為完善的辦學(xué)體系,該體系主要有書館、鄉(xiāng)塾和精廬或精舍構(gòu)成。書館是東漢啟蒙教育的場所,王國維考證:“漢時(shí)教初學(xué)之所名曰書館,其書名曰書師。”并指出書館“旨在使學(xué)童識字習(xí)字”。[9]之后,便可以進(jìn)入鄉(xiāng)塾,進(jìn)行基本的經(jīng)書學(xué)習(xí)。這一階段僅要求學(xué)生掌握經(jīng)書的大意,不求精深理解。最后就是精廬或精舍,要求專經(jīng)研習(xí)。精塾與精舍的開設(shè)主要是通經(jīng)大儒或著名學(xué)者。如“(劉)淑少學(xué)明《五經(jīng)》,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shù)百人。”[10]又如“(姜)肱博通《五經(jīng)》,兼明星緯,士之遠(yuǎn)來就學(xué)者三千余人。[11]
(三)經(jīng)學(xué)大師與私學(xué)的關(guān)系密切
經(jīng)學(xué)大師與東漢私學(xué)的關(guān)系主要包括兩個(gè)方面:一是東漢的經(jīng)學(xué)大師投身于私學(xué)教育。他們開設(shè)精廬精舍,廣收學(xué)徒,宣揚(yáng)學(xué)術(shù)思想,使私學(xué)成為傳經(jīng)研經(jīng)的最重要的陣地。例如“(馬)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yǎng)諸生,常有千數(shù)。”[12]而其他經(jīng)學(xué)大師如樓望,蔡玄,魏應(yīng)等皆開館授徒,弟子少則千人,多著萬人;二是私學(xué)中名家輩出,成績斐然。《后漢書·儒林列傳》所列名儒42人,有39人出自私學(xué)或直接興辦私學(xué)。
(四)私學(xué)類型多樣和形式靈活
東漢時(shí)期,對興辦私學(xué)者并沒有明確的身份限制,凡“通曉經(jīng)義”者皆可設(shè)館收徒。因而使東漢私學(xué)類型多樣,大體來說主要有三種類型的私學(xué):一類是官僚士大夫私學(xué),如樓望“建初五年,坐事左轉(zhuǎn)太中大夫,后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余人。”[13]一類是民間人士辦學(xué),如周澤“少習(xí)《公羊嚴(yán)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shù)百人。”[14]還有一類就是家學(xué)。東漢私學(xué)不僅類型多樣,而且對地點(diǎn)和場合并沒有特殊的要求。如桓榮既可“負(fù)土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shù)百人”,也可“抱其經(jīng)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yán)Вv論不輟”。[15]私學(xué)的類型多樣、辦學(xué)靈活,大大的擴(kuò)寬了私學(xué)的發(fā)展途徑。同時(shí)入學(xué)者也無身份、地域、年齡的限制。正是這樣,東漢私學(xué)才能繁盛一時(shí),顯現(xiàn)出無限生機(jī)。
三、豪強(qiáng)世族化的過程
東漢經(jīng)學(xué)的發(fā)展和私學(xué)的繁榮對當(dāng)時(shí)社會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而其中一個(gè)極為重要的結(jié)果就是豪強(qiáng)世族化,本文大體把豪強(qiáng)地主的世族化分為兩步:一是豪強(qiáng)的文化化,二是壟斷文化傳播,完成文化的家族化,成為世家大族。
(一)豪強(qiáng)的文化化
東漢時(shí)期私學(xué)繁盛,多名家大儒,官學(xué)所不能及。東漢豪強(qiáng)地主雖可以通過其社會地位進(jìn)入官學(xué),但是當(dāng)時(shí)豪強(qiáng)研習(xí)經(jīng)文,掌握經(jīng)學(xué)多選擇私學(xué)。豪強(qiáng)的文化化與私學(xué)有著極為密切的關(guān)系。豪強(qiáng)子孫游學(xué)各地,拜訪名師在東漢幾乎成為其掌握文化的通常道路。如南陽鄉(xiāng)里著姓樊宏,其子儵“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yán)氏春秋》。”[16]又如南陽豪族陰氏,在陰子方時(shí)“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頃,輿馬仆隸,比于邦君。”而到陰識時(shí)“識時(shí)游學(xué)長安,聞之,委業(yè)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余人往詣(劉)伯升。”[17]再如當(dāng)時(shí)的軍功豪族馬援一族,其兄馬余之子馬嚴(yán)“從平原楊太伯講學(xué),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18]河南豪族侯霸“家累千金,不事產(chǎn)業(yè)。篤志好學(xué),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谷梁春秋》”。[19]
(二)壟斷文化傳播,形成世家大族
豪強(qiáng)地主通過私學(xué)方式掌握經(jīng)學(xué),完成家族的文化化后,為了家族長久利益,講求家學(xué),壟斷文化的傳播,形成世代相傳的累世經(jīng)學(xué),即所謂的“傳父業(yè)”、“修父業(yè)”等。陳寅恪曾指出“夫士族之特點(diǎn)既在門風(fēng)優(yōu)美,不同與凡庶,而優(yōu)美之門風(fēng),實(shí)基于學(xué)術(shù)之因襲。”[20]如東漢世家望族楊氏一族,在楊震時(shí)“震少好學(xué),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明經(jīng)博覽,無不窮究。”楊震受業(yè)于私學(xué),而到了其子楊秉時(shí)“少傳父業(yè),兼明《京氏易》。”其孫楊賜“少傳家學(xué),篤志博聞”曾孫楊彪“彪字文先,少傳家學(xué)。”[21]再如當(dāng)時(shí)大族袁氏一族,在袁安時(shí)“安少傳(袁)良學(xué)。”其子袁彭“(袁安)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yè)”。[22]
東漢以經(jīng)取士,豪強(qiáng)地主不斷學(xué)經(jīng),進(jìn)而由文化壟斷變成仕途壟斷,由世代傳經(jīng)變成世代為官,最終完成向世家大族的轉(zhuǎn)化。同樣以東漢的楊氏一族為例,楊震“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楊秉“代劉矩為太尉”楊賜“代劉郃為司徒,”“復(fù)代張溫為司空”。楊彪“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23]再如被譽(yù)為四世五公的汝南豪族袁氏一族,“袁安官司空,又官司徒,其子敞及京皆為司空,京子湯亦為司空,歷太尉,封安國亭侯,湯子逢亦官司空,逢弟隗先逢為三公,官至太傅”。[24]楊袁二族正是因?yàn)槭来鷤鹘?jīng)而成為東漢極為顯赫的世代公卿家族。
四、結(jié)論
東漢時(shí)期的私學(xué)空前繁榮,并對當(dāng)時(shí)社會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豪強(qiáng)的世族化正是得益于東漢私學(xué)的發(fā)展。當(dāng)豪強(qiáng)地主轉(zhuǎn)化成世家大族后,對東漢文化政治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文化上使東漢繁榮的私學(xué)逐漸轉(zhuǎn)化成家學(xué)。政治上,世家大族依靠其經(jīng)濟(jì),社會乃至文化上影響力,壟斷仕途。成為東漢不可忽視的重要階層。到魏晉南北朝時(shí),皇權(quán)與世家大族相互妥協(xié),形成當(dāng)時(shí)特有的門閥政治。
參考文獻(xiàn):
[1]范曄.后漢書·卷一·光武帝紀(jì)[M].北京:中華書局,1965(5).
[2][7][13][14]范曄·后漢書·卷七十九·儒林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5).
[3]班固.漢書·卷七十五·夏侯勝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6).
[4]孫峰,肖世民.漢代私學(xué)考[J].西安聯(lián)合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9(3).
[5]蔣華.漢代私學(xué)以經(jīng)學(xué)傳授為主的原因[J].鹽城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6(5).
[6]吳桂美.從豪強(qiáng)宗族到文化士族[J].海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7(3).
[8]楊振梅.東漢經(jīng)學(xué)世家述論[J].曲阜師范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2006(4).
[9]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四[M].北京:中華書局,2004(6).
[10]范曄.后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5).
[11]范曄.后漢書·卷五十三·姜肱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5).
[12]范曄.后漢書·卷六十·馬融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5).
[15]范曄.后漢書·卷三十七·桓榮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5).
[16]范曄.后漢書·卷三十二·樊宏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5).
[17]范曄.后漢書·卷三十二·陰識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5).
[18]范曄.后漢書·馬援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5).
[19]范曄.后漢書·卷二十六·侯霸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5).
[20]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5).
[21][23]范曄.后漢書·卷五十四·楊震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5).
[22]范曄.后漢書·卷四十五·袁安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5).
[24]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五·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1).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xué)歷史與社會發(fā)展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