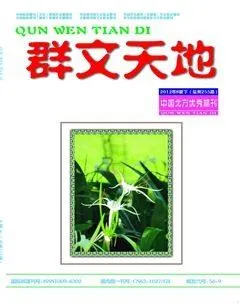周敦頤哲學思想簡述
摘要:作為理學開山的周敦頤,他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宇宙論,完成了儒學倫理“推本太極”的功業而被推為“道學宗主”。《宋史·道學傳》中,周敦頤被認定為孔孟道統的繼承者,“得圣賢不傳之學”,肯定了他在理學史上的地位,現就簡要介紹一下周敦頤的哲學思想。
關鍵詞:《太極圖說》;誠
一、周敦頤受道家影響
周敦頤處世超然自得,塵世名利,雅好山林,他窗前雜草叢生卻不鋤之,答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體現出一種要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人生胸懷,這里似乎有莊子觀魚樂之意,大有脫俗之向。周敦頤之恬淡遠志,無疑深受道家影響,性情上如此,思想上更是如此。從淵源上看,老學和易學是他思想的兩大源泉。尤其是老學及王弼注《老》《易》中的學說,成為周敦頤的哲學結構和方法的基干。周敦頤受道家哲學影響之最明顯者為《太極圖說》,對于“無極而太極”一句,爭議不斷。《易傳》中只有“無極”概念,而先秦典籍中說到的“無極”多指無窮意,儒家僅論太極,以之為“有”,道家則視其道為無極而太極,即恍惚之道與真精之一的關系。周敦頤的學說正是承接道家老子的思想而來的,因此,朱熹認為周敦頤“發圣學所未發”,此說法受到陸九淵的批評:“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圣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后人簸弄于頰舌紙筆之間也。無極二字,出于老氏《知其雄章》,吾圣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陸九淵雖與朱熹的觀點有差異,但是他指出周敦頤這一思想來自于老學則不誤。總之,周敦頤的思想受道家思想的影響,最終形成自己的道家化的儒家思想,融合儒家與道家,成為宋明理學的開端。
二、《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是一套宇宙生成系統,它的發展模式是太極——陰陽——五行——萬物。《太極圖說》認為,宇宙的最初階段是“無極而太極”,“無極”是指無形無象的最高實體,“太極”指的是最大的統一體。宇宙最原初實體為太極元氣,太極元氣分化為陰陽二氣,陰陽二氣變化交合形成五行,各有特殊性質的五行進一步化合凝聚,從而產生了萬物。《太極圖說》的宇宙發生學說表明,世界在本質上是從某種混沌中產生出來的東西,是某種發展起來的東西,是某種在時間過程中逐漸生成的東西。太極作為未分化的原始實體,它的運動是陰陽產生的根源。“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突出了宇宙本質上是運動的。運動的過程是動靜兩個對立面的交替和轉化,“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動”的狀態發展到極點,就要向相反的方向轉化,變化為“靜”。同樣,“靜”的狀態發展到極點,就又要轉化為“動”,整個宇宙過程中任何一種特定的運動狀態都不是恒常不變的。《太極圖說》給我們展現出了宇宙萬物如何化生,人作為天地間最有靈氣的生物是如何成己并且如何成圣這一整套理論模式,其中也不乏包含著一些具有辯證意義的觀點,值得我們學習。
三、以誠為本的圣人之境
自思孟學派提出“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以后,“誠”這一范疇一直被儒學所重視,李翱力倡“性命之道”,糅合儒、佛,更把“誠”規定為“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而與天地合一的“圣人”境界,進一步提高了“誠”在儒學倫理思想中的地位。這在周敦頤這里顯得尤為突出,“誠”不僅成了宇宙的精神實體,而且又是“圣人之本”和一切倫理道德的根基。他提出“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認為一個“士”應把成賢成圣作為一生追求的理想目標,應該“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黃宗羲指出:“周子之學,以誠為本,從寂然不動處握誠之本,故曰主靜立人極”《宋元學案 卷十二》。
《太極圖說》說:“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矣。”他認為,人得陰陽五行的優秀材料而生,為萬物中最靈的。身體既然生成了,精神發生,就有知識了,剛柔善惡等品質相互影響,萬事層出不窮。所以必須建立一個最高標準,叫做“人極”,人極的內容就是“中正仁義”,而以“靜”為主。這種“中正仁義而主靜”的境界,也就是“誠”的境界。周敦頤自己解釋“主靜”說:“無欲故靜”。所謂“靜”就是安定、安寧。所謂“無欲”,就是沒有私欲的干擾。他認為,人能“無欲”,仁義道德的本性也就發揮出來了,這就是他所說的“誠”的境界。
圣人為什么要以“誠”為本?這是因為“誠”自有妙用,周敦頤說:“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圣人。”《通書·圣》,“寂然不動”也即《誠幾德》章所說的“誠無為”,意為至靜無思,此謂“誠”之體。“神”即“誠”之用,它能通達明照,是“誠”所固有的一種神妙的認識功能。“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意即善惡之未形。這是說,“誠”作為道德的本體,本身就是一種先驗而神妙的認識主體,一旦感應而動,不必通過思慮,即能明照一切,自可直覺微而未形的善惡。圣人以誠為本,就具備了“誠”、“神”、“幾”三者統一的品格,“圣,誠而已矣”《通書·誠下》。作為圣人之本的“誠”,是“寂然不動”的,只有主靜,才能達到與“誠”合一的境界,也才能“立人極”,也才能達到圣人之境。
參考文獻:
[1]方克立,李蘭芝.中國哲學名著選讀[M]. 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2]錢穆.宋明理學概述[M].九州出版社,2010.
[3]馮達文,郭齊勇.新編中國哲學史[M].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簡介:姜 樂(1987-),男,安徽大學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