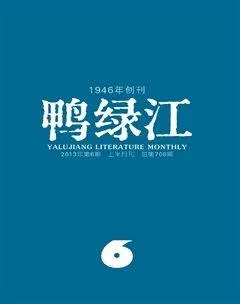河流史
萬一波,遼寧丹東人,現居沈陽。中國鄉土詩人協會會員,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1987年發表處女作,以詩歌、散文創作為主。詩文常見于多種報刊和各種選本,多次在全國性詩文大賽中獲獎,獲首屆“楊大群三農文學獎”(詩歌)。著有詩集《熏風點燈》、《翅膀上的雪》。
題記:河流就是前進著的道路,它把人帶到他們想要去的地方。
——[法]帕斯卡爾
創世
沉浸在遠古狂歡中,我是上天賜孕的
母牛分裂生靈
我巡視大地巡視藍天巡視馬盂山和克
什克騰巡視一只羊的內心
一股清泉和一把大草撐起胃囊撐起身
軀撐起目光
我聚攏盛大節日,揮灑王者光芒,居高
臨下撫慰近處羔羊和遠處時光
我傾瀉情欲傾瀉愛意傾瀉綠色光芒
在蹄窩撒下羊羔花種子給一塊頑石化
妝在風的耳邊掛滿鈴鐺
我在綠氈上分娩獺兔原鼠草狼分娩一
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分娩青牛和白馬分娩萬千之象,我沉
浸在創世的快樂中
沉浸在生產的幸福里沉浸在一只鷹的
空曠。一只綠色種子
在我膝蓋上開花,在手指間開花在薩
滿的手鼓上開花
藍天的藍飄過眼睛,催我重生的色彩
浸潤面皮
我的后代生下來就有一雙綠中泛藍的
眼睛
馬奶流成彎曲的河長調驅走烏云,套 馬桿定格奔跑
酒香四溢馬蹄花四溢。是什么給我力量?讓我聚集星星趕走太陽換算羊群
是誰給我昭示,讓我柔情如風衣袂如風雙臂
如風,而風如長發
我在自己的體內行走,在曠世中飛奔,長發
如馬尾飛揚
腿部肌肉烈火般燃燒而內心靜似湖水,沒有
什么迷程可穿越
走到哪里都留下清晰的線條,我的子民以及
我的兒子
在路上爬行,他們的動作遠沒有我想象的那
么輕盈
是什么給了他們羈絆?我百思不得其解。放 下吧放下所有的不快
我的旅程沒有結束,那些在冬季開放的花朵
召喚我
那些產下母羊的羊羔召喚我,那些催生大地
的野草召喚我
一些未知的召喚,讓我心神不寧,我的前程
未卜但我必須飛翔
不可違背的召喚如強大的神祗,給我肉身套
上光環
讓我在許多贊語中死去。難道生,只是為了
死嗎?
難道白天只是為了等待黑夜嗎?有沒有一種 恒久的力量能夠
驅散我心中的疑慮,我心有疑慮,飛翔的
姿態
便沒有那么流暢,我看見一團陰云悄然而
起,越滾越大
江山抽失顏色,羊羔露出祈求的目光。我試
圖掙扎
騰躍,翻轉,沖挺。但翅膀被死死捆住,羽毛
被拔光
毛孔幻化許多眼睛,而每一只眼睛里都滴下
熾熱的淚水
在淚水的短暫澆灌下,生機復現平安復現和
諧復現
這是最后的節日。手鼓響起,馬頭琴長調悠
揚進夜色的一霎
一條白色的帶子,一條長長的帶子從天邊飄
來,我知道
我的死期已至。生于河流必將死于河流
干旱
以匍匐的姿勢走完一座村莊那些細小的
干沙
就像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是一些細小的卵
在我的背上匍匐玩耍。我像一只沙龜匍匐
前行
耳蝸充滿巨大的水聲,風聲和水聲何其相似
可是我為何只有干癟的眼窩?嗅到一株夾竹 桃的香味兒
嗅到一只花大姐的香味兒,嗅到馬糞的香
那些香味兒因失水更濃烈。裹在干茶里的香 跟融在水里的香不同
干茶是一粒風干的蝙蝠屎。趁著兒子們熟睡
我到處搜集罐體,一些上世紀的咸菜壇子像
廢棄的村莊
壇口聚集一些鹽分和尿堿,聚集帶血絲的
痰跡
一座廢瓦窯灰燼里我盡量找尋那些弧形的
薄片
尤其注意那些有水紋那些浸過水的薄片
一塊一塊對接然后用唾液黏合起來妄想它
們重生
我反復抱起它們打量它們孕婦般的身段
被我反復抱起的還有我愛的人和一些破
漁網
如今她(它)們已經抱著一滴淚遠走他鄉
我搜集變了形的鐵洋皮桶糟了一塊板的木
桶扭曲的水舀
用麻線縫過而又復裂的水瓢,就連一只干
葫蘆
也不放過,如果有水它會重新硬撐起來像帆
一樣飄走
陰云涌過山頂該下雨了我一門心思這么想
而雷聲從遠處滾過漸近漸小,這讓我對聽覺
產生了懷疑
多年來我發現我的耳朵有些異樣
兩只耳朵像蝙蝠的耳朵長于頭頂與身體極
不協調
我經常做出尋聲的舉動但結果往往風吹耳
毛無功而返
但我的努力終究沒有白費六月初十果然下
了一場大雨
等我牽著羊跑回家中抱出那些罐子雨就
停了
可悲的是那些罐子不僅沒有接到多少雨水
那一點點雨水反而拉開它們的傷口
讓它們直喊疼。疼痛之上何以療傷?我不忍 疼痛踽行于河床
我抖落兒子們大聲喊,我狂奔,頭發一綹綹
豎起劍指蒼天
我爆皮的嘴唇喊不出聲音活像一只丟了吹
嘴的銅喇叭
何以給我安慰!何以給我安慰!
我返回原始的匍匐狀態去哭那些待哺的草
去哭輕薄如紙的蚌殼,就在我啞然失聲淚水
全無的夾當兒
舊時官道的車轍里我看到一條魚一條泥鰍
一樣長有翅膀的魚
試圖飛起復落入我的掌心
我把它小心揣起,放進一只陶罐僅有的水里 ……
洪荒
以此種繁復的形式寫詩,正好詮釋我的心
態,我以無以復加的蒼涼
懷念美好懷念凄厲懷念一只羊的溫柔。而此 前所見到的
一條沾滿污血的臍帶,瘦小干癟,連接著一
顆顆巨大的腦袋
寄生的腦袋蒙昧的腦袋圓滾滾的腦袋。它們 相互壞笑
搓掉褲腳上的泥巴,披上文明的外套,走進
城市逍遙
而河道遠逝,如一截鞭影只留下彎曲的形
狀,沒有了羊草
沒有了花俏,昔日走進垂暮,生機偶現一段
歌謠
佝僂身子的人,有半邊臉,只看見巴掌大的
天下,他們有
勤勞的身段卻沒有富裕的大腦。繼而是殺伐
斷子絕孫的殺伐肝腦涂地的殺伐,勛章鼓動
的殺伐。砍倒一棵樹
叫作勞動砍倒一千棵樹叫作模范,紅旗飄飄
人歡馬叫
轟鳴的噩耗驅散了鳥鳴鴿哨。北極熊越過
國界
進入西伯利亞之北;曾經傲視群雄的森林
之王
被一口“順山倒”嚇破了苦膽
膽汁四濺后開始了悲壯的遷徙,一個種群開
始萎縮,從一百到三十,從南長白山流落到北西伯利亞狹長的
犄角。我的祖國本應該
花枝招展枝繁葉茂,而盈目的卻是暗瘡百孔
風雨飄搖
山石不再安分,厚土不得固牢,風吹沙瞇草
木凄凄河道阻塞舟楫如瓢
而或天旋地轉房舍潦倒,而或驟然怒發洪濤
開道
來自地心的警報不斷拉響,汶川驚懼玉樹驚
懼雅安驚懼
人們驚懼地在一條斷裂帶上舞蹈
十年九旱無異地,十年一澇便成災,一座大
湖現身龜板
一條大河頓滔滔。有別于創世的洪荒,一邊
是燈火招展
一邊是無盡蕭條,城市在長高,農田在減少
田間皆老叟,村姑四下逃。田園美景不復再
悠然南山失淘淘
等同于創世的洪荒,逡巡在田野的人,腰桿
有同樣的弧度
而一條河的介入,讓他們有不同的反應:創
世者
有充足的淚水膜拜水母;這個人卻眼光憂郁
欲哭無淚
捶胸頓足無以期許
這是誰的錯?這是誰的惱?洪荒中獨行的人 呀
你也許會知道。水生木,水以木貴,一條河流 的歡洽
是草木擺出的盛宴,是鳥獸合歡的祈禱
洪荒中獨行的人呀,你看沒看到
一片沙漠的潮正在把你淹沒,一條孤獨的蛇
正在把你撲倒?
漁火
那是記憶中的一點光亮嗎?每一次打撈
都有微弱的收獲,而人影卻
日漸嶙峋。水草間
一只水鳥撲棱而過,白刃的翅劃進骨縫
暗傷一條細長的腿
微光下,一張快速起伏的肚皮
使肋骨更清晰。起網時,卵石狀的聲音
砸進河水,夜涼濺上額頭
他蹲坐,燃一只煙鍋。一船,一人
喉結翻動如一只魚鷹
河道外,天光熹微處,亮起一縷歪歪扭扭的炊煙
古渡
那條船,那支篙,那個人
如今都不在了
河岸上,荒草遮蔽下一坨厚實的夯土
留有草席的紋理
那些個紅襖小腳的新媳婦,大腳力巴漢
剪了頭發的革命黨早已作古
燈火下一個大臉盤女人的后代
依然在堤圍的村落里隱姓埋名
春風又渡。許多人事,如那枚從東到西的
日頭
白日渡過,夜里潛回
責任編輯 王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