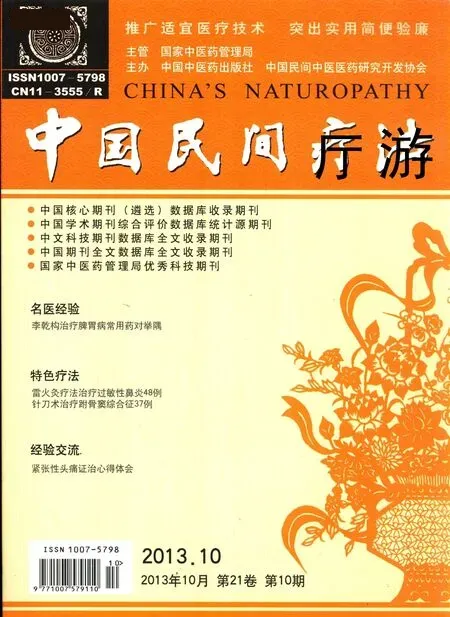兩種手術入路空心螺釘固定治療肱骨大結節撕脫骨折比較
王述偉 蘇山林 馬象武 楊志全 張永青
(山東省壽光中醫醫院,262700)
肱骨大結節撕脫骨折在臨床上較為常見,多為高能量損傷所致[1]。手術入路的選擇與肩關節功能恢復關系密切[2],以往手術多采用傳統的肩前三角肌和胸大肌間隙入路,對肩關節軟組織損傷較大,影響了肩關節恢復。我院2009年3月~2011年12月收治肱骨大結節撕脫骨折患者47例,分別采用肩前外側經三角肌入路和肩前三角肌和胸大肌間隙入路行切開復位空心螺釘內固定術,比較兩種入路的臨床效果,報道如下。
一般資料
患者47例,隨機分為試驗組和對照組。試驗組25例,男15例,女10例;年齡19~61歲,平均(32.3±5)歲;交通事故傷11例,高處墜落傷9例,摔傷5例;受傷至手術時間4~8h,平均(5.23±1)h;左側11例,右側14例。對照組22例,男13例,女9例;年齡18~65歲,平均(35.3±4)歲;交通事故傷8例,高處墜落傷6例,摔傷8例;受傷至手術時間5~10h,平均(7.19±2)h;左側10例,右側12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致傷原因、左右側別、受傷至手術時間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納入標準:肱骨大結節撕脫骨折,年齡及性別不限,傷后10h內入院。
排除標準:嚴重合并傷影響康復鍛煉者、嚴重的基礎疾病(如嚴重的心腦血管、內分泌、肩周炎、肢體偏癱等影響患者康復期功能鍛煉者)、開放性肩關節損傷、合并其他部位骨折者均排除在本研究之外。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診斷、手術均由同一組醫師完成,兩組手術器械采用的空心螺釘均由武漢德骼拜爾器械公司提供。
試驗組:臂叢麻醉成功后,患者取仰臥位,患肩墊高,取肩關節外側小切口,以肱骨大結節體表處為中心長約3~4cm(注意不要超過肩峰下5cm),于三角肌上1/3鈍性分離,保護軟組織血供及腋神經,直接顯露肱骨大結節骨折斷端。將骨折復位后,在導針引導下擰入2枚長短合適的空心螺釘固定。
對照組:臂叢麻醉成功后,患者取仰臥位,患肩墊高,取胸大肌及三角肌間隙入路,切口長約8~10cm,將三角肌牽向外側,頭靜脈與胸大肌牽向內側,顯露肱骨大結節骨折斷端,將骨折復位后,在導針引導下擰入2枚長短合適的空心螺釘固定。
術后處理:兩組術后常規抗感染治療;術后1周開始肩關節被動小范圍功能鍛煉,3周后開始主動功能鍛煉;術后3個月待X線片復查示骨折愈合后,增加功能鍛煉范圍和力量。
結果
療效評價指標:記錄兩組切口長度、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及骨折愈合時間。隨訪時按照肩關節Neer評分標準[3]評定療效。
試驗組與對照組各指標比較見表1。
表1 試驗組與對照組各指標比較(±s)
評價指標 試驗組 對照組切口長度(cm)87.2±2.6 80.1±2.1 3.4±0.5 8.6±1.7手術時間(min) 40.2±5.3 62..6±11.6術中出血量(ml) 78.85±26.79 136.78±28.65骨折愈合時間(周) 13.9±2.8 14.1±3.1肩關節功能Neer評分
切口長度、手術時間和術中出血量兩組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所有患者均獲得隨訪,隨訪時間15~29個月,平均24.3個月,骨折愈合時間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所有患者術后1年肩關節功能Neer評分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討論
肱骨大結節和小結節作為肩袖群肌的附著點,對維持肩關節功能非常重要。肱骨大結節骨折移位超5mm時,需手術復位固定,以防止肱骨大結節和肩峰發生撞擊;移位不足5mm時可保守治療[3~7]。目前肱骨大結節骨折傳統的手術入路是經肩關節內側三角肌、胸大肌間隙入路,該入路顯露清楚,方便骨折復位,但顯露時需切斷三角肌,軟組織損傷大,術后易發生瘢痕粘連,影響肩關節功能恢復,且因切口較大,存在損傷血管、腋神經及切口壞死的可能。本研究結果顯示,與試驗組入路比較,對照組手術切口較大,手術時間長,術中出血量增多,術后患者肩關節功能恢復差。試驗組采取肩前外側經三角肌入路,其優點是:切口小,不損傷腋神經,術中避免切斷三角肌,對肩關節外展功能影響小。
綜上所述,采用肩前外側經三角肌入路較傳統的肩關節內側三角肌、胸大肌間隙入路在手術切口長度、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及術后肩關節功能恢復方面均有明顯優勢。另外,本次研究內固定物使用的是空心螺釘,臨床上也有眾多醫生采取可吸收螺釘固定,對于內固定物的選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1]Bissell BT,Johnson RJ,Shafritz AB,et al.Epidemiology and risk factors of humerus fractures among skiers and snowboarders[J].Am J Sports Med,2008,36(10):1880-1888.
[2]曹烈虎,翁蔚宗,宋紹軍,等.微創空心釘與切開復位鋼板內固定治療肱骨大結節骨折的療效比較[J].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2013,27(4):418-422.
[3]Neer CS 2nd.Displaced proximal humeral fractures.Ⅰ.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J].J Bone Joint Surg Am,1970,52(6):1077-1089.
[4]Green A,Izzi J Jr.Isolated fractures of the greater tuberosi-ty of the proximal humerus[J].J Shoulder Elbow Surg,2003,12(6):641-649.
[5]Park TS,Choi IY,Kim YH,et al.A new sugges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minimally displaced fractures of the greater tuberosity of the proximal humerus[J].Bull Hosp Jt Dis,1997,56(3):171-176.
[6]Crowell MS,Plank RJ.Fractures of the greater tuberosity of the humerus[J].J Orthop Sports Phys Ther,2010,40(7):447.
[7]Gruson KI,Ruchelsman DE,Tejwani NC.Isolated tuberosityfractures of the proximal humeral:current concepts[J].Injury,2008,39(3):284-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