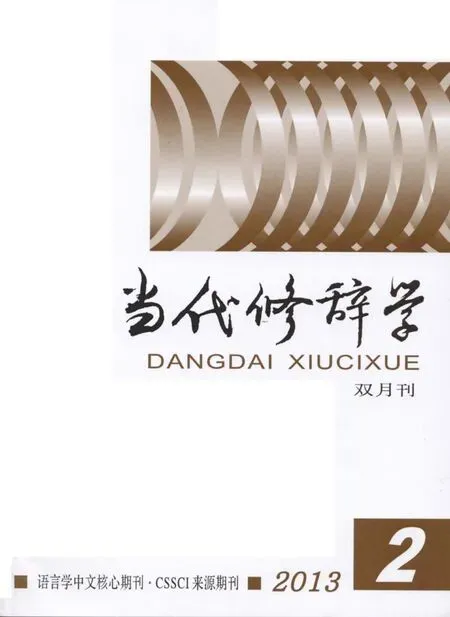“起承轉合”與西方語篇模式理論*
金春嵐
(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上海200062;華東理工大學外語學院,上海200237)
提 要 古人有豐富的關于篇章結構的論述,“起承轉合”是其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理解和把握“起承轉合”的內涵意義重大,因為它體現了古人對文章內容和形式的和諧統一的追求,也表現了中國人在文字使用過程中的智慧和藝術的修為。本文梳理了“起承轉合”的源起和內涵以及在八股文中的表現,并試圖通過對比“起承轉合”結構與英語語篇模式來挖掘二者的差異及其形成的文化背景和認知因素。
一、“起承轉合”的源起及內涵
從現存文獻看,作為詩學問題的“起承轉合”之說,學者認為“最早見于元人詩法”(蔣寅2001:72),具體說就是楊載《詩法家數》與傅若金《詩法正論》。其中,楊載《詩法家數》于“律詩要法”一段首列“起承轉合”四字,并以“破題”、“頷聯”、“頸聯”、“結句”與之對應。也有人認為“起承轉合結構說萌芽于更早的唐代試律、律賦中”(黃強2006)。盡管唐人對試律詩作法論述很少,但以“起承轉合”之說對現存唐人試律詩進行結構分析,大致可通。
就文章而言,“起承轉合”是篇章不言自明的基本結構,從《大學》篇開始,至現代漢語的許多文章都可以分析出個“起承轉合”來,如張志公(1996:135-138)認為:“‘起承轉合’四個字勾勒出各種體裁、各種內容文章的篇章結構規律,基本上符合寫文章的實際情況。”而“起承轉合”這一名稱在有據可查的文論中出現時間,大約是宋末。據元代倪士毅《作義要訣》(十萬卷樓叢書本)說,到宋末,經義的篇幅都較長,而且有固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有小講,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后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有大講,有余意,有原經,有結尾。”這繁復的格式已具八股雛形。
有學者對于幾種文體的“起承轉合”結構做過分析,如下表所示(聶仁發2009:117):此表雖有不完善之處(比如唐代試律、律賦就已經出現“起承轉合”之雛形而未收入,另外八股文不一定全部都有“起比、中比、后比、束比”結構,如“兩扇對”就是在對股內形成的“起承轉合”結構),但是基本可以看出,從宋元經義、宋試論、律詩到八股文就“起承轉合”結構經歷了穩步的發展,到八股文階段被推至極致。

表1:幾種文體的起承轉合
就“起承轉合”范疇而言,雖然可以泛化為漢語(主要是古代漢語)中各種文體(詩歌、論為主)的篇章結構理論,但是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比如曹逢甫先生就研究過非“起承轉合”結構的絕句(曹逢甫2004:9)。因此,本文以為“起承轉合”原本是詩、文寫作結構章法方面的術語,后來被廣泛應用于學詩或者學文的技法解釋。
作為詩、文寫作結構章法方面的術語,“起”是開端;“承”是承接上文加以申述;“轉”是轉折,從正面反面立論;“合”是結束全文。姜望琪先生認為“起承轉合”結構思想來源于劉勰的《文心雕龍》(姜望琪2012),有明確“起承轉合”說法的應該是元代的詩話和宋代的文話,比如元代楊載《詩法家數》在“律詩要法”一段首列“起承轉合”四字與“破題”“頷聯”“頸聯”“結句”對應,并詳細闡述如何寫作。
清乾隆初年袁若愚說:“時文講法,始能學步;詩不講法,則又安能學步乎?且起承轉合四字,原為詩家章法,時文反為借用。”(乾隆二年刊本《學詩初例》卷首) 因此,“起承轉合”大致可以理解為寫詩、文和看詩、文的基本“法式”,有助于初學者盡快掌握詩文的寫作、理解力。如果對初學不用這樣的法式或者規律而以其他“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方式講授,很難引人找到學習的竅門和方法。
此外,“起承轉合”應用于學詩或者學文的技法解釋時,是一個概括性的解釋方法,或者說是“大法”、“活法”,并非不能增減的刻板公式。古代詩文一般由“起承轉合”或“起、承、鋪、敘、過、結”幾種主干成分構成,但在具體的詩文中,成分多少,“或用其二,或用其三四,以至五六,皆可隨宜增減,有則用之,無則改之。”(陳繹曾《文說》)古代詩文家在謀篇運思時,常常于變中求不變,靈活地運用此一法則。眾多的名篇佳作在結構上大多顯示出起承轉合的基本規律。如何“起”、如何“承”、何時“轉”、何地“合”,則隨題旨表達與文風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唯其如此,則體現出這一基本章法規律的靈活多變,創意不斷。
二、八股文法中的“起承轉合”
“起承轉合”在詩法中變化無窮,文法亦然,八股文的“起承轉合”亦是如此。下面借清代著名學者李元春所編《四書文法摘要》中所述“起承轉合”之法在八股文中的應用,來看看“起承轉合”的真正內涵所在。
李元春與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賀瑞麟等人尊奉理學,通過講課授徒,培養了大批理學后進,他根據教學經驗編寫的《四書文法摘要》(以下簡稱《摘要》)可以被視作八股文作文之法的綜述。就“起承轉合”之法,他在文章中提出:“起法五:直起,陡起,引起,按題大概起,另起。承法五:承即接,有直接,有陡接,有緊接,有緩接,有遙接。轉法七:轉入題中,轉擲題外,小轉,大轉,暗轉,徑轉,疊轉。合法二:合即落,有驟落,有徐落。”單從這一本八股文文法書就可以看出“起承轉合”的變化多端了,因此深刻體會“起承轉合”之內涵,不僅可以擺脫形式上的教條,更加有助于文章閱讀和寫作。
1.“起”與“合”
“起”與“合”的重要意義凸顯了開頭和結尾在八股文中的特殊位置,應苦心經營。起法指的是文章開篇之法,可以指依照文題,直接起筆;或者用看似與文題相異的起筆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或者指以正題的反題為開頭,即從相反的意思說起,從而在正反對比中產生意義;或者指倒敘式的敘事倒裝,以結果和高潮為開頭,如同“奇句”奪目,如李漁說:“開卷之初,以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李漁1995:72)當然也可借引用的話來起筆,總之開頭須提示全篇內容,總攬全文,起到領起全篇,為全篇定基調的作用。
“合”的意思是歸結起來,照應前文。其具體操作,主要是與起相對的“結”的問題。“結”很重要,這不僅對于八股文是如此,對于其他文體也是這樣。就詩來說,姜夔《白石道人詩說》認為,“一篇全在尾句”,“多見人前面有余,后面不足;前面極工,后面草草。”對于詞,張炎《詞源》說:“末句最當留意。”林紓《春覺齋論文》也認為結尾很重要,他說:“為人重晚節,行文看結穴。”
2.“承”
“承”接之法在八股文中總的要求是自然、縝密、文氣貫通。倪士毅《作文要訣》說:“一篇之中,凡有改段接頭處,當教他轉得全不費力,而又有新體。此雖小節,亦看人手段。”因此,能否用好過接法是文章貫通的關鍵。連接時可以是下文直承前文文意而來或者下文對上文所提出的論點,或抒發的感情,敘述的人物、事件,做進一步闡述和表達,使其擴展開來,繼續下去,而不做相反的或另一方面的闡述的表達。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由開頭的“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至“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這里漁人發現桃花源是正接。反承之法也常被文人使用,其特點是下文對上文所提出的論點,敘述的人物、事件做反面闡述和表達。運用這種技法,可使詩文情節跌宕,文勢起伏變化、搖曳生姿,避免平鋪直敘、呆板平淡。
另外“遙接”亦是一法,又稱遠接、遠承,和近接相對,是一種在文意上隔段相連接的承接法。唐彪的《讀書作文譜》是一本非常有影響力的關于八股文的教學的書籍,書中說:“如一段文章雖發揮未盡而有不得不暫住之勢,若復加闡發,氣必懈馳,神必散慢矣,惟將他意插發一段,則神光如振動華膽也。發揮之后,復接前意立論,謂之遙接。”運用這種銜接方法,可使文章增加容量,收到錯綜見意、曲折生姿的藝術效果,因此常被人們用到線索復雜、思想豐富、內蘊深刻的作品中去。
3.“轉”
“轉”指八股文行文中辭意變換或者上下兩層意思出現不同。“轉”時便要注意輕重和方法了,可以由題外轉回題中,也可以從題中轉會題外。劉坡公《學詩百法·章法》解釋說:“轉者,就承筆之意,轉捩以言之也。其法有三:一,進一層轉;二,退一層轉;三,反轉。總以能與前后相呼應,活而不板者為佳。唐詩之注重轉筆,而上下一氣者,當推杜甫《春望》一首。”轉化時有輕重或者稱為大小,大轉指大幅度的跳躍轉接的方法。小轉的時候,一定用緩辭,所以也叫它或者緩轉。古人說“急脈緩受”,這便是前一段用了急辭,底下一段便緩辭去承接。大抵用轉的時候,一定是上下兩層意思不同,所以要轉。
“轉”還可分“暗轉”、“徑轉”、“疊轉”。“暗轉”指寫作時在轉折處轉得極為自然,不著痕跡的方法,八股文如此,詩詞也如此。如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說道:“作詞須知‘暗’字訣。凡暗轉,暗接、暗接、暗頓,必須有大氣真力,斡運其間。非時流小惠之筆能勝任也。駢體文亦有暗轉法,稍可通于詞。”(況周頤2006:62)暗轉比明轉更需有高超的技巧。“徑轉”和“疊轉”指轉的方式是直接一次轉還是曲折地轉換的。“徑轉”表現出直接且干凈有力而“疊轉”則強調造勢或者曲折地轉換意思。
從作文教學法來看,八股文的要求“主意要純一而貫攝,格局要整齊而變化,字句要刻畫而自然”(劉熙載《藝概·經藝概》)可以說是文章寫作的基本原則,具有普遍意義,而“起承轉合”之法則是對歷代文論、詩論中的沿襲,即所謂“帶著鐐銬跳舞”,在逼仄的空間里發揮創造力才是真諦所在。
三、“起承轉合”結構與英語語篇主張—反應模式對比
與漢語中的“起承轉合”結構的語篇功能相似,英語的語篇模式(text pattern)也是指語篇組織的宏觀結構(macro structure),指語篇中各個主要部分的組合結果。在英語教學中,我們常常借用語言學家Michael Hoey、Eugene Winter以及Michael McCarthy和Ronald Carter等對英語的語篇模式的研究,來探討英語中可能存在著許多種語篇模式。在語篇交際與互動過程中,語篇生成者根據自己的交際目的來選擇相應的語篇模式去服務其交際目的,以實現有效交際。語篇語言學家Hoey(1983)等對英語語篇的組織模式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認為英語中可能存在著許多種語篇模式,但常見的模式如:問題—解決模式、一般—特殊模式、主張—反應模式、機會—獲取模式、提問—回答模式等。正如McCarthy和Carter(2004:54)所說,“要理解一個語篇,讀者面臨的任務之一就是理解語篇不同組成成分之間的聯系。”其中,問題—解決模式一般由情景(situation)、問題(problem)、反應(response)、評價(evaluation)或結果(result)四個成分組成。一般—特殊模式又可稱作“概括—具體模式”(General-Specific Pattern),該模式的宏觀結構由三個成分組成:概括陳述、具體陳述和總結陳述。主張—反應模式又可稱為“主張一反主張模式”(Claim-Counterclaim Pattern)或“假設—真實模式”(Hypothetical-Real Pattern)。該模式的宏觀結構有叫“情景”、“主張”、“反應”等三個組成成分。機會—獲取模式的宏觀結構由情景、機會、獲取、結果組成。提問—回答模式主要組成成分是提問和回答。
有學者認為問題—解決模式與“起承轉合”相似(Yang Yuchen&Yang Zhong2010,下面簡稱楊文),特別是在話題產生或者觀點發展過程方面是一致的。本文認為如果從觀點發展過程來看,主張—反應模式與“起承轉合”更加相似。理由如下:
第一,主張—反應模式與“起承轉合”在事件,主題或者觀點的發展進程方面相似。主張—反應模式如圖1(見下頁,譯自Hoey(2001:180)筆者添加了與“起承轉合”的對應關系)。這個結構中與“起承轉合”結構從內容到形式都非常相似:就一個問題提出主張恰似“起”;對主張的確定恰似“承”;反對主張及理由恰似“轉”,而最后的修正似“合”。
第二,楊文提出,英語中的問題—解決模式可以應用于漢語,雖然“問題”部分在漢語中并不一定出現,沒有“問題”出現會導致觀點發展最終形成原因—結果模式;而“問題”部分在英語的問題—解決模式中則一定要出現。這樣的說法顯得有點不能自圓其說。首先,顯而易見的是原因—結果模式不等于問題—解決模式;其次,“一般來說,問題一解決模式的結束標志是對‘問題’提出了有效的解決方式,提供了肯定的評價(或結果)。”(胡曙中2005:157)缺乏關鍵詞“問題”的模式則很難說符合問題—解決模式的要求,否則有削足適履之嫌。

圖1:Hoey(2001:180)的主張 - 反應模式與“起承轉合”的對應

圖2:Hoey(2001:127)的問題 - 解決模式
問題—解決模式(見圖2,譯自(Hoey2001:127))比起漢語的“起承轉合”來說,似乎相差太遠,首先“轉”的概念沒有出現,另外從上文看“起”的部分可以是“問題”也可以不是“問題”,比如觀點、說法、事件、行為等都可以是“起”,而“合”與問題的“解決”更加不能說是同一個理路了,漢語篇章中的“合”往往是對“起”與“承”的總結,并非總是回答問題。
另外,Hoey(1983)等提出的英語語篇的多種組織模式,如問題—解決模式、一般—特殊模式、主張—反應模式、機會—獲取模式、提問—回答模式等,都可以在漢語篇章中找到例子來解釋它們的適用性,但是卻不能完全推斷漢語的篇章模式就是如此。
主張—反應模式與“起承轉合”的相似看來,合理的解釋大概是這樣的:
首先,語言結構本身有隱性的范疇設定,而這種范疇的設定往往與人類認識和理解世界相關聯,因此語言之間有相似結構也不是奇怪的事了。
其次,對于文章結構的組織,無論是英語的主張—反應模式還是“起承轉合”結構,都反映了分析問題時方法論上的科學性:既有詮釋和解析,也需要批判和反思,有問題的提出,也需要最后的總結,才是完備且科學的論述。
但是,除卻外在形式上的相似,主張—反應模式與“起承轉合”內在蘊含意義的差異也很明顯:主張—反應模式是英語篇章結構中的具體可操作模式,而“起承轉合”不僅是漢語篇章的具體可操作模式,也是一種篇章宏觀結構的思路。
提起英語語篇宏觀結構研究,范迪克(T.A.Van Dijk)的貢獻是非常顯著的,因為他的“宏觀結構研究的不是句列之間的線形排列的內部關系,而是研究把這些句列看成是一個整體”(徐赳赳2010:411)。因為有了整體觀的概念,才使得篇章在理論上獨立于傳統的段(范迪克稱之為“句列”)或者句群的概念。不同于英語篇章中的語義的緊密關聯(從句到段再到篇),漢語中的語篇概念雖也強調整體觀念,“起承轉合”之間有“主意”的貫通,然各部分之間的結構關系不似西方式的全文結構的龐大復雜,而是建立在有秩序的均衡交錯關系上,就如中國的古典建筑“整組建筑群體的藝術處理,如大小、高低、長短、明暗等,節奏甚為生動悅目”(劉致平1957:49)。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文章的布局需要兼有厚重與靈巧,然而以西方的概念來看,均衡交錯可能導致偏離基本意圖,或者成為邏輯性不嚴密的對象,如學者研究發現:“英語的句子與句子之間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平緩性:在正式語篇發展中,主句或是從句在前,兩者機會大致均等;在小說中,這種相對的平緩性體現得突出些:其發展以基本句為基礎,通過重復基本句而連續提供條件(次要句),并在基本句的基調上向各個方面推進。相比較而言,漢語復句組織以及復句與其他句子的連貫,則表現出更多的起伏性,因為這些復句的編碼方式大都是暫時偏離‘基本意圖’,從不同側面或角度確立敘述的出發點,這樣,言說者的基本意圖被暫時放到一邊,待原因、時間、方式、條件、讓步等提供完畢以后,再回到‘基本意圖’上,如此反復。”(彭宣維 2000:347)
英語的語篇與漢語的語篇都對整體性和連貫性有一定的要求,強調在分析問題時需要詮釋和解析,也需要批判和反思,還要有總結,才是完備且科學的論述,符合人們認識世界的客觀規律。只是從主張—反應模式與“起承轉合”的內在差異看來,漢語的篇章宏觀結構各個成分之間的均衡交錯關系是篇章秩序或者邏輯的體現,主題或顯或隱于其中,結論的陳述也常常是“起承轉”之后才能得到,在篇、章、句、字的統攝關系中是由上而下的;而英語的句與句的關系有嚴格的句法邏輯、線性推演關系,繼而成段(也有稱句列),再成章(宏觀結構),在篇、章、句的統攝關系中是由下而上進行推演發展的。
這也印證了徐盛桓(2001)所言:“我們看到了漢語語篇同英語語篇大異其趣的一個特性:不強調外顯的粘連性,語句之間的聯系更多是通過‘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來實現的,這靠的就是語篇內部語義和功能的內聚性,也可稱為語句之間的‘互參性’。”“起承轉合”所強調的在語篇內部語義和功能的“內聚性”體現在兩個方面語序和“主意”的連貫。因為語篇連貫不僅僅是語言本體的銜接機制,還更側重于讀者的認知心理、和社會文化的影響,也就是說“語言的意義系統網絡中系統及其特征的空缺或者不同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概括起來可以歸納為不同語言的系統自身的特點和社會文化系統的不同兩個方面”(張德祿2003)。漢語的語言實踐中語序是非常重要的語法特征之一,語序是不具備顯性的邏輯聯系語的漢語語篇銜接連貫重要的手段。語序可以使語篇達到意合連貫的目的,句際間語義導向及內容的相互關聯來實現意合,“起承轉合”及“主意”的貫穿則是實現這種語序的手段。相反,如果以英語語篇的“連貫”的標準來要求,漢語的篇章是很容易被闡述為“松散”、“不直接”或者“無邏輯性”。
這樣的為文之法的傳統雖很難得到當代文論的共鳴,卻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人的思維和寫作習慣,以至于兜兜轉轉之后,又有研究發現,在各種論說文結構中,“起承轉合”“是傳統形式,而且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其優點:適應性強、廣(度)深(度)兼顧、富于變化,同時又便于把握。”(尹振海、田衛平 2005:104)
四、“起承轉合”研究對篇章結構研究的意義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語言學家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1966)通過從邏輯層面和篇章結構層面分析500多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英語學習者所寫的作文,他發現學習者的寫作修辭方式不同表現出不同文化在交流模式上的不同。當然,對于他所認為的來自中國文化的英語學習者善用迂回手法(indirection)的說法雖受到許多的質疑(如王墨希、李津1993),也有學者認為他的研究揭開了對比修辭研究(the contrastive rhetoric approach)的序幕(Connor1996)。在英語教學中,對比修辭研究及對比語篇分析在兩個方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第一,在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領域,從宏觀層次上探索學習者母語對英語學習的影響,可以從對比語篇分析與對比語用分析等著手;第二,在實際英語教學中,英、漢語在修辭領域里的差異給教學帶來的有益啟發,可以應用于英語作文教學以及翻譯教學方面。
對比修辭研究的產生,來自社會學、哲學和人類學的影響。不少學者把邏輯一種文化現象,把語言與哲學聯系起來,把滲透文化精髓的語言類型和結構看作是人類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而代表了傳統文章結構理論的“起承轉合”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理解客觀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在學習英語時也不可避免地把這種母語的思想理路帶到了英語寫作中。因此,傳統的語篇宏觀結構的分析有助于語言教學者和學習者對語篇結構能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增強對不同文化背景下語篇的理解能力和應用能力。從古代漢語文論的發展史上看,形式結構的凝聚性大于變動性,以至“老譜不斷的被襲用”(魯迅語),因為文本的篇章結構,受語言文化因素的制約,在抽象層面上體現為一種以文化為特征的圖式表象。
傳統文章學、修辭學正面臨巨大的挑戰,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突破了以往寫作研究的格局,“開創了在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框架下利用‘信息加工’的概念和方法對寫作過程中語言、認知、情景的交互作用進行研究的新局面”(王松年1996:350);另外一方面,寫作傳統在語言、文學和文化中的強大存在仍然值得我們去關注,在當前寫作研究走向交叉學科的過程中,應該冷靜思考,根源于傳統,又超越傳統,如王佐良先生(1980)所說:共時之中包含著歷時,當代的語言之中存儲著過去的積累。這不僅對寫作研究、修辭對比的研究有益,而且對探索人類語言特征、人類文化乃至人類的本質也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