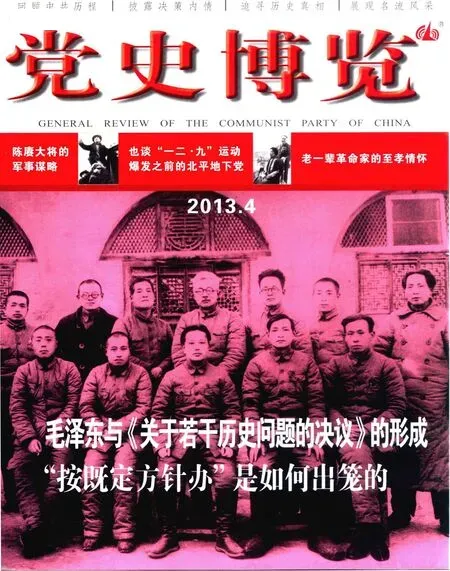也談“一二·九”運動爆發之前的北平地下黨
■ 錢承軍
自20世紀80年代始,有關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之前北平地下黨的一些情況,研究界一直是眾說紛紜,觀點迥異,難以形成一致性定論。由此,筆者結合近十年來具有代表性的幾種觀點,談談個人看法。
關于運動前北平地下黨組織的名稱
眾所周知,“一二·九”運動爆發前夕的北平地下黨組織是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但這個臨委是怎么成立的,之前的黨組織是什么情況、何種稱謂,臨委書記是誰等問題卻一直混淆不清,至今懸而未決。
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2011年1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 (以下簡稱《黨史》)第一卷上冊一書中這樣寫道:
此時,活動于北平的黨組織是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在臨時工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組織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 (簡稱 “北平學聯”)。
12月9日,在以李常青、彭濤、周小舟等組成的中共北平臨時工委領導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黃敬、宋黎等在學生中工作的共產黨員的組織和指揮下,東北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師范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學的學生擁上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
本文以下主要圍繞上述表述展開討論。
時至今日,當年“一二·九”運動發起者和組織者的回憶錄,已正式發表的主要有彭濤、周小舟、姚依林、郭明秋、谷景生等人的。
周小舟于1944年6月在延安寫的自傳材料中描述道:
楊子英 (陜西人)當時是北平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1935年4月末介紹我參加了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 (簡稱 “武衛會”)。……不久,王健 (王學明)通過楊子英與我談話,我經楊子英介紹于5月在北平入黨。
九十月間,黨市委增加了朱子貞 (冷楚),原黨市委為王健、楊子英、彭濤三人,王是書記。我是武衛會黨團負責人之一。谷峰 (谷景生)大概是社聯黨團負責人。……開會的時候,彭、谷和我堅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認為這樣能團結廣大學生群眾。王、朱堅決反對提民主要求和向國民黨要求民主自由,認為當時不是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問題,而是堅持打倒國民黨,這兩種意見相持不決。……此時楊子英已在天津,找到了省委的關系,把北平的情形報告給省委。彭、谷又推我去天津向省委報告,省委接談的姓劉,省委決定撤銷北平市委,成立北平臨時市委,以谷峰為書記,彭濤為組織,我為宣傳,并同意當時提出的口號與進行的工作,決定派人去北平整頓組織,這大概是11月20日前后的事。王、朱不服從省委的決定,由一姓梁的前往天津找省委,省委決定仍照此前決定處理。
周的回憶首次將運動前北平地下黨內在要不要開展群眾運動問題上產生的意見分歧,且雙方爭執不下又如何向河北省委報告及省委怎樣處理的情況較詳細清楚地披露出來,時間、地點和人物也交代得較清楚,《黨史》及其他已出版的一些重要黨史專著均在不同程度上以此為依據。其中,1986年2月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運動史要》,1997年9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通史》,2000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這三本書都據此認為:河北省委于1935年11月決定撤銷北平市工委,成立了北平臨委。
彭濤于1960年11月24日的一次講話中談道:
1934年時北平黨的組織已幾乎全受破壞,北平有幾個黨員,但是沒有組織。1935年初才開始恢復起來,這時和河北省委取得了聯系……與省委聯系上后,北平就成立臨時市委,成員有王學明、我、冷楚等,還有谷景生,他是共青團的負責人,市委書記是王學明。在民族武裝自衛會活動的是周小舟。姚依林、郭明秋、董毓華、邵清華、孫敬文、劉杰等也是當時進行活動的一些人。
對照彭、周二人的回憶便不難推斷,至少在1935年的六七月間,北平地下黨組織已經恢復,這個組織正是“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前身,但彭和周對該組織名稱的說法不一。彭說是“臨時市委”,而周說是“北平市委”,那誰的說法更準確呢?若從二人黨內資歷對比來看,周于1935年5月入黨時,彭已是市委領導成員之一,應該說對當時北平地下黨恢復重建前后的組織結構、名稱變更情況比周了解得更加直接和清楚。
彭濤的“臨時市委”一說得到姚依林、郭明秋的佐證。
姚依林于1979年7月回憶道:
北平市委被破壞后,當時北方局指定北平團市委暫時代替黨市委的領導工作。團市委是王學明同志負責。他當時是東北中山中學學生,大家叫他小王 (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財政部副部長)。團市委組織了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沒有正式的市委。臨委委員有哪些人我不太清楚,我知道的有王學明,還有彭濤同志。
郭明秋在1980年2月是這樣回憶的:
1935年春天,我入共青團之后,經楊彤介紹認識了曾去過察北抗日同盟軍的共產黨員彭濤、王學明等。彭濤、王學明都告訴我,他們正在恢復北平的黨組織。他們重新建立的臨時市委,是由團市委書記王學明代書記的,彭濤是宣傳部長。
彭、姚、郭三人的回憶清楚地表明,“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前身應為北平臨時工委,也即臨委,前后兩個組織在名稱上本無變化,研究界一直以來主要根據周小舟的回憶而形成前一個組織是“北平市委”的看法缺乏準確性。鑒于此,筆者認為,研究者今后再出版或發表相關專著和論文時,或以諸如“河北省委于1935年11月決定撤銷(或改組) 原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新的北平臨委”這樣的用語來表述,應該更加貼近事實。
北平臨委與“一二·九”運動前的準備工作
根據現有材料,1935年四五月間(可能還會更早一些)成立的北平臨委,由王學明任書記,楊子英和冷楚先后負責組織工作,彭濤負責宣傳工作;周小舟是“武衛會”北平市委負責人之一,谷景生是北平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盟”) 和左聯黨團書記。周、谷二人雖都不是正式臨委委員,但參加臨委召開的重要會議,亦屬決策層人物。
1935年8月,由“武衛會”北平分會發起組織了北平大中學校學生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并到北平市政府社會局立案,取得了公開合法的地位。此后,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通過聯系一批學校的愛國進步學生,發動廣大同學開展募款、募物資等一系列救災活動,產生了良好社會影響。這個公開團體的建立,不僅使得之前被國民黨搞垮了的二三十個學校的學生組織逐漸恢復元氣,又重新團結集中起來了。而且,募捐所得2000多元白洋大部分捐給山東賑災,只留下約500元備用,這筆錢即后來“一二·九”運動的經費來源之一。
1935年10月22日,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召開全體學生大會,授權學生會由哲學系研究生高明凱起草了一份給正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的電文。這份電文隨即演變成《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明確要求政府開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學生。該宣言迅速得到積極參加救災活動的清華、師大、匯文、貝滿女中、女一中等校的支持。天津的匯文中學、河北女師、法商學院、中西女子學院也簽名擁護,并以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聯名同啟的方式發送到全國各大中學校、通訊社、報刊社。這份宣言有力抨擊了國民黨政府迫害青年學生,扼殺民主自由的政策,最早刊登在1935年11月初天津的英文報紙上。“可以說,它是‘一二·九’運動爆發前的一顆信號彈。”
1935年10月賑災結束后,彭濤聯系姚依林、黃敬、周小舟、郭明秋等人,不失時機地主張將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轉化成一個學生抗日團體——北平學生聯合會,經反復醞釀商討及各方聯系,于11月18日在中國大學召開了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學生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成立大會。會議選舉郭明秋(女一中)為主席,姚依林(清華大學)為秘書長,孫敬文(鏡湖中學)為總交通,鄒魯鳳(東北大學)為總糾察,黃華(燕京大學)為交際股長。學聯機關地址設在女一中。成立北平學聯,即意味著“一二·九”運動指揮中心的建立。
北平臨委成立后不久發生的以上這三件大事,與北平臨委之間是何種關系呢?
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是由“武衛會”出面發起組織成立的,而“武衛會”相當于黨的外圍組織,臨委委員楊子英任“武衛會”北平分會書記,周小舟任宣傳部長。臨委書記王學明曾告訴郭明秋,“河北省委的意見,直接組織抗日革命團體很困難,對國民黨不宜從正面攻擊,而可以從側面攻擊它;公開的場合,可以采用灰色團體,使國民黨不認為它是革命組織”。王所說的“灰色團體”,即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之類的組織。可見,成立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并領導學生開展賑災救濟活動,黨內從上到下意見一致,并在臨委領導下進行,具體組織領導者有彭濤、周小舟、姚依林、黃敬、郭明秋等。

再看《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據當年燕大學生會領導人黃華、陳翰伯等人回憶,當時他們還不是黨員,燕大學生的抗日民主運動之所以在北平學運中處于骨干地位,有兩個原因:一是燕大是美國人辦的學校,政治環境較寬松,學生的抗日思想能較自由地抒發;二是中共《八一宣言》已秘密傳到校內,其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在學生中引起強烈共鳴。雖然這份重要宣言的產生與臨委并無直接關系,但彭濤、周小舟、姚依林等人因勢利導,決定將此作為“一二·九”運動的宣傳材料,并到印刷廠制作成傳單分發到各校,從而在運動中發揮了極大的宣傳作用。按黃華的說法,“燕大學生自治會倡議建立北平學生聯合會,得到北平黨組織的支持”。
關于臨委是否領導成立北平學聯,近年來有一種說法是:“北平學聯的成立,既不是中共北平臨委的意見,也沒有黨的組織領導,而是自發搞起來的。只有一兩個黨員參與了領導,如彭濤、姚依林。”這一說法的依據主要源于姚依林的回憶。
姚依林曾于1979年7月、1982年8月和1984年4—6月三次對“一二·九”運動作了回憶。綜合其中有關北平學聯成立情況,大致內容為: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公開活動成功后,北平臨委內部就是否成立學聯,要不要發動群眾運動,提什么樣的口號等一系列問題產生激烈爭論。以彭濤為代表的極少數一派認為,應在賑濟會的基礎上成立學聯,搞一次公開的游行示威活動,向政府要求言論、結社、集會自由,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而以王學明為代表的多數一派則不贊成搞群眾運動,堅持要在學生中公開提出打倒國民黨和擁護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口號。由于兩派意見爭執不下,王學明撒手不管,致使臨委產生分裂而開不成會,彭濤站出來說:咱們自己干吧。于是,在臨委不起作用的狀況下,經彭濤、姚依林、黃敬、郭明秋這個無名義的四人領導核心小組的研究籌備,成立了北平學聯。
實際上,參與籌備成立北平學聯的核心人物不止這四個人。據周小舟回憶,臨委產生兩派意見對立后,“以彭濤為首,我們領導幾個基礎較好的學校:清華、燕京、師大、輔仁、女一中、女二中等,仍繼續進行抗日民主自由工作。我介紹了黃敬參加了武衛會,那時黃在北大,并通過我與彭濤、谷峰見了面,我們籌備成立了全北平學生組織。”谷景生在晚年回憶這段史實時,也印證了周小舟的說法。可見,北平學聯的成立,雖然北平臨委開會沒有達成一致性意見,但并非“只有一兩個黨員參與了領導”,臨委中彭濤這一派也不是什么“極少數”。根據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當年全北平的黨員也就十個左右,參加臨委會贊成搞學聯的有彭濤、楊子英、周小舟、谷景生,反對的有王學明和冷楚,對比下來倒好像是不贊成搞學聯的是“極少數”。客觀而言,正是臨委中以彭濤為首代表了廣大愛國學生心聲,堅持正確路線的一方在籌備學聯成立過程中體現出了黨的領導作用。
姚依林在學聯成立時是個剛入黨的新黨員,對臨委的了解只是間接地聽彭濤說的,而周、谷二人則是參加臨委會議討論重大問題的決策層人物,他們對臨委成員之間的分工及配合、矛盾產生的由來及激化、上級的調查及處理等情況應比姚了解得更加直接和清楚。事隔40多年后,姚依林在1979年至1984年間作回憶時,既未看到周小舟的自傳(1987年正式發表),又沒見到谷景生寫的回憶文章(最早發表于1995年),故其說法有一定局限性。而有的研究者僅憑此就斷言學聯的成立沒有黨的組織領導,是自發搞起來的,這就難免失之偏頗了。
通過對“一二·九”運動前環環相扣的三件大事作層層剖析,我們不難看出,北平臨委在“一二·九”運動的醞釀和準備階段中,確實發揮了重要的直接或間接的發起、組織和領導作用。
“一二·九”運動前夕臨委改組情況
如前已述,1935年四五月間成立的以王學明為書記的北平臨委,由于產生嚴重意見分歧而分為勢不兩立的兩派。彭濤這一派的楊子英、周小舟先后到天津找河北省委反映情況,河北省委遂于1935年11月20日左右作出改組原北平臨時工委,成立新的北平臨委的決定,由谷景生任書記,彭濤為組織部長,周小舟為宣傳部長,同時打算派人到北平整頓組織,此為臨委第一次改組。
問題在于,當時河北省委沒有立即派人到北平來宣布這一重要決定,而是先由周小舟將此決定帶回傳達宣布,這就引起王學明這一派的質疑和不服,他們同樣也派了一個姓梁的到天津找省委反映情況。一直到運動爆發前的12月7日、8日,省委特派員李常青才到北平與臨委聯系上,調查了解,著手解決糾紛。有關事情的整個過程,且看幾位當事人的回憶。
彭濤回憶:“‘一二·九’前兩天,河北省委派人(姓李)來北平,同意在北平搞運動,并指示要抓緊時機,發動學生,把學生團結起來。”
周小舟回憶:“12月7日、8日,李常青奉省委之命來北平,先找了我,我把北平黨內的糾紛及當時工作的情況都報告了他,表示聽從省委的意見處理,這時,正是‘一二·九’運動緊急發動之時。李與王、朱、彭、谷都分別談過話,李也了解到王、朱是不服從省委意見的。為了順利解決糾紛,李決定改組臨時市委,在解決此事中,李當時未作明確的結論。我于1936年1月即另調其他工作了。”
姚依林回憶:“那個時期北方局還是河北省委,大概是省委特派員李常青,他是來跟我們聯系的。李常青同志對我們的行動采取中間態度,既不熱情支持也不反對。所以,‘一二·九’運動前兩天他就來了,他跟北平市臨委王學明、彭濤,找我和黃敬都談過,他也不表示明確態度。”
歸納以上三人的回憶,并結合現有史料,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李常青到北平與臨委取得聯系的準確時間是1935年12月7日左右,正值運動爆發前兩天,而非一些圖書和文章所言的這年的六七月或11月。
二、從李常青與彭、周二人的談話可看出,李不僅代表省委明確表態支持搞運動,而且為了順利解決糾紛,他當機立斷,決定再次改組北平臨委(即1935年11月20日左右成立的以谷景生為書記的臨委),由他自己兼任臨委書記,“直接領導北平市各黨團、青年團和黨組織的工作”。這是一個果斷、正確的決定,因為在爭執雙方誰都不服誰的情況下,無論是王學明還是谷景生都不適合再當書記了,而李常青以省委特派員的身份兼任書記,對雙方來講都可以接受。
三、李常青之所以給人留下“采取中間態度”“不明確表態”和“當時未作明確的結論”的印象,并非他無原則立場要和稀泥,而是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談話對象的身份地位不同,談話內容也不一定相同;二是采取了有利于團結大局的一種策略。事后證明,李常青整頓組織的做法不失為加強組織內部團結,集中力量搞運動的明智舉措。
四、河北省委在處理北平臨委內部糾紛的過程中,自始至終支持以彭濤為首堅持搞運動的一方,體現了“一二·九”運動發動之前中共領導機構應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