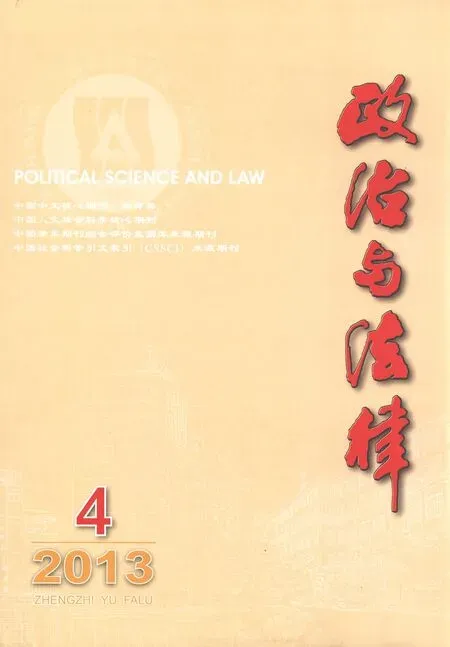論維多利亞宗教法律思想*
于 浩 曾 航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100872;西南政法大學人權教育與研究中心,重慶401120)
弗朗西斯科·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toria 1480年-1546年)為西班牙神學家、多明我會修士、薩拉曼卡學派的創始人,是十六世紀天主教歐洲極具影響力的政治理論家。他的著述涵蓋諸多領域,而對公民權利和王權的本質、教會權力以及歐洲侵略擴張的正當性等問題的論證,使其獲得崇高的學術聲譽。維多利亞是第一個提出人民權利(ius gentium)的人,因此成為奠定現代人權概念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將社會的合法主權理論進一步擴展至國際層次,并進一步認為這一層次的統治者也必須尊重并對全體成員負起責任。世界的公共利益在這一層次上要優于每個國家單獨的利益。他表示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不能用武力來正當化,而是必須以正義和法律作為依據。維多利亞也藉此提出了國際法的概念。維多利亞一生大多數時間都在薩拉曼卡大學任教,教授神學和法學,其后薩拉曼卡學派的重要人物索托(Domingo de Soto)、莫里納(Luis de Mol ina)、蘇亞雷斯(Francisco Suárez)皆受其影響甚巨。遺憾的是,國內學界對維多利亞的譯介及研究較為不足,僅兩部譯著即努斯鮑姆的《簡明國際法史》和沃格林的《政治觀念史稿(第五卷)》對維氏的思想有所涉及,而維多利亞本人的著作更無一本被翻譯出版。近年來國際上對于維多利亞的文本研究多從國際法的角度切入,而維氏作為中世紀著名的神學家,在神學方面的造詣同樣精深。故筆者將維氏的宗教思想與法律思想相結合,將“教權超然”與“政權既在”這一組概念作為維多利亞宗教法律思想的中心論點,借助《維多利亞政治著作選》,重釋中世紀末歐洲基督世界教權與政權的爭紛和妥協,希望能在梳理維多利亞宗教法律思想的同時推動國內學界對維多利亞的研究。
一、教會的起源和內涵
公元四世紀初,君士坦丁大帝頒布了著名的《米蘭敕令》,藉此基督教在羅馬獲得了合法地位,并迅速發展成為羅馬國教。同時,教會作為帝國的統治工具也由此濫觴。在傳統基督教觀念之上,教會作為“耶穌基督的身體”,由“上帝之選民”組成。從這一觀念出發,教會成為了一種神圣化的由上帝意志支配的超越世俗的共同體。而維多利亞進一步為教會賦予了抽象觀念之上的意義。
考察源流,維多利亞指出,希臘文的“教會”(ekklesia)原初乃表群集之義,隨之引申代指市民大會,進而琉善(Lucian)在其對話錄(Dialogue of Mercury and Maia)中又使用了ekklesiazo一詞作召集與會之義,隨后又出現了ekklesiates,義為召集之人;及至羅馬,即基督教出現之后,ekklesia的變體ecclesia才頻繁地在基督作家的作品中出現。1接下來,維多利亞又依據奧古斯丁的說法辨析了希臘語中ekklesia與其近義詞synagoga之間細微的差異,即后者尤指猶太人之間的群集,而前者的召集之中兼有呼喚之義而無人種之別,強調的是一種“聲音”上的召喚。然而,毋論ekklesia抑或synagoga在基督教的經文(舊約、新約)中都幾乎沒有出現過,而出現得最多的詞是以上兩者的又一次進化——congregation,我們可以稱其為圣會,這又朝純基督語境上的教會(church)邁進了一步。至此,我們已經可以厘清維多利亞從詞源上為教會的演進過程梳理出的邏輯脈絡:從單純的人的聚集到成規模的聚“會”,并在對象與方式上初步形成了特異性(ekklesia,聲音上的呼喚;synagoga,猶太人的聚集);進而人之群集又被賦予了某種目的性,并且此種目的性逐漸成為所在群體的共同意志,因而聚會的本身亦變得神圣起來(congregation);最后,群體的目的性終被塑造成了信仰,群集者、與會者皆為有信之人,是時,教會(church)便告誕生了。
維多利亞之所以要從詞源上對教會的誕生進行解讀,是因為從詞義的源流嬗變之上,可以更清楚地發現自雅典而耶路撒冷,ekklesia至church內在因素的增補與缺失,從而對教會這一抽象觀念產生總體的把握。這里,維多利亞刻意突出了教會的抽象觀念。強調教會并不單純只是“人”的集合,更為重要的是,教會是“信”的集合。這里的“信”是一種超越社會政治與國家政治維度的抽象觀念。2既然個體的“信”在某種程度上已然超越了社會與國家的政治維度,那么“信”的集合又何如呢?維多利亞將教會(亦即“信”的集合)定義為“精神權力與實體權利之間的紐帶”,3既不完全從屬于精神,又不徹底墮入到實體,這樣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再者,倘若賦予“信”的集合(共同體)以實在意涵,從此岸跨至彼岸之后又從彼岸跨回此岸,那么“上帝之國”與“塵世之國”便將不再有云泥之別。而確認教會的抽象觀念將問題引向了以下兩個相互關聯的結果。
其一,基督教會是世上存有的唯一的“信”的集合。維多利亞稱其為“信”的共同體。也就是說,“認信基督”這一抽象行為本身是建立在對基督之外的“信”的否認的基礎之上的,即否認多元宗教的正當性。
其二,有關異教徒的準則,是建立在第一條的基礎之上的。既然世上只有一個“信”的集合,即基督教會,那么也可以說,世上實際上也同樣只有一種“信”,即“唯憑基督”。所有無此種“認信”行為之人抑或放棄“唯憑基督”論斷之人皆可稱其為異教徒。“若不聽信他們,便告之教會;若是不聽信教會,便視之為可鄙的異邦人和稅吏。”(《馬太福音》18:17,這里的“聽”又對照了ekklesia意涵之中的“呼”,有了ekklesia的“呼”才會有“認信者”的“聽”以及異教徒的“不聽”)而早在公元五世紀,波西米亞人胡斯(John Hus)便歸納了異端的三種類型:買賣圣職(simony)、褻瀆上帝(blasphemy)以及變節叛教(apostasy)。4就此,維多利亞提出了四點有關異教徒的準則:(1)教會可立法對“認信者”進行甄別,并對異教徒進行審判;(2)異教徒須服從教會之訓誡;(3)浸洗乃是教會之圣禮,異教徒只有在適當時刻方可享受;(4)當牧師甚至教皇成為異教徒,在未革除教籍之前,仍視為教會成員。5
維多利亞提出異教徒準則的目的實際上是試圖構建一種基督秩序觀。維多利亞提出了兩套等級秩序,一套是天上的秩序(宇宙秩序);一套是人間的秩序(塵世秩序)。維多利亞認為,上帝最初的設想是為塵世萬物創造各自多元的價值,但最終萬物的價值都趨向了同一,即塵世秩序服從宇宙秩序的安排。6此觀點承襲了公元九世紀末大主教坎特伯雷的安瑟倫(Anselm of Canterbury)提出的真實秩序,即教會(塵世秩序)反映了上帝心意中的秩序(宇宙秩序)。
二、教權超然及法的超越價值
(一)教權的確認
維多利亞對權力的領域重新做出了區分,即分為人世領域與超自然領域,二者各自獨立,互不影響。其后薩拉曼卡學派學者大都延續了這一譜系。7由此,世俗統治者國王再無統治精神領域之權力,反之,作為耶穌基督身體的教會亦同樣不能染指人世領域之權力。8然而作為精神與世俗雙重載體的“人”,卻在這一譜系之中產生了矛盾。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與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對米蘭地區大主教的職權之爭便是一個最為典型的例證。格里高利七世提出的立場是,既然皇帝需要教皇為其加冕,那么在基督世界之中,代表世俗權威的皇帝必須要服從代表超自然權威的教會,進而革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而亨利四世則根據君權神授理論對教會做出回應,認為教皇此舉是凌駕于上帝之上,違背了律法。眾多學者將其解讀為基督世界的最高權力之爭,其實,這樣的論斷忽略了“人”的雙重載體作用。“人”到底可以具有怎樣的屬性,這個問題才應該是論爭的關鍵。如果說“人”通過恩賜而獲得神性,而這樣的神性又與其世俗的性質彼此獨立,那么基督世界的最高權力便成了一種基于“人”之上的思辨事業。
對于“人”在權力譜系之中的作用,維多利亞認為,雖然上帝權威的傳承與認知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自然的啟示或是所謂的信仰之光(the light of faith),但也不可否認“人”的內在因素所起的作用。而此種傳承與認知(追求的不僅是自然與政治上的目標,同樣也有超自然的精神上的目標)需要一種引導的權力,進而形成一種基于共同體之上的權力,即教權,因而,教權雖然有一部分是歸屬于實體法,但大部分仍歸屬于神法。9
另外,維多利亞還認為教權的形成,最初便是一個“神形結合”的過程,不僅需要信仰上帝的靈魂與智慧,還需要信仰他外化的身體上的行動。這樣的論斷具有濃厚的男權意味。“你必戀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轄你。”(《創世記》3:16)也就是說,正是由于此種原始的“管轄關系”,才產生了最初的塵世權力。因而維氏認為這樣一種最初的“管轄關系”(塵世權力)是正義的(righteously)、無罪的(innocent),因而男權是可以被神圣化的,經過長期的衍化過程,最終形成超然神圣的教權。針對“神形結合”并基于男權而產生的教權,我們可以做出兩個層面上的理路區分。
其一,教權的形成是有關善惡觀的塵世“降落”。阿奎那認為“人”的內在具有一種辨善去惡的洞見,而這樣的洞見是上帝所賦予的一種“理性啟示”(rational apocalypse)。“人”只要遵照這樣的啟示,便是獲得了一部分永恒法的指引,并完全符合自然法之原理,所思之念想,所行之諸事則必然會被認為是善的,即所謂的“善即存在”10。依據奧古斯丁的教導,存在的一切便是上帝,惡則是上帝的缺席,那么便可得出,上帝即是善,沒有上帝即是惡的結論。最根本的善為永恒世界所有,我們在塵世所看到的善是由于其“降落”,而惡是永恒世界所不具有的,我們所看到的惡本身便是起源于人間世界,是故,只有善的“降落”卻不曾有惡的“上升”。11從永恒世界到人間世界,便是善的“降落”過程,其“降落”在塵世的表現分為四個方面:(1)自我保存之本能;(2)愛慕異性,生育兒女之傾向;(3)求真祛魅之熱望;(4)形成自然共同體之需求。正是由于善在塵世的“降落”,教權才有了存在的正當性。首先,教權可以通過從上帝之處獲取的理性來引導世人避免塵世中某些情況下由于上帝的缺席所帶來的惡;其次,教權可為人類繁衍居寧傳遞福音帶來便利;再次,教權可為認信基督確立一個“一”的標準;最后,教會作為認信基督者的共同體,進一步對教權的超然性進行了確認。
其二,教權的演進導致了教會中的世界主義。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地中海沿岸各國所獨有的民族神迅速地消亡了,最初猶太人獨有的民族神成為了世界的神,教會的權柄也由此伸向世界各地。“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你們從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里,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墻……并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以弗所書》2:13-17)“所以,你們因信耶穌基督都是上帝的兒子。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了。并不分猶太人,希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里都成為一了。”(《加拉太書》3:26-28)在這一層面上,教權成為了推進福音在世界范圍內傳播的力量,而上帝又應然地成為了其唯一的主權者。這一觀點又從另一個理路上對教權的超然性進行了確認。
(二)維多利亞對法律的劃分
維氏對法律的劃分在某種程度上參照了阿奎那的法律四分論,即將法律劃分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四種類型。他將法律直接分為兩個層面:神圣的與人世的,而前者又分為自然的和實在的兩類。維多利亞認為,所有的神圣法在上帝之處是永恒的,然而卻并非在人世永恒,自然法則是起源于永恒法之中的,當神圣之法不存在,人類也可以通過自然法得救,并且神圣之法對于幼兒的重要性要更甚于成人,因為“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詩篇》51:5)
有關法律本質的問題,阿奎那認為法律是一種理性的功能,屬于我們的自然理性。而lex(法)是從l igare(約制)起源的。法只能存在于觀念或是智識之中。維多利亞就此問題參考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見解。首先維氏分析了里米尼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Rimini)的論點。格列高利引用了奧古斯丁的著述(《反福斯圖斯的摩尼教》Contra Faustum Manichaeum):“永恒法是一種理性,抑或上帝的意志。”因而,法律屬于意志的范疇,或至少是上帝的理性與意志。作為十四世紀奧古斯丁主義的代表學者,格列高利自然旗幟鮮明地反對將信(faith)與理性(reason)混為一談,同時也極力強調了人理性的局限性;而維氏引述的另一種觀點來自倫巴德(Peter Lombard)所著的《第一語錄》(SentencesⅠ),其中,倫巴德詳細區分了兩種神圣的意志:一種是上帝的真實偏好與內在意愿(uoluntas beneplaciti);另一種是第一種意志的外在表現(uoluntas signi),即所謂的“上帝之怒”,從這樣一個維度來看,法便僅僅只是意志的外在表現而不能稱其為內在的意志。維多利亞則更傾向于后者,維氏以為,意志并不能藉自然法而施行,而自然法并不是一種意志而是一種理性和啟示:“耶和華啊,求你仰起臉來,光照我們。”(《詩篇》4:6)“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馬太福音》19:21)是故,維多利亞得出結論:建議只能和理性產生關系而與意志無關,若想要稱為意志(法律行為),則必須要通過立法,并且只要是合乎法律的,則必然合乎理性,倘若不合乎法律,便必然不合乎理性。
對于法律的頒布,維多利亞專門對其進行了探討。首先,維氏認為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立法權。這一論點是基于阿奎那的共同體理論,以并非所有人都熱心于共同體事務為假設基礎。阿奎那將共同體分為了兩類,一類是非完整的共同體,另一類是完整的共同體。12在這一體系之下,前者是不具有立法權的,因為一個非完整的共同體的自行立法所指向的只能是私益,這便與阿奎那的法律“第一原則”,即立法指向共同的善好(善即當行)相違背。在立法層面上,維多利亞則進一步區分了誓言與法,其殊異在于前者不具有強制性而后者具備。譬如在圣徒日所進行的齋戒行為,維氏便認為是一種誓言而非法律,因為對于個體而言,齋戒僅僅屬于“律己”之范疇而不可“由此及彼”地自我演繹。
在維多利亞看來,一些基于自然法的精神之力是源于人類神圣的本能或行為。這同樣也是教會超然權力之基礎,作為“信”的抽象集合,惟有人擁有了某些神圣的本能即自然法上的理性,教權的超然性才可以在個體之上得到映射。然而歸根結底,世上一切精神之力皆來源于上帝,“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馬太福音》28:18)隨后上帝又再將一部分權柄交與教會。不論是引導之權力,“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希伯來書》13:17)還是赦免之權力,“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馬可福音》2:10)維氏認為“精神之力”13較之世俗權力更為完美與卓越,并且“精神之力”與世俗權力之間存在一種佑(bless)與被佑(blessed)的關系,是故“精神之力”位于世俗權力之上。對此維多利亞用了這樣一句話作結:“如若我們不想永遠陷入謬誤險惡的怪圈,便必須要正視那超然的真實存在。”14順理成章,教會亦便擁有了立法權和司法權,主教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教區的法官。
在立法問題上,維氏沿襲了阿奎那提出的“第一原則”,認為立法須指向共同的善,卻質疑人法是否能將人引向既定的善。就此,維氏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立法三原則:其一,世俗立法者(國王)之追求乃是“自然之善”,即共同體之善,精神立法者(上帝—教會)則追求“道德之善”;其二,教會之立法權獨立不受塵世權力影響,其神圣性亦不由塵世權力確認,就如同國王不可為教會立法一樣;其三,世俗立法者之目的乃是區分“循法”與“悖法”,精神立法者則是主要按照“善”與“惡”來進行劃分。
三、政權既在:宗教外衣之下的萬國法
(一)萬民法浪潮
維多利亞早年思想受人文主義、唯名主義和托馬斯主義三大流派影響最深。15然而隨后維氏發現,它們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世紀后(特別是加爾文宗教改革之后)基督世界解體為多個教會和民族君主國所面臨的困境。“帝國和教皇的代表性自然近乎消失,但西方人仍然被體驗為一個精神和文明的統一體(unit)。如果該秩序的各種制度已經喪失了它們的代表價值,災難將會刺激人們去尋求新的制度,而通過這些制度,實際延續下來的文明的實質(civi l izational substance)就能夠獲得更為充分的表達。如果我們提早使用后來的術語的話,帝國基督教時代之后就是國際主義和國際組織時代”。16是進一步踐行宗教改革還是面臨民族戰爭之虞?維多利亞是那個時代立于風口浪尖的人物。
對此,我們首先需要留意這樣一個論斷,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浪潮之中,隨著板結的基督世界共同體的瓦解,歐洲各國的民族問題第一次變成了所謂的國際問題。維多利亞在基于國際主義的語境之下提出了一個新型的概念:“一個高于單一共同體的一個超越共同體”。17此概念打破了古代與中世紀基督世界世俗國家的封閉觀念,解決在這個“超越共同體”之下的普通單一共同體之間的沖突所依靠的將不再是十字軍的堅甲利刃,而是一種國際政治模式之內的法律技術。既然基督教世界的外延已經無法覆蓋整個世界,并且隨著美洲新大陸以及東印度的殖民,一種新的“萬民法”之概念應運而生。對于這一新的“萬民法”,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為是一種獨立政治體之間的關系調整,“萬民”在此種意涵之下便衍生為了“萬國”,因而此種新型的法律概念并不是一種“人際間”的規則,而毋寧是一種“民族政體間”的準則。根據前文論及的維多利亞所建構之權力譜系,對于教會的“圣靈權威”與國王的“世俗權威”已有了確然的界分,換句話說,只要某種基于國際主義的政治體之間的世俗行為的發起者(行動者)是教會,那么此種行為便是違悖法律的;如果此種行為的發起者(行動者)是世俗統治者(國王),而教會之所為僅僅是履行授權之職,那么此種行為便是合法的。
有關基督教民族與非基督教民族之間所產生關系之合法性,維多利亞總結了三項基本原則:其一,一方進行相關的任何行為都需要一個合理的協商程序,并且毋論其是否合乎法律,此種行為首先要確定是符合良知的;其二,如若協商之結果顯示此行為不合乎法律,那么此結果必須得到尊重,并且法律將不保護藐視此協商結果之人,即使先前之行為事實上是合乎法律的;其三,一旦接受了協商之結果,認定相關行為合乎法律,那么即使事實上此行為不合乎法律,也必須保障其法律之內的權利。
隨著西歐各國對美洲擴張步伐的加快,維多利亞所提出的民族政體之間的法律原則愈加顯現出其重要的時代特征。不論是手握上帝權柄的教會,還是掌控世俗權力的國君,都亟待一種基于統治權威且復作用于民族政體之間的法律技術來消弭基督世界與非基督世界之間的精神裂縫。可以說,“隨著中世紀英雄主義和圣徒精神道德的崩潰,理性道德不光彩的一面出現了,因為缺乏強烈的精神,維多利亞不能以蔑視或聽之任之的態度來接受存在的不合理性……因此,維多利亞成為雙重意義上的背叛者:當拒絕承認戰爭是萬物之父時,他背叛了自然;當扭曲的理性為勝利者做正當性論證時,他背叛了精神”。18是故,維多利亞只有通過一種民族政體之間法律技術的影響來對這個他已然“雙重背叛”了的時代進行總體的把握。美國法學家斯柯特(James Brown Scott)在論及維多利亞所處時代境況時有言:“帝國之日已然升起,其夕照為途經新世界之唯一光亮。然而,自某一處觀,舊世界雖與之并立,卻鮮有觀照,僅當忽略羅馬法之精神時,舊世界方可重現。眾謂之為十五、六世紀之法律復興,其本質在于根源與功用,而非數個世紀之后驟然的法律復歸之熱望。”19
(二)新世界:戰爭法與基督信仰
從十六世紀開始,對于基督教世界裂解為若干主權國家之間關系的規范性研究已經開始系統化,與維多利亞同時代的幾乎每位學者都在撰寫基于民族主權國家沖突背景之下的題為《論法律、權利與正義》(De legibus and De iure iustitia)的著作。維多利亞稱其所在的那個時代正在發生“現代歷史中最為重大的事件”,并且此事件將毋庸置疑地成為“中世紀與現代世界的分水嶺”。20隨著天主教會在西歐主要國家的日漸式微,西班牙接過了保持經院哲學傳統連續性的重任,既然傳統的基督世界大廈已轟然倒塌,那么以維多利亞為首的薩拉曼卡學派就只能在此大廈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的政體之間的統一秩序,即超越個體的“共同體之共同體”。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一種對傳統基督世界封閉的國家概念的反向發展,從一種“人類身體之共同體”發展為一種“人類理性之共同體”。
而用自然法代替神法處置民族政權之間的關系,則是維氏賦予那個時代國際法體系的最為顯著的特征。21調整此類關系的主體并非代行上帝權柄的教會而是世俗的統治者國王。維氏依據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推導出遵循自然法的功效便是防止人(基督民族、非基督民族)由于權利義務的不對等而趨于分崩離析。我們并且可以將維多利亞的國際法體系理解為萬民法的自然法化,自世俗社會的開端,這樣的自然法系統便開始影響到了人間的正義問題。此處,自然法對于世俗政權的影響展開為兩個方面。
對于西班牙帝國來說,維多利亞的普遍性共同體框架僅僅是一種普遍主義的偽裝,一種來源于整個世界范圍之內的自然法所構筑的一種交互體系。其實質是在民族政權間的經濟、貿易、人際沖突等事由上獲得自然法授予之權利。
對于印第安人(野蠻人)來說,他們有同等地參與到此普遍性共同體框架之內的權利,維多利亞主要闡述了二者間平等的貿易權,如印第安人有用當地充裕的黃金白銀來向西班牙人換取當地或缺的陶瓷器具之權利,并且具有自行評估交易價值之權利。在維多利亞所建構的體系中,西班牙人與印第安人在貿易層面上具有同等的福利與權利。
顯而易見,維氏建構的以上普遍模式僅僅是針對政治體之間溫和的沖突形式,當西方政治文明與非西方政治文明最為基本的沖突根源即基督教社會與非基督教社會彼此間的對立變得尖銳起來之時,一種極端的沖突解決方式即戰爭便凸顯出來。關于戰爭,特別是基督政治體與非基督政治體之間的戰爭,維多利亞首先提出了四個原則性問題:(1)到底基督教政治體可否發動戰爭?(2)發動戰爭需要憑藉何種權力?(3)何為應然之正義戰爭?(4)在與地方進行正義戰爭之過程中可采用何種措施?22
針對第一個問題,基督教政體可否發動戰爭,一方面,依據《圣經》的指引:“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馬書》12:19)“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馬太福音》5:39)“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馬太福音》26:52)同時,路德也認為:“當魔鬼發覺它不能通過強力來戰勝某些人的時候,它會嘗試著從長遠的角度來戰勝人……為了抵擋魔鬼不斷的攻擊,我們必須忍耐,要耐心地等到魔鬼厭倦了它的把戲的那一天。”23
而維氏則從八個方面對其進行了反證。其一,他援引了奧古斯丁的說法“善待于人,知足常樂”,也就是說如果發生了戰爭,我們應遵循此指引。其二,借用阿奎那的觀點,基督徒有合法權利拔出利劍,與惡人和損害秩序之人作戰。其三,認為戰爭是符合自然法原則的:“亞伯拉罕聽見他侄兒被虜去,就率他家里生養的精練壯丁三百一十八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間,自己同仆人分隊殺敗敵人,又追至大馬士革左邊的何把,將被擄掠的一切財物奪回來。”(《創世記》14:14-16)。其四,維多利亞指出戰爭之目的不僅僅是保障財產的安全,同時也是對重大錯誤的一種懲罰與報復措施。其五,維氏提出發動戰爭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基于對敵人所造成的損害的懲罰與報復,也只有此種“懲罰”的存在,才可避免敵人卷土重來,造成第二次侵害。其六,戰爭的目的必須是維護共同體的安定與和平。其七,倘若罪孽得不到救贖,且影響到了共同的善好(縱然不可能全世界都獲得善好),那么發動戰爭便是正當的。其八,對于神圣善意的教民來說,發動正當的戰爭不僅是為了保護其人身與財產之安全,同時也是在進行一場道德的捍衛戰。24
針對第二個問題,發動戰爭需要憑藉何種權力,維多利亞從三個方面對其進行了論證:其一,根據《法律匯編》(Digest)之中“強力須由強力約制”的原則,任何人,即使是個體公民皆可發動自衛戰爭,并且自衛戰爭的目的不僅僅是保障其人身安全,同時亦保障其財產安全;其二,任何共同體皆有權力宣布及發動戰爭;25其三,依據奧古斯丁著作《反福斯圖斯的摩尼教》(Cont ra Faustum Manichaeum)中有關發動戰爭權柄之歸屬問題的論斷,國王乃是共同體所選出的代表,故被授權代表共同體發動戰爭。26
針對第三個問題,正義戰爭的原因與起源,維多利亞首先進行了一個假定:在一場戰爭之中,總有一方是正義的,同時另一方一定是非正義的。事實上維氏有關正義戰爭的論斷都是建立在這一邏輯假設的基礎之上。對此,維氏專門列出了不屬于正義戰爭起源之原因或條件,即不同的宗教信仰、帝國擴張、個人榮譽與國王之好惡不可成為正義戰爭起源之原因,正義戰爭起源必須在侵害發生之時,并非所有的侵害都可作為正義戰爭起源之原因。
針對第四個問題,對于在正義戰爭之中所采取的措施,維氏提出了五點:其一,在正義戰爭之中,個體可以為共同體的利益做出任何舉措;其二,在正義戰爭中,勝利的一方可以合法地改造失敗的一方,并且重構其價值體系;其三,在正義戰爭結束之后,勝利的一方可以合法地掠奪失敗的一方的財產以彌補其“非正義”所造成的損失;其四,在正義戰爭中,國王可以采用一切必要手段來維護共同體的安全;其五,即使在正義戰爭結束之后,兩國回到和平狀態,損害的權利得到修復,被強奪的財產物歸原主,戰勝方仍可合法地對非正義方所造成的損害進行報復。
通過解答以上四個原則性問題,維多利亞最終為自己的戰爭法體系找到三劑良藥。首先,既然國王已獲發起戰爭之權柄,那么他在獲得發起戰爭的權柄之時亦獲得了避免戰爭之天職。“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羅馬書》12:18)國王在其國家無可避免地卷入戰爭之時也要盡量保證減少戰爭所帶來的死亡。其次,一旦發起正義戰爭,國王需要保證其所發動戰爭之最終結果是指向和平而非毀滅,旨在伸張正義而非踐行殺戮。27最后,戰爭的勝利者必須保持基督徒的節制與謙遜,其身份也由“訴訟方”演變為“法官”來對戰爭進行審判,補償受損的一方,同時也讓施虐方(有罪的共同體)不至于應懲罰而毀滅。
而格勞秀斯對這三劑良藥具有清醒認識,他在《戰爭與和平法》序言中寫道:“在整個基督世界中我看到的是泛濫的制造戰爭的許可證,即使是野蠻民族,這樣的行為都應該是令人羞恥的;我同樣看到世上的人們因為微不足道的理由甚至無理由亦可拿起武器,發動戰爭,此時,神法抑或人法都被棄之如敝履,恰如一紙敕令可以讓一個瘋狂的人行無法無天之惡事。”28格勞秀斯作為維多利亞思想深遠的“繼受者”,也同樣敏銳地洞察到了戰爭法體系與教權、政權之間的沖突。
針對第一劑良藥,關于國王在操持戰爭權柄的同時承擔避免戰爭之天職,格勞秀斯在經歷了歐洲歷史上最為慘烈的三十年戰爭之后認識到不可能存在或是創設一種道德力量來禁止國家戰爭,而只能通過一種國家體系之內的行為/關系準則來限制戰爭的破壞性。而這樣的行為準則同樣是基于中世紀以來便根植于歐洲大陸基督世界的道德要求和法律規范,作為戰爭的發起者,國王不能超越這一規范;作為戰爭的終結者,國王同樣需要在這一規范之內。在這里,格勞秀斯首先就否認了“主權在民”的思想,如果說戰爭是作為一國行使主權的一種形式,那么這樣的權力是在國王手里而非民眾手里;其次,國王又不能脫離基督世界所形成的習慣和規范來單獨行使這樣的權力。
針對第二劑良藥,早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已經有了“生活的必須”和“好生活”這兩重社會目的。格勞秀斯所要帶到的最終目的也就是維多利亞所追求的結果事實上也沒有達到亞里士多德的第二重目的“好生活”,而是一種“必須”的底線,賦予戰爭在國際關系的框架內最起碼的人性,也就是法律所能保證的最基礎的人性。
針對第三劑良藥,格勞秀斯將自然法視作國際法的基礎,基于自然法,一國對于另一國所造成的超出理性范圍的損害應該予以補償,這同樣也是維多利亞認為的戰爭勝利者所應行之事。不同的是,格勞秀斯進一步區分了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有關補償問題的區別,在他看來,只有非正義的戰爭才存在補償的問題,正義戰爭則不存在補償問題。
也正是由于維多利亞開出的這三劑良藥,其戰爭法體系才不至于被冠以“毀滅政權”甚至“毀滅人類”之稱號,這也使得維氏的戰爭法體系與新教派(尤其是路德派)的勸勉產生了一絲共融之可能。民族政權在維氏的戰爭法框架之下的“既在”亦同樣是遵循“個體—共同體—個體”這一邏輯理路的。29
維多利亞有關民族政權之間關系的另一重要思想是教會法在非基督教世界中存在的合理性論證。德國法學家魏爾克爾(Car l Theodor Welcker)有言:“人道主義絕不可能從希伯來人的超自然主義產生,因為人們對這種思想的領會越認真越高超,則一神的權威和法律,對于人的一切力量和快樂以最優良和最高尚形式借以表現的人類宗教自由的抑壓也必越甚。”30維多利亞則嘗試為信仰合一的基督教在新世界的傳播與發展探尋另一條進路。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馬可福音》16:15-16)基督教在美洲大陸的傳播便是遵照這一邏輯:(1)基督徒有權利在世界范圍內傳福音;(2)非基督信仰者可認信可不認信;(3)認信者獲救恩,不認信者獲罪。維多利亞亦未跳出這一《圣經》中基督教到世界宗教的傳統邏輯。維氏認為,基督世界以外的人倘若不知基督,其所言所行并不為罪,然而一旦當福音傳至于斯,當地人知曉了上帝之存在,那么若再言觸犯上帝之論,行褻瀆神靈之事便要獲罪。32對此維氏亦從六個方面進行了論證。其一,任何政權的存在都必須經過上帝之授權,因為上帝創造萬物,除非其交與一部分權柄,否則任何人都不得進行統治。其二,“耶和華差遣我膏你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撒母耳記》15:1)“這是守望者發出的命,圣者發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予誰,或立極卑微的人執掌國權。”(《但以理書》4:17)其三,“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照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世記》1:26)故統治者乃依據上帝之形象創造,并且上帝之形象是無罪孽的,也就是統治者無罪孽。其四,罪人所犯乃是冒犯主之罪,因而順理成章地失去統治權。其五,據奧古斯丁所言,罪者甚至不配其所食之面包,更何況統治權。其六,上帝賦予人類祖先亞當、夏娃伊甸園的統治權,而后由于其罪孽又將之剝奪。
根據以上六點,得罪之人應然地失去了其塵世的統治權,也就是說,褻瀆上帝的統治者將受到自然法(萬國法)的懲治,從而失去其統治權。35同時,此項神圣事業的執行者只能是天主教廷授權的西班牙人,從而避免了新教等勢力的染指之虞。及至當地基督信徒的數量達到了一定規模,教皇便可合法地重新加冕一位新的基督徒統治者,且毋須聽取當地民眾的意愿,從而使得原統治者的統治地位自動失效。同時,在美洲新大陸上,西班牙的神圣法庭即宗教裁判所也赫然建立。教權開始插手殖民地事務,在新世界里,與政權合為一體,維多利亞的萬國法體系失效。
而沃格林將維多利亞稱作狂熱地匯集了所有能夠想的、將會證明西班牙征服之正當性觀點的“狂熱的帝國主義分子”,33實際上是有欠妥當的。維氏在其萬國法體系之中為西班牙帝國在美洲統治的合法性進行了論證,然而他是用一種含蓄的、有所限制的方式,其對于非基督教世界既在政權的權力保護,承認既在的非基督政權的合法性,以及在其戰爭法框架下對人自然權利之伸張皆對后世的國際法乃至整個國際政治體理論產生了顯著影響。
四、結語
維多利亞在研究了教會的起源和內涵之后將教會定義為信者的集合,同時這一信的集合有且只有一個,便是唯憑基督的教會。維氏受阿奎那思想影響頗深,進一步發展了他的思想,將權力兩分,分成了世俗的政權與超自然的教權。而教權雖不能染指世俗權力,卻有著自己超然的權力,便是有關宗教生活的立法權和司法權,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就是這一理論的產物。維多利亞同時作為一名神學家和法學家,依據《圣經》構建了一個基于萬民法原則的高于普通共同體的超越共同體,建立這一超越共同體的初衷是調和基督民族與非基督民族的矛盾,通過戰爭法的規范作用,并納入到一個統一的體系之中。其后通過不斷地發展與衍變,逐漸成為了我們今天所見的國際法的雛形。維多利亞跟同時代的眾多經院哲學家相比,在政權與教權的紛爭之中更為強調的是一種秩序的理性。在繼承阿奎那的法律“第一原則”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將教權的本質剝離出來——一種精神之力,同時追求精神之善。雖然在維多利亞那里,世上一切權力之根源仍來自上帝,但是作為個體,在塵世生活中所享受之權利已越來越和至高無上的上帝權柄形成了官能上的界分。
在探討基督教世界和非基督教世界中的既在政權時,維氏則是以一個法學家的睿智思維來確認各民族政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一種政治體之上的“存在即合理”論。對于基督教政權在拉丁美洲的殖民擴張,維氏依據基督教義確立了上帝子民在異邦傳福音以及衍生而來的諸多合法權利,同時又對一部分違悖自然理性和自然秩序的行為進行了聲討與規制。在維氏建立的民族政體共同體框架(即國際法體系雛形)之中,對不論是基督政權在非基督世界的既在問題,還是非基督政權其本身的既在問題都進行了基于自然法上的平衡。
事實上,有關維多利亞思想的兩大中心問題,即教權超然與政權既在的問題,在《圣經》上早有明斷:“凱撒之物當歸凱撒,神之物當歸神。”(《馬太福音》22:21)
維多利亞作為近代國際法的拓荒者,從中世紀教會思想中汲取解決新問題的知識工具,如對“萬民法”的洞見使國家概念較早期經院哲學更為清晰,甚至預見了主權理論。而其所持守的普遍人類社會并為共同法所支配的思想,成為國際法學的理論基點。因而研究維多利亞思想對于追問國際法形成的社會基礎而言,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34
注:
1 Vitoria: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47.
2參見劉小楓:《圣靈降臨的敘事》,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頁。
3 Vitoria: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50.
4 Hus:The Letters of John Hus,trans,Matthew Spinka,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2,p7.
5 Vitoria: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48-49.
6 Vitoria: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55.
7維多利亞之后的薩拉曼卡學派代表多明戈·索托(Domingo de Soto)在權力譜系上繼承了維多利亞的兩分論,并根據亞里士多德、西塞羅、伊西多爾等人的思想,將權力領域的兩分延續到法律領域,強調了法在普遍領域的作用與法在超然領域的作用。見Fernandez-Santamaria:Natural Law,Constitutional ism,Reason of State And War,Peter Lang Pub Inc,2005,p80-81。
8 Vitoria: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72-73.
9 Vitoria: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73-74,138.
10阿奎那所謂的“善”的意涵是“什么是可欲的”,而存在表明的是“是什么”,并不涉及可欲性的問題。參見[美]克拉克、吳天岳、徐向東主編:《托馬斯·阿奎那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頁。
11維多利亞認為這也是使徒給某些哲人定罪的原因,因為哲人們將永恒世界的某些組成塵世化,從而導致了惡的“上升”。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72.同樣,關于惡的“上升”,中世紀出現的一些異教作品中也可窺其一斑,有關“以賽亞的異象”,便是描述先知以賽亞在天際觀看撒旦與上帝使徒之間的戰爭,而作品中所用的形容詞為惡的(evi l),即為惡者的戰爭。如此便悖離了奧古斯丁的教導。Wakef ield,Evans edt:Heresies of the High Middle Ag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450.
12維氏在這里并未就基督徒與異教徒的立法權做出甄別,由此便產生了一個矛盾,倘若立法者所頒布的法律是一代一代傳承的,那么追根溯源法律的源頭便在摩西和先知的訓誡之中,然而對于異教徒而言,是不能了解到摩西和先知的話的,那么異教徒的法律從何而來?對此,圣約翰·克里索斯托姆(St.John Chrysostom)做出了解釋,他認為,法律是上帝從一開始就灌注在人的理性之中的,即自然法,而非由摩西或是先知所“傳達”的。見Stanley Ber tke:“The Possibi lity of Invincible Ignorance of the Nature Law”,The Cathol 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Studies in Sacred Theology,Vol55,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41,p8。而艾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則進一步指出這樣一種“理性灌輸”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上帝降臨西奈山這一事件并不是人類法律從無到有的“分水嶺”,其原因在于,“摩西十誡”中的每一條誡命都可以在上帝降臨西奈山這一事件之前找到源頭,因而,人類立法這一歷史事件也同樣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見Alan M.Dershowwitz:The Genesis of Justice,Warner Adul t,2001,p215-216。
13見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82-83。
14 Ramón Hernández:“The International ization of Francisco de Vitoria and Domingo de Soto”,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15,Issue4,1991,p1042.
15在人文主義上,維多利亞受鹿特丹的伊拉茲馬斯(Erasmus of Rot terdam)影響最深,同時還與客居巴黎的西班牙人文主義學者比維斯(Luis de Vives)建立了友好的關系;在唯名主義上,維多利亞最常提及的是瓦倫西亞的唯名主義者塞拉亞(Juan de Celaya),同時也涉及阿梅恩(Jacob Almain)、梅杰(John Major)等同時代學者;在托馬斯主義上,維多利亞稱自己有兩位最為欽佩的導師,其一是費納里奧(Juan Fenario),其二是布魯瑟蘭斯(Peter Bruselense)。Ramón Hernández:“The International ization of Francisco de Vitoria and Domingo de Soto”,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15,Issue4,1991,p1035-1036.
16[美]沃格林:《政治觀念史稿(第5卷):宗教與現代性的興起》,霍偉岸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頁。
17 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53.
18[美]沃格林:《政治觀念史稿(第5卷):宗教與現代性的興起》,霍偉岸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頁。
19 James Brown Scott:The Spanish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Law:Francisco de Vitoria and His Law of Nations,Lawbook Exchange Ltd,2000,p7.
20此觀點是維多利亞在薩拉曼卡大學任教期間的一次講演中提出的,維氏認為,及至當時,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已然面臨了深重的危機,而這一歷史事件對于應對此危機是“有益的,適時的”。并且維氏將此歷史事件看作是國際法的起源。見James Brown Scot t:The Cathol ic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Francisco de Vitoria,Founder of Modern Law of Nations,Lawbook Exchange Ltd,2007,p63-64。
21維多利亞提出的用自然法代替神法作為國際法調整政體之間關系基礎的理論遭到了后世眾多思想家的反對,霍布斯(Thomas Hobbes),澤茨(Richard Zouche)以及瑞切(Samuel Rachel)等提出了用人法代替自然法成為國際法基礎的觀點,其認為,萬國法(Law of Nations)乃萬國間法(Law among Nations),由眾多習慣與條約構成,而非基于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自然理性。見Harold Hongju Koh:“Why Do Nations Obey International Law”,The Yale Law Journal,Vol.106,1996-1997,p2608。
22見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95。
23[德]路德:《〈加拉太書〉注釋》,李漫波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07頁。24斯柯特(James Brown Scott)對于維氏提出的“懲罰與報復”從現代國際法的角度提出了兩個延展性的問題:其一,與“履行職責”(due di ligence)與違悖正義(denial of justice)之關系;其二,國家人格化的問題,斯柯特認為維多利亞的“懲罰與報復”理論使得國家具有了人格化的“恐懼”,使得其在做出了錯誤的舉動之后會懼怕隨著而來的“懲罰與報復”。見James Brown Scott:The Cathol ic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The Lawbook Exchange,Ltd,2007,p33-34。
25 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00.
26 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01.
27參見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15-317.
28 Hugo Grotius:The Law of War and Peace,in Peace Projects of 17th Century,1972,Para.
29維多利亞之后美國的一些實證主義法學家如肯特(James Kent)、維頓(Henry Wheaton)等就維多利亞的“個體—共同體—個體”的邏輯理路進行了修正,他們認為國際法(戰爭法)特別是在美國是受到普通法的影響最重,即從個體的習慣到共同體的習慣,即“個體—共同體”的邏輯,與奧斯丁(Jonh Austin)所提出的政權之間的“道德制裁”(moral sanctions)、“普遍敵意”(general hosti lity)、“強力受制”(violate received)等概念有著一定的契合,而沒有像維氏一樣,最終將政治體沖突之結果又復歸到個體(君主)的身上。見Harold Hongju Koh:“Why Do Nations Obey International Law”,The Yale Law Journal,Vol.106,1996-1997,p2608-2610。
30[德]施特勞斯:《耶穌傳》(第一卷),吳永泉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56頁。
31 Vitoria:Vitoria Pol 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40.
32此處維氏對剝奪得罪之人統治權的法律進行了巧妙的處理,維氏將諸冒犯上帝者之因由歸結為缺乏統一規范所導致的對上帝的“不適”(inappl icable),于是需要一個普遍性的規范即萬國法(jus gentium)來規誡懲治諸得罪之人。這樣,便巧妙地規避了神法對于世俗權力之影響,從而教權仍可位居幕后窺伺政權之爭而不必擔心破壞其超然性。見Antony Anghie:“Francisco de Vitoria and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Internation al Law”,Social Legal Studies,1996,5,p328。
33參見[美]沃格林:《政治觀念史稿(第5卷):宗教與現代性的興起》,霍偉岸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頁。
34參見[美]努斯鮑姆:《簡明國際法史》,張小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8-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