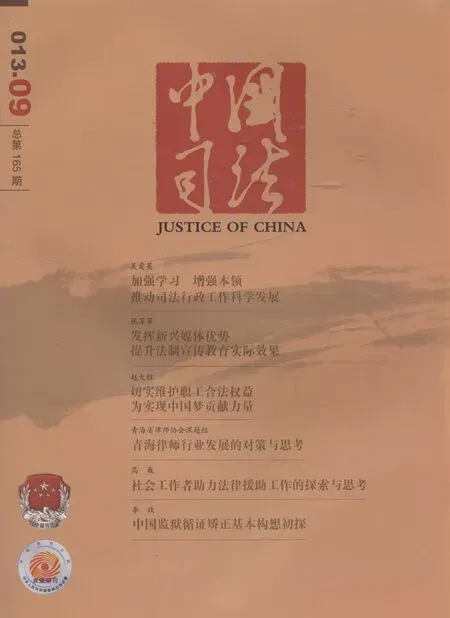律師緣何 “死磕”?
■冀祥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方志出版社社長、總編輯)
律師緣何 “死磕”?
■冀祥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方志出版社社長、總編輯)
在我國,律師界素有“技術派” (憑業務水平執業)和“藝術派”(憑社交關系執業)之分。近期,又出現了第三派律師—— “死磕派”,即律師在辦理案件過程中,拒絕與公安司法機關合作,用“死磕”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方式代理或者辯護案件。在職業法曹中,律師既沒有官帽,又沒有警械,也不吃“皇糧”,只有一張“三寸不爛之舌”,緣何要“死磕”公權力機關和有關人員?這些律師是逼上梁山?還是嘩眾取寵?在全面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之當下,如何看待“死磕”現象?“死磕”能否磕出一個法治中國?
在筆者看來,律師“死磕”現象是中國司法制度轉型時期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文明及法治建設現實碰撞交織的一種綜合反應。
首先,從傳統法律文化層面上看,一方面, “恥訟”、“厭訟”一直是中國古代傳統訴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是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中人們對于訴訟的一種主流觀念。封建統治者信奉“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非訟”是社會的主流追求,“訟則終兇”是民眾的一種較普遍的心態。在這樣的一種文化氛圍下,律師即“訟師”,多不為社會所接受,他們常常被稱為“訟棍”,被認為是“挑詞架訟、搬弄是非”之徒,是為了謀取私利而“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是非無度”的自私之人。律師的社會地位較低,對于維護當事人的權益作用較小,有的律師甚至連生存之地都難保。注重個人權利保護、追求民主、倡導平等、保護私權等訴訟文化在我國的傳播,特別是保障人權,弘揚公平正義的法治理念的不斷深入,盡管使得律師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律師的生存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中國律師至今仍然戴著“富而不貴”的帽子。
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的審判,一直是由代表統治階級、地位高高在上的判官來掌控裁決大權的,而且地方官常以百姓的“父母官”自稱,也就是說地方官審判百姓的案件就像父母處理子女間的糾紛一樣,是可以搞“一言堂”而不允許外人插手的。對抗制的模式進入中國的訴訟制度中,用了幾千年的時間,至今還有機體不適應的排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公安司法機關又怎么容得下犯罪嫌疑人的代言人——律師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指手畫腳呢?如此,一方要對公安司法人員辦的案件“挑刺”,一方則橫看豎看律師不順眼,出現律師的“死磕”也就不足為奇。
其次,從現代法治文明層面上說,當今中國,無論是政界、學界或是實務界,到處活躍著律師的身影。雖然律師的處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還有許多民眾和司法人員、政府工作人員依然對律師持有較多的偏見,部分律師的思想上也依然有傳統訴訟文化的印跡。他們崇尚公平正義,但始終對中國的司法體制十分不滿,橫看豎看都覺得司法腐敗大行其道;他們呼吁權利保障,但總是對司法程序充滿懷疑,覺得公安司法人員總是有意刁難他們;他們追求社會地位,但又一直懷有自卑感,覺得公安司法人員總是高其一等,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加之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典型的人情社會,人們解決爭端必先考慮一個“情”字,其次是“禮”,再是“理”,最后才是“法”,使得這些律師矛盾的心理更加激烈,導致其對司法機關不信任,與控審雙方的溝通越來越困難,誤解也就會越來越多,律師“死磕”公安司法人員也就成為必然。
再次,從法治建設現實層面上講,雖然中國的法律制度在不斷的進步,被追訴人的權利得到保障的越來越多,律師執業環境也越來越好,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這種不足既表現在立法上,也表現在司法上。例如,法律規定律師有會見權,但是有關部門就是不讓律師會見,律師奈何?法律規定律師有查閱、復制、摘抄案卷的權利,但是有關部門就是不讓律師閱卷,律師能奈何?法律規定在一些訴訟環節應當聽取律師的意見,但是有關部門就是不征求律師的意見,律師又奈何?辦案人員隨意限制甚至剝奪律師的調查取證權、舉證權、質證權,不理睬律師的調取證據申請權等,律師又能奈何?有哪個律師不希望順順利利地辦理案件?有哪個律師不愿意與公安司法人員融洽相處、彼此尊重、相互支持?有哪個律師愿意“拉下臉”、冒著風險與公安司法人員“死磕”?但是,如果律師在執業中處處碰壁,常常被難,又投訴無果,走投無路,那么,就會不在“被欺負”中忍受,就在“被欺負”中“死磕”。
以上分析中,似乎在說律師“死磕”是“逼上梁山”的無奈之舉,但是,我們也應當清楚地看到,有的律師“死磕”卻是在嘩眾取寵,甚至是以“死磕”來掩飾自己知識與能力的不足。這一種“死磕派”律師,早已將當事人的利益置之度外,把自己扮作“正義”的化身,而公安司法機關就是天大的敵人,將一場官司當成了“正義”與“邪惡”的較量。該種“死磕派”律師慣用的方法就是通過網絡、博客、微博、微信等“爆料”、 “揭露”公安司法機關的“黑暗”,發泄對公安司法人員的不滿,博取網民的同情,呼吁民眾的支持,贏得案件的勝算或者博得當事人對自己“無能”的諒解。
不可否認,有些“死磕派”律師初衷是好的,他們或許確實就是想犧牲自己,“死磕”對手,以求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進而維護司法公正,推動中國的法治發展。但是,當律師癡迷于“死磕”時,是否就沒有一點“個人炒作”或著“英雄主義”的嫌疑呢?當看到成千上萬的“粉絲”對自己的“死磕”行為“叫好”、把自己奉為“正義的化身”時,是否又有那么一點點的虛榮心作祟,讓自己無法“停手”呢?
律師是當事人合法權利的捍衛者,適當地與公安司法機關“較真”是必要的。但是,當“較真”發展成“死磕”時,律師的職業發展道路便朝著一種扭曲的方向發展了。如果不加控制,“正義的使者”很有可能就變成了“墮落的天使”。“死磕”只能是律師無奈之下的“可以有”,但不應當是律師與法律職業共同體相關人員的一種常態關系。應當清楚地認識到,“死磕”是控辯關系、審辯關系的一種扭曲,是一種不正常的訴訟狀態,是現代司法制度異化和法治文明的悲哀。
如果說,在對抗制的訴訟模式之下,律師與控方“死磕”尚有其合理性與正當性解釋,但是,律師與作為中立者的法官“死磕”,卻是中國司法制度不應該有的一個“特色”。
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在擴張辯護權的同時,引入了對抗制。在一些地方,控方對指控風險的防范與忌憚帶來了辯護風險的增加,立法變動追求的控辯之間應有的理性對抗異化為司法實踐中的非理性對抗。控方以會見、閱卷的強權優勢限制律師,以律師偽證罪“打壓”律師,律師則“死磕”公訴人。正因為如此,辯護制度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成為了《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導火索。根據筆者的觀察,在律師“死磕”公訴人的時候,以及圍繞著《刑事訴訟法》再修改中辯護制度的完善,相當一部分法官、特別是學者型法官是與律師的立場基本一致的。
可是,為什么后來又出現了律師不“磕”公訴人而“磕”法官了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近年來,有不少的法院和法官,對律師尊重與協商不足,防范與冷硬有余,甚至在制度上制造了一些不利于雙方溝通的隔閡,導致交流不暢,乃至相互猜疑,日積月累,出現“死磕”就不是意外了。
第二,律師與法官同為“法曹人員”,盡管有著共同的教育背景、知識基礎及法律思維,盡管有著共同的維護法律尊嚴和社會正義的價值追求,但是,律師所追求的一方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與法官整體評判案件時對法律正義的理解,還是有所不同、甚至沖突的。對此,一些思維與行為極端的律師就有可能試圖用“死磕”的方式求得己利。
第三,盡管世界刑事訴訟的第一次革命行政權與司法權的分離和第二次革命審判權與公訴權的分離已經在中國司法制度的建設層面完成,但是,在法律實踐層面,行政權對司法權的干預、檢察權對審判權的監督以及審判權對公訴權的“本是同根生”的關照,嚴重影響了法院審判權行使的獨立以及法官的中立。應該中立的裁判者站到了控方的陣營一邊,就難怪作為辯方的律師的“死磕”了。
律師用“死磕”的方式辦案也許能夠嘗到一兩次“勝利”的甜頭,但是這對律師成長卻有著十分不利的影響,也有違世界刑事訴訟的發展趨勢。在世界范圍內,以控辯合作為主、對抗為輔的刑事訴訟第四次革命已經到來,尤其是在法治中國、平安中國和和諧社會的構建背景下,律師應當有更多的責任擔當。“死磕”作為一種司法亂象,是中國律師的悲哀,是中國司法制度的悲哀。
當然,對于律師“死磕”的現象出現,也沒有必要大驚小怪。雖說律師“死磕”是其與公安司法機關矛盾升級的一個結果亂象,但是律師“死磕”也著實暴露出了我們制度設計與制度運行中的若干不足。“死磕”或許能讓我們看到法治中國建設中一些亂象之下更深層次的問題。然而,我們必須清醒:法治中國建成是多元合力的結果,“死磕”“磕”不出法治中國。
(責任編輯 張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