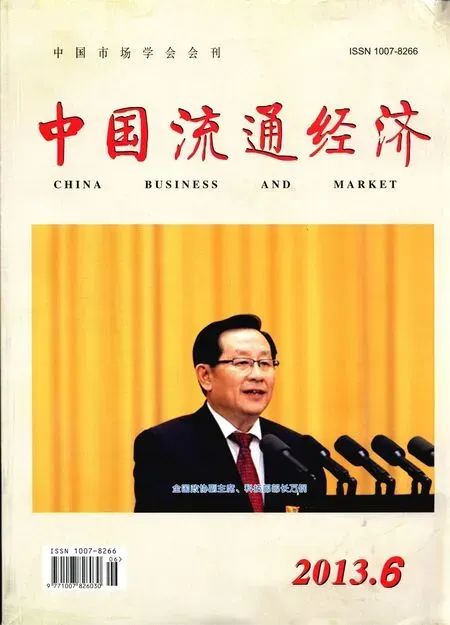社會資本理論及其發展脈絡
曹 永 輝
(1.河南科技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河南 新鄉453003;2.浙江大學管理學院, 浙江 杭州310058)
最近幾年來,社會資本理論成為研究的熱點,因為通過社會資本的視角,可以對經濟學、社會學以及管理學中的許多現象和理論進行分析和研究。社會資本的理論已經對個人、組織以及社會進行了各種層次的分析,其中針對社會發展的具體領域已經有了突破性的研究。社會資本在經濟學方面,突破傳統的經濟發展視角,通過社會的規范來研究其對經濟的推動以及阻礙作用。同時,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觸角已經深入管理領域,給破解管理領域中的難題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角度。
一、社會資本理論的社會學來源
從字面看,社會資本是“社會”和“資本”兩個詞語的組合體,因此,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自然就是其最基本的一個來源。大多數學者認為,雅各布斯(Jacobs)是最早對社會資本進行研究的,后來許多學者在其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和完善。波特斯(Portes)[1]就曾在其論文中提到,對社會資本概念第一次進行系統描述的是布迪厄(Bourdieu),他主要是在研究不同形式的資本轉化中,對社會資本進行了詳細研究。布迪厄是法國的社會學家,在20世紀80 年代,他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社會資本隨筆》,正式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并進行了界定:實際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與擁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識和認可的關系網絡有關。從布迪厄提出的概念可以看出,社會資本最緊要的一個詞語就是“聯系”(Connections),正是因為有了彼此的聯系,人們之間才擁有了社會義務及其賦予的資本。在文章中,布迪厄對社會資本的構成進行了分析,認為社會資本由兩部分組成:第一是社會關系本身,它可以使社會中的個體獲得群體所擁有的資源;第二是所擁有的這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同時,他在研究中提到,個體不斷增加的收益是通過參與群體活動獲得的,同時為了獲得和創造這種資源,個體會對社會能力進行策劃與構建。社會網絡必須通過投資于社會群體關系的制度化戰略進行建構,它不是自然產生的,這種建構將會給個體本身帶來其他收益。[2]
布迪厄分析了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等各種形式的轉化,并認為社會中的個體通過社會資本能夠獲得經濟資源,這些經濟資源包括投機方法、補助性貸款以及市場的保護等等。另外,行為主體通過與擁有知識的專家交往,可以提升其知識資本以及文化資本等。最后,通過社會網絡可以與網絡中的機構形成密切的關系,建立相應的關系網絡。總之,社會資本的積累主要依靠網絡中的行為主體擁有的資本數量和質量,依賴于其關系網絡的規模以及主動性。布迪厄在理論上進行了系統和清晰的分析,是將社會資本的概念與理論引入社會學語境中的優秀學者之一,但因為其是法國學者,發表論文所用的主要是法文,影響了其理論的傳播和關注度。
在推動社會資本理論發展的過程中,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和林南(Lin Nan)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其中林南主要是研究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源之間的關系,在他的論述中,沒有使用社會資本這樣的詞匯,但提出的社會資源與社會資本的含義基本相同。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3]在1973 年則提出了“弱關系”的概念,并進行了深入分析,他在研究個人求職問題時引入這一概念,認為求職者不一定要通過強關系去獲得與自己匹配的工作,而是通過弱關系。這種“弱關系理論”引起了很多學者的共鳴。在1985 年,他又研究了“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和問題。[4]《社會結構與經濟行動:嵌入性問題》這篇文章發表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上,他提出一種觀點,即經濟生活不是獨立存在的,是在社會之網中嵌入的。這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學者科爾曼(Coleman)的贊揚。林南在格蘭諾維特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社會資本可以獲得資源,這些資源可以讓個人得到更多的益處,以滿足自己的發展需要,但是社會資本必須嵌入網絡社會中才能獲得這些資源。他在研究個體擁有這些資源的時候,分別從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方面予以論述,認為有三個因素影響資源的獲得。第一是異質性,也就是個體在社會網絡中與其他個體相比具有與眾不同的特點和資源;第二是網絡成員的資源擁有量,也就是網絡成員在網絡社會中的地位;第三是關系連接強度,也就是個體與網絡成員之間的聯系頻率及交往的深入程度。同時,林南又基于格蘭諾維特的“弱關系”理論,認為在社會結構中,社會是分層式的,如果個體進行工具性行動時,他通過“弱關系”將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這也是他發展和創新的一個方面。為了對社會資本的指標進行度量,在2001 年,他建立了社會資本指標體系,并對社會資本進行了理論建模。
上述主要是針對個體進行的研究,將社會資本理論的運用擴展到宏觀層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帕特南(Putnam)。在20 世紀90 年代初期,他運用調研的方法對社會資本在政府中的運用進行了研究,他和同事對意大利政府進行了長達20 年的跟蹤調查和對比分析,提出社會資本在地區之間具有差異性,這些差異是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企業存在差異的根本原因,這些觀點在其專著《讓民主政治運轉起來》中有詳細論述。[5]然后,他又對人力資本、物質資本以及社會資本三者進行了對比分析,認為社會資本的基本特征是基于社會組織提出的,比如信任、規范以及相應的網絡。這些基本特征如果能夠在社會中體現出來,將能夠提高社會效率,因為人力資本以及物質資本可以通過社會資本予以提高。在另外的論文以及論著中,帕特南[6]認為,社會資本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有推進作用,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在1995 年,帕特南[7]提出社會資本與其他資本不同,社會資本不是一種私有財產,它常常是其他社會活動的副產品。如果一個社會是信任和互惠的,將使得社會更加和諧,因為信任、規范和網絡對于社會的發展具有潤滑作用,且具有積累和強化的效應。這些觀點引起了世界銀行的高度關注,并被一些政策制定者所采用。這也大大拓展了社會資本研究的視角。
二、社會資本理論的經濟學來源
經濟學思想對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很多經濟學家在對經濟理論研究中運用了社會資本的概念,比較典型的學者有勞里(Loury)、科爾曼(Coleman)等。1977 年,勞里[8]論證了社會資源和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提出了社會資源對人力資本具有重要影響的觀點。在論證中,他使用了社會資本的概念,認為社會資本是存在于家庭或者社會組織中的重要資源之一,對家庭成員尤其是兒童的社會化發展、人力資源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他分析了種族之間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并對新古典理論進行了批判,批評該理論只是過于重視人力資本的作用,永遠不能降低或者消滅種族不平等,提出只有從政策上規定機會平等并對雇主對種族的歧視現象進行根治,才能夠促成一個平等的社會。勞里用黑人作為例子,說黑人由于不具有平等的教育機會、缺乏物質資源,因此缺少市場信息和工作機會,也就從根本上喪失了與勞動力就業市場的關系,缺乏社會網絡資源獲得途徑。在勞里的論述中,他借鑒布迪厄關于社會資本理論分析了經濟學的問題,并得到了具有一定意義的結論,但是,勞里沒有對社會資本的理論進行系統的展開論述。
另外一個具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是科爾曼,他研究了勞里對社會資本理論在經濟學中的分析以及相應的結論,并在社會化發展過程中對社會資本的影響作用進行了研究。在1988年,科爾曼[9]主要從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關系出發,研究了社會資本對人力資本的作用。在研究中,他從功能的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了定義,認為“社會資本就是人們為了共同的目的在集體和組織中一起工作的能力,它是由具有兩種特征的多種不同實體構成的,這些實體由社會結構的某個方面組成,并促進了處于該結構中個體的某些行動”。該文發表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上,具有重要影響。他對社會資本的定義主要借鑒了勞里、格蘭諾維特和林南的理論,從社會結構角度對社會資本的概念進行了論述。他提出了一出生就擁有的三種資本和五種社會資本的形式。其中,作為自然人,與生俱來具有三種資本,這是誰都具有的資本形式。第一,由于遺傳從而具有的人力資本,這是由于遺傳因素造成的,因此每個人具有的人力資本是有所差異的。第二,物質資本,這也是生下來就具有的不同資本,比如擁有的貨幣、擁有的土地等。由于每個人出生的背景不一樣,因此具有的物質資本形式就不一樣。第三,社會資本,這是由所處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由于社會資本是擁有社會資源的財產,因此它必須存在于社會網絡關系中。社會資本是一個高階概念,擁有不同的形式。科爾曼論述了社會資本的五種形式。一是義務與期望;二是信息網絡;三是規范和懲罰;四是權威關系;五是社會組織。在第一種形式中,他提出個體為他人服務時確認別人也會對自己目前或者未來進行義務回報,如果這種形式成立,個體就擁有社會資本,他對這種形式進行了隱喻,比喻成“義務賒欠單”;在第二種形式中,個體可以通過社會網絡獲得有益的社會信息,這種信息可以給個體帶來就業或者其他方面的收益,如果這種社會關系存在,個體就擁有社會資本;在第三種形式中,他論述了規范和懲罰的關系,認為規范可以通過有效的懲罰解決問題;在第四種形式中,因為權威可以影響他人,從而為解決網絡中個體產生的矛盾和問題提供幫助,尤其是在解決共同性問題時發揮重要作用;第五種形式就是通過有意創建的社會組織從而擁有社會資本。在此基礎上,科爾曼于1990 年出版了專著,即《社會理論的基礎》,他運用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將社會資本概念進行了擴展,使得該定義的研究觸角涉及到水平型關系和垂直型關系。對于水平型關系的聯盟以前學者多有論述,但是對于垂直型實體聯盟的則相對較少。科爾曼從中觀層次對社會資本進行考量,突破了微觀層次研究社會資本的范疇。
科爾曼從經濟學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了系統的論述,但是有學者認為其提到的概念諸如社會資本擁有者、社會資本的源泉等經常被混用,因此對以后的研究不利,需要從根本上界定社會資本的起源,也需要對社會資本的性質進行全面研究。波特斯就是這種觀點的支持者。波特斯比較認可格蘭諾維特的觀點,尤其是對嵌入性理論推崇有加。格蘭諾維特借鑒嵌入性理論,對社會資本進行了重新定義,即“個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身份在網絡中或者在更寬泛的社會結構中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個人固有的,而是個人與他人關系中包含著的一種資產。社會資本是嵌入(Embeddedness)的結果”。[10]同時,在對嵌入性的研究中,他將其分為兩種形式:結構性嵌入和關系性嵌入。其中關系性嵌入和結構性嵌入出現的時期是不同的,一般來說,關系性嵌入建立的基礎是社會網絡中雙方對于互惠的期望,當雙方能夠嵌入成為網絡的一部分時(這時候的嵌入性稱為結構性嵌入),信任就會增加,同時各種約束因素也會被社會網絡強制推行,從而增加更多的有利于雙方發展的特征。為了對科爾曼的資本形式進行更為細致的分析,他對社會資本兩種形式進行了區分,即“價值內向投射”和“有限團結”。其中“價值內向投射”是指在社會網絡中,由于價值的積累效應可以使得其在網絡中進行內化,從而形成一個社會聯系價值的氛圍和道德,從而推動個體能夠在與他人聯系時,對方由于價值使然而可以將資源轉讓;“有限團結”是指能夠認同網絡集團內部的目標和價值觀,從而推動個體建立社會關系的時候可以考慮資源的轉讓。波特斯主要借鑒了“嵌入”理論,分析了個體社會關系特征的不同,并對社會資本結構化的動因進行了區分。[11]
1990 年以后,社會資本的概念成為熱門詞匯,并被國際組織包括政府組織和贏利機構所采用,在國際組織的文獻中,社會資本出現的頻率也非常高,這充分說明了社會資本的受關注度。在一些學者的研究中,從經濟學視角研究社會資本,分析社會資本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主流。這些學者包括埃文斯、方丹和福山(Evans、Fountain & Fukuyama)等,他們從宏觀的經濟政策、中觀的制度以及創新的視角運用了社會資本理論,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1996 年,學者埃文斯(Evans)[12]基于發展經濟學的視角,研究了社會資本的內涵,提出社會資本的核心是規范和網絡,只有兩者俱備,才能稱得上是具有意義的社會資本。同時,埃文斯提出社會資本推動了市場交易制度完善,提高了市場的效率,而當代的發展理論過分重視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視角比較狹窄,沒有充分重視宏觀制度的功能,因此從社會資本的角度研究制度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帕特南(Putnam)等當代理論家也研究了社會資本中的關系,并把基本關系具體化為具有潛在價值的經濟資產。另外一個學者方丹(Fountain)研究了社會資本和科技創新的關系,提出社會資本推動了科技創新發展,并對美國聯邦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議。他和阿特金森撰寫了論文《創新、社會資本與新經濟——美國聯邦政府出臺新政策支持合作研究》,并提出社會資本是組織網絡能夠收益的庫存。比如,公司和自己的上下游組織建立關系或聯邦政府制定政策促進企業的相互信任等,都能使創新順利進行,從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他的建議和思想得到了聯邦政府的認同。學者福山(Fukuyama)在1995 年連續撰文,論述社會資本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以及社會信任的影響,提出在進行經濟發展分析時,除了對傳統的資本(如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以及資源進行分析,還要充分考慮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具有比傳統資本更高的價值和收益,因為社會資本可以增加社會網絡中人們之間的信任關系,使得社會更加具有信任度,這就具備了進行創新的基本條件。社會網絡中的信任增加,不但能夠為創新提供基本條件,同時能夠使企業規模快速擴大從而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使得小型企業加入該網絡中,并通過信息化手段增進企業之間的聯系。[13]、[14]
三、社會資本的定義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有的學者從管理學視角分析社會資本,有的學者則從經濟學范疇研究社會資本,這也就說明了社會資本的概念是具有爭議性的,但其共同的觀點就是社會資本是一種新的資本形式,是區別于傳統資本的概念。但是,對社會資本研究的不同視角,使得給出的定義具有明顯差異。第一,在論述中,對社會資本的本質研究視角不同,社會資本的作用以及來源也存在較大差異;第二,對社會資本關注的焦點論述不同,其中包括個體之間的關系、集團內部的關系以及個人與集團的關系等三個方面。因此對社會資本定義的時候也包含了三個方面:關注外部關系、內部關系以及內外部關系。
第一種觀點,對社會資本定義的論述主要關注外部關系,這種關系也稱為社會資本的“橋梁”形式(Bridging Forms)。這種觀點認為,社會資本必須是個體與個體之間具有聯系性的外部資源,是必須存在于社會網絡中的,更關注于外部之間的聯系以及關系的建立。這種觀點被運用于很多方面,比如個人在競爭中的差異、企業在競爭中的差異、個人行為被網絡中其他個體直接間接影響以及集體行為受到網絡其他集體的影響等,也就是說,從這個角度分析社會資本的概念,更容易受網絡理論的影響。
第二種觀點認為,社會資本的定義應該關注社會的內部關系,這種關注內部關系的社會資本稱為社會資本的聯結形式(Bonding Forms)。這種觀點在社會中心論中有重要體現,網絡社會學也傾向這種觀點。
第三種觀點認為,社會資本的定義應該在外部和內部之間中立。這種觀點得到了較多學者的支持。他們認為,對社會資本的研究,所謂內外部的差異就是研究和分析的單元的差異,其實質并非相互對立的概念,是相互影響并共同作用的結果。比如,集體行為主體在采取行為的時候,不僅僅受到網絡外部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企業內部聯系方式和結構的影響,因此其行動的效果是內外部共同作用的函數。
以上是針對社會資本定義分析的三個不同方面,但也提煉出一些一致的觀點:社會資本是一種新型的資本,區別于傳統的資本,它能夠使得社會網絡中的主體獲得一定的資源和收益,而信任、規范以及網絡等是社會資本的核心詞匯,構成了社會資本的核心特征。
四、社會資本的測量
社會資本是促進兩個或更多人之間合作的一種非正式規范。一個組織社會資本的多寡,反映了該組織內部所共同遵守規范的強弱和成員之間凝聚力的大小,或者說組織對成員影響力的大小。那么,如何度量社會或群體的資本呢?社會資本的測量一直存在爭議,這也更加激勵了現行領域內的專家去繼續探索更為全面的理論,使社會資本理論發展愈加全面。國內外學者經過一系列研究,形成了不同的測量方法和指標體系規范,其研究均與各自對社會資本的不同定義有關。以下主要從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對社會資本測量進行分析。
布迪厄[15]認為,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對某種持久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這一網絡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認的一種體制化的關系網絡。在獲取更多的、不同的和有價值的信息方面,網絡中“橋梁”的占據者有可能擁有競爭性優勢。關系強弱也被證明是測量“橋梁”有效性的網絡位置尺度。格蘭諾維特指出,隨著信息傳遞路徑長度的增加,信息傳遞所需的成本也增加,且順利到達目的地的可能性縮小,“弱連帶的重要性在于……可以創造更多而且更短的路徑。”
目前,主要從社會資本的三個基本成分(信任、規范、網絡)出發尋求替代指標對其進行測量。一些學者采用概述個人網絡的方法(即互動法、角色關系法、情感法和交換法)構造問卷進行調查和分析,其區別也就是提問的項目各有側重,尋找那些具有背景相關性的指標,并與指標建立起實證關聯。帕德姆(Paldam)[16]通過進一步對社會資本概念的分析認為,對社會資本的度量有直接的實驗方法和間接樣本或案例方法兩種;總體來看,社會資本的理論表述要遠遠大于測量的實證數據積累。克里希那和施拉德(Krishna & Shrader)構建了一種更加復雜的調查表,試圖包括社會資本所有形式。他們將調查研究按社會的層次分為四類:個人—家庭、鄰居—社團、地區、國家。懷特利(Whiteley)合并一些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作為解釋變量,提出了外生成長模型。雖然也有多個解釋變量,他只對134 個國家按照每單位資本的GDP進行了回歸,缺點在于經濟變量從時間上先于社會資本測量指標,這會引起社會資本和經濟業績之間關系存在隨機性的爭論。
厄普霍夫和帕克斯通等人將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分類后再進行測量。厄普霍夫認為,社會資本對發展的影響是通過結構型社會資本和認知型社會資本在相互作用中體現的。結構型社會資本與作用、規則、先例和程序以及大量有助于合作的網絡特別是互惠集體行動相聯系;認知型社會資本獲得于智力過程及其引起的思想,通過文化和意識形態得以加強。林南指出,還有許多其他的測量如社會網絡的規模、密度、同質性、異質性、內聚性和封閉性,也是測量個人社會資本的候選指標。他認為,決定個體所擁有社會資源數量和質量的有下列三個因素:一是個體社會網絡的異質性;二是網絡成員的社會地位;三是個體與網絡成員的關系強度。具體說來,就是一個人社會網絡的異質性越大,網絡成員的地位越高,個體與成員的關系越弱,則其擁有的社會資源就越豐富。
以社區或社群等為研究范疇的學者對社會資本作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同時提出了很多測量方法。帕德姆對如何維持良好運作的測度指標基于一系列不同因素,包括政府提供服務的有效性、公民對郵政和電話需求的充分滿足、司法體系的質量等等。福山對帕特南的方法加以修改,以誠信等調查數據來測量社會資本。布倫(Bullen)和奧尼克斯(Onyx)通過8 個因素對社會資本進行了小規模研究測量,設計了對社區的參與、社會背景中的能動性、信任和安全感、鄰居間的聯系、家庭與朋友的聯系、差異化的承受力、生活價值、工作聯系等問題,繼而從人們對問題的回答中測量社會資本水平。
在個人及社區層面對社會資本測量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各國學者及政府部門開始對國家層面的社會資本進行分析與研究。新西蘭統計局將社會資本測量分為三個維度:人口數據、參與數據、態度數據。施佩勒貝格(Spellerberg)[17]也認為,態度數據是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之一,因其可體現出共同的價值觀、期望與信念。弗奈普(H.D.Flap)認為應從三個方面測量社會資本:公民有個人需要時,其社會網絡中可提供幫助的人的數量;該人群中愿意提供幫助的強度;該人群中所能提供幫助的能力,即所擁有社會資源的數量。朱國宏[18]認為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自己所擁有的網絡關系即更廣闊的社會結構來獲取稀有資源的能力,提出社會資本測度要抓住兩個方面:對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等認知性要素的測量;對社會性關系、社會性網絡等結構性要素的測量。帕特南在說明美國社會資本衰減問題時,將美國社會資本從兩個層面進行測量:一方面是美國人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情況,他用公民參加各類社會組織機構的人數來表示;一方面是美國人參與政治的情況,他采用投票率和公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來表示。帕特南根據測量結果,得出了美國社會資本正在逐漸衰減的結論。
五、社會資本研究評述
綜上所述,社會資本是包括經濟學和社會學在內的個體或團體之間的社會網絡、互惠性規范和由此產生的信任,是個人、群體、社會、國家間緊密聯系的關系和狀態。社會資本在眾多領域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具有社會生產力的特點,像人力、物質資本一樣能為國家與社會提供幫助和支持。目前,雖然對社會資本的概念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但社會資本的概念已經被各國社會資本理論研究者普遍認可,隨著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不斷加大,該理論的研究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企業層面、個人層面都將得到很大發展,同時也為經濟領域中企業社會資本的研究提供支持,從而提高企業的經營效能。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我國重大裝備產品質量管控模式與方法研究”(項目編號:12&ZD206)、河南省教育廳自然科學研究項目“基于集聚效應的河南省高新技術產業創新體系建設研究”(項目編號:2011B790008)、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可持續發展導向下我省產業集群升級的路徑選擇研究”(項目編號:2011-ZX-093)的部分成果。
[1]、[2]Portes A..Social Capital: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98(24):1-24.
[3]Granovetter 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1360-1380.
[4]Granovetter M.S..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81-510.
[5]Putnam R.D..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35-36.
[6]Putnam R.D..The Prosperous Community: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J].American Prospect,1993b:35-42.
[7]Putnam R.D..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Journal of Democracy,1995(6):65-78.
[8]Loury G.C..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Wallace P.A.and Mond A.M.L.,Women,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M].Lexington:Lexington MA Heath,1977:46-58.
[9]Coleman J.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4(Supplement):95-120.
[10]Coleman J.S..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28-48.
[11]Portes A..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A Conceptual Overview,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M].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5:136-142.
[12]Evans P..Government Action,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Reviewing the Evidence on Synergy [J].World Development,1996(24):1119-1132.
[13]Fukuyama F..Social Capital and the Global Economy[J].Foreign Affairs,1995(5):89-103.
[14]Fukuyama F..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New York:Free Press,1995:17-28.
[15]Bourdieu P..Waequant L.J.D.,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56-82.
[16]Paldam M.. Social Capital: One or Many?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0,14(5):629-653.
[17]Spellerberg A.. Framework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Capital in New Zealand [M].Wellington:Statistics New Zealand,2001:101-128.
[18]朱國宏.經濟社會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7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