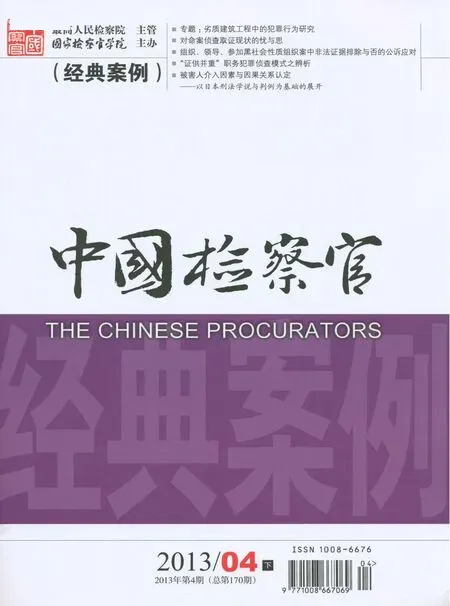建筑工程中嚴重偷工減料行為的定性
文◎時延安 許麗娟
建筑工程中嚴重偷工減料行為的定性
文◎時延安*許麗娟**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刑事法中心特聘研究員,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檢察院掛職副檢察長[101400]
**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偵查處副處長、檢察員[101400]
【典型案例一】某國有建筑企業承建經濟適用樓(高20層)。在地基打樁完成后,開始蓋第一層時,有人舉報該企業存在嚴重偷工減料問題。而后有關部門進行了檢測,發現基樁少打了20根,而且打下去的樁經抽查發現樁心沒有用混凝土澆灌實。技術人員檢測后建議,為保障樓房的安全質量,必須完全拆毀已蓋好的地下層,重新打樁補樁,初步估計要花費數百萬元。
一、關于本案定性的爭論
關于該建筑企業及其直接責任人員嚴重偷工減料行為的定性,存在五種意見:
(一)以重大責任事故罪論處
理由是該行為符合刑法第134條重大責任事故罪的基本特征:(1)行為人在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2)因其偷工減料行為而導致數百萬元的重修費用屬于該條中的“其他嚴重后果”。由于該罪的主體并不包括單位,應對直接責任人員以該罪論處。
(二)以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論處
具體理由包括三點:(1)該建筑企業屬于刑法第137條規定的“建設單位”;(2)該建筑企業在施工中嚴重違反國家規定,降低了工程質量標準;(3)因偷工減料行為導致重大經濟損失,屬于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第13條第2項所規定的“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應視為“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一種具體情形。
(三)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具體理由有兩點:(1)該建筑企業的行為已經對不特定或多數人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形成重大危險,對公共安全形成了侵犯;(2)該行為與放火、爆炸等情形類似且相當,都可能對人身和財產安全造成重大損害。為重修建筑地基而可能的花費,并不屬于刑法第114條和第115條的“嚴重后果”,因而該案屬于以危險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情形,應適用刑法第114條論處。
(四)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具體理由有三點:(1)建筑產品雖然不屬于《產品質量法》所規定的“產品”,但其仍屬于產品的具體類型,而且是一種事關民生的重要產品;(2)在建設樓房中偷工減料屬于生產偽劣產品的行為,具體而言,屬于刑法第140條“摻假”和“以次充好”的情形;(3)刑法第140條的罪狀中并未規定“違反產品質量法”這樣的表述,因而構成本罪并不需要以違反《產品質量法》為前提,而是只要違反相關產品質量法律法規就可以認定該行為具有行政違法性,就本案來說,建筑產品偷工減料的行為違反《建筑法》的有關規定。
(五)不構成犯罪
其理由是,雖然本案中建筑企業及其直接責任人員的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但出于維護罪刑法定原則的考慮,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不應作為犯罪處理;該建筑企業及直接責任人員的行為不符合以上四種犯罪的基本特征,因而不應以犯罪論處。
我們認為,建筑安全是關系民生的一個重要問題,而建筑質量問題同樣也關系到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障,以及建筑市場的正常秩序,因而對于在建筑領域的偷工減料行為,不能僅僅從公共安全角度加以考慮,同時也要從維護消費者權益和建筑領域的市場經濟秩序來理解其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就本案而言,筆者即認為,應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定罪處罰。
二、本案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
對這種情形是否符合刑法第140條規定的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論證,應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判斷:
(一)建筑工程中嚴重偷工減料,屬于一種生產偽劣產品的行為
根據刑法第140條規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罪狀為生產者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且銷售金額5萬元以上不滿20萬元。判斷某一行為是否符合該罪的罪狀,應著重三點判斷:
1.是否屬于“產品”。一般而言,刑法第140條中的“產品”通常是指以動產形式出現的商品,不過,從一般語意分析,房屋等不動產也屬于“產品”。換言之,在日常用語中,將房屋等不動產理解并界定為“產品”,符合人們的使用習慣,也在“產品”的可能含義之內,因而以文義解釋方法來判斷,房屋等建筑應包含在刑法第140條所規定的“產品”范圍之內。
2.是否實施了摻雜、摻假等行為。對于在建筑工程中嚴重偷工減料的行為,在將該建筑本身視為一個完整產品的情況下,這一行為屬于“摻假”和“以次充好”的情形。具體來講,當行為人以不合格或者不適宜用于該建筑的建材用于該建筑時,就屬于 “摻假”。例如,將不符合標號的鋼筋用于建筑當中。在建筑質量不合格,不適宜居住或者使用的情形,則屬于“以次充好”。因此,可以認為,在建筑工程中實施的嚴重偷工減料行為,符合刑法第140條所規定的具體行為特征。
3.是否達到定罪所要求的銷售金額的水平。對于生產并銷售偽劣建筑產品的,應當根據其實際銷售金額進行判斷,而對于處于生產環節的行為,可以考慮已經約定的交易價格或者市場同類建筑的價格來加以計算。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規定,偽劣產品尚未銷售,貨值金額達到刑法第140條規定的銷售金額3倍以上的,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未遂)定罪處罰。從上述三點可以看出,建筑工程中嚴重偷工減料的行為,符合刑法第140條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罪狀要求。
(二)建筑工程中嚴重偷工減料行為侵犯了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制度和消費者權益,侵犯了市場經濟秩序
作為侵犯市場經濟秩序的一種具體犯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客體就是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制度和消費者權益。通說認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客體僅限于 “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制度”[1]。這一認識是不準確的,產品質量的好壞直接與消費者權益相關,而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制度的設立與運轉,其目的也在于維護消費者權益。換言之,如果不考慮消費者權益,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就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對該罪客體的界定,理所當然地應著重強調消費者權益。建筑工程中的嚴重偷工減料行為,實際上就侵犯了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制度和消費者權益。關于建筑的產品質量問題,由《建筑法》等法律法規加以規范,而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制度實際上也涵蓋了《建筑法》等法律法規規定的具體內容。如果將這一制度僅限定在《產品質量法》所規定的范圍,那么,顯然是不當地理解了這一制度的內涵和外延,也會不當地限縮刑法第140條的處罰范圍。從實踐上看,因建筑工程偷工減料行為導致房屋等建筑存在嚴重問題,對消費者權益造成的損害遠遠超于一般偽劣商品造成的損害。同為偽劣產品,對危害程度相對較低的行為處以刑罰,而對危害程度相對較高的行為卻聽之任之,這是沒有道理的,從保障民生角度,對建筑工程中嚴重偷工減料這一嚴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更應進行處罰。
(三)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行政從屬性問題
否認這一行為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最有力的理由,或者說,證成這一行為構成本罪的最大障礙,就是本罪的行政從屬性問題。從沿革上看,本罪的立法確實與《產品質量法》具有相當緊密的聯系。《產品質量法》(1993年2月22日由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通過)第38條首次確立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刑事責任,而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決定》(1993年7月2日)(以下簡稱 “《決定》”)再次以單行刑法的方式規定了該罪,其條文與前者基本一致。受到這一法律沿革的影響,通說認為,本罪中的產品僅限于《產品質量法》中的“產品”。[2]現行《產品質量法》第2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產品是指經過加工、制作,用于銷售的產品”;第3款規定:“建設工程不適用本法規定;但是,建設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構配件和設備,屬于前款規定的產品范圍的,適用本法規定。”在通說看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中的“產品”與《產品質量法》中“產品”內涵和外延應當是一致的,那么,生產、銷售偽劣建筑工程的行為,即不在本罪評價范圍之內。然而,這一看法是缺乏說服力的。
刑法的功能在于保護法益,換言之,是保護正常社會利益關系,因而刑法與民法、行政法等法律中使用的術語,在內涵上可能不盡一致。就本罪的解釋而言,從客觀解釋論出發,即應從刑法第140條的規定進行判斷,以是否有利于保護法益進行目的解釋。具體來講,刑法第140條的“產品”應從一般用語來進行把握,是記述的構成要件要素,而非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在框定可能含義之后,進一步考慮有利于保護法益的角度進行分析和判斷。如前所述,本罪的客體(相當于法益)是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制度和消費者權益,而且主要是消費者權益,那么,將建筑工程中的嚴重偷工減料行為納入其中,是有利于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同時有利于國家對產品質量的監督管理活動。
上述通說所采取的立場實際上是主觀解釋論。不過,即便堅持主觀解釋論,同樣也應認為,本罪中的產品與《產品質量法》中的“產品”并不相同。《決定》的引言部分指出了該單行刑法的立法目的,即“保證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保護用戶、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從這一表述看,該單行刑法的立法目的就是保護消費者(廣義的)合法權益,而不是確認和維護國家的產品質量監督制度。如果立法者認為,該單行刑法的立法目的包括維護國家的產品質量監督制度或者與《產品質量法》所確立的法律制度保持一致,那么,立法者起碼會在該單行刑法中作出四種類型的明示:一是,在引言中加以明示,即提及與《產品質量法》的關系;二是,具體條文的罪狀中明示“違反產品質量法律法規”,尤其是在第1條(即現行刑法第140條的前身)中作出類似規定;三是,在該單行刑法對“產品”作出規定;四是,在附錄法律有關條文部分列舉《產品質量法》的法律條文,然而,在該單行刑法后只附錄了《藥品管理法》的有關條款。在該法中,立法者并未以這四種模式中的任何一種來明示該法與《產品質量法》的關系,因而可以由此推論,立法者并未將該法中“產品”等同于《產品質量法》中的“產品”。所以,即便是出于主觀解釋論來解釋本罪,也不能得出本罪中“產品”就是《產品質量法》第2條第2款所說之“產品”的結論。
綜上,無論是從客觀解釋論還是從主觀解釋論出發,都不能得出本罪中“產品”就是《產品質量法》中“產品”的結論,更不能根據《產品質量法》第2條第3款的規定將“建筑工程”排除于“產品”之外。當然,并不能由此否定本罪是一個行政犯,其刑事違法性的確立以行政違法性的確立為前提。《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都是判斷本罪行政違法性的前位法,而《建筑法》中的一些規定也可以作為判斷行政違法性的根據。例如,《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第74條規定:“建筑施工企業在施工中偷工減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構配件和設備的,或者有其他不按照工程設計圖紙或者施工技術標準施工的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于該條中所說“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即應指本罪。
通過以上三方面的論述,可以得出結論,在建筑工程中嚴重偷工減料的行為,應依照刑法第140條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定罪處罰。當然,在實踐中,并不是將所有的各種偷工減料行為都以本罪論處;對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應根據刑法第13條的規定,做無罪處理。
三、對其他觀點的回應
對于其他三種構成犯罪的觀點,應給予必要的回應:
該建筑企業直接責任人員的行為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由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屬于一種“兜底”性的規定,其法律規定存在較大的模糊性,在實踐中已經被實質性作為“口袋罪”加以適用,因而在解釋上必須對其加以必要的限制。一般認為,該罪的“危險方法”應當是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的危險性相當的危險方法。這一相當性的判斷,是一種實質性的判斷。就建筑工程中嚴重偷工減料行為的危險性來看,與放火罪等相比,還沒有那么嚴重。因而以該罪處理并不妥當。就本案而言,行為人在建設中偷工減料行為尚未對公共安全造成具體危險,因此更無構成本罪的可能。
該建筑企業直接責任人員的行為不構成重大責任事故罪。重大責任事故罪屬于過失犯罪,且以發生重大責任事故為犯罪成立的必要條件。而就本案而言,并未發生重大責任事故,因而也不構成本罪。
該建筑企業直接責任人員的行為也不構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該罪也屬于過失犯罪,且以發生“重大安全事故”為犯罪成立的必要條件。這里的“重大安全事故”,是指在工程建設過程中由于責任過失造成工程倒塌或報廢、機械設備毀壞和安全設施失當造成人身傷亡或者重大經濟損失的事故。[3]顯然,本案中所說的損失只是可能的損失,不屬于該罪中“重大安全事故”的范疇。
注釋:
[1]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五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75頁。
[2]同注[1],第375頁。
[3]李希慧主編:《刑法各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頁。
編者按:在我國,房地產領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吸引人們的關注,諸如建筑物安全、房地產的畸高價格、產權制度等均牽動著整個社會的神經。為保障建筑質量、確保房地產行業的健康發展,我國從四個方面構建了房地產行業健康發展的制度,即企業內部管理制度、標準化制度、招投標制度和工程監理制度。我國《公司法》的出臺既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也是企業內部管理制度不斷完善的標志。標準化制度的建設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期《標準化法》的出臺,該法明確規定了建設工程的設計、施工方法和安全要求應當制定標準;根據《標準化法》,建設部對工程建設質量標準做出了詳細的規定。招投標制度的價值在于通過引入市場良性競爭,確保建設主體及建設方案的最優。工程監理制度則是通過引入外部監督機制,保證建設工程質量和建筑安全生產。一般而言,只要房地產領域的各項制度規范不存在天然的缺陷,有關實施主體切實予以落實,建筑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均不會出現較大的負面問題。事實上,建筑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問題頻發,甚至嚴重危害到刑法所保護的法益。作為最后法的刑法,也通過不同的規范設計,對房地產生產過程中的嚴重違法行為予以懲治。本期選取幾篇文章,對建筑產品的生產過程中犯罪行為的定性問題予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