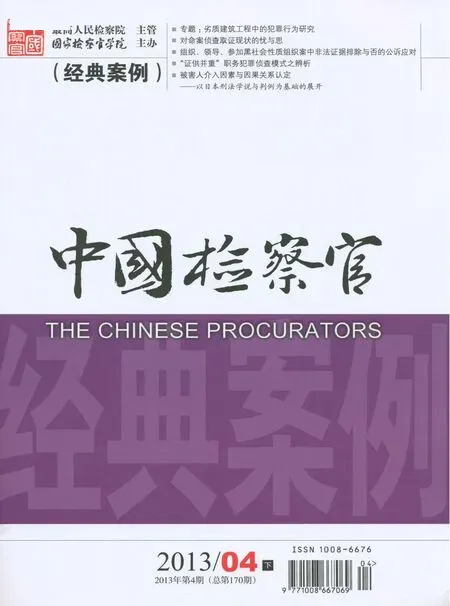銀行工作人員私自將資金挪借他用的行為定性
文◎張淑臻
銀行工作人員私自將資金挪借他用的行為定性
文◎張淑臻*
*山東省濟南市天橋區人民檢察院[250031]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某商業銀行支行行長王某與劉某相識,劉某介紹A公司到王某所在支行進行定期存款,并告訴王某:已經和A公司總經理說好了,以單位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在銀行幾天后,提前支取用于經營一個項目。劉某讓王某復印A公司的定期存款證實書給劉某。王某覺得業務不正常,但認為能提高自己的業務量并沒有向企業核實,就指示經辦人員復印定期存款證實書給劉某。兩天后王某拿著A公司的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來銀行提前支取,定期存款的提前支取必須要開立一般結算戶過渡一下才能轉賬和取現,但劉某沒有A公司的營業執照原件等開戶資料,于是在劉某的要求下,王某強令經辦人員用A公司在銀行定期存款時所留的開戶資料復印件重新開立了一般結算賬戶 (按人民銀行規定開戶資料必須是原件),劉某順利將存款取走。該筆存款為400萬元。劉某的行為A公司并不知情,劉某所持的開戶證實書是比照王某提供的復印件偽造的。
二、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王某的行為是違反人民銀行規定的行為,并不觸犯刑法,不構成犯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王某的行為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A公司的存款歸劉某使用,用于經營,構成挪用資金罪。
三、評析意見
(一)主體及主觀方面
挪用資金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王某身份是某商業銀行的行長,符合挪用資金罪的主體要件。挪用資金罪在主觀方面只能出于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是在挪用或借貸本單位資金,并且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而仍故意為之。在該案中,劉某告訴王某說和A公司的總經理說好了。后在單位定期存款之后兩天提前支取,這里成為判斷王某主觀方面是否明知劉某挪用的關鍵所在。我們都知道銀行的行長對銀行業務是非常熟知的,對于各種違規操作可能帶來的損失應該能預料到。我們試想如果劉某說的是事實,那么為什么存了定期之后這么短的時間內就取走,A公司直接將錢借給劉某即可,為什么要通過銀行過渡一下呢?對于這筆可疑的業務,王某為什么沒有電話照票呢?(所謂電話照票是指對于大額款項提前支取必須電話核實存款單位)單位存款開戶證實書作為單位存款的證明,上面有存款單位的財務章、公章、法人章,按照規定是不能私自復印給他人的,王某作為行長應該意識開戶復印件會被劉某非法利用。且事實上,王某意識到這筆業務的不正常,但是存有僥幸心理,輕信自己擁有單位定期存款開戶證實書,自己能讓銀行不承擔損失。王某的心態在銀行的工作人員中具有代表性——知道有問題,客戶資金有可能被挪用,仍鋌而走險。王某的種種違規幫助劉某的行為,表明王某明知自己的行為在幫助劉某挪用客戶資金,仍然利用職務便利故意為之的行為,符合挪用資金罪的主觀方面。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首次明確瀆職罪主體涵蓋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規定,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有瀆職行為的,依照刑法關于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兩高負責人對于這一問題做出解釋:刑法第168條與立法解釋的規定并不沖突,前者針對企業管理事務,后者限于國家行政管理事務。因此,解釋第7條規定: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管理職權時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立法解釋的規定,適用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二)客體及客觀方面
該罪所侵害的客體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資金的使用權,對象則是單位的資金。所謂單位的資金是指由單位所有或實際控制使用的一切以貨幣形式變現出來的財產。在該案例中,公司存在銀行的錢是否屬于銀行的資金呢?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曾提到:“對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已經記入金融機構法定存款賬戶的客戶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吸收客戶資金不入賬,卻給客戶開具銀行存單,客戶也認為將款已存入銀行,該款卻被行為人以個人名義借貸給他人的,均應認定為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資金罪。”也就是說A公司存入銀行的錢,已經成為銀行的資金,不管A公司的經理是否同意,未經合法手續,非法轉走即為挪用。
挪用資金罪在客觀方面表現兩種方式。第一種是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第二種是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在本案中銀行工作人員王某是何種行為呢?本案中其實是劉某利用王某提供的開戶證實書的復印件偽造的開戶證實書,私自將A公司挪用。王某作為行長,對于全行的業務都有直接管理的權力,但王某沒有遵循中國人民銀行的規定,強令經辦人員予以違規辦理,在劉某轉走該筆資金的時候,王某利用了職務便利予以幫助。劉某和王某共同實施了部分行為,王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A公司資金歸劉某使用,用于經營,符合挪用資金罪的第二種表現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理解刑法第272條規定的“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問題的批復》:“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本人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或者挪用人以個人名義將所挪用的資金借給其他自然人和單位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272條第1款的規定定罪處罰。”也就是說所謂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應理解為歸個人和他人使用,借貸給他人應理解為行為人以個人名義將所挪用的資金借給其他自然人和單位。在適用法律時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例如,當挪用人和使用人不一致時,如果挪用人確實不知使用人利用資金進行何種活動,對挪用人就不能按挪用人進行的活動適用法律,而只能根據挪用人明知的內容來確定挪用資金的用途。在本案中王某明知的是劉某用于經營即營利活動,假如劉某將資金不用于經營,也要以挪用人王某明知的內容——挪用資金進行營利活動規定來處罰。
另外“挪用”一詞由“挪”、“用”兩種行為結合而成的。“挪”就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的資金轉移到本人或者他人控制之下。“用”就是將資金用于本人或者他人的某種需要。挪是前提,用是目的,但并不是行為實現了用的目的才是既遂,只要行為人已經將資金轉移到本人或者他人控制之下,單位失去了對于資金的控制,即標志其占有權、使用權已經實際遭到侵犯,對于是否使用,如何使用對于定罪沒有實際的影響[1]。且挪用資金罪的既遂是以行為人或者他人對于資金的實際控制為既遂的標準。劉某將錢私自轉走之后如何使用并不影響王某挪用資金罪的既遂。
注釋:
[1]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