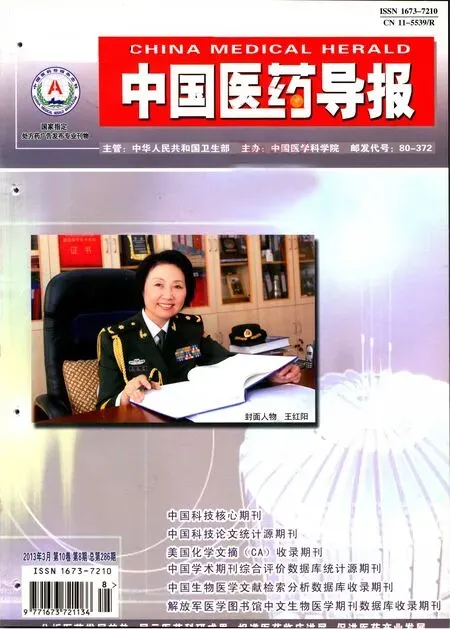面對腫瘤高發現狀,必須強化“全民預防”和早診——訪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王紅陽教授
文圖/《中國醫藥導報》記者 詹洪春 劉志學
據記者了解,由于城市化、工業化、老齡化及全球化進程的加劇,生態環境惡化、職業暴露、食品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物學和遺傳學因素的影響,全球惡性腫瘤發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態勢,腫瘤已成為影響人類生命健康的重要疾病。世界衛生組織最新數據顯示,全球死于惡性腫瘤的病例約占全部死亡人數的13%。預計到2030年,將有1300萬人死于癌癥。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際合作生物信號轉導研究中心(SMMU)主任、上海交通大學“癌基因及相關基因”國家重點實驗室名譽主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醫學科學部主任、全國政協委員王紅陽教授,在“兩會”上提出了關于“改變我國腫瘤高發現狀,必須更加關注腫瘤的全民預防和早期診斷”的建議。
現狀:每分鐘有6人被診斷為惡性腫瘤
采訪一開始,王紅陽院士就向記者介紹了我國目前惡性腫瘤的發病現狀。她首先回顧說:“自上一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惡性腫瘤逐漸呈現出了年輕化的發病趨勢,許多腫瘤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也呈持續上升趨勢。據一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腫瘤發病率以每年3%至5%的速度持續增長。到了2009年,我國的腫瘤發病率為每10萬人中就有285.91人的概率,每年新發腫瘤病例約為312萬例,平均每天8550人、每分鐘有6人被診斷為惡性腫瘤!”
王紅陽院士進一步介紹說:“在各類惡性腫瘤中,我國的乳腺癌、肺癌、結腸癌、肝癌、甲狀腺癌等腫瘤的高發年齡段均在提前,已經呈現出了年輕化的發病趨勢。2009年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當年全國腫瘤死亡率為每10萬人中有180.54人的概率,每年因惡性腫瘤死亡的病例高達270萬例。我國民眾因腫瘤死亡的幾率高達13%,也就是說,每7人至8人當中就會有1人因癌癥死亡。而惡性腫瘤患者的平均5年存活率僅為20%至30%!”
談到這里,王紅陽院士感慨地說:“觸目驚心的一組組數據,已經讓老百姓談癌色變,也常讓醫護人員束手無策。在消耗了大量衛生資源的情況下,許多惡性腫瘤不僅難以治愈,還使一些民眾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因此,目前我國的腫瘤防控形勢極不樂觀。”
短板:“重治輕防”的現狀亟待改變
在采訪中,王紅陽院士提及了我國惡性腫瘤的防治現狀。她介紹說:“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及相關部門十分關注大眾健康,重視腫瘤研究和治療,提出防控戰略計劃,并有相當的和逐步增長的資金投入。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腫瘤的終末期治療方面消耗的衛生資源,大大超過腫瘤的預防和預測,而在腫瘤流行病學調查、發病基線確定和預防腫瘤的科普教育上的投入,更是捉襟見肘。與此同時,我國各類腫瘤發病數據的報告也時常有不統一、不準確的現象,這使國外專家多有質疑。”
王紅陽院士繼續介紹說:“近年來,‘降低腫瘤發病率、病死率必須注重腫瘤的預防和早診’的觀點,已經逐漸被認同,但是如何糾正‘重治輕防’的現狀,有效推進腫瘤預防,使之成為國民的自覺行動,仍然是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2008年,在中央財政支持下,我國全面開展了一項針對53萬適齡女性的乳腺癌普查。其普查結果顯示,通過普查檢出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患者的比例達40.5%,但在同時期醫院門診診斷的乳腺癌患者中,早期腫瘤僅有17%。防癌普查和篩查明顯提高了早期乳腺癌檢出比例,治愈率和生存期隨之大大提高。但是,由于經費和技術所限,其他多種惡性腫瘤高危人群的大規模篩查未能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也較少有相應的隊列研究。一份調查表明,同是肝癌多發的日本,其診斷篩查出的早期肝癌約占40%,而我國治療肝癌的主要單位早診率卻比較低。因此,‘重治輕防’一直是我國惡性腫瘤預防和早期診斷的‘短板’。”
談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癌癥的早期預防干預問題,王紅陽院士介紹說:“2011年,世界衛生組織即確認了包括吸煙、飲酒、空氣污染、HPV感染等在內的9種腫瘤危險因素,并提出近40%的惡性腫瘤是可以通過改變或避免主要的危險因素而實現預防的。而且,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腫瘤預防的概念;上一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的腫瘤預防工作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有關腫瘤病因和腫瘤預防及干預手段的研究成果使得一些發達國家的腫瘤發病率和死亡率開始出現下降趨勢。我國臺灣地區自1984年實施大范圍的新生兒乙肝疫苗接種計劃以來,幾乎所有的HBV垂直傳播均已得到控制;預期到2040年,與乙肝和丙肝相關的肝癌將成為少見疾病。但在我國大多數地區,惡性腫瘤防治工作仍是‘重治輕防’,腫瘤預防尚未得到足夠重視。針對我國經濟尚不發達,著眼于我國腫瘤高發、且是個癌癥大國的實際情況,從長遠利益、經濟效益和社會需求來看,開展腫瘤預防是我國控制腫瘤的經濟而有效的途徑,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呼吁:五項建議旨在盡快改變現狀
基于我國惡性腫瘤高發以及防控方面的諸多問題,王紅陽院士認為:“已經備受關注的問題如注射疫苗等,我就不再重復了;我只是從加強腫瘤預防的角度提出五條建議,以盡快改變我國癌癥高發的現狀。”
Therapeutic drug(Yupingfeng granules,Z10930036)and placebo(placebo granules)were manufactured by Guangdong HuanQiu Pharmaceutical Company(Guangdong,China).
接著,王紅陽院士詳細介紹說,首先,我們應加強腫瘤流行病學研究,完成發病率基線調查。因為“癌情監測”是防治工作的基礎,是制定規劃、評估防治措施與效果、引領科研方向的重要依據,既造福于當代人,也惠及子孫后代,必須予以加強。但目前這項工作在我國還相當薄弱,存在著機構不健全、經費不穩定和專業人員少等諸多問題。由于腫瘤流行病學和隊列研究缺少長期穩定的經費支持和訓練有素的穩定研究隊伍,我國正規和/或不正規發布的統計數據往往不夠準確,發病率和病死率多以登記數據推算,大量未登記病例被遺漏;生存期的隨訪調查往往把失訪的病人漏算,造成來自不同人群的數據誤差很大;某些地區利益也影響真實數據的獲得與發布……因此,加強基線調查既要求政府有穩定的專門資金投入,又要有決策層的高度重視和制度法規,以保證規范化的監測能不間斷地順利實施。
其次,我們還要重視高危人群篩查,并提高預測、早診水平。眾所周知,腫瘤二級預防的目的是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防患于疾病初始。對高風險人群應進行隊列、社區、高發現場的定期監測和篩查,提高腫瘤的早診率。只有早期預測、監測,才能早期預防、阻斷;只有早期發現,才能徹底治愈。在這方面,加拿大早就專門設立了“國家癌癥篩查項目咨詢委員會”,并在全國構建癌癥篩查的研究和評估網絡,定期出版監測報告,積極推進了腫瘤二級預防工作。建議我國也應加強腫瘤的咨詢和預測,整合相關研究機構和臨床醫院,制定適于我國的標準、規范和實用的常見惡性腫瘤篩查方案,共同推進常見腫瘤的早期診斷和高危人群篩查工作。同時,還應改革公共衛生政策,加大醫療保障體制對高危人群的覆蓋面,使更多的高危人群能夠方便、免費、或低價地進行腫瘤篩查。
第三,我們還要快速發展適于監測、早診的新技術,加強轉化應用。在我國推進創新研究,加大科研投入的新形勢下,各科研院所前期已發現和篩出一系列具有應用潛能的腫瘤檢測標志物和新技術。國家相關部委應積極創造條件,開辟綠色通道,精簡中間步驟,加快審批進程,使方便、有效的新方法不要長期滯留在實驗室或耽擱在談判桌上,盡快推向產業化和推廣應用。
第四,要建立居民保健檔案,推進信息化管理。因為目前國內腫瘤發病與死亡登記報告大都基于大醫院,再用其他渠道數據加以補充更正。隨著社區建設的日臻完善和城鎮化進程,建議在鄉鎮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建立和完善腫瘤登記報告制度,并為居民建立體檢保健檔案和電子病歷,逐步使腫瘤流調數據、發病率和死亡率的數據更加準確詳實,實現實時動態的全國聯網監測與報告體系。
最后,我們還需要加強科普宣傳,推動全民腫瘤防控。在這方面,腫瘤防治研究機構在腫瘤防控知識的社會普及,政策的規劃和建議,措施的組織運行和指導監督,以及管理協調等方面均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美國癌癥學會1980年就出版了《癌癥早期發現指南》,近年來不斷加以修訂和對執行情況進行評估,力圖使全社會充分認識早期發現對降低腫瘤死亡率的作用。我國腫瘤預防工作發展很不平衡。部分腫瘤防治機構并沒有完成所在地的癌癥篩查、評估和監測工作,更沒有切實開展全社會防控腫瘤的科普宣傳。當然,科普宣傳是全社會的任務,因此建議政府部門在建立、健全全國腫瘤防治研究的職能管理體系的同時,強調國家和地方的癌癥中心、科研院所、醫學院共同承擔科普宣傳任務,使廣大民眾懂得腫瘤可以預防,養成健康生活習慣,保護生態環境,與醫護人員共同應對腫瘤挑戰。
科研:發現早期肝癌分子標志物
采訪前記者了解到,王紅陽院士不僅是文職將軍、還是我國最年輕的女院士之一,而作為我國著名的腫瘤學分子生物學專家,王紅陽院士長期從事腫瘤的基礎與臨床研究,對腫瘤信號轉導有重要建樹。
王紅陽早在第二軍醫大學畢業后不久,即遠赴德國科學院馬普生化研究所,在著名國際腫瘤研究大師和信號轉導研究先驅烏爾里希教授指導下,開始生物信號轉導研究。
對此王紅陽院士介紹說:“所謂生物信號,就是基因的表達、介質與蛋白分子的相互作用,如同人與人交往時的語言。及時捕捉并理解破譯這種信號,對人類認識各種疾病的發病規律十分重要。”
在當時,她決定從基因入手,弄清腫瘤的基因和分子水平的發病機理,并先后克隆了受體型和非受體型酪氨酸磷酸酶等多個新基因,揭示了信號調節蛋白介導生長激素信號途徑的重要意義。
在取得一系列的科研成就后,王紅陽院士于1997年回國創辦了國際合作生物信號轉導研究中心和綜合治療病區,形成基礎與臨床結合的創新基地。她研發了新的肝癌診斷標志物及血清檢測單克隆抗體,并獲得國際和國家發明專利;她曾經克隆了4個新的肝癌相關基因并闡明功能;首次發現新的抑制性受體對肝癌細胞生長、凋亡的調控機制和癌基因P28調控肝癌的異常信號網絡,為肝癌防治提供了新的靶標;分離新的磷酸酶3種,提出新的酶分類法;發現了磷酸酶PCP-2調控β-catenin介導的腫瘤信號通路,與同行合作提出新的抑制性受體調控機制在多器官存在的新概念。
而在此前不久,上海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國際合作信號轉導研究中心王紅陽教授率領的研究團隊,經10余年研究、1000多例臨床實驗發現,人體內一種叫GPC3的蛋白聚糖物可作為檢出早期肝癌的分子標志物。而且,該研究已獲得了國際、國內發明專利,并進入診斷試劑研發應用階段。
對此消息,業內人士普遍樂觀地認為,這一發現將能夠大幅提高肝癌診斷的正確率。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如果這一發現能夠廣泛推廣應用于臨床的話,那么,對于肝癌的早期診斷,不僅具有巨大的學科價值,還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
借此機會,記者希望王紅陽教授能詳細地介紹一下這項研究的相關情況。對此,王紅陽教授首先對記者“科普”道:“我們知道,肝癌是惡性程度極高、異質性極強的惡性腫瘤,包括原發性肝癌和轉移性肝癌兩種,人們日常說的肝癌指的多是原發性肝癌。原發性肝癌是臨床上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根據最新統計,全世界每年新發肝癌患者約60萬,半數以上在中國。原發性肝癌按細胞分型可分為肝細胞型肝癌、膽管細胞型肝癌及混合型肝癌。以往的醫學研究認為,肝癌的自然病程可分為4個階段:一是早期亞臨床階段。即由發病到亞臨床診斷成立,這要通過驗血給予診斷。二是亞臨床期。即由亞臨床診斷成立至病患者有癥狀出現這個階段。三是中期。即由癥狀體征出現至有黃疸、腹水或遠處轉移階段。四是晚期。指出現黃疸、腹水或遠處轉移至死亡。”
王紅陽院士繼續闡述說:“和其他惡性腫瘤一樣,肝癌的最佳治療時期無疑也是發病的早期階段,因此盡早診斷對肝癌的治療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部分肝癌患者只要肝癌初始,他們血清中的甲胎蛋白就已經開始升高。目前,甲胎蛋白作為唯一一個應用最廣的血清學標志物,在肝癌的診斷和監測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對早期肝癌的檢出率并不令人滿意。”
王紅陽院士告訴記者,與所有的腫瘤診斷標志物相同,作為理想的肝癌診斷標志物必須具備四大要素,即對肝癌具有高度特異性,在不典型增生結節及其他腫瘤中檢測不到;敏感性高,能夠在肝癌發生的早期被檢出;檢測方法簡便、結果穩定,重現性好;取樣檢測創傷小,便于醫生操作,患者依從性好。
基于上述因素,王紅陽院士說:“GPC3基因定位于人染色體X26.10,參與了生長、發育以及細胞對生長因子的反應等生命過程。”而王紅陽帶領她的團隊歷經10余年的研究揭示,GPC3作為特異的肝癌診斷標志物,對早期肝癌的敏感性為72%,特異性幾乎可達100%,在患者小于3厘米的腫瘤組織中仍可檢測到GPC3的存在,而甲胎蛋白檢出率僅為22%;34名肝癌患者中有18名血清中檢測GPC3為陽性,而20名肝硬化病人僅有1名檢測結果呈陽性。更為重要的發現是,如果GPC3與甲胎蛋白檢測聯合應用,其肝癌敏感性可提高到72%。
王紅陽院士最后闡述說:“由于肝癌這種疾病的病因復雜、病程較長,如僅依賴一個診斷標志物肯定是有缺陷的,因此,需要有一組能夠互補的標志物來發現早期肝癌已成為世界各國科學家的共識。所以,GPC3不僅有助于早期發現肝癌,而且具有很強的肝癌特異性,如作為甲胎蛋白的補充,能夠大幅提高肝癌診斷的正確率。它是一個具有良好應用前景、非常有潛力的肝癌早期標志物。”
采訪結束了,王紅陽院士走進了即將開始的政協分組討論會會場。望著她的背影,記者衷心期待王紅陽院士包括GPC3在內的諸多科研成就,能夠造福于更多的癌癥患者,并期待她“改變我國腫瘤高發現狀,做到全民預防和早期診斷”的愿望,能夠早一天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