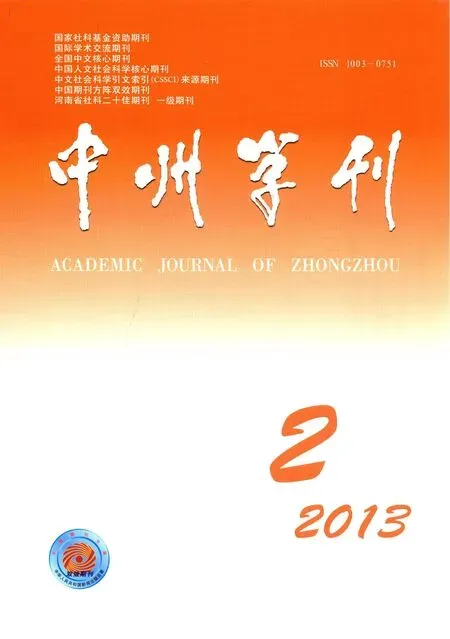公共批評研究范式:大眾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兼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研究的范式問題
吳 慧 肖明華
一、大眾文化的特點
隨著全球市場化程度的日益加強、現代大眾社會的逐漸興起和大眾傳媒的不斷普及,大眾文化逐漸成為我們當下文化生產與消費的主導形態。依照大眾文化的實際存在樣態,我們對大眾文化的特點作如下界定:
從文本形態看,大眾文化文本往往不會有意去脫離受眾的期待視野,更不會刻意去追求新奇獨特,這就使得大眾文化的文本具有程式化的特點。以文體觀之,大眾文化常使用當下大眾喜聞樂見的、與日常生活較為貼近的體裁、語體、風格。
從價值追求看,大眾文化文本與那種私人形而上學的價值常常格格不入。也即大眾文化文本對縱向的深度價值追問持拒絕態度。它不追求所謂的終極真理、終極自由、終極審美。它要追問的價值往往是那種在一個世界中的、平面的、可以體認得到的、塵世中的公共價值。
從傳播方式看,大眾文化的傳播渠道是大眾媒介。在今天,不借助于大眾傳媒的復制性生產和廣泛性流通,幾乎不可想象。無論是通過印刷媒介,還是電子媒介傳播的大眾文化,鮮有非機械復制和媒介技術者。
從消費主體看,大眾文化要進入市場,遵循商品法則,這就使得大眾文化的接受者必定是世俗社會的平民大眾。平民大眾才是市場消費的主體,那種將文化接受的對象定位在精英層的大眾文化生產者是難以占有市場份額的,因此也難以持久存在。這里強調的是:大眾文化要公眾參與,讓公眾成為主體,不故意保持文化的稀缺性,以至于只有少數人才能參與其中。
從接受效應/文化功能看,大眾文化與大眾或者說大眾文化創作者與接受者的關系是一種互選互適的關系。大眾文化選擇大眾,大眾也選擇大眾文化,他們在這種平等的交往關系中,幾乎不存在高姿態的啟蒙價值的流通,不存在虛無縹緲的救贖論調的宣傳,存在的往往是現時而理性的娛樂、挪用、批評,參與感、團結感、共通感,等等。
二、大眾文化研究的三種范式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眾文化研究出現了形態各異的研究范式。對此,已有學者指出過各種研究范式的可取性與局限性,并在此基礎上對大眾文化研究范式進行過規范性的建構。①就當代中國而言,若不考慮各種研究范式的具體差異,我們可以把已有的大眾文化研究范式大致分為三類。
其一,精英主義研究范式。
這種研究范式主要通行于20世紀90年代,備受具有人文精神與終極意義追問慣習的知識分子所認同。幾乎所有涉足大眾文化研究領域的學者都曾持有過這種立場,否則也會因自己不持這種立場而備受責備,或深感另類。這種研究范式所倚重的理論資源主要是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阿多諾、霍克海姆的《啟蒙的辯證法》中把大眾文化看成是“文化工業”的理論。
這種研究范式下的大眾文化,往往被認為是道德敗壞、趣味低俗、機械復制、欲望沉淪、虛假欺騙的文化。大眾文化的審美價值、道德意義和公共價值幾乎為零,大眾文化文本的創作、消費和接受,幾乎被認為是由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完全決定和控制的。為此,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目的就是,揭示大眾文化中的意識形態運作機制,批判大眾文化的道德墮落、審美低俗以及終極理想缺失等,進而否定大眾文化存在的合法性。
若撇開歷史語境而只從學理上來說,這種研究范式的理論價值主要在于它有一種對生存狀況與意義價值問題的積極關懷,同時對市場可能加之于大眾文化的負面影響如大眾文化的完全他律化、去價值化和極度娛樂化現象等,也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但這種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也很明顯:太精英化而不信任大眾文化,太悲觀化而把世界結構主義化。它還有本質主義的嫌疑,把大眾文化本質化為一種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場所。而它對大眾文化的批評持絕對的否定態度,也是一種二元對立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表現。對此,以陶東風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已做了較為深刻的指認。②
其二,民粹主義研究范式。
持這種研究范式的學者深受康德啟蒙思想影響,有較為自覺的語境意識,對現實的社會文化發展有較為理性的思考,把大眾文化置于社會文化的現代轉型的整體框架中進行分析。同時,他們較為樂觀,對大眾、大眾社會充滿信任,認為大眾在消費大眾文化時,正在遠離意識形態。如李澤厚先生所說:“大眾文化不考慮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慮要改變什么東西,但這種態度卻反而能改變一些東西,這就是……對正統體制,對政教合一的中心體制的有效的侵蝕和解構。”③大眾文化在這種研究范式下往往被塑造為有積極意義的形象,它能滿足人們日常娛樂消遣訴求,能為現代文化社會的祛魅提供合法的經驗支撐,并可推動文化的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世俗化走向。這種范式的大眾文化研究主要關注大眾文化的現實文化政治功能,至于審美價值、道德意義則不是其興趣所在。精英主義理論研究范式所提倡的終極價值,更是它要極力否定的。
從學理上說,持這種研究范式的學者對精英主義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有較為深刻的反思,他們大多實際參與了與精英主義研究范式研究者的學術辯論,并建構了大眾文化研究的民粹主義理論范式。從語境上看,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提倡民粹主義研究范式的合理性遠大于精英主義研究范式。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市場化程度逐漸加深,整個中國的社會結構形態也在慢慢發生改變,伴隨于此的大眾文化逐漸得以發展和成熟。與此相應,人們的心性結構、價值認同和生存理想等各個方面也慢慢地走向了現代,具有了主體意識、獨立人格和塵世存在認同,對那種或真理或道德或審美的形而上學的價值追求失去了興趣。這樣,民粹主義研究范式便得到人們的更多認同。
然而,民粹主義理論范式也有其局限性。它忽略大眾文化所應具有的公共性意義建構,將大眾文化理想化,對大眾文化所具有的消費享樂主義、去政治化等局限性關注不夠。它似乎絕對地反對任何精英式升華與超越,即使是后形而上學思想旨趣,它也不是完全放棄,而只是要放棄那種傳統的從另一個世界來獲取超越力量的形而上學,進而在一個世界中去尋找理想。當然,這是民粹主義研究范式所存在的線性敘事所致。
其三,新意識形態研究范式。
新意識形態研究范式凸顯了階級敘事和實體政治追求,可謂與新近文化研究中興起的政治經濟學范式(以韋伯斯特、加恩海姆為代表)有相似的旨趣。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他們考慮正義、民主、和平等公共價值要優先于自由。而面對自由時,他們對消極自由有自覺的警醒。
這種研究范式下的大眾文化被看成是中產階級的文化,而不是大眾的文化。④對于民粹主義理論所提倡的大眾,在他們看來倒是真正的“去大眾”。因為,雖然大眾有權利去消費這種文化,但受經濟能力及生活方式的限制,大眾實際上很難消費這種文化,因此大眾文化所表征的自由是強人的自由。因此,他們基本上把大眾文化看成是一種新意識形態,一種與真實狀況不相符的符合表征和觀念神話。⑤
應該說,這種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學理意義和現實作用。它繼承了精英主義理論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學術批判旨趣,對民粹主義理論研究范式所存在的去政治化問題有一定的反思作用。這種研究范式對現實存在的兩極分化現象有較為自覺的關注,對底層大眾和弱勢群體實際的文化生活現狀有較為切身的關懷。它依靠市場的力量,以一副消極的政治冷漠的顏面,對那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政治具有明顯的解構功能,對推進公共領域的進程起到了較好的作用。雖然由于種種原因,它的這一使命并沒有完成,還存在明顯的公共性不足而私人娛樂消費有余的局限。
然而,新意識形態研究范式也存在較大的理論局限性。它對大眾文化業已發揮的公共性沒有同情的理解,并試圖徹底否定大眾文化的存在合法性。依靠市場、消費而存在的大眾文化的確有平等不足的嫌疑。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大眾文化所表征的價值與平等并非天然對立。相反,依靠市場、消費的大眾文化本來就有平等的預設,只是這種預設在經驗層面上還未曾完全實現,離事實上的平等還相差甚遠。但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因此摧毀、否定和放棄它的存在。一個更為合理的選擇應該是,完善大眾文化,增加它的“大眾性”。
此外,如果我們注意到大眾文化的消費還具有意義層面上的相對能動性與自足性,那么我們就不能完全以經驗事實上的能動性與參與性來判定大眾文化的去大眾性。菲斯克曾主張從生產的角度看待大眾的文化消費,認為大眾在消費時是有生產性的,因此他主張“我們必須將問題從人們在解讀什么轉移到他們如何解讀”⑥,這種對大眾有較多信任的能動觀念,的確也不應該被新意識形態研究范式所完全忽視。
從上述三種大眾文化研究范式的簡要評述中可以看出,這三種研究范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建構一種怎樣的大眾文化研究范式呢?其實上面關于大眾文化的界定及對三種研究范式的分析中都已然貫徹了一種分析范式,即公共批評研究范式。
三、大眾文化研究的新方向:公共批評研究范式
在我們有限的學術視野里,大眾文化的公共批評范式最早是由陶東風先生以政治批評的名義提出來的⑦。但只要理解了這種政治批評的政治所指,是一種純粹的政治,或說是公共領域的政治,那么我們就會發現政治批評其實與公共批評的旨趣一致。所謂公共批評研究范式是一種以后形而上學為思想旨趣,以公共性為價值立場,堅持語境化和學理式的對大眾文化現象進行分析的理論和實踐。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它認同后形而上學思想型
首先,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后形而上學思想更具當下的可取性。
黑格爾之后的西方思想史,其主導的基調就是后形而上學。所謂后形而上學不是一個實體的概念,而是一個思想型的概括。在這種思想型的裝置中,人們不再采取主客二分的認知方式,把世界一分為二去尋找那種所謂純粹的、終極的、永恒的知識與價值,因為在后形而上學思想看來,根本就沒有那種知識與價值。
這里僅以真理觀為例。后形而上學的真理觀至今約有一個多世紀。在尼采時代就開始認為“真理根本就不存在”⑧,所謂的真理也只是對世界的一種闡釋,“一切事物的本質不過是關于此物的見解而已”⑨。尼采的這種后形而上學的真理觀對后世影響深遠。無論是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哲思,還是以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的科學主義哲思,都沒有完全脫離尼采的這種思考路徑。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就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后形而上學真理觀。他之所以要提出“此在”、“在之中”等一系列范疇、要區分存在與存在者、要將存在與時間相勾連,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他看來,此前幾千年的哲學思想總是以一種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在尋找真理,在尋找一種存在者的真理,認為真理是一個實體,是一個純粹的存在,甚至是另一個世界的東西。依海德格爾之見,這無疑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虛設,不利于思想的現代轉型,與現代人的生活世界更是格格不入。于是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第一篇的最后一節專門探討了真理問題。在對傳統真理觀的三個命題逐個進行分析之后,海德格爾認為它們共同表征了一種傳統本體論的“符合的真理”,這種真理不具有源始性,源始性的真理應該是“此在的展開狀態”。由于此在是不可能離開對存在的領悟而獲取所謂的真理的,因此說真理離不開此在,也即真理離不開存在。而存在是什么?存在是一個不能用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來提問的東西,或者說存在就是一種不能用主客二分來追問的“境界”,這種境界正是真理等價值的顯現場所。看得出來,海德格爾力圖去除原來那種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學的真理觀。為此,他痛快而莊嚴地宣布:“唯當此在存在,才‘有’真理。唯當此在存在,存在者才是被揭示被展開的。唯當此在存在,牛頓定律、矛盾律才在,無論什么真理才在。此在根本不在之前,任何真理都不曾在,此在根本不在之后,任何真理都將不在。”⑩
此后,海德格爾對后形而上學的真理觀有了更為自覺的認識與追求。1949年,海德格爾在《論真理的本質》的注解里,就更明確地認為:“真理的本質乃是本質的真理”[11]。這即是說真理是存在論的,而不是認識論的,我們沒有辦法去認識一個真理,去發現一個真理,因為真理不是可以離開這個世界的“對象物”。因此,海德格爾后來甚至直接到藝術作品、到語言中去傾聽這種真理。
維特根斯坦在早期的《邏輯哲學論》中就提出了諸如“對于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12]這樣的反對追問世界的形而上學真理的思想,認為諸如“美是什么”這樣的真理/知識問題是無意義的,因為這種對真理/知識的欲求是因為我們忽略了語言的邏輯分析所產生的一種幻象錯覺。在后期的《哲學研究》中,維特根斯坦在清理自己前期的思想的基礎上更徹底地提出“語言游戲”、“家族相似”等一些更具后形而上學意味的范疇,認為:“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達式來刻畫這種相似關系:因為一個家族的成員之間的各種各樣的相似之處:體形、相貌、眼睛的顏色、步姿、性情等等,也可以同樣方式互相重疊和交叉。——所以我要說:‘游戲’形成一個家族。”[13]也就是說,世界的本質是不存在的,同樣,語言的本質以及語言與世界的同構性本質也是不存在的,“一個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使用”[14]。“當哲學家使用一個詞——‘知識’、‘存在’、‘對象’、‘我’、‘命題’、‘名稱’——并試圖把握事物的本質時,人們必然經常的問自己:這個詞在作為它的老家的語言游戲中真的是以這種方式來使用的嗎?”[15]也就是說,試圖通過研究語言的確定的本質從而來把握世界的確定本質,這只是一種幻覺,世界沒有共同的本質,只有相似處和親緣關系,語言是一種游戲,一種行動中的存在。
通過上述簡要的勾勒與論述我們發現,現代以來的思想家的確都在不停地叩問這種后形而上學真理的合法性。其原因主要是這種后形而上學的真理觀,符合現代性的世俗性、人文性,它不把人的現實人生與生活世界虛幻化、否棄化,同時也具有后現代性的差異性與多元性。為此,后形而上學的真理觀得到了當下更多認同。與之相應,公共批評研究范式也認同于這種后形而上學的思想旨趣,而對于精英主義研究范式所倡導的所謂終極的審美、純粹的道德則保持高度的警覺。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后形而上學的真理觀正與阿倫特意義上的政治的真理觀有內在的一致。
其次,大眾文化研究的對象——大眾文化自身有后形而上學的訴求。
從發生學的角度看,大眾文化是消費社會的產物。雖然對于消費社會的具體發生時間存在著不同理解,但大都認同消費社會的發生是20世紀以后的事情。相較而言,中國的情況更為復雜。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中國,隨著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力度的加大,大眾文化迅速發展。但此時的中國是否進入了消費社會,至今仍是聚訟紛紜。然而,大眾文化是這個世俗化時代的文化則確定無疑。因此從思想型的角度看,它必然是后形而上學的。也即大眾文化在價值追求上是去形而上學的,它不會再到另一個世界去追求什么終極的關懷、絕對的價值和抽象的意義。當然這并不是說,大眾文化就不會有價值追求,而是說,大眾文化的價值追求是后形而上學的價值追求。這種后形而上學的價值追求,也就使得公共批評的研究范式應該調整價值立場。
2.它立足于公共性的價值立場
由于公共批評是后形而上學的思想型,這就使得它的價值立場也必定要與之一致。那么,后形而上學旨趣的價值如何呈現呢?
前已述及,后形而上學思想不再追問那種另一個世界的真理,認為根本就沒有一個絕對的真理,這很契合阿倫特所提倡的政治的真理觀。所謂政治的真理觀,它有三層含義:
一是真理只是一種意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并都可向世界公開,每個人的意見中都有真理的成分,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的意見。我們要如蘇格拉底一般,用辯證法將這些意見呈現出來,然后依靠一種交流理性,盡量使意見達成共識。但達成共識,并不是要取消意見,而是要形成意見式的真理。在阿倫特看來,真理要在意見中去尋找。只有那種意見式的真理,而沒有那種非意見式的真理。那種所謂非意見的真理,是柏拉圖以來的哲學玄想,是對蘇格拉底的一個誤解。政治的真理,即是一種意見,或說政治的真理是意見式的真理(truth of poinion)[16]。這種真理即意見的政治真理觀,正是公共批評堅持的真理觀。公共批評堅持這種真理觀,就使得大眾有可能參與到這種學術研究中來,就使得公共批評視野下的大眾文化,有可能成為一個有差異存在的公共領域,這無疑適合于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里的文化旨趣。
二是意見是存在論的。也即意見不是一個認識論范疇,不是一個純粹的主體行為,不是個人的玄想、任意的虛構。意見是對這個有公共性的、塵世的世界的傾聽。因為世界總是向我敞開其自身的世界,人們在世界中各有不同的位置,因此世界向每個人展現出不同的面貌。然而,“那向每個人所展現的是同一個世界,盡管在這個世界中人們以及他們的立場有多么的不同,因而他們的意見也就不同,但是‘你我同樣都是人’”[17]。這即是說,世界的公共性,保證了意見是有可交流性的,是有可能通達意見的真理的。
三是意見需要一個公共空間予以呈現。對于意見來說,公共空間至關重要。一方面意見的表達離不開它,沒有一個公共空間,意見就不能呈現出來。另一方面,要尋找意見的真理,也離不開它。只有在公共空間,在一個允許差異、有自由表達保障的領域中,不同的意見才能夠依靠友誼,經過說服,達到意見式的真理。
對于政治的真理而言,最為重要的是要有公共空間。只有有了公共空間,才有可能有意見,才有可能有作為價值論的意見式的真理存在。因此,從價值追尋的角度看,公共批評研究范式要立足于公共性的價值立場。這種公共性的價值立場,具體而言:一是公共批評要堅持公共性,要努力推動公共領域的建設。二是公共批評的價值都是公共性的價值,都是阿倫特意義上的政治價值。在阿倫特看來,我們應該在公共性中去尋找自由——政治自由;在公共性中尋找審美——政治審美;在公共性中尋找神圣——政治神圣;在公共性中去尋找言說——政治言說。
由于公共批評研究范式把大眾文化的價值定位于公共性價值,因此在這種理論視域中,大眾文化是否有公共性,便成為其思考的一個重要質素。民粹主義研究范式的主要局限性之一,就是把那種沒有可見性的私人文化消費當成公共性,把政治冷漠、去公共性價值當成一種積極性價值來提倡。新意識形態研究范式對民粹主義研究范式的批評之所以成立,最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民粹主義研究范式沒有把政治自由這一重要問題處理好。
當然,公共批評研究范式往往在規范的意義上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眾文化視為公共領域的表征,同時也是公共領域推動的力量。這就多少會與政治相關聯。其實,公共批評研究范式中所涉及到的政治不是黨派政治或實體政治,而是一種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政治,是一種學術政治乃至校園政治。
3.它堅持語境化和學理式的探討風格
落到實際的大眾文化研究操作層面,公共批評研究范式往往把自己的批評實踐塑造為語境化和學理式形象。
語境化是指在批評實踐中,將研究對象重新置入在關系場域中,對文本進行仔細解讀,具體分析這個文本所表征的場域關系,如它如何發生,為什么這樣發生,有哪些力量參與了這種發生。這就不是抽象的從理論到理論的邏輯演繹,不是套用理論而毫無現場感和語境感的分析,更不是把大眾文化生硬地置入好與壞、積極與消極等二元對立之中,而是把它看成是“一個由不同的文化力量構成的相互矛盾的混合體”[18],一個有待我們語境化的具體分析的混合體。這種去除二元對立的大眾文化觀,不僅與前面提到的公共批評認同后形而上學的思想旨趣一致,同時,也與互聯網這種大眾文化生存的新公共性空間所具有的復雜性是一致的,關于后者,陶東風先生已作了較為深入的探究[19]。
公共批評還特別注重學理式分析,倚重一種可交流的公共理性,對大眾文化現象作合乎學術理路的分析和反思,探討它所表征的文化邏輯。簡言之,公共批評對那種純粹的思想臆想,對那種毫無學術史意識與指向的知識生產,基本上持一種謹慎的態度,它是有學術追求的。如此說來,公共批評與一般的社論標簽式、口號標語式的批判是不相容的。這也就是公共批評為什么要研習政治哲學、社會理論等思想知識,為什么要強調自己所涉及到的政治是學術政治的一個原因。
四、公共批評研究范式的一個研究案例
為有一個較為感性的理解,我們可以近年來對紅色經典的惡搞現象為例對公共批評研究范式加以說明。對于近年來涌現的對紅色經典的惡搞現象,公共批評并不抽象地認為,惡搞是非審美、不道德的,更不簡單地認為惡搞紅色經典,就是階級政治的隱喻。公共批評主張對惡搞的文本進行詳盡分析,看看惡搞發生的語境、文化邏輯是什么,給我們的啟發有哪些,等等。
首先,公共批評認為不能抽象地對某一現象進行批評。我們以惡搞雷鋒這個文本為例。對于這個文本,我們要分析它是如何惡搞的。據考察,首先是傳言要拍網絡電影《雷鋒的初戀女友》,后來被廣電總局叫停;但網上還是出現了雷鋒與初戀女友的圖片;后來又出現了“雷鋒安全套包裝”、動畫片《雷鋒的故事》;另外還有諸如“雷鋒是因為幫人太多累死的”、“雷鋒做好事不留名但都記日記里了”等等惡搞言論在網上流行開來。要更為仔細地分析上述惡搞,我們還應該找到雷鋒的文本本身。僅以惡搞雷鋒談戀愛這一點看。《雷鋒日記》的確提到過雷鋒談戀愛之事。1962年7月29日,雷鋒當年的指導員找雷鋒談話,原因是有人說雷鋒和一位女同志談情說愛,在《雷鋒日記》中,雷鋒的想法是被這樣記載的:“從內心往外說,我沒有和哪個女同志談情說愛……我是在黨哺育下長大成人的,我的婚姻問題用不著自己著忙。”[20]看得出來,雷鋒生前的確有過關于愛情方面的傳聞。然而,雷鋒究竟是否談過戀愛,本來是一個事實真理的問題,卻由于種種原因得不到回答。有人說,雷鋒在參軍前的確談過戀愛[21];也有人說,雷鋒生前沒談過戀愛[22]。這兩種對立的說法都出自雷鋒的生前戰友之口。我們若信前說,就不能信雷鋒;若信后說,那倒是有《雷鋒日記》為證,也有后說可支持。但問題是,《雷鋒日記》中也有關于雷鋒戀愛的傳聞,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而從日記中看,雷鋒也不是沒有戀愛的訴求,雖然他將這種訴求投射給了組織。但不管怎樣,我們得不到雷鋒是否戀愛過的真相,這種真相得不到言說,只好以惡搞的方式來表征。
其次,公共批評主張語境化的闡釋。雷鋒戀愛之所以被惡搞,其發生的語境不容忽視。與此有關的語境至少有兩種:一是雷鋒當年所處的語境,二是當下惡搞所處的語境。前者應以《雷鋒日記》為文本來觀照,讀過《雷鋒日記》的人就會知道,里面的確有明顯的敵友二元對立之分。深受意識形態教化的雷鋒,在那個年代寫這種日記非常正常。也是在那種語境下,包括雷鋒在內的私人生活都被組織化了,甚至出現了去私人領域的圖景,這也很正常。然而,時過境遷,離開了那個語境,走到了當前這樣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講求和諧的社會語境下,私人生活的高漲也就合乎邏輯了。此時對當年的去私人領域進行一番搞笑式的滑稽模仿與重構,與當下大眾文化的娛樂本性有了相通之處。同時,這也是一種對當年語境告別,對當下語境試探乃至對未來語境希望的隱喻。
再次,公共批評追問大眾文化的邏輯。雷鋒被惡搞,這已然是一個大眾文化的文本,但這種文本的文化邏輯并非如上面說的這樣簡單,其內在的邏輯是較為復雜的。如果我們從上述惡搞雷鋒戀愛的隱喻式的表達中可以發現一種公共性的情結的話,那么廣電總局叫停有關雷鋒戀愛的大眾文化生產,則多少說明了當代大眾文化存在的復雜性,即大眾文化的存在需要一個公共領域的維護,同時,大眾文化的存在也需要為一個公共領域的存在進行伸張。這個公共領域,在目前看來還非常模糊和混雜。甚至可以說,一方面,主流文化希望借助于大眾文化來傳播其經典性價值,而另一方面,大眾文化又根本沒有這個能力,甚至還會起到反面作用,即顛覆主流文化所希望的經典性價值。這是否說明,惡搞雷鋒本身就是一種娛樂行為,一種沒有多少直接意義上的公共性的娛樂呢?而隱藏在其背后的商業利益驅動或許是一個主要的文化邏輯。對此,有學者敏銳地指出了惡搞的復雜文化邏輯,認為包括惡搞雷鋒在內的惡搞紅色經典文化是“在消費主義話語和革命政治話語的夾縫中生存”[23],并且清醒地指出:“大眾文化遵循的是‘有奶便是娘’的實用主義邏輯。如果完全本真地翻錄和復制十七年時期的革命經典不但能夠得到主流話語的嘉獎而且能夠贏得利潤,那么,大眾文化的制作者仍然會不顧一切地擁抱這個原汁原味的革命敘事。”[24]這當然主要是對大眾文化的制作方來說的,對于大眾文化的接受而言,情況也許會復雜得多。因此,作為大眾文化的批評理論就有存在的合法性了,至少它是有規范的公共性價值追問的,這多少對大眾文化的惡搞會有爆破與反思的作用。
最后,公共批評堅持公共性價值。雷鋒戀愛之所以能被惡搞,甚至作為一種對主流文化的反抗而存在著的亞文化形態[25],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主流文化代表的價值不具有公共性了。舊有的價值規范已然失效,才有可能出現惡搞。雷鋒時代的戀愛觀與今天很不一樣了,現在極少有人說自己的“婚姻問題用不著自己著忙”。這種把婚姻等私人領域的問題公共化的做法,是對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雙重摧毀[26]。在這樣的語境下,如果國家機器還將包括雷鋒在內的紅色經典塑造為一種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和意識形態[27],就難免不被惡搞。然而,如果沒有一點正經,僅僅是一種無聊的娛樂與商業利益的惡搞,就應該引起公共批評的反思。諸如惡搞紅色經典的公共性價值在哪里,大眾文化的文化意義該如何來建構,如何把大眾文化生產引入常態[28]等,都是值得我們不斷思考的問題。畢竟公共批評,是一種在后形而上學時代追問文化公共性乃至文化意義的批評形態。簡言之,公共批評并不放棄批判的立場和獨立性的追求。
注釋
①②⑦[16]陶東風:《文學理論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評》,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65—188、167—171、1—22、439頁。③李澤厚等:《關于文化現狀與道德重建的對話》,《東方》1994年第5期。④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頁。⑤王曉明:《半張臉的神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7—26頁。⑥[英]約翰·菲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王曉玨、宋偉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49頁。⑧[德]恩斯特·貝勒爾:《尼采、海德格爾與德里達》,李朝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89頁。⑨[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張念東、凌素心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91頁。⑩[德]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熊偉校,陳嘉映修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260頁。[11][德]馬丁·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上卷),孫周興編,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235頁。[12][英]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轉引自江怡:《〈邏輯哲學論〉導讀·正文選譯》,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4頁。[13][14][15][英]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李步樓譯,陳維杭校,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67、43、116頁。[17][德]漢娜·阿倫特:《哲學與政治》,賀照田編《西方現代性的曲折與展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6頁。[18][英]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第二版),楊竹山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6—17頁。[19]陶東風:《網絡交往與新公共性的建構》,《文藝研究》2009年第1期。[20]雷鋒:《雷鋒全集》,人民武警出版社,華文出版社,2003年,第78頁。[21]《雷鋒確實談過戀愛》,http://www.harbindaily.com/200603/K20060328108C47012382524A8C418E9B27E43D40.html.[22]《我沒和雷鋒談過戀愛》,http://www.jschina.com.cn/gb/jschina/news/luntan/zzpl/userobject1ai1174156.html.[23]陶東風主編《當代中國文藝思潮與文化熱點》,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24頁。[24]陶東風:《后革命時期的革命書寫》,《當代文壇》2008年第1期。[25]趙勇:《當紅色經典遭遇惡搞》,《勵耘學刊》(文學卷)2008年第2期。[26]阿倫特:《集權主義的起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574—596頁。[27]劉康:《在全球化時代“再造紅色經典”》,《中國比較文學》2003年第1期。[28]童慶炳:《在歷史與人文之間徘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69—4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