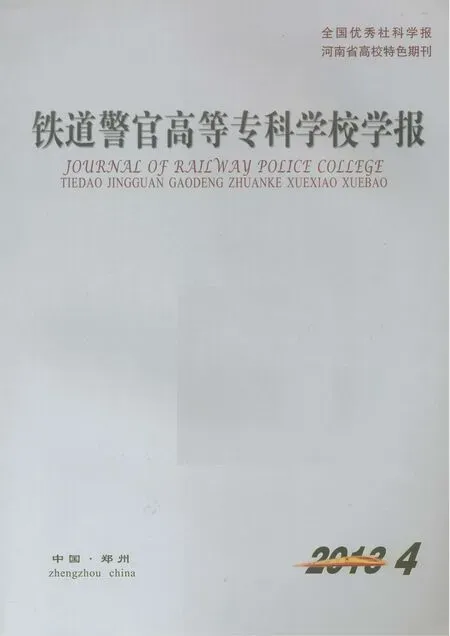徇私枉法罪疑難問題探析
肖晚祥,許浩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 200031;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上海 200003)
徇私枉法罪疑難問題探析
肖晚祥,許浩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二庭,上海 200031;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上海 200003)
徇私枉法罪主體“司法工作人員”的界定應采職責說。“徇私”、“徇情”動機是主觀方面構成要件,不包含徇單位、集體之私。利用職務便利是隱含的構成要件。在該罪的三種枉法行為方式中,“明知”是指有確定性的認識,但不一定要有實質性的認識;“有罪的人”的認定應采涉嫌犯罪說,“有罪的人”之外,皆為“無罪的人”;故意輕追訴可以納入枉法行為范疇,但故意重追訴因不能為徇私枉法行為方式的最大可能含義所覆蓋,故按照現行刑法規定,不能構成徇私枉法罪。
徇私枉法罪;徇私;徇情;枉法
根據《刑法》第399條的規定,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為。
一、“司法工作人員”的界定
徇私枉法罪是一種比較典型的瀆職犯罪,犯罪主體必須是司法工作人員。所謂“司法工作人員”,根據《刑法》第94條的規定,是指有偵查、檢察、審判、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刑法》第94條是總則條款,其對“司法工作人員”的界定是一般意義上的,并不是僅僅針對徇私枉法罪,因此,盡管其對“司法工作人員”的界定包含了有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但實際上結合刑法關于瀆職罪立法的體系以及徇私枉法罪的客觀行為方式來看,有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①此處對有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是作狹義理解的,不包括獄偵部門。筆者認為,把獄偵部門歸入有偵查職責的工作人員之列更為合適。實際上不能成為徇私枉法罪的主體,因為其缺乏對刑事案件的追訴和審判職責,這種職責正是構成徇私枉法罪的關鍵所在。有監管職責的工作人員,如果有徇私枉法的行為,構成瀆職犯罪的,一般會構成徇私舞弊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罪。因此,作為徇私枉法罪主體的“司法工作人員”實際上只包括負有刑事案件的偵查、檢察和審判職責的工作人員。
關于徇私枉法罪的主體“司法工作人員”到底是一種身份還是一種職責,曾經一度存在爭議,并大致形成了身份說、職責說和身份與職責兼具說三種觀點。筆者認為,對徇私枉法罪的主體“司法工作人員”界定標準采取職責說更為合理。首先,身份說不符合刑法立法的精神,也和相關的立法解釋相沖突。結合瀆職罪的立法體系來看,徇私枉法罪的規定顯然是僅針對刑事案件的追訴和審判過程來說的,因此,作為其主體的司法工作人員應當是從事刑事案件的追訴和審判工作的人員,而不能包括具備司法工作人員身份的從事民事、行政審判工作的人員。對于負有民事、行政案件審判職責的工作人員,其徇私枉法的,刑法有相應的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加以規制。《刑法》第94條對于“司法工作人員”的解釋也是以職責為標準的,因此,刑法立法對于徇私枉法罪中“司法工作人員”的界定也是以職責為標準的。另外,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規定: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雖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在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時,有瀆職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關于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這一解釋實際上明確了瀆職罪的主體界定采“職責”標準。其次,身份與職責兼具說既不當地限制了徇私枉法罪的打擊范圍,也與立法精神和立法解釋的規定相沖突。如果按照身份與職責兼具說的觀點,不具有司法工作人員身份而實際負有刑事案件追訴和審判職責的人員就不能構成徇私枉法罪的主體,但這些人員徇私枉法,同樣構成對其所承擔的職責的褻瀆,其社會危害性與既有身份又有職責的人員徇私枉法并無二致,如果對其不能以徇私枉法罪論處,顯然是不合理的。最后,職責說符合瀆職罪的本質,與立法精神和立法解釋的規定相契合。徇私枉法罪本質上是一種瀆職犯罪,其社會危害性體現為行為人對其所承擔的職責的褻瀆,而非對其身份的褻瀆,因此,在徇私枉法罪主體的界定中,身份只是表象,職責才是本質,雖然身份與職責之間往往存在著常態的聯系,但如果身份不體現為特定的職責,其本身在徇私枉法罪的認定中是沒有意義的。
二、“徇私”、“徇情”的含義、性質及定位
(一)“徇私”、“徇情”的含義
關于徇私枉法罪中“徇私”、“徇情”的含義,刑法和司法解釋都未作出明確規定。但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徇私舞弊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徇私曾作過如下規定:司法工作人員為貪圖錢財、袒護親友、泄憤報復或者其他私情私利,具有第1條(1)至(7)款行為之一的,應當依照《刑法》第188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該解釋雖然系1997年《刑法》實施之前的規定,但現行刑法的徇私枉法罪系從1979年《刑法》中的徇私舞弊罪細分而來,從歷史角度來看,該解釋對于正確理解現行刑法徇私枉法罪中“徇私”、“徇情”的含義具有積極的參考意義。根據該解釋的規定,“徇私”既包括徇私利,也包括徇私情。所謂私利,主要是指個人所能得到或占有的物質利益,如金錢、物品等有形的具有價值的物,其次還應該包括無形利益,如職務升遷等。所謂私情,則包括親情、友情、愛情等,外延相當廣泛。1997年《刑法》把“徇私”和“徇情”并列加以規定,其原因固然可能是出于對“徇情”的強調,但筆者認為按照刑法解釋的原理,“徇情”已經從“徇私”中獨立出來了,因此,“徇私”不應當再包含徇私情的內容。所以,在徇私枉法罪的條文中,“徇私”應當指的是徇私利,而“徇情”則是指徇私情。
關于徇“單位、集體之私”是否屬于徇私的范疇,司法實踐中存在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徇“單位、集體之私”不屬于徇個人私利,而是屬于徇“公”,因此不屬于徇私的范疇,不能構成徇私枉法罪。其理由是:(1)將徇“單位、集體之私”理解為徇私并不符合邏輯,單位、集體是與自然人個人相對應的概念,將徇“單位、集體之私”說成是徇私并不合理。(2)出于單位利益而實施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等行為,不視為徇私,也有相應的罪名可以適用,不會放縱犯罪[1]。(3)《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也規定: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的徇私是指徇個人私情、私利。從刑法體系解釋原則看,也不應將徇私理解為單位之私[2]。另一種觀點認為,徇“單位、集體之私”雖然屬于徇“公”,但徇私枉法罪的罪狀,既規定了徇私枉法,又規定了徇情枉法,因此,徇“單位、集體之私”的行為可以通過解釋歸入“徇情”的范疇,同樣可以構成徇私枉法罪[3]。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徇“單位、集體之私”同樣屬于徇私的范疇,構成徇私枉法罪是沒有任何障礙的。其理由是:(1)“公”和“私”都是相對的概念,相對于國家之公而言,單位、集體之公即為私。把“單位、集體利益”視為“公”,實際上是一種集體本位主義。在以徇私為要件的犯罪中,司法工作人員正當履行職責所實現的利益、刑法所要保護的法益就是“公”,非出于實現“公”的利益和保護“公”的法益的意圖,便應評價為“私”。(2)徇單位、集體之私侵害的法益與徇個人之私并無區別,都是對職責的褻瀆。(3)單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往往密切相關。(4)將徇“單位、集體之私”排除在徇私枉法罪之外,不符合立法意圖[4]。
筆者贊成第一種觀點,認為徇“單位、集體之私”的行為一般不屬于“徇私”、“徇情”的范疇。首先,“公”、“私”相對性的觀念是無限的。如果單位、集體利益可以解釋為私,那么一省一市的利益也可以解釋為私,筆者不知道這種相對性該到何處截止,秉持這種觀念容易陷入相對性的泥沼。其次,如果把司法工作人員正當履行職責所實現的利益、刑法所要保護的法益理解為該罪中的“公”,那么該罪關于“徇私”、“徇情”主觀要件的規定就毫無意義,因為“徇私”、“徇情”的主觀動機與刑法保護的法益聯系甚微。這種理解導致的結果就是刑法關于“徇私”、“徇情”的規定被虛置,因為這會導出“只要是枉法的行為就一定是徇私的”這一結論。再次,“徇私”、“徇情”只是動機,是主觀方面的東西,與犯罪行為侵害對象的法益沒有多大關系。是否具備“徇私”、“徇情”動機確實都不影響瀆職的構成,但侵害相同的法益并不一定構成相同的犯罪。最后,將“單位、集體之私”排除在徇私枉法罪之外也已為《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所采納,該文件第6條第(4)項規定:“徇私舞弊型瀆職犯罪的‘徇私’應理解為徇個人私情、私利,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了本單位的利益,實施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397條第1款的規定定罪處罰。”
(二)“徇私”、“徇情”的性質
關于“徇私”、“徇情”的性質,主要存在犯罪動機說、犯罪目的說、行為說、動機與行為說等幾種觀點。筆者認為,“犯罪動機說”的觀點相對比較合理。首先,“犯罪目的說”混淆了目的和動機。一般來說,犯罪動機先于犯罪目的,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心理動因,它直接導致犯意的產生,而犯罪目的則是犯罪行為人期望通過犯罪行為所達到的目標。有犯罪動機不一定會產生犯罪目的和犯罪行為,而犯罪目的則與犯罪行為緊密關聯。在徇私枉法罪中,“徇私”、“徇情”只是犯罪動機,“出入人罪”才是犯罪目的。其次,“行為說”也不能契合司法實踐的要求。行為人是否“徇私”、“徇情”,當然要通過其客觀行為進行推斷,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并沒有獨立的“徇私”、“徇情”行為,比如說在袒護親友、泄憤報復動機下的枉法行為,實際上行為人只有一個枉法的行為,總不能說枉法行為就是“徇私”、“徇情”行為吧?另外,如果把收受賄賂的行為解釋為徇私行為的話,那么受賄行為在徇私枉法罪中就沒有獨立的意義,而只是徇私枉法罪的客觀要件行為之一,這與《刑法》第399條第4款關于受賄罪與徇私枉法罪擇一重罪處罰的規定是相沖突的。最后,“動機和行為說”不僅將“徇私”、“徇情”作為客觀方面的要素,同時也作為主觀方面的要素,顯然犯了將主客觀要件混為一談的錯誤。既然認為“徇私”、“徇情”是犯罪的動機,而不是故意的內容,那么就不能要求有與“徇私”、“徇情”相對應的表現故意內容的客觀事實。所以,認為“徇私”、“徇情”既是主觀方面的犯罪動機又是客觀方面的表現的觀點,本身就有自相矛盾之嫌[5]。因此,筆者認為“徇私”、“徇情”作為徇私枉法罪的犯罪動機是相對合理的。
(三)“徇私”、“徇情”在犯罪構成中的定位
關于“徇私”、“徇情”是否是徇私枉法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問題,學界存在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徇私”、“徇情”只是行為人的一種主觀動機,是引起枉法犯罪的原因,但不是徇私枉法罪的必備構成要件,它不影響犯罪的性質,只是可以影響量刑的因素[6]。另一種觀點認為,“徇私”、“徇情”是徇私枉法罪的必備構成要件,雖然在刑法理論上,犯罪動機不應作為犯罪構成的要件,但如果刑法條文對其作了明文規定,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則,就應當把其作為犯罪的構成要件,不然,就有違背罪刑法定原則之嫌[7]。
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認為“徇私”、“徇情”是徇私枉法罪的必備構成要件。刑法立法一般不將犯罪動機規定為犯罪構成要件,因為犯罪動機是行為人產生犯意并實施犯罪行為的原因,是藏于行為人內心深處的東西,具有先刑法規范的特征,往往是犯罪學研究所關注的問題。現代刑法基于客觀主義的立場,其關注的焦點是犯罪行為,而不是犯罪人。現代刑法體系基本上都是以犯罪行為為中心建立起來的,與犯罪行為緊密聯系的是犯罪目的和危害結果,而犯罪動機相對來說距離犯罪行為這個中心比較遙遠。犯罪動機的作用往往只是導致犯意的產生,因此,刑法對犯罪動機的評價往往不會上升到構成要件的高度,而經常是作為評價犯罪人主觀惡性的一項指標在具體量刑中加以考量。然而,一般理論并不排除特殊情況下的例外,徇私枉法罪恰恰就是刑法立法的一個例外,立法者將“徇私”、“徇情”動機明確規定在刑法條文中,使其成為徇私枉法罪的構成要件,可能有其特殊的考慮,也可能僅僅是傳統觀念使然。“徇私”、“徇情”作為徇私枉法罪的構成要件有其積極的作用,也可能存在不合理之處,但不管如何,在司法實踐中,應該嚴格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則,正確把握徇私枉法罪的構成要件,在行為人不具有“徇私”、“徇情”動機的情況下,即使其實施了枉法刑事追訴或枉法刑事審判的行為,也不能以徇私枉法罪論處。
三、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理解與把握
(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徇私枉法罪的隱含構成要件
徇私枉法罪的罪狀中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規定,對于成立徇私枉法罪是否必須具備“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這一要件,實踐中存在肯定和否定兩種觀點。筆者認為,徇私枉法罪作為典型的瀆職犯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題中應有之義。對此,應作體系解釋,認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徇私枉法罪的隱含構成要件。
(二)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理解
對于何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存在狹義和廣義兩種解釋。狹義說認為是指直接利用自己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自己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務便利,也包括利用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廣義說認為,除了包括狹義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之外,還包括利用自己的職務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即利用自己的職務和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借助與自己在職務上沒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
筆者認為,在徇私枉法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應作狹義解釋,即只能直接利用自己職務上的便利,而不能通過自己職務上的影響和工作聯系,利用他人職務上的便利,這是因為徇私枉法罪屬于瀆職犯罪,瀆職犯罪的構成以行為人必須負有相應的職責為前提。具體而言,行為人必須負有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檢察、審判等職責,否則就不可能單獨構成徇私枉法罪。當然,利用自己的職務和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借助與自己在職務上沒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實施徇私枉法的行為,理論上很有可能與枉法行為的具體實施者構成徇私枉法罪的共犯,但這在本質上還是枉法行為的具體實施者的瀆職行為。因此,對于利用自己的職務和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聯系,借助與自己在職務上沒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實施徇私枉法行為的,應當視實際情況或者以徇私枉法罪的共犯論處,或者以刑法中其他相關罪名論處。
四、“枉法”的認定
根據刑法規定,徇私枉法罪中的枉法行為表現為三種形式:(1)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 (2)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 (3)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
(一)“明知”的界定
筆者認為,徇私枉法罪中的“明知”應當是一種確定性的明知,但不一定是實質性的明知。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簡稱《立案標準規定》)中將“明知是有罪的人”解釋為“明知是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該規定是從徇私枉法行為人角度而言的,即明知被包庇者是“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人”。至于被包庇者最終是否會被法院依法確定為實質有罪,尚需經過司法機關一系列的訴訟活動。同時需要明確的是,司法機關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與徇私枉法行為人對被包庇者“明知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二者中“認為”與“明知”的標準和內容是不同的,司法機關作為“認為”的主體,有著強大的查證能力和廣泛的證據來源,某些案件在立案前已經過初查,而徇私枉法行為人的“明知”是指犯罪主體對犯罪對象——“有罪的人”的明知,“明知”的標準和內容理應低于司法機關“認為”的標準。
如某司法工作人員聽說其朋友殺了人,該司法工作人員即屬明知其朋友是“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人”。也就是說,法律在規定該司法工作人員的徇私枉法行為時,要求明知其朋友是“有罪的人”,對其朋友殺人的時間、地點、過程、動機以及最終能否被法院確定為實質有罪等不要求其明知,這就是一種確定性認識。而司法機關認為該司法工作人員的朋友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予以立案,則需要掌握一定的證據材料,證明被立案者有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事實的存在,這就是一種具體的實質性明知[8]。
“明知是無罪的人”的情況則相對來說比較簡單,所有不具有犯罪嫌疑的人都應當被認為是屬于“明知是無罪的人”。
在“明知”的把握上,應當是在實施行為之前,或者至少在實施行為之時,行為人應當就處于“明知”的主觀狀態,如果是在事后才知道的,則不應當認定為“明知”。如郭某系某市刑警隊中隊長,在一起摩托車被盜案中,郭某懷疑該案系元某所為,遂帶領民警前去傳喚元某到刑警隊接受訊問。因元某的親屬向郭某索要傳喚手續雙方發生爭執,郭某和其他民警強行用手銬將元某帶至刑警隊。經過訊問和辨認,無法確認元某是該盜竊案的犯罪嫌疑人,但郭某未將這一情況向上級領導匯報。后元某和其父被公安機關以涉嫌妨礙公務罪刑事拘留。
公訴機關認為,郭某在不能認定元某系犯罪嫌疑人時不如實向領導匯報,隱瞞了元某不能認定是犯罪嫌疑人這一重要情節,致使元某和其父被公安機關以涉嫌妨礙公務罪刑事拘留,其行為觸犯了《刑法》第399條第1款的規定,構成徇私枉法罪。
郭某的辯護律師認為,根據《人民警察法》第9條的規定,對被指控有犯罪行為的或有現場作案嫌疑的人,人民警察即可將其帶至公安機關留置盤查,無需出具任何書面手續。因元某在當時被失主及當地派出所民警指控有盜竊嫌疑,所以,身為人民警察的郭某等人有權將元某帶至刑警隊。元某是被帶至刑警隊后,經過辨認和訊問才被排除盜竊嫌疑,故在此之前,不能認為郭某“明知”元某是無罪的人,郭某對元某的盤查和訊問行為只是正常履行職責的行為。在經過辨認和訊問,排除了元某的盜竊嫌疑之后,郭某雖未將這一情況上報,但其也并未對元某實施枉法追訴行為。元某及其家人為了抗拒警方傳喚,暴力圍攻、毆打執法民警,并當場將民警打傷,是暴力妨礙公務的現行犯。公安機關對元氏父子以妨礙公務罪立案追究與郭某未將元某不具有盜竊嫌疑的情況上報之間并無必然的聯系,以妨礙公務罪對元某父子進行追究并非出于郭某的決定,并且這一追究也并無不當。被告人郭某既無徇私枉法的主觀故意,也無徇私枉法的客觀行為,所以不構成徇私枉法罪。
法院最終采納了辯護律師的意見,認定郭某的行為不能構成徇私枉法罪。
(二)“有罪的人”和“無罪的人”的界定
1.對“有罪的人”的理解與認定
徇私枉法罪要求行為主體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對于“有罪的人”應如何理解,存在法院判決說、立案偵查說、涉嫌犯罪說等幾種觀點。筆者認為,應當采納“涉嫌犯罪說”觀點。理由如下:第一,在前文關于“明知”的分析中提到,徇私枉法罪中的“明知”必須是在行為之前或者行為當時。如果依照法院判決說的觀點,那么在法院的判決結果出來之前就沒有任何人能夠“明知是有罪的人”,這樣,涉嫌徇私枉法的偵查、檢察人員就都不符合在枉法行為之前或者之時就是“明知是有罪的人”的要求,也就不可能構成徇私枉法罪,這顯然不合常理。第二,立案偵查說的明顯缺陷則在于無法將司法工作人員明知他人涉嫌犯罪,但徇私枉法不立案的情形包含在內,這顯然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的立法意圖。第三,涉嫌犯罪說最能契合徇私枉法罪的立法本意。徇私枉法罪的設立是為了強化司法工作人員的職責意識,規范司法工作人員的行為,有效地打擊徇私枉法行為。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放縱涉嫌犯罪者的行為褻瀆了其職責,應納入該罪規制的范疇。
2.“無罪的人”的理解與認定
對于徇私枉法罪中“無罪的人”的理解,司法實踐中同樣存在爭議。有觀點認為,“無罪的人”包括事實上無罪的人和法定無罪的人[9]。也有觀點認為,“無罪的人”并不等同于“不需要進行刑事追究的人”,而僅是指沒有實施犯罪行為或者不符合犯罪主體資格等不齊備犯罪構成要件的人。還有觀點認為,“無罪的人”是指無特定之罪,比如說司法工作人員明知行為人犯了搶奪罪而徇私枉法,以搶劫罪對其進行追訴,因為行為人并未犯搶劫罪這一特定之罪,故也應當認為其屬于“無罪之人”[10]。
上述第一種觀點將“無罪的人”擴張解讀為包含“有罪但不需進行刑事追究的人”顯然是不妥的,這種解讀超越了“無罪的人”這一刑法用詞最大的可能文義和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明顯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上述第二種觀點對“無罪的人”的含義作犯罪構成要件意義上的界定,似乎與徇私枉法罪的立法原意不太契合,而且實際操作起來會與“有罪的人”界定標準的“涉嫌犯罪說”產生沖突,因此也不可取。第三種觀點更是陷入了相對性的泥沼,依此觀點的邏輯,如果司法工作人員明知行為人犯搶劫罪而徇私枉法,以搶奪罪進行追訴,那也應該屬于“使無罪的人受追訴”的情形,但這又明顯是屬于“出罪”的行為,這在司法理念的解釋上本身就是有矛盾的。
筆者認為,對“無罪的人”的理解應當結合其“有罪的人”的理解來把握,該罪中對于“無罪的人”和“有罪的人”的判斷標準應該是統一的。簡單地說,界定了“有罪的人”之后,“無罪的人”就不言自明了,“有罪的人”之外的人都應該屬于“無罪的人”,這里不存在中間狀態。
(三)故意加重追訴或故意減輕追訴的問題
徇私枉法罪中的枉法行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枉法追訴行為,包括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的行為和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的行為。另一類是枉法裁判行為,即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為。刑法對枉法裁判行為的規定較為概括,但對枉法追訴行為則規定得相對比較細致。于是,司法實踐中就產生了故意加重追訴或者故意減輕追訴的情況是否屬于徇私枉法罪的枉法追訴行為的疑問。如王某系某公安派出所的治安警長,在查處祝某販賣毒品案中,從祝某身上查獲購毒者童某支付的購毒款2100元,從祝某隨身攜帶的包內查獲幾包白色晶體和百余粒紅色藥片狀顆粒及人民幣1萬余元;從童某處查獲祝某賣給童的甲基苯丙胺6.55克。據祝某交代,從其包內查獲的物品分別是甲基苯丙胺(約20克)和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麻古”。后王某接受請托,利用辦理祝某販毒案的便利,將從祝某包內查獲的幾包白色晶體和百余粒紅色藥片狀顆粒藏匿在自己的辦公桌抽屜內。后祝某因被認定販賣毒品甲基苯丙胺6.55克,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罰金4000元。
該案中王某的行為是否構成徇私枉法罪,這里涉及的一個爭議問題就是故意減輕追訴的行為是否屬于徇私枉法罪中“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的行為”。一種觀點認為,根據《立案標準規定》,故意加重或故意減輕追訴行為可以認為屬于該規定“其他枉法追訴、不追訴、枉法裁判行為”中“其他枉法追訴”的情形[11]。因此,本案中王某的行為可以認定為徇私枉法罪。另一種觀點認為,《立案標準規定》中的“其他枉法追訴、不追訴、枉法裁判行為”是對法律不能窮盡的其他的“對無罪之人的枉法追訴行為”、“對有罪之人的枉法不追訴行為”、“刑事審判中的枉法裁判行為”等情形的概括,這個解釋的含義并不包括對“有罪的人”不是不進行追訴,而是進行一種不合法的追訴行為,即故意加重或故意減輕追訴行為。也就是說,刑法條文本身僅規定了對“有罪的人”枉法不追訴行為是犯罪行為,而沒有規定對“有罪的人”進行故意加重或故意減輕追訴的行為也是犯罪行為。把這種行為硬拉進“其他枉法追訴”的情形顯然是不符合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的[12]。因此,本案中王某的行為不能構成徇私枉法罪。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本案中王某的行為可以構成徇私枉法罪,應當歸入“明知是有罪的人而不使他受追訴”的情形,不使他受追訴包括全部不使受追訴,也包括部分不使受追訴[13]。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認為該案中王某的行為可以構成徇私枉法罪。同時,筆者認為,對于故意加重和故意減輕追訴應當區別對待,在判斷能否構成徇私枉法罪上,不僅要考慮徇私枉法罪的立法意圖,也要考慮徇私枉法罪的文字表述,應當秉持一種在刑法立法文字的最大可能含義的范疇內最大限度地實現立法意圖的態度,合理地平衡好實質和理性與罪刑法定原則之間的關系。具體來說,對于故意減輕追訴,可以通過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不使他受追訴”的擴大解釋來將其納入其中,這種解釋并未突破文字的可能文義,并不違反罪刑法定的原則。但對于故意加重追訴,顯然不屬于“明知是有罪的人而不使他受追訴”的情形,那么是否可以將其納入“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其受追訴”的情形呢?筆者認為不可以,因為故意加重追訴的對象是“有罪的人”,雖然其實質上的枉法性質和社會危害性與故意減輕追訴并無不同,但由于其行為方式不能為徇私枉法罪條文的最大可能含義所包容,如果將其納入徇私枉法罪就會違背罪刑法定原則,因此是不可取的。不少論者都關注將故意加重追訴行為納入徇私枉法罪的實質合理性,但筆者認為,這種實質合理性的實現應該通過立法的手段,而不是通過解釋的方式。
[1]張明楷,等.新刑法問題探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400-401.
[2]王飛.徇私枉法罪問題研究[A].李希慧,劉憲權.中國刑法學年會論文集[C].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317.
[3]潘曉甫,吳良勇.徇“公”情能否構成徇私枉法罪[J].檢察實踐,2005,(5).
[4][13]朱利軍.對徇私枉法罪法律適用中幾個問題的理解[J].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6,(2).
[5]張明楷.論瀆職罪中的“徇私”、“舞弊”[A].李希慧,劉憲權.中國刑法學年會論文集[C].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177-178.
[6]劉艷紅.罪名研究[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120.
[7]牛克乾,閻芳.試論徇私枉法罪中"徇私"的理解和認定[J].政治與法律,2003,(3).
[8]陳劍,王天寶.試論徇私枉法罪的幾個問題[J].當代法學,2001,(4).
[9]劉順昌.徇私枉法罪研究[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10.
[10]吳學斌,余娟.徇私枉法罪的基本問題研究[J].政治與法律,2005,(2).
[11]王作富.刑法分則實務研究[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185.
[12]劉志高.“故重故輕”追訴能否構成徇私枉法罪[N].檢察日報,2002-11-14(3).
責任編輯:趙新彬
D924
A
1009-3192(2013)04-0047-06
2013-05-20
肖晚祥,男,法學博士,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長;許浩,男,法學碩士,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