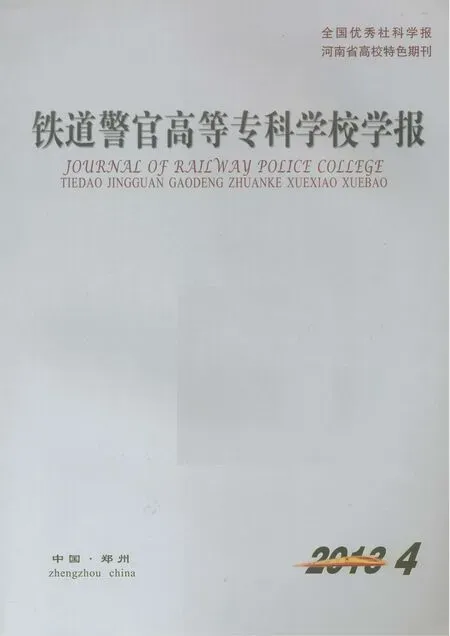自殺關聯行為的刑法類型化認定路徑探析
劉洋
(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檢察院,上海 201620)
自殺關聯行為的刑法類型化認定路徑探析
劉洋
(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檢察院,上海 201620)
自殺關聯行為包含勸說、幫助、欺騙、強迫、相約自殺等多種行為方式。傳統“教唆、幫助自殺行為”的討論范式掩蓋了各類行為的差異性,對行為定性失之泛泛,缺乏準確性。將自殺關聯行為區分為勸說幫助、欺騙強迫、相約自殺三種類型會使行為定性更加精細和準確。受罪刑法定原則的制約,勸說幫助型自殺關聯行為并不具有可罰性;在欺騙、強迫他人自殺的場合,只有當欺騙、強迫達到了剝奪他人自主意志的程度時,才可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相約自殺的情況,即使相約自殺的發起人未死亡,也同樣不能將其定罪。
自殺關聯行為;可罰性;勸說幫助;欺騙強迫;相約自殺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生活節奏的加快,人類面臨的生活、學習、工作壓力日益增加。心理承受力脆弱的人往往無法抗拒和排解外部壓力,自殺成為其逃避現實、尋求解脫的一種方式。長期以來,自殺行為雖然為倫理道德所摒棄,但并未上升至刑法的高度予以規制。而自殺關聯行為,如幫助自殺、勸說他人自殺、強迫他人自殺等,因為侵犯了他人生命權而存在入罪的空間。然而,由于這類自殺關聯行為與故意殺人罪中客觀行為的“曖昧”關系,司法認定總是徘徊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之間。面對自殺關聯行為,定罪標準不一是當下司法實踐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本文有意回避“教唆、幫助自殺”的概念范式,而試圖對自殺關聯行為進行更加深入的解構,以探尋其背后類型化的定罪路徑。
一、概念的厘清
自殺關聯行為是指與自殺行為相關聯的輔助行為,包括勸說他人自殺、幫助他人自殺、欺騙(引起)他人自殺、強迫他人自殺以及相約自殺等行為。傳統上,對于這類行為的討論習慣于在“教唆、幫助自殺行為”的語境內展開,也即上述各類自殺關聯行為統稱為教唆、幫助自殺行為,并由此展開對教唆、幫助自殺行為可罰性以及定罪路徑的探討[1]。筆者并不認同這樣的討論范式,原因有二:
其一,“教唆、幫助自殺”的稱謂易造成概念混淆,使討論陷入誤區。“教唆、幫助自殺”易使人們誤認為該類行為人為共同犯罪理論中的教唆犯和幫助犯。實際上二者并非屬于同一范疇。教唆、幫助自殺的行為人并不是教唆犯或幫助犯。教唆犯、幫助犯教唆或幫助的對象是其他犯罪人,其教唆行為和幫助行為服務于其他犯罪行為。而自殺不是犯罪行為,自殺者更不是犯罪人。
其二,“教唆、幫助自殺”的稱謂失之泛泛。所謂教唆自殺行為,是指行為人用慫恿、請求、命令、挑撥、刺激、引誘、指使等方式,唆使他人產生自殺意圖,實施自殺行為。而幫助自殺,是指他人已有自殺意圖,行為人對其在精神上加以鼓勵,使其堅定自殺的意圖,或者在物質上加以幫助,使他人得以實現其自殺意圖[2]。由于“教唆”和“幫助”之下包含了太多的行為類型,而自殺行為又有其特殊性,各類“教唆”、“幫助”自殺行為的性質并不相同,其是否可以成立犯罪,成立何種罪名,不能簡單地以“教唆”、“幫助”兩種情況加以界分。例如,從廣義上講,虛構某種事實欺騙他人使其自殺,也是教唆自殺的一種方式,然而這種欺騙引起他人自殺的行為與單純勸說他人(可能是飽受疾病折磨的病人)自殺的行為無論在主觀惡性上還是客觀行為方式上都存在質的差異[3],所以不可籠統地認為教唆自殺行為可罰或者不可罰,應當深入“教唆”、“幫助”自殺行為的內部對自殺關聯行為進行進一步的解構,梳理類型化的行為方式。
二、自殺關聯行為的可罰性及其定罪思路
在原“教唆、幫助自殺”的語境內,對于教唆、幫助自殺行為是否可罰存在爭議。肯定論者認為,此類行為雖然沒有導致法益侵害的直接危險,但為法益侵害的發生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因此此類行為是應受刑罰處罰的參與行為[4]。而否定論者認為,自殺者基于自由意志結束自己的生命,死亡結果是自殺者自己意志和行為的體現,“參與他人在法規范上完全自由地處置生命的行為,不是殺人行為”[5]。對于自殺關聯行為是否可罰的問題,筆者認為不可一概而論。在罪刑法定原則業已確立的今天,我們將某一行為認定為犯罪,該行為必須符合刑法分則的規定,也即其必定是刑法分則類型化的犯罪行為。在具體犯罪事實與刑法分則類型化犯罪行為對接的過程中,犯罪構成是行為成立犯罪的依據。而我國傳統四要件的犯罪構成是形式違法與實質違法的統一,我們既不可因為自殺關聯行為具有反倫理、反道德的實質違法性而忽略犯罪構成對客觀行為方式的定型作用,也不能僅看到死亡的結果而忽視行為的實質違法性。由此筆者認為,對于自殺關聯行為是否可以認定為犯罪的問題,應當嚴格依循罪刑法定原則,并系統考量犯罪構成理論對認定犯罪的形式與實質要求,在具備嚴重社會危害性的前提下,只有當某自殺關聯行為符合刑法分則規定的某一罪名的類型化行為時,這一行為才可被認定為犯罪。
然而,當前學界通說認為教唆他人自殺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但由于社會危害性較小,應按情節較輕的故意殺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幫助他人自殺則應區別對待,對于精神幫助不應以犯罪論處,因為其社會危害性較小,而物質幫助原則上構成犯罪,但對于幫助者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6]。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對于教唆、幫助自殺行為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的案例[7]。筆者認為,自殺關聯行為并不存在“一刀切”的定罪標準,況且有些自殺關聯行為并不構成犯罪。在一些情況下,自殺關聯行為的客觀方面可能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犯罪構成,但還需考察其主觀故意的內容。而且,在刑法另有規定的情況下,應當依照規定,如相關司法解釋來定罪,例如邪教組織人員以自焚、自爆或其他危險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自殺關聯行為的類型化認定與歸罪
自殺關聯行為方式的多樣性決定了上述“一刀切”的認定思路無法經受罪刑法定原則以及犯罪構成理論的檢驗。犯罪構成是行為成立犯罪的依據,是犯罪行為的類型化,也是罪刑法定原則在犯罪認定階段的具體實現。以故意殺人罪為例,其類型化的是主觀上存在殺人故意、客觀上實施了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以此為參考的基點,不同的行為方式,無論是投毒還是刀刺,也無論是作為還是不作為,只要屬于這種行為類型,就可以成立故意殺人罪。至于自殺關聯行為是否屬于故意殺人罪犯罪構成類型化行為,筆者將多樣的自殺關聯行為解構為以下三種行為類型展開分析。
(一)勸說幫助型
這種自殺關聯行為僅指行為人勸說、幫助他人自殺的情況,幫助既可以是物質上的幫助也可是精神上的幫助,但在勸說、幫助過程中并不存在強迫、欺騙的內容。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一般這類行為并不是故意殺人罪所類型化的殺人行為,不具有可罰性。
首先從客觀行為方式的角度看,行為人沒有實施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勸說、幫助他人自殺不等于去直接剝奪他人的生命,自殺依然是自殺者自由意志和行為的體現。最終實施剝奪生命行為的人是自殺者本人,而非自殺行為的勸說者或者幫助者。
其次,從因果關系的角度看,勸說、幫助行為僅是造成他人死亡結果的條件,并非原因。根據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只有當條件在通常情況下能夠引起結果時,該條件才與此結果相當,才能成為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如果在通常情況下,具備該條件并不一定會造成該具體結果,結果的發生“完全違反規則”或者偏離常規,則該條件并不是造成該結果的原因[8]。
最后,從主觀惡性的角度看,勸說幫助行為有許多是出于對自殺者不幸遭遇的同情與無奈,因而行為人具有性格柔弱的一面[9]。無論是語言刺激引起的自殺,還是出于無奈為他人自殺提供物質幫助,其主觀上并沒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其主觀惡性無法與通常理解的故意殺人行為相當[10]。對于有學者提出的自殺行為本是一種反道德、反倫理的行為,而勸說、幫助自殺行為會助長這類行為的發生,危害社會管理秩序,破壞社會利益的觀點[11],筆者并不認同。一方面,在人類是否有權利“自殺”這一哲學問題尚存爭論的時候,將勸說、幫助自殺行為認定為犯罪顯然是一種為了社會利益而犧牲個人行為自由的社會本位立法的表現;另一方面,在勸說、幫助自殺場合,行為人實行一定行為,為他人自殺提供幫助,但勸說、幫助行為對自殺的影響程度是極低的,并且這種影響是否發生取決于被害人的自由意志。此時,對勸說、幫助行為進行刑法規制的必要性和實效性不無疑問。
基于上述三點理由,筆者認為,勸說、幫助型自殺關聯行為并不成立故意殺人罪,不具有可罰性。
(二)欺騙強迫型
欺騙強迫型自殺關聯行為,指的是他人本無自殺的決意,行為人通過虛構事實或者強迫的方式,使他人陷入意思不自由的狀態,而實施了自殺行為。這類自殺關聯行為與勸說,幫助型自殺關聯行為存在本質的區別,后者是行為人自由意志的體現,而前者是行為人陷入意思不自由狀態后做出的。這種區別也決定了兩類自殺關聯行為的刑法評價不同。
在欺騙引起他人自殺的場合,如甲與乙有仇,某日乙去看病,甲事先指使身為醫生的好友丙謊稱乙身患絕癥,余日不多,且病癥極其痛苦等,致使事前本無自殺決意(甚至沒有自殺意念)的乙實施了自殺行為,那么甲與丙就成立故意殺人罪的共犯。這種情形中,由于乙的自殺行為是基于對甲與丙所編造事實的錯誤認識,其意志受到了欺騙行為的影響,雖然乙同樣可以選擇不自殺,但其自殺的危險性和可能性明顯增加,欺騙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具有刑法因果關系所要求的“相當性”。而對于這種致使他人自殺的可能性和危險性,甲和丙顯然是已經預見到的,他們對于他人可能自殺的結果至少存有放任的態度,所以欺騙引起他人自殺存在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的空間。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只有當欺騙使對方完全陷入錯誤認識以至達到無法自拔的程度才符合這里所說的欺騙他人引起他人自殺的情況。對于一般的欺騙行為,只是由于對方多疑等個人原因自殺的,同樣不能成立故意殺人罪,因為此時行為人自殺依然是其自由意志的體現,欺騙行為與自殺結果之間并不存在構成要件意義上的“相當性”。
在強迫他人自殺的場合,成立故意殺人罪的空間更大。因為在欺騙的場合,行為人的意思僅是處于自由或不自由之間,而在受到強迫的情況下,多數行為人的意志則處于完全不自由的狀態。如在孤立無援的狀態下,甲威脅乙說,“如果你不自殺,我就殺了你全家”,這種情況下,自殺成為乙唯一的選擇。對于強迫他人自殺的情況,有學者認為應是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12]。筆者對此并不認同。在我國刑法理論中,間接正犯是指利用無責任能力的人實施犯罪的情況。而在強迫他人自殺的場合,一方面,自殺并不是犯罪;另一方面,被強迫者同樣也并非都沒有責任能力。筆者之所以認為強迫他人自殺的行為可以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是因為行為人對他人自殺的結果具有支配性,自殺僅是其達到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目的的手段而已。這里同樣存在一個強迫程度的問題,脅迫行為只有在達到了相當的強度,很大程度上已經排除了自殺者的意志的反抗(不愿自殺),對于自殺者的意志具有強制性和支配性時,才能成立故意殺人罪[13]。也就是說,并不是所有的強迫引起他人自殺都可以認定為故意殺人罪,如以揭露隱私相威脅逼他人自殺的情況,即不能成立故意殺人罪,因為強迫尚沒有達到完全剝奪行為人自主意志的程度。只有當強迫使得對方陷入意志完全不自主時,才可認定這一強迫行為屬于故意殺人罪的類型性行為。
(三)相約自殺型
相約自殺是指兩個以上行為人基于自己的真實意思而一同自殺的行為。在約定自殺的過程中,各行為人之間沒有欺騙或者強迫。倘若存在欺騙或者強迫,則可以直接按照欺騙強迫型自殺關聯行為定罪處罰。若相約自殺的行為人均死亡,當然也沒有認定犯罪的必要。司法實踐中較為棘手的問題是相約自殺過程中有行為人沒有死亡,對該自殺未完成者是否該定罪,定為何罪。在司法實踐中,對相約自殺中途放棄者一般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理論界對相約自殺行為的分析則更為詳細,一般認為,自殺意圖是各方的真實意思,在自殺過程中各方均未為他人提供幫助,自殺未完成者,無論是中途放棄還是客觀原因未遂,均不成立犯罪;若一方勸說或者幫助他人與自己相約自殺,而這種相約自殺發起者自殺又未完成的,則對發起者認定故意殺人罪;若相約自殺過程中,采取了一方先殺死對方,然后自殺的方式,后自殺者未死亡,無論是中途放棄還是客觀原因未遂,均成立故意殺人罪。筆者贊同第一種情況的結論,認為第二種情況中對相約自殺行為的定性并不準確。相約自殺的發起者,其對于其他后加入的相約自殺者無非是實施了一定的勸說或者幫助行為,其行為性質屬于勸說幫助型自殺關聯行為,上文已經論及該類行為并不可罰。至于中途放棄的行為,同樣也并不是導致他人死亡結果的原因,自殺依然是行為人自由意志的表現,是行為人對自己生命權予以處分的行為。當前網絡技術發達,有自殺傾向的人往往在虛擬世界中組建自殺討論組或相約自殺論壇,在網絡世界中,存在大量的自殺發起者和自殺鼓動者,倘若將勸說、幫助相約自殺的行為均認定為故意殺人罪,那么虛擬世界背后的那些真實的個體都將是潛在的犯罪分子。這顯然與刑法的謙抑性相悖。至于最后一種情況,筆者對其認定結論并無異議,但這種先殺死別人再自殺的方式顯然已超出了自殺關聯行為的范疇,直接即可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的實行行為。
綜上所述,相約自殺雖然有違社會倫理道德,與現代社會所倡導的精神文明相背離,但由于刑法缺乏對該類行為的類型化規定,不可將其輕易認定為故意殺人罪。
四、結語
自殺關聯行為包含勸說、幫助、欺騙、強迫、相約自殺等多種行為方式,從廣義上講,勸說是一種教唆,欺騙、強迫同樣可以成立教唆,但是勸說他人自殺與欺騙和強迫他人自殺的行為性質顯然不同。而傳統“教唆、幫助自殺行為”的討論范式掩蓋了這種差異性,使得行為定性失之泛泛,缺乏準確性。將自殺關聯行為區分為勸說幫助、欺騙強迫、相約自殺三種類型可使得行為定性更加精細和準確。勸說幫助型自殺關聯行為并不具有可罰性;在欺騙、強迫他人自殺的場合,也只有當欺騙、強迫達到了剝奪他人自主意志的程度,才可認定為故意殺人罪;在相約自殺的情況,相約自殺的發起人未死亡,也同樣不能將其定罪。在討論各類自殺關聯行為的可罰性時,應當嚴格依循罪刑法定原則和犯罪構成對行為定性的要求,完成事實與規范之間的對接。
[1]陳興良.教唆或者幫助他人自殺行為之定性研究[J].浙江社會科學,2004,(6).
[2]王志遠.論我國共犯制度存在的邏輯矛盾——以教唆、幫助自殺的實踐處理方案為切入點[J].法學論壇,2011,(5).
[3]馮軍.刑法的規范化詮釋[J].法商研究,2005,(6).
[4]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470.
[5]羅燦,徐輝.劉祖枝故意殺人案——提供農藥由丈夫自行服下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導致丈夫中毒身亡的,如何定性[J].刑事審判參考,2012,(1).
[6]高銘暄.刑法專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87.
[7]楊興培.一起夫妻爭吵引起自殺案的刑法思考和倫理思考[J].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4,(6).
[8]趙秉志.中國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分則篇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3.
[9]黎宏.日本刑法精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47.
[10]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639.
[11]彭偉.自殺加工行為的定罪及立法完善[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2010,(8).
[12]黃瓊,等.三人網上相約自殺一人身亡變卦者獲故意殺人罪[EB/OL].http://news.hsw.cn/system/2012/08/ 02/051408381.shtml.
[13]王圣志,鮑曉箐.專家吁“網絡教唆”應入罪[N].新華每日電訊,2012-12-04(5).
責任編輯:趙新彬
D924
A
1009-3192(2013)04-0075-04
2013-05-28
劉洋,男,法學碩士,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檢察院科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