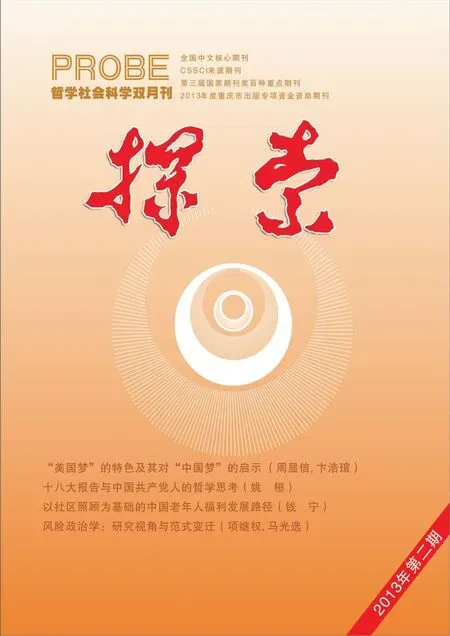破解“困局”:報(bào)刊編輯部體制改革走向態(tài)勢(shì)評(píng)析①
林士平
(西南政法大學(xué)期刊編輯部,重慶 401120)
按照中央的部署,全國(guó)報(bào)刊業(yè)分類(lèi)改革和體制機(jī)制轉(zhuǎn)變已基本完成,但被稱(chēng)為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最后一塊“領(lǐng)地”的高校學(xué)報(bào)編輯部的改革一直懸而未決,處于“困局”。某文化體制改革試點(diǎn)城市的新聞出版管理機(jī)構(gòu)建議將學(xué)術(shù)期刊單列,以區(qū)別于時(shí)政類(lèi)和非時(shí)政類(lèi)報(bào)刊,但方案至今沒(méi)有得到權(quán)威部門(mén)的認(rèn)可。
國(guó)家新聞出版總署2011年7月30日公布并一度激起強(qiáng)烈“反彈”的《關(guān)于報(bào)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shí)施辦法》(以下簡(jiǎn)稱(chēng)《改革辦法》)現(xiàn)實(shí)際上已處于暫時(shí)“停擺”狀態(tài),但文化體制改革的總體方向并沒(méi)有因此而改變,改革的到來(lái)只是遲早的問(wèn)題。鑒于事關(guān)學(xué)術(shù)期刊編輯的職業(yè)前途和個(gè)人命運(yùn),本文據(jù)此略作思考,并對(duì)改革的走向態(tài)勢(shì)等問(wèn)題初作分析評(píng)判,且嘗試提出一些建設(shè)性意見(jiàn)。
一、對(duì)《改革辦法》所持的不同態(tài)度分析
針對(duì)《改革辦法》,作為全國(guó)社科期刊主管部門(mén)的中宣部出版局的有關(guān)領(lǐng)導(dǎo)向媒體傳達(dá)了這樣一種態(tài)度:“條件成熟的改革,條件不成熟的不一定要硬性并轉(zhuǎn)。”②轉(zhuǎn)引自:趙大良.對(duì)期刊體制改革動(dòng)態(tài)的再評(píng)析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721-614172.html。本文許多觀點(diǎn)受到趙大良主任的啟發(fā),在此深表謝意。筆者認(rèn)為,改革只設(shè)定了“路線圖”并沒(méi)有設(shè)定“時(shí)間表”③據(jù)有關(guān)方面提供的消息,改革方案討論中曾有人提出設(shè)定明確的“時(shí)間表”,但正式公布的《改革辦法》中并沒(méi)有這一內(nèi)容。,更沒(méi)有“軍令狀”。《改革辦法》規(guī)定“中央各部門(mén)各單位和各地區(qū)要切實(shí)加強(qiáng)對(duì)報(bào)刊編輯部體制改革工作的組織領(lǐng)導(dǎo),周密部署,精心組織,抓好落實(shí),依照本通知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jìn)改革。”如何才能既積極又穩(wěn)妥地推動(dòng)改革進(jìn)程,目前尚無(wú)權(quán)威解說(shuō)。在此,我們不妨簡(jiǎn)略回溯一下對(duì)《改革辦法》的四種不同看法[1]:
(一)政策“倒退論”——認(rèn)為改革政策在抵制聲中出現(xiàn)了讓步。由于來(lái)自各高校的反對(duì)呼聲異常強(qiáng)烈,并通過(guò)教育行政管理和期刊行業(yè)組織等各種渠道反饋至行政決策部門(mén),從穩(wěn)妥角度出發(fā),改革議程實(shí)際上處于暫時(shí)的“停擺”狀態(tài),各方的意見(jiàn)處于形成過(guò)程之中,加之目前國(guó)務(wù)院大部制機(jī)構(gòu)改革方案沒(méi)有正式出臺(tái),直屬?lài)?guó)務(wù)院的新聞出版總署同樣面臨如何適應(yīng)行政機(jī)構(gòu)改革的問(wèn)題,因此,政策“倒退論”似乎占了上風(fēng)。
(二)改革“無(wú)理論”——認(rèn)為改革政策不具合理性。《改革辦法》公布不久,在由重慶市新聞出版局、重慶市高校期刊研究會(huì)在西南大學(xué)于2012年8月底舉行的“《改革辦法》專(zhuān)題征求意見(jiàn)會(huì)”上(以下簡(jiǎn)稱(chēng)“征求意見(jiàn)會(huì)”),多數(shù)人認(rèn)為改革既然是行業(yè)主管部門(mén)的行政措施,不執(zhí)行也說(shuō)不過(guò)去;但也有不少人對(duì)改革提出質(zhì)疑,認(rèn)為“改革不利于學(xué)術(shù)期刊的發(fā)展及品牌建設(shè),可能導(dǎo)致期刊出版單位在實(shí)際運(yùn)作過(guò)程中片面追求經(jīng)濟(jì)效益,還可能導(dǎo)致亂收費(fèi)”;同時(shí)還有人認(rèn)為,現(xiàn)有的學(xué)術(shù)期刊沒(méi)有找到恰當(dāng)?shù)内A得模式,此種情形之下,進(jìn)行報(bào)刊編輯部體制改革沒(méi)有解決學(xué)術(shù)期刊如何贏利的問(wèn)題,這樣的改革不會(huì)取得積極成效。亦有人不解:為什么要改革?現(xiàn)行報(bào)刊編輯部體制并沒(méi)有重大缺陷,改革沒(méi)有理由①甚至還有代表提出,編輯部沒(méi)有并入出版企業(yè)的義務(wù),現(xiàn)有的編輯部應(yīng)當(dāng)都是獨(dú)立法人。還有代表認(rèn)為,《改革辦法》與教育部會(huì)同新聞出版總署之前發(fā)布的《關(guān)于高等學(xué)校出版體制改革工作實(shí)施方案》(教社科〔2007〕5號(hào))相沖突。該《方案》在“高校出版單位體制的類(lèi)別”中明文規(guī)定:“不參與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的少數(shù)高校出版社,以及高校學(xué)報(bào)、學(xué)術(shù)性期刊和校報(bào)實(shí)行事業(yè)體制。”《改革辦法》突然實(shí)行轉(zhuǎn)企改制屬“朝令夕改”,失去了政策的連續(xù)性。。2012年11月12日,在鄭州舉行的“全國(guó)高等學(xué)校文科學(xué)報(bào)研究會(huì)第七次會(huì)員代表大會(huì)”上(以下簡(jiǎn)稱(chēng)“會(huì)員代表大會(huì)”),張積玉認(rèn)為,學(xué)刊盡管具有一般讀物的商品屬性,但它是為精神文化公共產(chǎn)品。學(xué)刊與時(shí)政、文化生活類(lèi)雜志不同,不應(yīng)進(jìn)行市場(chǎng)化。學(xué)刊編輯部與出版社也不同。出版社具企業(yè)性質(zhì),其產(chǎn)品看重經(jīng)濟(jì)效益,實(shí)行企業(yè)化管理以商業(yè)利潤(rùn)為目標(biāo)。我國(guó)學(xué)術(shù)期刊關(guān)注社會(huì)效益,學(xué)術(shù)評(píng)價(jià),不應(yīng)重點(diǎn)考慮商業(yè)利益。新中國(guó)成立前,大學(xué)學(xué)報(bào)都是“非賣(mài)品”(封面上方印有這樣的字樣)。②以上觀點(diǎn)根據(jù)張積玉所長(zhǎng)在會(huì)議上發(fā)言的記錄整理,未經(jīng)本人審閱。該觀點(diǎn)代表了相當(dāng)一部分人的看法。
(三)政策“個(gè)人論”——認(rèn)為政策制定有人為的因素,這樣,就會(huì)由于各種不可預(yù)見(jiàn)的原因而將政策擱置。在“征求意見(jiàn)會(huì)”上有人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會(huì)同兩個(gè)部級(jí)單位聯(lián)合發(fā)文,這樣才利于改革的推進(jìn)。否則,針對(duì)高等學(xué)校的改革撇開(kāi)教育部由新聞出版總署單獨(dú)發(fā)文,難免帶有“部門(mén)立法”的意味。在“會(huì)員代表大會(huì)”上,有學(xué)者指出,改革風(fēng)險(xiǎn)注定是承擔(dān)風(fēng)險(xiǎn),如果實(shí)踐證明《改革辦法》有誤,對(duì)編輯出版隊(duì)伍和學(xué)術(shù)期刊的“傷害”將無(wú)法挽回;如果造成損害,誰(shuí)來(lái)承擔(dān),有無(wú)問(wèn)責(zé)機(jī)制?
(四)改革“緩行論”——認(rèn)為現(xiàn)在不具備實(shí)施改革的環(huán)境和條件,應(yīng)當(dāng)使“緩兵之計(jì)”。建議幾年后再實(shí)施《改革辦法》。不顧現(xiàn)實(shí)主客觀條件急于硬性改革采取“一刀切”的辦法,會(huì)引起諸多負(fù)面效應(yīng),改革將得不償失。在前述“會(huì)員代表大會(huì)”上有代表還提到改革面臨的一些新問(wèn)題,如工資獎(jiǎng)金、福利待遇、醫(yī)療保險(xiǎn)等如何處理等難題。還需要解決注冊(cè)啟動(dòng)資金誰(shuí)出,辦公場(chǎng)地和租金誰(shuí)出等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從管理上講,應(yīng)當(dāng)防止拔苗助長(zhǎng),不能放棄基本生存條件于不顧,追求形式上的改革效果。與會(huì)者建議對(duì)從業(yè)人員的基本情況、收支、發(fā)行情況做進(jìn)一步調(diào)查研究分析,在此基礎(chǔ)上考慮落實(shí)《改革辦法》的規(guī)定。筆者認(rèn)為,這些看法存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不過(guò),并非持上述觀點(diǎn)的人都反對(duì)《改革辦法》,“緩行論”者并不反對(duì)改革,只是對(duì)如何設(shè)置改革進(jìn)程持不同看法。教育部社科司的問(wèn)卷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多數(shù)期刊編輯部不贊成立即實(shí)施改革措施③教育部社科司出版處(教育部期刊轉(zhuǎn)企改制辦公室)按照教育部領(lǐng)導(dǎo)的要求,牽頭對(duì)全國(guó)高校期刊情況進(jìn)行調(diào)研。據(jù)悉,教育部領(lǐng)導(dǎo)認(rèn)為,目前最需要的是摸清高校期刊家底,提出切實(shí)可行的高校期刊管理辦法。教育部社會(huì)科學(xué)司于2012年9月25日向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教育廳(教委)發(fā)出《關(guān)于開(kāi)展高校期刊調(diào)研的通知》(教社科司函[2012]188號(hào))。該函件說(shuō)明:“為進(jìn)一步推動(dòng)高校期刊提高質(zhì)量,穩(wěn)步推進(jìn)高校期刊改革工作,社科司擬于近期開(kāi)展高校期刊調(diào)研活動(dòng)”,并發(fā)放《全國(guó)高校期刊調(diào)研問(wèn)卷》若干,且將對(duì)返回的問(wèn)卷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學(xué)上的分析。筆者沒(méi)有檢索到此次問(wèn)卷的詳細(xì)統(tǒng)計(jì)結(jié)果,但有人在重慶市高校學(xué)報(bào)期刊研究會(huì)常務(wù)理事會(huì)提到上述調(diào)查結(jié)果,據(jù)說(shuō)投反對(duì)票者占90%以上。,但這同時(shí)也意味著沒(méi)有仍有一部分人公開(kāi)支持改革方案,贊成立即實(shí)施改革措施,另一部分人同樣支持改革,只是不贊成立即實(shí)施;在“會(huì)員代表大會(huì)”上有學(xué)者從實(shí)證數(shù)據(jù)分析梳理了改革的某種必要性:④以上觀點(diǎn)源自《全國(guó)高校文科學(xué)術(shù)文摘》編輯部姚申主任在會(huì)議上進(jìn)行的以《期刊多元化發(fā)展路徑》為題的發(fā)言記錄,整理后未經(jīng)本人審閱。新聞出版總署《新聞出版業(yè)十二五時(shí)期發(fā)展規(guī)劃》規(guī)定的今后五年新聞出版業(yè)發(fā)展目標(biāo)中的關(guān)鍵性指標(biāo)與學(xué)報(bào)有密切關(guān)系。“十一五”時(shí)期最后一年的2009年新聞出版業(yè)總產(chǎn)值是10 668.09億,3年后要翻一番,到“十二五”期末實(shí)現(xiàn)全行業(yè)總產(chǎn)出29 400億元,實(shí)現(xiàn)增加值8440億元⑤參見(jiàn)《新聞出版業(yè)“十二五”時(shí)期發(fā)展規(guī)劃》。,誰(shuí)來(lái)翻番?這個(gè)現(xiàn)實(shí)必須面對(duì)。期刊業(yè)在新聞出版業(yè)中的總產(chǎn)值中的比例只占新聞出版業(yè)的4%。這4%還是由1000多家面向市場(chǎng)的期刊所創(chuàng)造。⑥目前,全行業(yè)有報(bào)紙1739種,期刊9884家,期刊中,科技期刊4700多種,學(xué)報(bào)2000多種,行業(yè)期刊1000多種,三者占9000多種的3/4,但創(chuàng)造出版業(yè)GDP為200多億元,廣告為100多億元。(據(jù)姚申主任主題報(bào)告中列出的數(shù)據(jù))。也就是說(shuō),2/3的期刊沒(méi)有創(chuàng)造價(jià)值,沒(méi)有貢獻(xiàn)GDP,沒(méi)有為“十一五”規(guī)劃作貢獻(xiàn),因此有必要對(duì)這部分期刊實(shí)行市場(chǎng)化再造。
對(duì)于政府部門(mén)出臺(tái)新政持不同見(jiàn)解并在公開(kāi)場(chǎng)合直接表達(dá),表明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逐漸形成了一種新型政治訴求機(jī)制,也標(biāo)志著我國(guó)政治民主和法治社會(huì)進(jìn)程業(yè)已加速。通觀改革開(kāi)放30余年以來(lái)期刊界所經(jīng)歷的種種變革和調(diào)整,如1999年奏效的“停辦內(nèi)刊,創(chuàng)建高校出版系列刊號(hào)”,以及近年來(lái)業(yè)已經(jīng)完成的“高校出版社轉(zhuǎn)企改制”等政策,沒(méi)有哪項(xiàng)經(jīng)受過(guò)如此大的挑戰(zhàn)和置疑。
二、對(duì)學(xué)報(bào)編輯部體制改革合理性的考量
當(dāng)前我國(guó)政治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已步入“深水區(qū)”,社會(huì)矛盾處于突顯期,出臺(tái)和推進(jìn)任何一項(xiàng)改革措施既要符合頂層設(shè)計(jì)方案,又要考慮是否有利于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穩(wěn)定。穩(wěn)定是發(fā)展的基礎(chǔ)和前提,繁榮進(jìn)步是目標(biāo)。積極穩(wěn)妥地實(shí)施《改革辦法》固然必須著眼于這個(gè)大局,但穩(wěn)妥不等于消極,穩(wěn)定不等于僵化。頑強(qiáng)地保持模仿前蘇聯(lián)高校學(xué)報(bào)模式遺留下來(lái)的現(xiàn)有學(xué)報(bào)編輯部體制①限于篇幅與本人學(xué)識(shí),本文擬不討論報(bào)紙(含高校校報(bào)等)編輯部的改革問(wèn)題。既無(wú)實(shí)證依據(jù)也找不出充分的理由,相反,改革的現(xiàn)實(shí)合理性和迫切性正日益凸現(xiàn)。對(duì)于本輪改革的合理性,經(jīng)筆者粗淺思考,茲簡(jiǎn)述如下。
(一)從學(xué)報(bào)發(fā)展史上看,高校學(xué)報(bào)編輯部體制產(chǎn)生于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如何協(xié)調(diào)與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關(guān)系需要重新定位與理性思考。我國(guó)目前5000多種②據(jù)2011年9月7日國(guó)家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產(chǎn)業(yè)發(fā)展司公布的2010年全國(guó)出版信息,我國(guó)共出版期刊9884種,其中學(xué)術(shù)期刊5000多種,包括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類(lèi)2466種,自然科學(xué)學(xué)術(shù)期刊2500多種(參見(jiàn):國(guó)家新聞出版總署出版產(chǎn)業(yè)發(fā)展司.2010年全國(guó)新聞出版業(yè)基本情況[Z].中國(guó)期刊協(xié)會(huì)通訊,2011,(4))。學(xué)術(shù)期刊中絕大多數(shù)創(chuàng)辦于改革開(kāi)放期間。1959年我國(guó)大學(xué)自然科學(xué)學(xué)報(bào)僅34種[2],現(xiàn)有1000多種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中90%以上是新辦的[3]。期刊大量涌現(xiàn)源于我國(guó)改革開(kāi)放初期國(guó)家大力發(fā)展科學(xué)技術(shù)研究與繁榮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的迫切需要。建立有中國(guó)特色的社會(huì)主義傳媒體系以來(lái),由于注重學(xué)術(shù)出版工作在占領(lǐng)意識(shí)形態(tài)主陣地和推動(dòng)科學(xué)技術(shù)進(jìn)步方面的積極作用,出于國(guó)家文化安全等因素的考量,我們?nèi)匀槐A袅藗鹘y(tǒng)的高校學(xué)報(bào)編輯部出版體制。1999年新聞出版總署治理整頓出版物市場(chǎng)“撤銷(xiāo)內(nèi)刊”,建立高校出版系列刊號(hào)的改革措施,又使得國(guó)內(nèi)多數(shù)高校幾乎都獲得至少一個(gè)公開(kāi)出版的刊號(hào)資源,這使得傳統(tǒng)體制之下的期刊數(shù)量大幅攀升。
(二)從學(xué)報(bào)現(xiàn)狀看,部分高校學(xué)報(bào)質(zhì)量低劣,面臨學(xué)術(shù)道德風(fēng)險(xiǎn)的考驗(yàn)。且不論“垃圾論”、“泡沫論”、“核心期刊異化論”、“小散濫”論的合理成分究竟占幾成,單就“每校一刊”的出版方陣布局而言,其合理性與科學(xué)性值得懷疑;同時(shí),部分高校學(xué)報(bào)質(zhì)量低劣也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誠(chéng)然,我們應(yīng)當(dāng)正視各校的綜合實(shí)力存在差異,也贊同學(xué)者和科研人員實(shí)際上分布于不同層級(jí)結(jié)構(gòu)當(dāng)中,但差異不能成為低劣的借口或托辭。學(xué)術(shù)期刊在文化發(fā)展大繁榮中應(yīng)當(dāng)致力于“傳承文明、創(chuàng)新理論、資政育人、服務(wù)社會(huì)”,不辱文化強(qiáng)國(guó)的使命。我們不能容忍雙重標(biāo)準(zhǔn):一方面享受計(jì)劃經(jīng)濟(jì)“鐵飯碗”體制的保障,另一方面謀取小團(tuán)體甚至個(gè)人經(jīng)濟(jì)利益。這勢(shì)必會(huì)嚴(yán)重地削減學(xué)術(shù)公共產(chǎn)品的誠(chéng)信力,污染學(xué)術(shù)生態(tài)環(huán)境,由此而生。文化是民族的命脈,就傳播學(xué)本源上說(shuō),學(xué)報(bào)是“科學(xué)備忘錄”,但在現(xiàn)實(shí)條件下,學(xué)報(bào)也在“潛規(guī)則”,“命根”在于“拿學(xué)位”和“評(píng)職稱(chēng)”及各項(xiàng)科研項(xiàng)目資助結(jié)題的巨大需求。質(zhì)量低劣的“學(xué)術(shù)垃圾”混雜期間,各項(xiàng)評(píng)價(jià)機(jī)制面臨學(xué)術(shù)道德風(fēng)險(xiǎn)的考驗(yàn),實(shí)有必要加以嚴(yán)歷整飭。
(三)從改革發(fā)展視角看,合理地改革不但不會(huì)導(dǎo)致學(xué)術(shù)期刊消亡,反而能夠提升學(xué)術(shù)期刊的品位與質(zhì)量。誠(chéng)然,學(xué)界反對(duì)學(xué)報(bào)轉(zhuǎn)企的呼聲不斷高漲。如尹玉吉提出“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使命不許轉(zhuǎn)企”論[4],并從10個(gè)方面加以論證。從尹教授提出的理由看不乏某些深層次的理性思考和人文主義關(guān)懷,但我個(gè)人認(rèn)為,學(xué)報(bào)使命屬于價(jià)值追求,而是否轉(zhuǎn)企則是方法或路徑,很難以“使命”來(lái)證成“事業(yè)編制”的合理性。至于“企業(yè)化”是否與“學(xué)報(bào)使命”沖突,我個(gè)人認(rèn)為仔細(xì)分析矛盾主次。表面上看,基礎(chǔ)科學(xué)和純學(xué)術(shù)研究因?yàn)樽x者小眾化很難市場(chǎng)化,財(cái)力雄厚的主辦單位(高等院校)也不在乎開(kāi)支總數(shù)不大的辦刊維持費(fèi)(約20萬(wàn)/年)和“人頭費(fèi)”支出(每刊3~5人),因此,維護(hù)現(xiàn)狀是“最佳”選擇。但從實(shí)質(zhì)上分析,“企業(yè)化”所謂的市場(chǎng)其實(shí)并非單一的讀者市場(chǎng)。國(guó)際通行的做法是機(jī)構(gòu)團(tuán)體資助辦刊,這不失為市場(chǎng)化期刊的合理生存方式。同時(shí),中國(guó)的學(xué)術(shù)期刊數(shù)字傳媒產(chǎn)業(yè)經(jīng)歷了1997年的初創(chuàng),新世紀(jì)的產(chǎn)業(yè)升級(jí),現(xiàn)已經(jīng)十分發(fā)達(dá),市場(chǎng)前景并不暗淡,完全有理由借助新型傳播平臺(tái)整合資源,促進(jìn)學(xué)術(shù)傳媒的進(jìn)化。回顧西方國(guó)際學(xué)術(shù)傳播近代百年發(fā)展史,觀察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傳媒,《Science》《Cell》等眾多具全球影響力的科學(xué)與學(xué)術(shù)期刊品牌歷來(lái)都不是所謂“事業(yè)編制”,這是否會(huì)對(duì)當(dāng)今我們的改革具有某種啟示呢?
(四)從《改革辦法》的邏輯思路上分析,報(bào)刊編輯部體制改革合理可行。仔細(xì)地分析《改革辦法》的出臺(tái)背景及列出的具體措施,不難發(fā)現(xiàn)具有邏輯的合理之處。
1.非時(shí)政類(lèi)報(bào)刊體制改革的目標(biāo)沒(méi)有改變,對(duì)此我們應(yīng)當(dāng)堅(jiān)定不移地貫徹執(zhí)行。《關(guān)于深化非時(shí)政類(lèi)報(bào)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意見(jiàn)》(以下簡(jiǎn)稱(chēng)《19號(hào)文件》)③詳見(jiàn)2011年5月1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發(fā)布的中辦發(fā)[2011]19號(hào)文件。明確指出,“要充分認(rèn)識(shí)深化非時(shí)政類(lèi)報(bào)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非時(shí)政類(lèi)報(bào)刊出版單位中不具有獨(dú)立法人資格的報(bào)刊編輯部原則上不單獨(dú)轉(zhuǎn)制,區(qū)別不同情況,并入其他新聞出版?zhèn)髅狡髽I(yè)或予以撤銷(xiāo)”。《19號(hào)文針》對(duì)高校學(xué)報(bào)高校期刊專(zhuān)門(mén)規(guī)定“科研部門(mén)和高等學(xué)校主管主辦的非獨(dú)立法人科技期刊、學(xué)術(shù)期刊編輯部,另行制定具體改革辦法。”這里的“具體改革辦法”按筆者的理解就包括但不限于新聞出版總署《改革辦法》在內(nèi)。關(guān)注改革背景有利于解決《改革辦法》在遇阻時(shí)如何應(yīng)對(duì)問(wèn)題。
2.實(shí)施《改革辦刊》旨在繁榮發(fā)展學(xué)術(shù)期刊業(yè)。“原則上不再保留報(bào)刊編輯部體制”并非試圖削弱或限制期刊業(yè)的發(fā)展,而是試圖建立現(xiàn)代企業(yè)意義上的法人治理結(jié)構(gòu)。為此,《改革辦法》強(qiáng)調(diào)了“四個(gè)結(jié)合”。即:第一,改革的總體部署和要求與調(diào)整報(bào)刊結(jié)構(gòu)、轉(zhuǎn)變報(bào)刊發(fā)展方式相結(jié)合;第二,改革的總體部署和要求與實(shí)現(xiàn)報(bào)刊業(yè)集約化經(jīng)營(yíng)、培育大型報(bào)刊傳媒集團(tuán)相結(jié)合;第三,改革的總體部署和要求與推動(dòng)傳統(tǒng)報(bào)刊業(yè)向數(shù)字化、網(wǎng)絡(luò)化現(xiàn)代傳媒業(yè)轉(zhuǎn)型相結(jié)合;第四,改革的總體部署和要求與建立健全報(bào)刊準(zhǔn)入和退出機(jī)制、科學(xué)配置報(bào)刊資源相結(jié)合。這“四個(gè)結(jié)合”也就既指明了改革的必要性也明確了改革的目標(biāo)和任務(wù)。報(bào)刊出版體制改革有利于解放和發(fā)展期刊生產(chǎn)力,破解期刊出版業(yè)“小、散、濫”的結(jié)構(gòu)性弊端,實(shí)現(xiàn)期刊出版業(yè)的時(shí)代轉(zhuǎn)型和升級(jí),推動(dòng)期刊業(yè)又好又快發(fā)展,以增強(qiáng)期刊出版在現(xiàn)代技術(shù)條件下的傳播力。
3.《改革辦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現(xiàn)有期刊的行業(yè)規(guī)模。改革的目標(biāo)——取消“不具備獨(dú)立法人資格的報(bào)刊編輯部體制”并非取消學(xué)術(shù)期刊本身,而且采取多種辦法實(shí)現(xiàn)辦刊方式的轉(zhuǎn)換。具體措施主要是“關(guān)”、“停”、“并”、“轉(zhuǎn)”、“建”。“關(guān)”就是讓出公開(kāi)出版刊號(hào),改為內(nèi)部資料性出版物,僅限于在本部門(mén)本系統(tǒng)內(nèi)交流,不得征訂發(fā)行,不得刊登廣告等,這主要是針對(duì)“工作指導(dǎo)類(lèi)”期刊,主要不針對(duì)學(xué)術(shù)期刊。“停”就是對(duì)于不能適用文件列舉的改革辦法的期刊編輯部“予以停辦,對(duì)違法違規(guī)出版情況嚴(yán)重的”“予以撤銷(xiāo)”。后者是針對(duì)極少數(shù)個(gè)別的期刊編輯部。“并”就是保留刊號(hào)但并入本單位新聞出版?zhèn)髅狡髽I(yè)。“轉(zhuǎn)”是指應(yīng)當(dāng)轉(zhuǎn)制的報(bào)刊出版單位所屬報(bào)刊編輯部,一律隨隸屬單位進(jìn)行轉(zhuǎn)企改制。“建”主要是指通過(guò)“三合一”方式組建新的出版企業(yè)。“建”的條件比較嚴(yán)格,具體是指:在本單位沒(méi)有新聞出版?zhèn)髅狡髽I(yè)(在高校就是指高校出版社)、其主管主辦的報(bào)刊編輯部有3個(gè)(含3個(gè))以上的,可合并建立1家報(bào)刊出版企業(yè)。
無(wú)論采取何種方案,被吊銷(xiāo)刊號(hào)的只占極少數(shù),刊號(hào)資源用于非學(xué)術(shù)出版的也為數(shù)不多,有一半以上的學(xué)術(shù)期刊將會(huì)被保留,轉(zhuǎn)為內(nèi)部資料的出版物也并非就無(wú)傳播的空間。
總體而言,《改革辦法》旨在通過(guò)體制改革,在維持合理的出版規(guī)模的前提下提高辦刊質(zhì)量。面對(duì)我國(guó)占據(jù)學(xué)術(shù)期刊“半壁河山”的高校學(xué)報(bào)命運(yùn)的抉擇,新聞出版管理部門(mén)采取了審慎的態(tài)度。《改革辦法》肯定了學(xué)報(bào)和高校學(xué)術(shù)期刊的重要地位:“科研部門(mén)和高等學(xué)校主管主辦的科技期刊和學(xué)術(shù)期刊,是報(bào)刊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文化強(qiáng)國(guó)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是一致的。當(dāng)然,這里還涉及學(xué)術(shù)期刊出版在本質(zhì)上是否可以及如何企業(yè)化問(wèn)題,它是一個(gè)更為復(fù)雜的課題,這與如何厘清學(xué)術(shù)共同體、編輯職業(yè)群體與出版商業(yè)商三者的關(guān)系息息相關(guān),本文對(duì)此擬不鋪開(kāi)陳述。
三、對(duì)報(bào)刊編輯部體制改革走向態(tài)勢(shì)評(píng)析
無(wú)論《改革辦法》是“緩行”還是“緩而不行”,抑或是由新聞出版行業(yè)主管部門(mén)或相關(guān)部門(mén)出臺(tái)補(bǔ)充實(shí)施辦法,以推進(jìn)改革進(jìn)程,筆者認(rèn)為,就學(xué)術(shù)期刊編輯體制改革而言,有以下幾個(gè)方面是可以預(yù)見(jiàn)的。
(一)學(xué)術(shù)公益時(shí)代行將結(jié)束,部分學(xué)術(shù)期刊將實(shí)現(xiàn)商業(yè)化。
目前,主管部門(mén)將文化單位劃分為國(guó)有公益性與經(jīng)營(yíng)性兩種,非時(shí)政類(lèi)報(bào)刊社經(jīng)營(yíng)性轉(zhuǎn)企改制處于文化體制改革的中心環(huán)節(jié)。“要以建立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為重點(diǎn),按照創(chuàng)新體制、轉(zhuǎn)換機(jī)制、面向市場(chǎng)、壯大實(shí)力的要求,拓展出版、發(fā)行、影視等文化單位轉(zhuǎn)企改制的成果”為目標(biāo)[5],推進(jìn)非時(shí)政類(lèi)報(bào)刊社等文化單位的轉(zhuǎn)企改制。學(xué)術(shù)期刊的改革是大勢(shì)所趨,即便是整體轉(zhuǎn)制的方案難以實(shí)現(xiàn),部分學(xué)術(shù)期刊商業(yè)化則是完全可能的。建議在現(xiàn)有如北京卓眾出版有限公司轉(zhuǎn)型成功先例的基礎(chǔ)上,開(kāi)辟辟期刊出版體制改革試點(diǎn)“特區(qū)”,如果失敗,損失還可以彌補(bǔ),如果成功則可將經(jīng)驗(yàn)復(fù)制。沒(méi)有大膽的改革試驗(yàn),難以闖出一條新路。轉(zhuǎn)企改制實(shí)際上屬一種“倒逼”機(jī)制,它試圖以終極方案來(lái)觸動(dòng)現(xiàn)存體制。筆者認(rèn)為,一些學(xué)術(shù)期刊由于具有普遍而持久的學(xué)術(shù)影響力,辦刊基礎(chǔ)雄厚,有可能率先進(jìn)行法人轉(zhuǎn)化,并實(shí)行市場(chǎng)化運(yùn)作。
高校作為學(xué)報(bào)母體還沒(méi)有完全商業(yè)化時(shí),先期對(duì)高校學(xué)術(shù)期刊施行商業(yè)化改造,表面上難以接受但實(shí)際上并非不可為之。各高校出版社的成功轉(zhuǎn)企就已充分證明了這種預(yù)期。學(xué)術(shù)期刊商業(yè)化時(shí)代來(lái)臨之后,報(bào)刊業(yè)的一個(gè)時(shí)代隨即終結(jié),半個(gè)多世紀(jì)的公益學(xué)術(shù)時(shí)代行將結(jié)束,“狼真的來(lái)了!”后學(xué)報(bào)時(shí)代(或稱(chēng)“后學(xué)術(shù)時(shí)代”)即將來(lái)臨。①《福建師范大學(xué)報(bào)》編輯部陳穎主編對(duì)《改革辦法》的實(shí)施影響進(jìn)行過(guò)精辟的分析。以上觀點(diǎn)參考自他在“會(huì)員代表大會(huì)”上發(fā)言,記錄未經(jīng)本人審閱。
商業(yè)學(xué)術(shù)時(shí)代能夠?qū)崿F(xiàn)資源優(yōu)化配置,充分運(yùn)用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提高辦刊質(zhì)量,但毋庸諱言,改革潛伏著危機(jī),學(xué)界所擔(dān)心的危險(xiǎn)并沒(méi)有制度性措施加以化解。由于“經(jīng)濟(jì)人假設(shè)”的現(xiàn)實(shí)存在,注重商業(yè)利益的結(jié)果可能導(dǎo)致學(xué)術(shù)不端日益嚴(yán)重。因此,有必要從職業(yè)道德的高度加以規(guī)制和約束,傳媒人須謹(jǐn)記:“在享受傳播自由時(shí),必須隨時(shí)自省與自制:新聞人既不能以一己之利借傳播之力謀名求利,更要積極地領(lǐng)導(dǎo)社會(huì)走向理性與和諧”。[6]
(二)競(jìng)爭(zhēng)加劇,學(xué)術(shù)期刊將逐步引入優(yōu)勝劣汰的機(jī)制。
通過(guò)合并或資源重組,學(xué)術(shù)期刊小、散、濫的情形因此得以整治,一些幸存的學(xué)報(bào)被收編或重組,“大洗牌后”可能出現(xiàn)辦刊資源相對(duì)集中,傳播優(yōu)勢(shì)得以確立,一些期刊將會(huì)因此“做大做強(qiáng)”。刊物質(zhì)量結(jié)構(gòu)將呈現(xiàn)兩級(jí)分化形態(tài)。一些期刊具有強(qiáng)大科研實(shí)力和雄厚學(xué)科支撐,它們會(huì)繼續(xù)擁有“多核心”的桂冠,并以此吸引更多優(yōu)質(zhì)稿源。已經(jīng)獲得國(guó)家社科基金第一批、第二批重點(diǎn)資助的學(xué)術(shù)期刊很快會(huì)應(yīng)驗(yàn)“馬太效應(yīng)”(the Matthew Effect),強(qiáng)者逾強(qiáng)。
(三)網(wǎng)絡(luò)出版將成為主流業(yè)態(tài),從而實(shí)現(xiàn)轉(zhuǎn)型升級(jí)。
紙媒出版注定了“夕陽(yáng)產(chǎn)業(yè)”的命運(yùn)。未來(lái)數(shù)字媒體的角逐戰(zhàn)中,學(xué)術(shù)期刊與大型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kù)平臺(tái)真正意義上博弈將正式拉開(kāi)序幕,但預(yù)期博弈的結(jié)果也可能不是淘汰對(duì)手,而是各方在市場(chǎng)中結(jié)成“利益共同體”,以“帕累托最優(yōu)”(Pareto Optimality)實(shí)現(xiàn)共贏。學(xué)術(shù)期刊在這一進(jìn)程中尤其要防范傳媒平臺(tái)利用核心技術(shù)壟斷學(xué)術(shù)資源。目前,部分期刊出版單位與CNKI或類(lèi)似傳媒平臺(tái)所簽署了不少“獨(dú)家協(xié)議”。“獨(dú)家協(xié)議”與新建的“國(guó)家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術(shù)期刊數(shù)據(jù)庫(kù)”等所發(fā)生的沖突已經(jīng)顯現(xiàn),值得重視。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傳播平臺(tái)應(yīng)當(dāng)充分引入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以合理配置學(xué)術(shù)資源。
綜上所述,《改革辦法》的出臺(tái)是新聞出版總署推行的一次重大改革舉措。無(wú)論下一步期刊改革如何發(fā)展,從總體情況分析,《改革辦法》提出的“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jìn)改革”的精神以及改革方向選擇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當(dāng)性。誠(chéng)然,《改革辦法》的確是“一劑猛藥”,尚需保持足夠的謹(jǐn)慎。如若配合科學(xué)合理及可行的相關(guān)實(shí)施細(xì)則②目前各地新聞出版管理機(jī)關(guān)也尚無(wú)率先試探啟動(dòng)改革進(jìn)程者,多采取“摸著石頭過(guò)河”的態(tài)度,其改革進(jìn)程正處于積極分析預(yù)測(cè)和謀劃之中。,做好編輯人員的說(shuō)服解釋工作,切實(shí)解決編輯人員的身份認(rèn)同、工資待遇、醫(yī)療保險(xiǎn)等各種具體問(wèn)題,定能順利推進(jìn)改革進(jìn)程,以醫(yī)治我國(guó)學(xué)術(shù)期刊界長(zhǎng)期存在的各種“頑疾”。
“沖開(kāi)樊籬天地寬。”筆者認(rèn)為,目前的“停擺”是政策形成過(guò)程中的暫時(shí)狀態(tài),報(bào)刊編輯部的體制改革如何實(shí)施最終會(huì)有一個(gè)明確的答案,“困局”終將被破解。可以說(shuō),改革的“破冰之旅”注定充滿艱險(xiǎn),但前景遠(yuǎn)大而光明。
參考文獻(xiàn):
[1]趙大良.對(duì)期刊體制改革動(dòng)態(tài)的再評(píng)析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1721-614172.html
[2]朱聯(lián)營(yíng).新中國(guó)高校自然科學(xué)學(xué)報(bào)的初次恢復(fù)重建--中國(guó)科技期刊史研究之八[J].延安大學(xué)學(xué)報(bào):自然科學(xué)版,2003,(2):87-90.
[3]尹玉吉.新中國(guó)60年學(xué)術(shù)期刊事業(yè)回眸[J].《四川理工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2-04
[4]尹玉吉,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使命不許轉(zhuǎn)企http://yj- yin.blog.163.com/blog/static/115657722012828102155357/
[5]蔣建國(guó).深化文化體制改革[M]//本書(shū)編寫(xiě)組.十八大報(bào)告輔導(dǎo)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63.
[6]鄭貞銘.總序[M]//陳國(guó)明,等.傳播研究方法.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