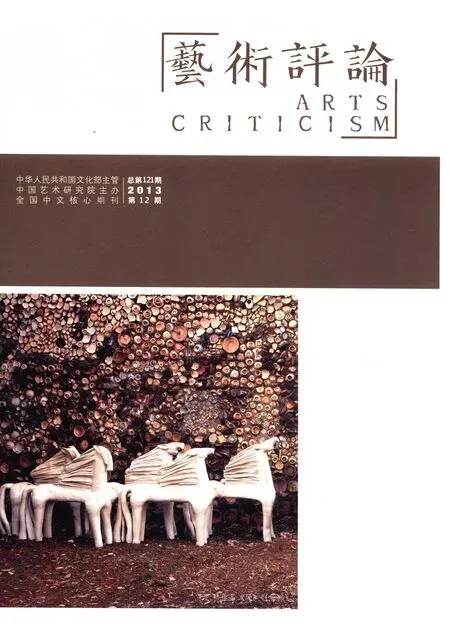長調之美與傳承之憂
和云峰
長調之美與傳承之憂
和云峰

2013年8月21號至28號,筆者參加了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內蒙古民間文藝家協會牽頭組織的“中國內蒙古少數民族原生態民歌采風”之旅。本次活動歷經鄂爾多斯市:成吉思汗陵、杭錦旗,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西烏珠穆沁旗、錫林浩特市,內容涉及蒙古族民間古如歌、長調、短調、呼麥、器樂及其傳承人與相關烏蘭牧騎。整個行程可謂收獲多多,感觸多多。
長調之美
蒙古族的傳統音樂豐富多彩、流傳廣泛、形式獨特。目前學界將其分為:民間音樂、宗教音樂、宮廷音樂三大系統;其中的民間音樂又劃分為:民間歌曲、民間器樂、說唱音樂、戲劇音樂、舞蹈音樂五種。
一直以來,蒙古族均依據自己對民歌的理解詮釋、命名歌曲名稱。例如按 “音樂內容或性質”分:為“圖林·道”和“育林·道”兩大類別;依“題材內容”可分為:狩獵歌、牧歌、贊歌、思鄉曲、禮俗歌、短歌、敘事歌、搖兒歌和兒歌;按“音樂特點”又被分為:長調(烏爾汀哆)、短調(寶格尼道)、混合調(貝斯日格道)、宣敘調(亞日亞道)等四種;如再按照“音樂色彩區”又可被分為:巴爾虎——布里亞特、科爾沁——喀爾沁、察哈爾——錫林郭勒、鄂爾多斯和衛拉特——阿拉善四大色彩曲。
(一)承襲之美
長調,蒙古語稱為“烏爾汀哆”,指蒙古族民間音樂中無固定節拍、節奏循環規律,氣息寬廣悠長、演唱節奏相對自由、即興的歌曲,其中亦有“宮廷之歌”的含義。
有人認為,長調集中體現了蒙古游牧文化的特色與特征,并與蒙古民族的語言、文學、歷史、宗教、心理、世界觀、生態觀、人生觀、風俗習慣等緊密聯系在一起,貫穿于蒙古民族的全部歷史和社會生活中。
有人認為,長調是流淌在蒙古人血液里的音樂,是民族識別的標志。你可以不懂蒙語,卻無法不為蒙古族長調所動容,因為那是一種心靈對心靈的直接傾訴;歌唱家拉蘇榮說,作為草原上的民歌,蒙古族長調是一種歷史遺存下來的口傳文化,堪稱蒙古族音樂的“活化石”。
也有人認為,長調民歌所包含的題材與蒙古族社會生活緊密相聯,它是蒙古族全部節日慶典、婚禮宴會、親朋相聚、“那達慕”等活動中必唱的歌曲,全面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心靈歷史和文化品位。長調民歌的研究涉及到音樂學的諸多分支學科。對它的研究與保護,實際上就是對歷史悠久的草原文明與草原文化類型最強有力的傳承與保護。
(二)地域之美
首先,長調是蒙古族傳統音樂中最具典型意義、且最具代表性及專業性的演唱形式之一。長調對蒙古族民歌的各個領域,如頌歌、宴歌、思鄉曲、婚禮歌、情歌乃至器樂曲等均產生了巨大影響。因而此種“長調美學”概念,滋生了蒙古族各個地域的民間歌曲之大美。
其次,長調一直以來均為口頭承傳的方式延續至今,且以不同地域的傳唱者或傳承人的個性特征為首要因素,因而豐富多彩的地域特征就成其之美的另一特征。
例如“會走路就會摔跤,會說話就會唱長調”的東烏珠穆沁旗的長調,就具備鮮明地域文化特征。2005年,東烏旗被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命名為“中國蒙古族烏爾汀哆(長調)之鄉”,并建立中國蒙古族烏爾汀哆(長調)研究基地,現已搜集到烏珠穆沁民歌200余首,內容極為豐富,其中部分民歌至今依然廣為傳唱;東烏旗是國內蒙古族長調民歌創作最多的地區,先后創編了《烏珠穆沁民歌》《烏珠穆沁民間故事歌集》《烏珠穆沁新歌專輯》等一大批長調民歌作品和音像制品。2006年,與內蒙古電視臺聯合錄制的《烏珠穆沁長調民歌》光盤,引起較大反響;還在旗內蒙語授課學校開設了長調、馬頭琴興趣班,將《烏珠穆沁長調民歌》正式編入中小學校課程規劃,并注冊了“蒙古長調”品牌商標。近年來,相繼成立了長調與馬頭琴俱樂部、長調民歌協會合唱團等民間組織。
(三)形態之美
根據蒙古族音樂文化的歷史淵源和音樂形態的現狀,長調可界定為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畜牧業生產勞動中創造的,在野外放牧和傳統節慶時演唱的一種民歌。長調具有優美的形態特征,可在多種場合演唱。
在演唱風格方面,其演唱具有裝飾音較為復雜、同一長音顫動(男性—顎顫音、女性—喉顫音)頻繁、“腔多字少”等特點;長調旋律悠長舒緩、意境開闊、氣息綿長,旋律極富裝飾性(如前倚音、后倚音、滑音、回音等),尤以“諾古拉”(蒙古語音譯,波折音或裝飾音)演唱方式所形成的華彩唱法最具特色。
在曲式結構方面,長調一般均為上下樂句的段落結構,也有“帶有再現意味的二部曲式、三部曲式以及多段體的聯句結構,在草原牧歌中也較為常見。”
在傳統曲目方面,較為傳統的長調有獨唱類的《走馬》《小黃馬》《遼闊的草原》《遼闊富饒的阿拉善》《孤獨的白駝羔》《圓蹄棗紅馬》《都仁雜那》《察干套海故鄉》《六十棵榆樹》,合唱類的《圣主成吉思汗》《原野》等。
在地域特色方面,烏珠穆沁長調,柴如拉呼(高音)和舒日古拉呼(泛音)等唱法的結合而產生獨特的韻味風格,區別于蘇尼特,阿巴嘎等地區。
傳承之憂
此次考察給我的總體印象是,以往教科書、歷史書中描述的“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生態已不復存在,以往長調之鄉“人人會唱”的民俗現象,似已成為歷史……傳承之憂,主要表現在其生態、傳承、審美、媒介、理念等幾個方面:
(一)生態之憂
有學者認為,蒙古族長調最大的魅力,就是與大自然的零距離依偎,或者說其本身就是一幅美麗的自然畫卷。但隨著社會發展的需求以及各地對GDP等的無度追求,加之遍地開采的煤礦、過度蓄養、放牧的牲畜,都使得草原沙化得以加速……就總體印象,此次考察的幾個地點,其“原生態”已失去原有的生態結構。因而筆者認為,在此基礎上種種的“人為”關照,恰恰只會違背藝術發展的自然規律,最終欲速不達或適得其反;加之近年來“馬背民族”逐漸走下馬背定居或融入城市,長調誕生的原生自然環與人文環境均發生了改變,馬背上的千年絕唱及一些獨特的演唱方式、方法瀕臨失傳。
(二)承傳之憂
筆者曾在《質疑“原生態”音樂》一文中言及:從以往大量的田野工作中我們不難發現:最為傳統、“原始”的音樂連同其表現形式,一般較多存活于交通、文化、社會等相對滯后的山區或半山區。由于歷史等原因,傳統音樂文化及其形式在這些地區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但隨著旅游業的不斷開發,這類地區的傳統音樂必將逐漸失去其原有的民俗根基,因而其變化在所難免。其主要表現在:
首先,個性化演唱面臨風格的終結。其表現為對長調“千人一腔”與“萬人一歌”的承襲現象或模式。可以說,這從根上終結了長調原本所故有的再生功能——即每個歌手稟賦的天才、創造、個性化的演唱傳統及風格;加之近年來,一些著名長調藝人(傳承人)相繼離世,此種只靠光碟或磁帶學習、模仿的長調民歌的現象,也將加速民歌再生功能的丟失。
其次,承傳鏈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隨著社會的轉型以及“村村通”(目前為“戶戶通”)工程的完結,會加速改變長調自然傳承與發展固有的傳統模式。
再次,發源地紛爭將陷惡性競爭與循環。筆者擔憂,內蒙古各地對長調、四胡、馬頭琴、呼麥以及其它項目“發源地”等的紛爭,既有可能加速各自間的“相煎”與排斥。本文此處所指“相煎”,僅限定于文化范疇。進一步說,僅指目前普遍存在于民族民間音樂范疇的一些“文化認同、遺產共享、利益之爭”的現象。本人借此警示并倡導:蒙古族音樂文化認同,應慎終追遠,不忘根本,地域遺產應共同分享、不忘其宗……
(三)審美之憂
第一,長調好聽的感覺沒有了。此指在一些地區的基層,經過藝術工作者(主要是藝術院校畢業生)的“甄別”、“指導”、“鑒定”或“挖掘”、“改編”后的長調民歌。難怪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民間長調藝人楊真策馬曾說:我非常不喜歡一些改編的歌,有人把民歌弄得亂七八糟的,就好像把一個好端端的東西弄得破破爛爛一樣,你們既然想創作,就另外創作一首歌吧,為什么要糟蹋我們民歌呢?其實,這也是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現代審美轉型中的另一特點,例如原先一些傳統音樂品種的音程關系被視為“音不準”而被“矯正”的實例比比皆是。
第二,長調動人的元素沒有了。原始、古樸的審美元素已逐步被流行音樂的審美取向所替代。例如蒙古族為主體結構的“草原”、“家園”、“黑駿馬”、“蒼狼”等等;當然,本人曾經認為,這也是少數民族傳統音樂逐漸轉型中的另一大特征,例如摩梭人以及西藏、新疆、內蒙、大小涼山等地區最為典型。
第三,長調好玩的體驗消失了。少數民族地區的一些傳統社交活動,被認為“原始”、“落后”而逐步受到青年人的冷落。例如以往長調所伴隨的那達慕、轉敖包等民俗活動的氛圍越來越淡,牧民自娛自樂的空間越來越小,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與商家越來越多的娛樂盛宴或文化品牌。
第四,長調神圣的氣氛淡化了。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許多傳統的祭祀音樂、儀式音樂已逐步失去其本來的面目,反之增添了許多的“表演”與“娛樂”成分。例如許多使用長調民歌的祭祀儀式或場合,更多了表演的成分而失去了原本的神圣與莊嚴。這在納西族的祭天祭風儀式、彝族的祭虎儀式、基諾族的祭大鼓儀式、瑤族的祭盤王儀式等也如此。
第五,蒙古民族的審美異化了。筆者認為,這個“異化”的根由,與本世紀以來的“烏蘭牧騎”模式相關。例如中西合璧的樂器配置,蒙漢民歌與舞蹈交相輝映的傳承模式,加之“文革”期間“樣板戲”、時下“現代化”等的觀念,也凸顯出為何在蒙古民族中,各類現代組合層出不窮的真正原因,之于今天全社會的傳承、保護語境而言,福兮?禍兮?
第六,固有的傳承模式改變了。此指蒙古族傳統音樂的傳承,不再遵循其固有的諸如自然傳承、家族(庭)傳承、師徒傳承等傳承模式,而逐步趨于相對單一的符號(樂譜)傳承、模仿(音響)傳承等傳承模式。加之各地興辦的傳習館、民俗村、藝術團、旅游點等,都清晰地表達出一個信息:即新的傳承模式,已逐步替代了固有的傳承模式。
(四)媒介之憂
2004年以來,原生態音樂在現代媒體的追捧下,逐步受到大眾(傳媒受眾)與小眾(行業學界)群體的普遍關注。今天看來,盡管兩者關注的焦點、理由各有不同,但此種持續關注均與新聞和電視傳媒的青睞、造勢密切關聯。譬如2003年以來漸次盛行的“原生態樂舞”系列、“歌王歌后”系列、“印象系列”、“展演系列”等等。長調在上述大環境與強勢輿論的裹挾、轟炸下,必然產生諸多“應景”之作,極可能在無形中誘導長調歌手們為參賽而“短平快”的速成,為展演而“千人一歌”的現狀持續良久。
(五)理念之憂
此次采風之旅,筆者似乎處處聽聞多地個別蒙古族文人、學者痛訴:“幾十年來,各級各類專業院校的培養,讓蒙古族這個天生能歌善舞的民族逐漸尚失了‘能歌與善舞’的天性……”對此筆者不予茍同——假如你稍微公允、客觀地審視這一話題,或是翻讀一下《蒙古族音樂史》等音樂類辭書、詞條等,就不難發見:專業院校不僅僅是培養、傳承蒙古族傳統音樂的重要基地,同時也是宣傳、弘揚蒙古族音樂文化的重要堡壘。
概括言之,蒙古族長調具有如下特點:第一,長調之美,美于上青天;第二,長調之憂,憂慮在心間:今天的長調會否成為落日的黃昏?明天的長調能否再續往日的輝煌!
筆者認為,蒙古族各支系(部落)在歷史上具有千絲萬縷的“親緣”關系,尤其在長調、呼麥、馬頭琴、胡爾等文化標識,因而其歷史源遠流長;在蒙古族各個部族歷史進程中,長調民歌保留有多有少,區域“涵化”甚至“變異”時有發生;蒙古族各個部族民歌的傳統稱謂、民間傳說、文獻記載、表演形式互為涵化、同多異少;長調的源流譜系等有待蒙古族學者作更進一步的考察與探究。
注釋
[1]即在重大場合唱頌的長調歌曲及有部分宗教信仰內容的“禮儀歌曲”。
[2]即指長調之外近似短調風格的“其他歌曲”。
[3]詳見斯仁·那達米德:《蒙古族傳統音樂》,載田聯韜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音樂》,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頁。
[4]參見長調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資料。
[5]參見札木蘇、斯仁·納達米德:《蒙古族音樂》,載《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頁。
[6]和云峰:《質疑“原生態”音樂》,載于《藝術評論》2004年第10期。
[7]麗江洞經音樂中的某些特色音已被還原;“擺時”中的“漸強”(向上方)的滑音傳統已逐步在改變;白族的大本曲、吹吹腔等已加入嚴格意義上的配器;摩梭人的打跳有交誼舞的痕跡,最為時尚、新潮的流行歌曲成為青年人趨之若騖的新寵;尼蘇人的“吃火煙草”被認為是低俗與落后的代名詞;新疆、西藏的現代音樂成為青年人首選的“民族音樂”……
[8]新疆、西藏的現代音樂(搖滾等)和新音樂(民族語言翻唱、老歌新唱等)成為青年人首選的“民族音樂”。例如彝族的“山鷹”、“彝人制造”,維族的“阿凡提”、“灰狼”、藏族的“珠目朗瑪”、“高原紅”、回族的“西部孩童”等現代組合如雨后春筍,走紅一方既為明證……詳見和云峰:《質疑“原生態”音樂》,載于《藝術評論》2004年第10期。
[9]指職業、非職業的學校音樂教育傳承模式;此類模仿用老藝人們通常的話說,就是“學皮不得筋、學相不得心”,亦如讓一個學戲曲的學生單靠讀譜學習唱腔一樣,難得真傳。
[10]即以楊麗萍《云南映象》為代表,后續在全國各地陸續出現的一系列相類似的表演形式。
[11]即2004年11月5-7號北京海淀劇院西北十大“歌王歌后”晉京表演活動。
[12]以張藝謀為代表打造的大型山水實景演出《印象劉三姐》、《印象麗江》、《印象西湖》、《印象海南島》以及2010年正式上演的《印象大紅袍》等。
和云峰:中央音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