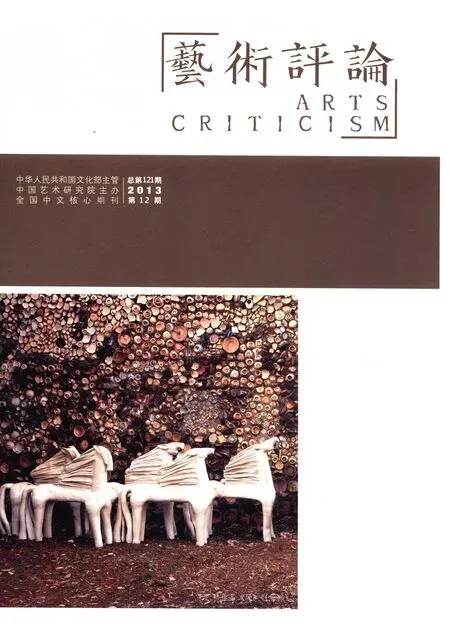進程
——寫在新時代的邊上
高士明
進程——寫在新時代的邊上
高士明
在越來越寬闊的漩渦中
旋轉、旋轉,
獵鷹再聽不到獵手的召喚
萬物分離,中心再也不再支撐
只有離亂在世間流散——葉芝《第二次降臨》
我們在等待什么?等待我們的是什么?——布洛赫《希望的原則》
為什么思考“進程”?因為——音樂史掩蓋了聲音的歷史;電影史掩蓋了影像的歷史;戲劇史掩蓋了身體的歷史;文學史掩蓋了寫作的歷史;建筑史掩蓋了筑與居的歷史……
進程
2000年千禧之夜,整個世界都在喧囂與歡樂中沸騰,我獨自坐在書桌前,第一次真切地感知到世代遷化、時間流轉的宏大力量。面對窗外襲來的陣陣寒冷與黑暗,我寫下這樣一段話:
凌晨一點/我摸索到/上帝的指紋/時間的形狀/那波浪如同/黑暗中涌動的群山/在大海疲倦的喘息里/綿延、起伏/撞擊、破碎/日以繼夜。
許多年來,當時那種錐心刻骨的感覺時常涌上心頭,令我不能自已。那種莫名的感受并非“歷史”所能涵蓋,因為所謂“歷史”,早已在學科化、科層化的現代知識生產中淪為了專家們操持的知識、文本與工具,成了與生命經驗無關的東西。千禧之夜,我經受到的,是一種無名的“進程”。“世”為遷流,“界”為方位,那世紀之交的黯夜中涌動、彌散、演進著的莫名事物,無形無質,無始無終,無窮無盡。
那么,這歷史的汪洋何以成為一種“進程”?這無名之“進程”究竟朝向何方?
基地
“西岸2013”的策展意念始于對“進程”的探究。而此“進程”在西岸的顯現方式首先是一種更生。黃埔江畔的這片狹長的土地,因2010世博會而被再次“發現”。留在這片土地上的,是上海現代大工業的記憶之場。碼頭、火車站、機場,以及生產城市肌體之基本質料的水泥廠……隨著上海世博會的舉辦,這些舊工業的遺跡被納入大規模的城市更新與營造計劃,成為一塊重獲新生、尚未定義的“土地”。
在世界范圍內,西岸作為現代工業的記憶之場也許并不獨特。半個世紀以來,大量工業廢墟正在不斷侵蝕著歐洲人當下的生活圖像,那些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的現代工業場所,正在成為時間的廢墟和紀念碑。這一切,都奇妙地吻合了現代性的時間邏輯,這也正是本雅明在巴黎拱廊街的迅速衰老中所體味到的:現代意味著,新事物很快會成為陳舊的象征,進步趕走進步。現代性正不斷地被“現在”背叛,所謂現代,只是永逝不返的時間之河上不斷擺渡的過客。正是因為這一點,本雅明才將偉大的19世紀比作“神童們的養老院”。不斷發展的現代性,也是不斷創造過時和過期的現代性。于是,沒有哪個時代比現代更加迫切地需求記憶,于是,非常吊詭地,博物館、歷史寫作、檔案制度與懷舊意識成為現代性的重要表征。
如何跳脫出一種決定論的、目的論的以及進步論的歷史幻象,同時避免陷入徒勞的紀念與懷舊?如何從現代性的廢墟上重新勾畫出一種具有生產性的未來愿景?我們需要再一次切近這個已為陳跡的記憶之場,去聆聽,去觀看,去體察。
2012年某個秋日的傍晚,我第一次面對這個原為預均化庫的巨大穹窿,它如一座天外降臨的飛行器,又像洪荒巨獸的骨骸,蟄伏在黃浦江畔,擱淺在歲月的河床上。“埋沒英雄芳草地,耗磨歲序夕陽天”。步入穹窿的黑暗門洞,我又一次感受到那股歷史的洪流,莫名的進程。
那現場還在,場所的魂魄尚未離散。滄桑歲月中無數人思想、身軀的聚集與運動、期待與生活、血汗和勞作,依然在這個巨大的廢墟空間里攪拌回旋。歷史的動力與幽蔽,時代潮流的順與逆,一個城市的生與死,無數人的幸與不幸,全都聚攏在這個巨大穹窿下凝結的工業動作之中,形成一種命運般的力量旋轉攪拌,不由分說,泥沙俱下。
從空間結構上,這個攪拌水泥的巨大車間酷似古羅馬的萬神殿,但是,這回環往復的歷史巨力,卻絕非來自亦非朝向那羅馬式的無盡透視的蒼穹。在歐式穹頂建筑的符號學構造中,那透視錐的頂端,原本是上帝的凝視。神圣的目光從天空降臨,穿透一切,無所不至。神目之所及,威能之所在。人只是被檢視者,是“看(守)”的對象。博爾赫斯失明后的寫作中,曾多次提及這無限透明的藍色蒼穹。“一扇天窗讓我們潛入那真正的深淵”,透過頂部的空洞所看到的是無限的深淵,那里躲藏著一個無限透明(因而不為我們所見)的實在世界——“在那晶瑩清澈的世界中/一切發生又不留痕跡”。
在“西岸2013”的框架中,“進程”所欲破解的,首先就是穹頂結構所蘊含的神學維度。“進程”所裹挾的,無關形而上的意旨,純是眾人的命運、人世的歷史、人間的記憶。這命運的巨力,這歷史和記憶,在宏大空間中浮沉隱現——聆聽、觀看和體察,這三種行動分別引出主題展中的三條藝術線索從不同角度映射出進程的歷史與軌跡。
聆聽
一百年前,未來主義藝術家洛基·盧梭羅(Luigi Russolo)以其“噪音調音機”開啟了現代聲音藝術的歷史。從此,工業機械與大都市開始成為聲音演出的重要主題;從此,樂音對面的噪音世界里不斷噴涌出感性的激流與創造的能量。
然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在“西岸2013”聲音藝術特展的框架中,聲音首先作為探測現場的一種方式。在這座占地6000平方米的圓形廠房的空曠廢墟中,我們聆聽到的首先是“沉默”。“語言破碎之處無物存在”,而沉默并非單純的無聲。沉默內置于人類的語言和音樂之中,是所有話語和聲響成為可能的基礎。然而,在現代大都市無止境的永續基調音和嘈雜聲場中,沉默作為一種聆聽經驗,已經永久地丟失了。城市之聲脫離了它發生的時間和空間,在現代媒體的廣播系統中發送、復制、混響、疊加……無休無止。聲音不再開始于沉默,也不會在沉默中消失。聲音已經無法回歸沉默,只能在其他的話語和聲響中轉義、離散。
然而,在這幽暗的穹窿之下,久違的沉默仿佛再次現身。此處的沉默是歷史幽蔽的一部分,空間中氣流的運動,廢棄物細微的窸窣聲,歲月深處機器的運轉,工人們曾經的低語,這一切交迭而成沉默之“殘響”。通過這歲月的“殘響”,我們繼而聆聽到更遠處塵世的喧囂與城市之聲的騷動。每個現代城市都是一個聲音劇場,在中國的聲音史上,上海必定是最精彩的那一個。從黃埔江上的汽笛到有軌電車,從百樂門的歌舞到里弄的叫賣聲,從“文革”廣播到上海清口……林林總總,所有的聲音碎片與日常生活史的絲絲縷縷交織在一起,形成上海這座城市永不消失的聲場和獨特的聲音文化。
然而,拋開這聲音表象的蕪雜叢林,我們是否能夠聆聽到歷史的耳語和社會演進的轟鳴?光碟時代,聲音的出現有賴于旋轉。作為“進程”的重要部分,姚大鈞策劃的聲音藝術特展以“轉速”為題,探討當下聲音現實中“每分鐘的革命”(RPM)。
觀看
屏幕上的現實是被觀看的現實,身邊的現實是包圍著我們的、我們所看不到的現實。屏幕上顯影的世界是“看見的世界”,“看見的世界”是“看得見的世界”,也是“被觀看的和用來觀看的世界”。
觀眾注視著被放大的影像,把它看作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忽喜忽憂;這些觀眾同樣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卻難以面對這個日常的世界。日常世界星星點點,又綿延不絕、難以琢磨,影像作品卻給出了一種面對世界的可能性。“透視法也許不再能夠代表我同世界間的距離,它以我為坐標確立世界的位置,把世界擺置在我面前,從而使我忘記了世界同樣在我身后和我在世界之中。而攝影機也在世界之外注視著世界。”在此,斯坦利·卡維爾說出了關鍵所在。電影的秘密正在于它是我們所渴望的景象,它是從我們自身的綿延中斷裂開去的,因而是可完整把握的。我們順從而舒適地看著那個世界,那個世界早已被另一只外在于世界的眼睛對象化、表象化了,因而已經是一個“看見的世界”。
正是這個“看見的世界”,這個“被觀看的和用來觀看的世界”,將我們定義為單純的觀者,并且日益取消了我們作為生產者的能力。這種景觀化的影像,正是名為“解像力”的影像藝術特展所欲批判、抵抗之物。影像特展由郭曉彥與劉瀟共同策劃,對她們來說,影像的解像力不止是為了讓現實更加清晰,而是要讓那幅清晰明確的現實圖像重返未定狀態。在媒體時代,我們無法直接地面對現實,我們所面對的、所看到的,只是已經被表述過的現實的現成圖像。“解像”之于現實圖像,不只是解讀,更重要的是解構。
而解構的力量,來自從影像中轉化出行動的能力。影像特展希望召喚出一種“行動影像”,然而這“行動影像”并非“直接電影”式的用影像去行動,而是讓影像成為行動。
在解放戰爭早期的晉冀魯豫邊區,每當發起沖鋒之前,隨軍攝影師會給每位敢死隊的戰士拍照。這是生命中的莊嚴時刻,也許是最后時刻。戰士們隱約知道,由于物資匱乏,相機里很可能并沒有膠片。但他們依然穿戴整齊,面對相機,擺好姿勢,拍完生命中最后一張或許是唯一的照片后,沖向九死一生的戰場。
沖鋒之前那無膠卷的攝影儀式,讓我們從另一種角度思考影像的本質。這些影像在眾人的意念中傳遞、累積,漸而生產出一種解放的能量,轉化為行動的勇氣。
解像,一種行動影像,不只是用影像召喚出現實行動,更重要的是,它召喚我們從被動的觀者處境中解放出來,重新成為影像的生產者,這就需要我們先行奪回被剝奪的影像之能力。在這里,“影像”是一個動詞,這個動詞意味著——用最切身地方式去觸動、去感知,在影像的生成創造中反求諸身,在生活-行動中,在切身-返身的辯證中去創造新的斷裂與詩意,在這新的詩意之展開中,讓影像成為行動,讓經驗不再現成,讓知覺始終保持敏感,讓世界重新變得生動。在這個意義上,解像力所指向的“行動影像”,不但是“生產者的影像”,也將是“解放的影像”。
體察
“進程”的戲劇部分,創作意念的起點是《彼岸》。1993年,牟森選擇高行健的劇本《彼岸》作為文本基礎,邀請詩人于堅創作長詩《關于彼岸的漢語語法討論》,從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兩個角度建構起他的“彼岸”。這是中國當代戲劇史上的一件轉折性作品。1993年的北京,《彼岸》的排演如同一場沉默的風暴,在城市的角落隱秘發生,卻必將席卷文藝界眾多躁動不安的人群。事實上,《彼岸》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跨領域、跨媒介的藝術運動,這場運動在無意識中悄然發生,卻一發而不可收。隨著這出戲的排演,戲劇、電影、舞蹈、音樂、當代藝術,所有領域都動了起來。在牟森的劇場中,“彼岸”,是一個動詞”。
把我們心中的感激與歡樂告訴所有人!
把我們身體的解放告訴所有人,讓每一個人都動起來!
讓我們為動命名!
命名吧!為神圣的動命名!
命名吧!為這個給我們身體自由的動命名!
命名吧!為這個讓我們重獲生命的動命名!
命名吧!命名!
好吧---讓我們命名——彼岸!
彼——岸!
正如影像中可以轉化出行動的能力。作為一個動詞,彼岸不止于烏托邦,通過于堅的長詩,彼岸構造出烏托邦的反面,在正與反的辨證中,形成巨大的意義張力,帶給我們席卷一切的力量。牟森常說,主題即結構,1993年的《彼岸》可謂個中典范。

除“光啟”、“匯通”、“洪流”這些眩目的奇觀之外,《上海奧德賽》召喚回了《彼岸》中的若干元素——出演者的非職業性、編導與表演的一體化、“變演為做”的身體感與反表演性。同時,20年前的諸多要素都在不斷轉義中獲得新生——《關于彼岸的漢語語法討論》化作雅克·布朗華麗的高音吟唱,《彼岸》中連接、束縛所有肉身的繩索,成為工人與巨型機械兩種身體感彼此依戀、抗爭的血親紐帶,繼而成為引導我們走出命運迷宮的阿里阿德涅之線,最終又化為通向彼岸之橋。
《上海奧德賽》并非通常所謂“先鋒戲劇”,對導演團隊來說,“先鋒戲劇”在1990年代后期的類型化和品牌化,是一個巨大的悲劇。先鋒性在所有時代的戲劇中閃現,先鋒性只有在真正改變了人之感受力的時刻才發生。今年是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一百周年,為此,導演團隊邀請了上海的不同社群,從排舞老者,到水泥廠的工人,共同參與對《春之祭》的改編與排演。通過這個普通人集結成的城市劇場,《上海奧德賽》告訴我們:戲劇要回到它的本源,一種手工業的狀態,它通過身體、語言的連接和行動,開啟一個公共之場所(Arena),在這個場所中,人們可以獲得看待生活的詩意態度,可以重新定義自我和現實的關系,可以“無所畏懼地在一起”——格列托夫斯基說,這就是節日。
尾聲
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時代?
我們正在參與一個怎樣的進程?
千禧年之夜、步入巨大穹窿的瞬間,我感受到的那股洪流,那種無名的進程究竟是什么?此進程遠超出我們囿于這個時代的自我感知,也超出了歷史學試圖打撈的因果、試圖描述的畫面。此進程是莫名的,無名的,并沒有確定的目的和方向,卻猶如命運般不可阻擋。
170年前,上海開埠,這座偉大的城市開始了它的現代之進程。170年后,當我們回望、經驗并且辨識著這座城市的記憶與過往,諸眾的形象、帝國的倒影、現代文明的華麗景觀、民族國家的傳奇和夢想交織輝映;十里洋場、中西之辯、殖民與去殖民、革命與后革命、社會啟蒙和民族獨立、文化革命與改革開放……這段進程裹挾著無數人的姿態和運動、影與像交疊、聲與音的混響,泥沙俱下,演繹出百余年來國人的抗爭和尋覓、離合與悲歡。身處這復雜糾結又磅礴恣肆的宏大進程之中,我們如何自處?藝術如何作為?
在本文的最后,我再一次告訴自己,我們的時代是個大時代,并且,我們有幸活在一個新時代的邊緣。雖然這個新時代總是尚未到來,雖然它不過是宏大進程中的一幅臨時性畫面,雖然這幅畫面的意義總是在歷史的演進中被反復改寫,但是,進程中的歷史主體,卻不憚于成為里爾克詩歌中的困獸——“仿佛力之舞圍繞著一個中心/在中心一個偉大的意志暈眩”。
(本文為“2013西岸建筑與當代藝術雙年展”而作)
高士明: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