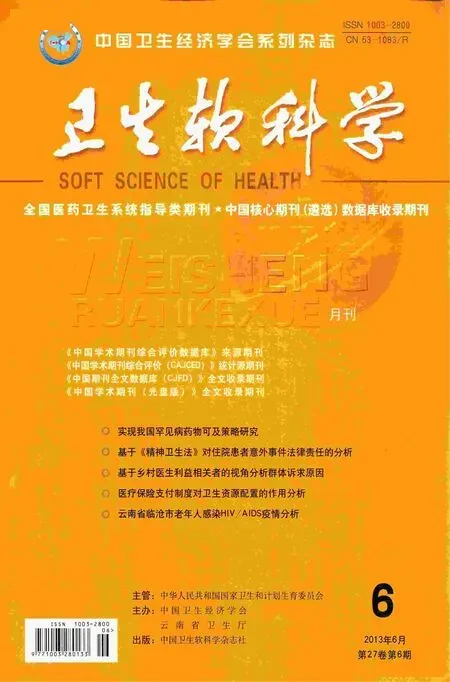實現我國罕見病藥物可及策略研究
谷景亮,魯艷芹,張 睿,岳 媛,段永璇,徐凌忠
(1.山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012;2.山東省醫藥衛生科技信息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062;3.山東省醫藥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山東 濟南 250062)
罕見病是指那些發病率極低的疾病。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罕見病為患病人數占總人口的0.65‰~1‰的疾病,像成骨不全癥、血友病、法布雷病,還有肺動脈高壓、戈謝氏病等都屬罕見病范疇。目前,世界各國對罕見病的認定標準仍存在差異。美國規定罕見病是指每年患病人數少于總人口0.75‰的疾病;日本規定為患病人數少于0.4‰的疾病;澳大利亞規定為每年患病人數少于0.1‰的疾病;歐盟規定指患病率低于0.5‰的疾病[1]。
罕見病藥物又稱“孤兒藥”,是指用于治療罕見疾病的藥物。罕見病藥物因為目標治療人群數目較少,市場用量稀少而沒有公司愿意研發,使得罕見病的治療藥物價格昂貴。如果沒有良好的社會保障系統,普通公民個人很難支付得起疾病的治療費用。這些都直接危及罕見病患者能否得到他們需要的藥物,能否享有和其他病人一樣等同的治病權利,這些都可能帶來一定程度的公共健康風險。
1 罕見病藥物可及性概念
可及性作為衛生服務研究中的基本術語是指將衛生服務系統和服務人群聯系在一起,通過個人實際發生的衛生服務利用,來研究潛在的促進和阻礙服務利用的各種因素[2~4]。1999年WHO將藥品可及定義為人群在距離家步行1小時范圍內的醫療機構或是藥品銷售點能持續地獲得可負擔的藥品就稱為可及藥品。WHO定義基本藥物的可及性為患者或消費者能夠在合理的距離內方便地在醫療機構獲得基本藥物,并在經濟上可負擔基本藥物。
2001年WHO指出影響藥品可及性的兩個決定性因素為可獲得性和可及性。可獲得性含義是指是否有令人滿意的產品被開發,是藥品從無到有的過程,包括藥品的基礎研究階段和藥品被發現、研制并上市的過程。藥品的可及性包含了四層含義:選擇藥品的恰當性(可靠質量、合理選擇、恰當使用),供給系統的效果與效率(有效的供給途徑和供應能力),經濟因素(籌資途徑、成本、定價政策、銷售價格)和患者的知識與健康信息的獲取行為(社群性質、受教育程度、社會經濟地位)。2004年WHO又提出促進國家基本藥物可及性的四大因素:合理選擇與恰當使用基本藥物、可負擔的價格、持續的財政支持和可靠的供應系統[5~7]。
罕見病藥物的可及性是實現罕見病患者的衛生服務需要變為需求的過程。這是罕見病患者需要經歷的漫長之路,也是急需得到平等治療的公平之路。罕見病患者和常見病患者的住院醫藥消費都為一種奢侈性消費,對常見病住院患者而言這種奢侈性更多是因為家庭收入偏低;而對罕見病住院患者而言,家庭收入不僅偏低,而且醫藥服務價格相對過高,尤其是藥品的價格居高,更顯得是雪上加霜,加劇了這種消費的奢侈性。有文章指出在11種罕見病中有4種罕見病住院醫藥服務的支出對農村居民家庭而言是一種災難性衛生支出[8]。所以,提高全民的家庭收入、降低住院醫藥服務費用、有針對性提高災難性衛生支出疾病患者醫療保險報銷水平,應是政府提高不同疾病患者的醫藥服務可及性的關鍵政策內容[8]。國際上促進患者罕用藥可及性的管理制度體系的構成是一種以產業激勵政策為導向的促進患者罕用藥可及性的公共衛生政策。但要解決罕用藥可及性問題,不僅是一部罕用藥傾斜政策的作用,而是與國家的醫學科學、生物技術、新藥研發的激勵制度、醫藥企業風險投資制度、藥品短缺供應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罕見病信息管理制度、醫務工作者的在職培訓計劃等全方位的制度設計相互配合共同作用的結果[5]。
2 國內外實現罕見病藥物可及現狀
罕見病是一個世界性問題,美國和歐盟把每個閏年的2月29日定為罕見病日,它們用這個4年才有的一天暗喻罕見病罕見的特征。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預防、治療、診斷罕見病的藥品因為產量少、適用范圍小、成本高,被國際上稱為孤兒藥。由于罕見病患者人數少,發病率低,這些年來一直被醫療機構和社會各界所忽視和冷漠。當前已經確認的6000多種罕見病,目前僅有1%的罕見病找到了有效的治療藥物[5]。
基于“孤兒藥”研發的高風險現狀,許多國家對其給予了政策上的支持。美國1983年通過的《孤兒藥法案》及后來的幾個修正案為孤兒藥研發提供了具體的經濟激勵。譬如向孤兒藥研發公司提供開發補助、研究基金和快速審批通道;上市后給予7年期市場獨家經營權等鼓勵措施;臨床試驗費用的50%可抵減稅額,新藥申請費用也給予免除。日本于1993年正式實施了《罕見病用藥管理制度》,研究的全過程可享受基金資助、減稅、優先審批、藥品再審查時間延長及國家健康保險支付上的優惠。我國臺灣地區在 2000年也制定并實施了罕見疾病醫療補助辦法,對醫療支付制度作了詳細的規定。對罕見遺傳病患者使用的藥物,及維持生命所需的特殊營養品費用實行全額報銷。
世界各國對罕見病藥物的法律法規激勵了生物醫藥公司對罕見病藥物的研發,也大大加速了罕見病藥物的上市。美國在 1983年罕見病藥法案實施之前僅有不足10個罕見病藥物上市,到了2012年7月,在FDA登記的罕見病藥物已達2642種,獲得上市批準的孤兒藥產品達到405種。在美國市場上,中小型制藥公司生產了超過70% 的孤兒藥,其中許多公司都是在1983年之后單純依靠孤兒藥而啟動、發展起來的[9]。歐盟在1999年罕見病藥物法規實施前,僅有8種孤兒藥被審核通過,至今已有1653種孤兒藥產品得到認定,139種獲得歐洲市場孤兒藥產品地位,其中64種先前獲批了孤兒藥設計,75種未先獲孤兒藥設計[10]。
可喜的是,我國在罕見病立法方面進行了許多有意義的推動探索。全國人大代表已經連續多年提出關于罕見病患者救助的建議,希望把罕見病納入社會保障系統,并呼吁制定《罕見病防治法》。2009年初頒布實施的《新藥注冊特殊審批管理規定》,將罕見病用藥審批列入特殊審批范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處日前透露,醫保藥品目錄確實未能涵蓋所有腫瘤和罕見病的治療藥物。下一步,隨著醫療保險籌資和保障水平的不斷提高,逐步將罕見病患者急需的特效藥物納入醫療保險藥品目錄,這無疑給“罕見病”患者帶來了希望。
3 實現我國罕見病藥物可及性策略探討
促進患者罕用藥可及,實際就是實現藥品從供方到需方的過程,反映了醫藥衛生系統滿足人們用藥需求的保障能力。美國的罕用藥法案被評論家譽為過去29年里改善美國藥品供應狀況最有力的政策[11]。現階段,我國對疾病尤其是罕見病的新藥研發尚未有明確的法律法規支持。我國對于孤兒藥產品的研發仍屬空白,基本上是靠國外進口,國家對罕見病的治療費用尚無保障政策,一般患者家庭無力承擔治療費用。因此,要實現我國罕見病政策的良好發展和罕見病藥物的可及,首先需要在借鑒國外政策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基本國情,從促進全民發展的思路,關愛罕見病患者,制定相關政策,完善醫療救助和保障制度。
3.1 要促進罕見病藥物的可獲得,支持藥物的研發
一是要明確我國的罕見病定義,盡快頒布罕見病制度,明確政策支持。目前我國的罕見疾病防治法草案已被全國人大立案,立法指日可待。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09至2011年全國醫療衛生預算總投入約為8500億元。希望罕見病防治法能夠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認真考慮并最終通過,讓中國的上千萬名罕見病患者從醫療保險中受益,并能有更多的孤兒藥可供他們使用。同時,期待有更多的跨國公司和國內制藥公司在罕見疾病防治法的保護和激勵下,開發出更多安全、有效、經濟的孤兒藥,實現制藥企業和罕見病患者的互惠雙贏。我國的藥物注冊管理辦法(2007年)和藥物特別審批程序(2005年)已建立了一些嚴重疾病和突發事件應急所必需藥物的特別審批制度。但這些政策在實施原則、審批標準和確保藥物評價準確性的管理措施等方面還需進一步明確[12~14]。
二是要加快扶持罕見病的相關科學研究,大力加強國家管理機關、科研機構、藥品研發機構和保險機構之間的相互協調配合。借鑒美國的《罕見病用藥法案》對罕見病藥品臨床研究費用減免稅金,并提供研究資助制度,研究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罕見病藥物研發配套激勵措施和扶持政策。
三是要利用世界各國罕用藥的發展給我國帶來的啟示,牢牢抓住現實發展機遇,搶抓罕見病現有樣本資源,積極申請專利保護,避免技術和觀念的滯后,帶來“藥貴病不醫”的嚴重后果,給社會和家庭造成沉重的精神和社會負擔。
3.2 增加藥物的利用支持,促進罕見病藥物的可及
在目前確認的6000余種罕見病中,絕大部分都是無藥可治的,只有少部分有藥可治,但是就這少部分特效藥還依賴國外進口,價格十分昂貴,一般的家庭難以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實現醫療衛生服務需求變為需要將是今后長期努力的方向[5]。
一是將罕見病納入社會醫療保障系統,實現醫療保障制度的全覆蓋,建立起多層次的罕見病藥品費用支付機制,提高患者支付能力。目前我國的居民醫療保障制度主要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制度、公費醫療、其他社會醫療保險,但均不能覆蓋罕見病的治療,使得最應該受到保障的人群反而沒有了保障,這也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二是將罕見病藥品逐步納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實施國家戰略,建立特效藥品儲備,保障罕見病患者權益,及時獲得救命藥品。
三是完善社會救助機制。如何救助罕見病患者,是各國都面臨的一個社會問題,世界上有不少國家已經通過立法的形式,來開展對罕見病患者的救助,使其有能力看得起病,看好病。近兩年,我國已逐步啟動了罕見病患者的救助活動,2009年3月中華慈善總會在京成立了罕見病救助辦公室,并于2009年12月正式設立了罕見病救助公益基金。
四是引入嚴重疾病新藥治療的擴充途徑和加快審評機制, 讓嚴重疾病患者更快更早地獲得有希望的治療新藥,及時滿足公眾的健康需要, 維護衛生公平。
[1] 馬 端,李定國,張 學,等.中國罕見病防治的機遇與挑戰[J].中國循證兒科雜志,2011,6(2):81-82.
[2] 陳英耀,王立基,王 華.衛生服務可及性評價[J].中國衛生資源,2000,3(6):279-282.
[3] 李 景,褚淑貞.國內外藥品可及性現狀淺析[J].上海醫藥,2011,32(6):278-281.
[4] 龔時薇,許 燚,張 亮.藥品可及性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中國衛生經濟,2011,30(5):72-74.
[5] 龔時薇.促進我國罕見病患者藥品可及性的管理策略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08.
[6] WIDDUS R.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health: their main targets,their diversity,and their future directions[J].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1,79(8):713-720.
[7] 龔時薇,張 亮,金 肆,等.提高我國罕見病患者用藥可及性的管理策略研究[J].中華醫院管理雜志,2010,26(2):126-130.
[8] 龔時薇,張 亮.我國常見病與罕見病住院患者醫藥服務需求彈性分析[J].中國衛生經濟,2011,30(2):39-41.
[9]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美國罕見病藥物產品數據庫[EB/OL].[2012-07-20]. http://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opdlisting/oopd/.
[10] ORPHANET.歐盟罕見病藥物產品報告[EB/OL].[2012-07-20].http://www.orpha.net/orphacom/cahiers/docs/GB/list_of_orphan_drugs_in_europe.pdf.
[11] SCHEINDLIN S.Rare diseases,orphan drugs,and orphaned patients[J].Molecular intervention,2006,6(4):186-191.
[12] 龔時薇,張 亮,都麗萍,等.美國促進用于嚴重疾病治療新藥可獲得性的審評機制分析[J].醫學與社會,2008,21(9):9-11.
[13] 黃尚志.思考中國的罕見病問題[J].醫學研究雜志,2010,39(11):3-4.
[14] 辛征駿,王子壽,陳祝君.我國罕見藥物現狀分析及對策探討[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11:349-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