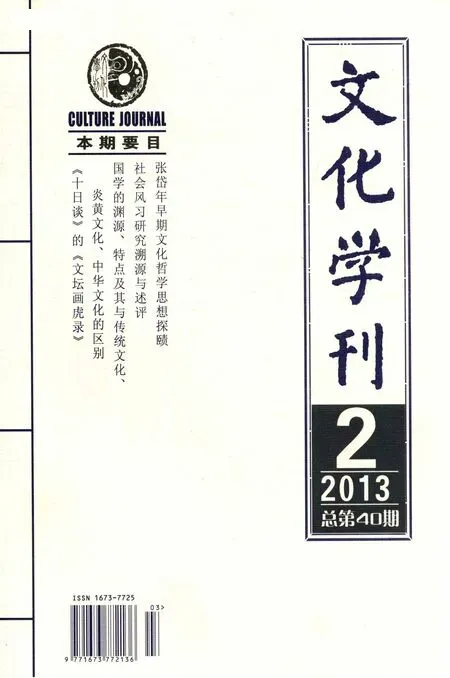中國法治困境的歷史文化根源
沈 慧
(遼東學院,遼寧 丹東 118001)
一、中國傳統法哲學文化中人本思想的生成及其對法制的影響
中國傳統法哲學文化中人本思想的生成是中國古代法制合理性的重要哲學基礎。人本思想的萌芽最早出現在中國的奴隸社會時期,在夏商時代崇拜神權的法哲學是統治階級推行的主流意識形態,主張“受命于天”、“王權神授”和“代天行罰”等宗教神權法思想,企圖利用當時人們對自然的畏懼感欺騙和麻痹人民來服從奴隸主階級的統治,但是終因他們的殘暴統治遭到了人民的反抗而走向末路。西周統治者在滅商之后總結吸取了夏商失敗的教訓,對原來的神權法思想進行了修改,強調“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逐漸將遵從天命的思想引向了對人民的重視上,主張“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桓公六年》),可見在西周社會人的地位較之前的夏商時期是明顯有所提高的。雖然西周統治者對人民的重視仍然是在“王權神授”的基礎之上,但畢竟開始了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因此,我們認為在奴隸社會中,具體是西周時期就產生了人本精神的萌芽。到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處于奴隸制走向瓦解崩潰、封建制走向興旺發達的社會大變革階段,民心的作用更加突出地顯示出來了。如齊國人管仲提出“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國語·齊語》)和“令順民心”(《史記·管晏列傳》),表現了他重視法治和以民心為歷史潮流評判標準的進步思想。又如鄭國執政子產嚴厲反對夏商以來的“代行天罰”思想,主張“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傳·昭公十八年》),其意思是,“天道與人道是兩回事,人間的吉兇禍福在于人事,而不在于天地賞罰,政治的興廢和國家的存亡的關鍵是爭取人民,而不是祈求鬼神。”[1]可見,子產的觀點已經將人從神權的主宰中解放出來,強調了人的價值的獨立性。再如楚國人老聃,盡管他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極力主張愚民政策,但是也提出了“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殺懼之也”、“民之不畏畏,則大畏將至矣”[2]的觀點,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他對人民具有反抗殘暴統治的歷史作用的認同。以上列舉的這些人物及其思想觀點只是體現了當時思想家對人已經有了一定的關注,而真正開啟了中國法哲學人本精神的則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魯國人孔丘所創立的“仁”學充分體現了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肯定,“仁者,愛人”(《論語·顏淵》)就是孔子看待世事和處理人事關系的基本準則。孔子的學說后來得到了孟子的繼承和發展,孟軻很重視民心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仁政”思想,如他所倡導的著名的“民貴君輕說”,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就充分體現了他鮮明的重民思想。到西漢武帝時期,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大一統”的思想方針,儒家思想遂一躍成為官方性質的封建正統思想,開始了對中國思想界長達兩千年之久的統治。這種思想專制雖然有很大弊端,但在當時,儒家思想確實在肯定人的價值尊嚴和提升人的地位方面發揮了積極意義,如董仲舒就對人的地位有很高的評價,“人受命于天,固然異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貴也。”[3]由此可見,西漢以后,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法哲學文化傳統生發的基礎,中國傳統的人本精神主要也是脫胎于儒家的人本理念。而儒家思想在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官方思想之后必然是從統治階級的立場出發進行發揚光大,因此,儒家思想中人本主義的內容更多的體現為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態度,最終儒家思想的民本觀念構成了中國法哲學文化傳統中人本思想的主要表現。
毫無疑問,中國傳統法哲學文化中人本思想的生成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律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一,德主刑輔的法制模式。在西漢時期,董仲舒總結了秦朝兩世即迅速滅亡的歷史教訓,認為秦法的酷刑暴虐是導致秦朝統治悲劇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主張利用儒家思想中的“仁”來革新法制,提出所謂的“大德而小刑”的法制原則,其實就是德主刑輔。董仲舒認為,德、刑之間是有主次之分的,“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天辨人在》)因此,應該以德治為主,刑罰為輔,這與陰陽之理是相通的。董仲舒的德主刑輔理論不僅是對先秦儒家“寬猛相濟”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也為后世法制模式的選擇提供了深刻的理論根據,如唐代名臣魏征也承繼了這一思想,主張治國之本在于廣施仁義,遵守德禮,不能依靠嚴刑峻法。其二,恤刑慎殺的刑事政策。儒家思想主張“仁政”,其人本精神也體現了對人的生命的重視,“民命為重”、“人命關天”等就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另外刑罰的殘酷性與受刑人的體質情況都是儒家人本思想所具體考慮的問題,減輕刑罰的痛苦性、減少刑罰對人的尊嚴的侮辱性和體恤處于弱勢地位的受刑者等都顯示了儒家仁政的人文關懷。可見,恤刑慎殺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既包括死刑的裁決程序、死刑的適用范圍,還包括刑訊和行刑過程中對各種情況的裁量等。縱觀各朝代的法制狀況,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統治者與大臣都以采取恤刑慎殺的刑事政策而名垂法制青史,如漢文帝廢除肉刑、唐太宗李世民對死刑程序的嚴格規定等,歷史的發展充分證明,這種寬仁的刑事政策對調和封建社會的社會矛盾,安撫民心起到了極其有益的效果,不僅維護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權穩定,還進一步促進了國家的發展與繁榮。
二、對中國傳統人本思想局限性的思考
在中國傳統法哲學文化中自生的人本思想表達了古代中國人民對自身價值和地位的認識,不僅在時間上明顯早于歐洲的人文主義思潮,而且在內容上也體現了與西方人文主義不同的特色,如天人合一的天人關系等。應該說,中國傳統的人本主義思想在古代社會當時是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的,不僅奠定了中國傳統法文化的哲學基礎,而且也影響了當時社會法律制度的構建與運行,涉及立法、司法和執法等各個環節,促進了中國法制的形成與成熟發展,為調節與緩和封建時代的社會矛盾提供了人本主義視角下的處理途徑。但是,自生于中國封建時代土壤的傳統人本思想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尤其在我們今天來看它所能起到的積極作用是極其有限的。對此問題中國法史專家張晉藩教授在其著述中有過深刻的反思,在此基礎上,筆者試圖對中國傳統人本思想的局限性進行以下思考:
首先,中國傳統人本思想是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自從儒家思想告別民間走進官方開始它就蒙上了明確的政治外衣,當然儒家思想自身就凝結著當時時代的政治目的和孔孟個人的政治追求,這一點特別符合封建統治階級中央集權的思想專制要求,不然也不會被統治階級選中。儒家經典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制度、“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制度以及“仁、義、禮、智、信”的五常倫理原則等都成為封建專制統治的思想武器,這種思想有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嚴格固化了人們的思維、僵化了人們的思想,使人們“心甘情愿”地被囚禁在封建專制統治的牢籠之中,臣服于封建統治階級的專制統治,可見,封建社會時代中人民對專制統治的價值認同無疑是儒家思想灌輸與引導的。由此看來,儒家傳統中的人本思想也難逃封建專制主義的定性,對人的價值與尊嚴的關注必須要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進行,皇帝被視為“天子”,因此,皇帝以及其他封建貴族大臣等都是與普通百姓不一樣的人,沒有真正的人的平等性的理念,這一點體現在法律制度,就是存在著很多的司法特權,如封建刑律中的八議制度,即“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如果這八種人犯了罪必須交由皇帝裁決或依法減輕處罰,這些享有特權的人顯然都是皇親國戚或對封建統治有功勞的人。
其次,中國傳統人本思想中沒有正當的權利義務觀念。儒家傳統思想中孕育的人本理念更多地體現了封建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恩賜與施舍,目的就是為了維護本階級的統治,害怕失去民心遭到人民的反抗從而危害自身的統治地位,因此,兩者之間實質上并沒有對等地位,封建地主階級的優越感以及嚴格的宗法等級觀念造就下的人本思想其實存在著嚴重失衡的權利義務觀念,地主階級是權利本位,庶民階級則是義務本位。這一點體現在法律制度上則更為直觀,在封建律典中鮮有關于庶民權利的規定,但卻有著多如牛毛的義務條款,“以《云夢秦簡》為例,它詳列了庶民對國家應承擔的徭役、兵役,遵守法令,力田生產,連坐告奸等義務。這些義務是法定的、具體的,必須履行的,違反者將會受到嚴厲的刑罰制裁。”[4]另外,在封建宗法體制下,廣大婦女也要承擔更多的義務和責任,最為典型的要求就是“三從四德”,“三從”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是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從這種義務本位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人本思想并沒有賦予人以真正的主體地位,沒有人的獨立性價值的體現,人更多是被視為對國家、家族和家長的依附性的存在,因此,“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思想更為根深蒂固,如果你生在了特權階級的家庭中,你就應該享有更多的權利;如果你生在庶民家庭中,那么更多的義務責任都是與生俱來的,你只能認命。在封建專制制度的體制下,廣大人民逐漸也認同了這種權利義務觀念,并充滿了對特權階級的向往,但也只能通過讀書與入伍來爭取改變自身命運的渺茫機會。
最后,中國傳統人本思想欠缺現代法治要素。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略是需要具備各種相關要素的,主要包括文化、政治和經濟三大方面,其中最為根本的是文化要素,如果沒有與法治相關的思想觀念作為文化基礎,那么法治的建設就會危如累卵。結合上文中國傳統法哲學文化中的封建人本思想可知,這三方面的法治要素都是中國法治建設中致命的薄弱環節,也是導致中國法治處于困境的主要原因,尤其體現在文化根基方面。可以說,我國在文化根基方面人治思想的傳統根深蒂固。與“法治”相對的“人治”在《辭海》中如是解釋,“一種治理國家的主張。認為國家治亂的關鍵在于統治者個人的道德和行為,而不是法律。統治者的道德、言行是規范被統治者道德、言行的尺度。它曾被各國專制統治者使用。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建立‘賢人政治’。中國儒家以此作為統治者的治國之本。《論語·顏淵》:‘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禮記·中庸》:‘文物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5]中國受到幾千年封建儒家人治思想的熏陶,人治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封建專制制度遺留的思想毒瘤始終沒有被徹底拔除,只有從根本上移除人治觀念并替換為法治觀念,真正從思想上樹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和平等科學精神才有可能實現民主制度。對此問題我國各界也給予了充分的重視,“20世紀中國各界關于法治與人治的歷次討論,已在理論上明確了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國方略的界限不在于是否承認法律運行中人的因素,而在于:從主體上,法治是眾人之治 (民主政治),人治是一人 (或幾人)之治 (君主專制和貴族政治);法治依據的是反映人民大眾意志的法律,人治則依據領導人個人的意志;法治之法是政治的目的性所在,人治之法是政治意志的工具。”[6]可見,在理論上我們早已作出了法治的選擇,只是在思想文化層面上人治的影子并沒有消散,體現在實際生活中的權大于法、以權壓法、封建官僚作風,以及義務本位的陳舊思維等現象最為典型,毫無疑問這嚴重阻礙了中國法治的進程,因此,文化上的法治觀念培養尤為重要也是最需要時間的。
綜上所述,中國傳統的人本思想受到時代背景和階級利益的局限,沒有形成關于人的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等的價值理念,而這些價值理念又是構建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和形成現代法治文明的要素,又由于中國長期以來實行以農業為本的封閉自給自足的傳統社會發展模式,以及封建地主階級的保守主義政策,使我國錯過了借鑒西方現代文明理念改造自身的機會,因此,中國傳統法哲學文化中自發生成的人本思想并沒有給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提供多少有益的觀念支持,相反卻使中國法治建設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難以對傳統人治思想束縛加以掙脫的困境。
[1]張國華.中國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39.
[2]老聃.老子[M].梁海明,譯注.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6.115.
[3][4]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9.50.
[5]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1999年版縮印本)[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865.
[6]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修訂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