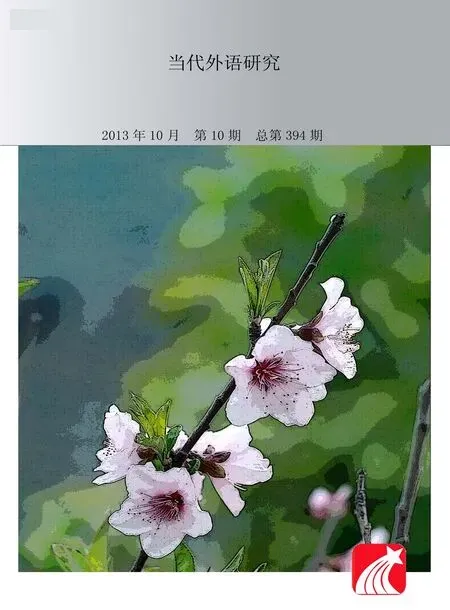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演變:小句之外
——J·R·馬丁教授訪談錄
王振華 張慶彬 (譯)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200240)
J. R. Martin is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ystemic theory, functional grammar, discourse semantics, register, genre, multimodality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ocusing on English and Tagálog—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ransdisciplinary fields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forensic linguistics and social semiotics. His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TheLanguageofEvaluation(2005, Palgrave) with Peter White; with David Rose, a second edition ofWorkingwithDiscourse(2007, Continuum), a book on genre (GenreRelations, 2008, Equinox)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enre-based literacy pedagogy of the “Sydney School” (LearningtoWrite,ReadingtoLearn, 2012, Equinox); with Clare Painter and Len Unsworth, a book o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ReadingVisualNarratives, 2013, Equinox); and a book on system network writing (SystemicFunctionalGrammar:ANextStepintotheTheory-axialRelations, 2013,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Eight volumes of his collected papers (edited by Wang Zhenhua,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have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Professor Martin was elected a fellow of 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in 1998, and was Head of its Linguistics Section from 2010-2012; he was awarded a Centenary Medal for his services to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in 2003. A book reviewing his contributions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Zhu, Y. S. & Z. H. Wang (eds.). 2013.OnJ.R.Martin’sContributionto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9pp.
(訪談基于2012年11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馬丁文集》發布儀式期間對馬丁教授的正式采訪。本文為錄音謄稿,經馬丁教授撥冗審閱刊載。局部有增刪。)
王振華(以下簡稱“王”):馬丁教授,您好,能有機會采訪您,我深感榮幸。您在上午的發言中提到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演變,您能否總體概述一下其發展歷程?
馬丁(以下簡稱“馬”):第一個時期應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即韓禮德(M. A. K. Halliday)(以下簡稱“韓”)從中國返回英國之后。此前(1947-1950)他在北京和廣州學習,加入了嶺南大學王力的研究小組,打算研究中國南方方言,完成博士學位。但因他拒絕保證不加入英國共產黨,進入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師從弗斯的申請遭到了拒絕,所以他改去了劍橋大學。韓想繼續研究中文,可劍橋大學對歷時文字學的重視(philological orientation)多過共時語言學,他只好改變計劃,研究普通話的起源,即《元朝秘史》(Halliday 1956a,b)。畢業后,(仍由于政治原因)他未能進入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文系執教,于1954年留在劍橋教授中文。1958年他移居愛丁堡,研究興趣轉向了英語。這一時期的重要性在于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他研究對象的轉變,從廣東方言到普通話,再從漢語到英語。
韓的劍橋導師辭世后,他拜弗斯為師。但他不住在倫敦,因此無法與弗斯及其同事日日相處,共同研討。這一時期,他所做的是嘗試用弗斯的理念來研究語法。弗斯對語法有一些基本論述,但其主要貢獻則是語境及音韻學研究(context and prosodic phonology)(Firth 1957a,b;Palmer 1970),后者理論化程度更高。韓便將后者改創并應用于語法分析。事實上,他的弗斯思想源自艾倫(1956),他研究普通話語法的博士論文以及研究英語語法的早期著作中體現了這一點(Halliday 2005a,b)。
這就是后來我在多倫多格蘭登學院學習時,邁克爾·格雷戈里(Michael Gregory)最先教我的語言學理論原型,即“范疇階語法”或“階與范疇語法”。韓之后又在《語法理論中的范疇》(1961)一文中發展了這個理論。不過此時韓的思想方法仍多少帶有弗斯的影子,即系統與結構互為補充(與派克的法位學[tagmemics]分析相同),以及建立橫組合關系的成分序列,每個位置又可建立聚合關系的選擇。韓對英語名詞詞組的分析(Halliday 1985)可視為這套理論的一個例示:系統選擇產生指稱語(deictic)、數量語(numerative)、修飾語(epithet)等功能成分。這一點可參閱辛克萊和庫塔哈德的代表作(1975),其中收錄了階與范疇理論并將其運用于語篇分析(尤其是課堂互動的語篇分析)。該書詳盡介紹了20世紀60年代前的韓氏理論,同時例證了如何將弗斯的系統與結構理論應用于語篇分析。辛克萊是韓在愛丁堡時的摯友兼同事,后來辛克萊去了伯明翰,在那里建立了著名的語料庫語言學中心。
第二個時期是上世紀60年代。韓從愛丁堡移居倫敦,成為倫敦大學的語言學副教授(1964)及語言學教授(1965-1970)。韓此時已脫離英國共產黨,且他申請的并非是亞非學院(這是所政治敏感的學校,在某種程度上肩負了培養英國外交官的重任),加之50年代麥卡錫主義政治迫害的減弱,這也許可以解釋他此時為何能被倫敦大學聘用。系統語法誕生于這個時期。我認為這個時期的關鍵在于,韓設計出了把聚合關系形式化為系統網絡的方法:把樹形圖逆時針旋轉90度,用系統表示選項,而不是組合。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想象他凝視著樹形圖思考,嗯,這是表示小句結構的辦法,那怎樣表示語言的意義潛勢呢?他的答案是把樹形圖往左旋轉,用它表示聚合關系而非組合關系。因此把系統視為深層語法,不再額外添加一層結構描寫的創新觀點就這樣誕生了(Halliday 1964,1966)
這里必須謹記韓是一位語法學家,主要研究英語小句的語法,即后來的及物性、主位、語氣三大系統(Halliday 1967a,b,1968,1970)。在把英語小句系統聚合關系形式化的過程中,韓注意到系統之間的相關性,即后來的元功能。他注意到及物性系統可以聚類,同樣語氣、主位系統也可以,且三類間彼此相對獨立,于是元功能思想便誕生了。值得一提的是,此時的理論模型已不同于弗斯,雖然兩者都視系統和結構為互補關系(因為結構體現并觸發系統),但韓氏理論的基本組織原則是重視系統多于結構。正是這種對系統的重視最終形成了該理論的名稱,使之鮮明地區別于其他語言學理論(其他理論一般重視結構過于系統,有時甚至只注重結構)。
同時,韓在60年代還發展了一套特殊的語法論證體系(grammatical argumentation),它可以追溯到沃爾夫。熟悉沃爾夫的人都知道他對隱性語法(cryptogrammar)很感興趣(1945/1956:89ff)。他認為若想弄清某種語言的語法,不能只注重顯性結構(如詞綴、功能詞及詞序等),還必須考慮被格里森(1965)稱為同宗(agnation)的現象,即只改變結構的一部分,保持其他部分恒定,以此考察結構變化,如此得到的特殊模型,沃爾夫稱之為反逆(reactances)。反逆揭示了隱性范疇,即隱性語法。比如把一個小句從主動態變為被動態,陳述語氣變為祈使語氣,極性疑問句變為特殊疑問句,無標記主位變為有標記主位,等式主位變為謂式主位,他們將有怎樣的變化?(如:Heburnedthetoast/whathedidtothetoastwasburnit,但hebakedacake/?whathedidtothecakewasbakeit。此例揭示了處置型和創造性物質過程的隱性語法。)這種語法論證體系研究的鮮明特色及豐碩成果由此可見一斑。
韓對這些同宗句式的探索引領他對同一單位作類別與功能(class and function)做兩種描寫(即范疇與關系)及同一單位做多種功能描寫。通過功能描寫(動作者、主位、指示詞、事件等等),韓演示了一個橫組合(即詞類序列)如何作為同一結構(即功能配置)參與到多種同構序列之中的(即聚類關系)。比如“名詞詞組∧動詞詞組∧名詞詞組∧名詞詞組”的橫組合可以識解一個活動(物質過程)(hefoundheragoodfriend-動作者+過程+委托者+目標),也可以識解一種屬性(關系過程)(歸屬者+過程+載體+屬性),不同之處在于,前者與hefoundagoodfriendforher同宗,后者與shewasagoodfriend同宗。同理,“形容詞∧名詞”的橫組合,可以分別實現數量、描述或分類功能(例如,oneprize是數量詞+物,niceprize是修飾語+物,firstprize是類別詞+物)。這里我們可以再次通過同宗分析來探究隱性語法:如果指第一份發出的獎金(用序數詞作基數計算),firstprize與oneprize同宗,但如果我們指與二、三等獎相對的一等獎,firstprize便不與oneprize同宗(這里我們是在分類)。
不幸的是,誕生于60年代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正處于語言學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其標志是喬姆斯基領導的美國形式主義如日中天。從體制上講,生成派以革命者自居,全面否定美國結構主義傳統(但結構主義正是其根基)。他們好似一個殘忍的政權,驅逐其他學派,導致許多語言學家舉步維艱、顛沛流離。某種程度上說,韓不但經歷了50年代的政治麥卡錫主義也親歷了60年代的語言學麥卡錫主義。政治,這次是“體制”上的政治,又一次影響了他的人生。他是位語法學家,但直至60年代末,他一直都是位被禁止研究語法的語法學家。當時唯獨允許以喬姆斯基的模式研究語法。因為學生畢業后無法找到工作,韓甚至覺得他在倫敦的語言學系都沒有教授系統功能語法的必要了。
之后,韓依然時乖運蹇。70年代,韓從倫敦大學辭職,準備去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執教。但由于他的政治背景,加拿大政府拒絕他入境,他只好暫時在倫敦做一個無業者——既是政治難民又是語言學難民。他曾想,若他以后無法從事語言研究,就只得改弦易轍了。這一時期,他不但呆在家里研究他兒子的語言發展,即我們后來看到的體現他獨特語言發展觀的個體發生學著作《了解如何表達意義》(Halliday 1975),還和哈桑一起研究了銜接理論,即我們熟悉的《英語的銜接》(Halliday & Hasan 1976)。另外,他還研究并發展了社會符號學取向的語言觀,即《作為社會符號的語言》(1978)。同時,他研究科學語篇的歷史,探討英語特殊推理模式的種系發生學及相關的英語語法演變(Halliday 2004)。總之,這一時期雖然諸事不利,卻也柳暗花明。韓雖不能成為“名正言順”的語法學家,但他做了如此多可以傳承發揚的事情。面對逆境,他隨遇而安,處之泰然,對知識的渴求從未停止。
70年代末,韓在悉尼建立了新的研究基地,我也于1977年加入他的團隊。幾經坎坷,時過境遷,韓終于重回語法研究之路。他在悉尼大學創辦了語言學系,教授本科生和碩士生功能語法課程,在我和克萊爾·潘特的相繼促請之下,他把授課用的17頁講義匯編成了一本關于英語語法結構描寫的著作,即其扛鼎之作——《功能語法導論》(以下簡稱《導論》,1985年第一版)。
同時,還有一個令人激動的項目也在進行,即克里斯蒂安·邁西森參與(比爾·曼負責)的加州大學信息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信科所)的項目(Mann 1984;Matthiessen & Bateman 1991)。這個項目通過電腦使韓的語法體系具備明確的生成能力,以此實現文本生成——將所有系統在計算機上形式化,編寫實現化程序,電腦自動計算匹配結果并“生成”句子等。該項目的關鍵之處在于,此時韓的語法體系相當復雜,人工檢查系統網絡已經力不從心,計算機輔助已是必不可少。因此,80年代可謂功能語法的復興——《導論》的結構描寫與信科所的系統構建齊頭并進。這一項目在計算語言學領域的最新進展可參考Bateman和O’Donnell(2005)。
這個時期的另一發展是哈桑在馬奎爾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與同事進行的語義變體研究(Hasan 2009)。該研究以韓和哈桑在60年代對伯恩斯坦的研究為基礎,從語言學視角分析編碼取向(coding orientation)。哈桑不僅以詳實的量化分析論證了對學前語言(pre-school discourse)使用者來說,其意義取向與性別、階層是相互關聯的,同時還對這些使用者入校后早期的意義表達與教師編碼取向進行了對比研究。該研究的關鍵貢獻在于它驗證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言觀,即把語言視為概率系統,各系統、各層級(strata)都與語言使用及使用者變體緊密相關。哈桑和我在80年代的語類理論都可以看作是這種思想的一部分,系統功能語言學已經發展成了一個比以往更具優勢的研究語言的理論(Halliday & Hasan 1980;Hasan 1977,1979,1984;Martin 1992)。
80年代后期,韓對學術研究中的行政干預忍無可忍,于1987年底從悉尼大學退休。他覺得自己的研究工作已是四面受阻、難以為繼,但我估計他當時還未預料后來發生的事:事實上,他所厭倦的行政干預現在反而比他退休時更加嚴重。
韓退休后,他親手創建的語言學系被美國形式主義學派占據,他們與系統功能語言學方枘圓鑿并對其嗤之以鼻,不過這反倒成了福禍相倚之事。形式主義學派的離心作用把語言學系里的功能主義學者離散到了悉尼市及周邊(甚至其他地區)的各種機構中,這些學者聯合制定了一系列跨機構的措施,保持聯系,包括每周研討,不間斷的學術工作坊,教育研究網,每年一度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大會(和集中培訓項目),紐鎮符號學小組(Newtown Semiotic Circle)(譯者注:Newtown為悉尼大學主校園所在地),及他們建立的新期刊《社會符號學》,通訊刊《系統網絡》,以及網絡討論網站sys-func。另外,我也不再糾纏于費時費力的行政工作,這些都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繼續發展壯大的契機。
首先,通過80年代的努力,整個90年代的教育研究碩果累累,形成了以語類研究為基礎的新一代教育語言學(genre-based educational linguistic initiatives),即外界所稱的“悉尼學派”(從韓60年代在英國時期的著作中而生,Halliday & Hasan 2006;Pearce等人1989中皆有相關論述)。90年代早期,作為教學法基礎的教/學循環模式(the teaching/learning cycles constituting its pedagogy)得到了改進,中學各科課程語篇與工作場所語言能力(科學產業、媒體、行政)的相關性得到了研究,并由此促進了(作為語境框架下層級模式的)語類和語場理論的發展。這些研究主要依托韓《導論》中豐富的語法描寫,以及我在《英語語篇》(1992)中從語篇語義系統與結構視角對銜接的再闡釋。這些研究的發展與貢獻在著作LearningtoWrite,ReadingtoLearn:Genre,KnowledgeandPedagogyintheSydneySchool(Rose & Martin 2012)中有詳述。它們不但論證了韓所說的適用語言學(appliable linguistics)中的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而且堪稱經典。
其次,語篇語義系統之一的評價系統也誕于這個時期。評價系統發端于對故事語類、新聞語篇、批判英語寫作以及中學視覺藝術的分析(Martin & White 2005)。同期發展的還有Kress和van Leeuwen(1996)以及O’Toole(1994)的理論,他們革命性地把系統功能語言學應用在非語言模態交際研究中。前兩位學者對圖像的分析尤其影響了我們的教育研究(Unsworth 2001),他們的《識解圖像》(ReadingImages)激發了后來一系列關于聲音、音樂、建筑、副語言以及人類行為的研究(參見Martinec 2005)。系統功能符號學(systemic functional semiotics)的誕生是90年代又一個重要的發展,它傳承了韓70年代把語言視為社會符號的思想。
另外,90年代還掀起了一股把系統功能語言學研究應用到英語之外的其他語系的熱潮,其中大部分來自克里斯蒂安·邁西森。90年代中期,他來悉尼大學語言學系時,韓已經退休,后者在研究氛圍更寬松的馬奎爾大學繼續系統功能語言學研究工作。這股熱潮產生了《語言類型學:以功能為視角》(LanguageTypology:AFunctionalPerspective)這本系統功能語言學語言類型學奠基之作,它分析了多種語系語言的及物性、語氣、主位系統,其最后一章由邁西森執筆,論述了從功能視角跨語言描寫的重要性,其內容豐富、影響深遠,堪稱全作精華。
到了本世紀的頭10年,這一時期最主要的發展與系統功能語言學框架下多模態語篇分析遇到的阻力有關。我這一時期的研究生或多或少都對多模態語篇產生了興趣,這迫使我們去思考怎樣處理模態之間的互動關系,這是實例化研究的主要動力。比如Bednarek和Martin(2010)論證的耦合(coupling)、擔責(commitment)、偶像化(iconisation)以及綁定(bonding)關系。同時,多語現象的研究中(Matthiessenetal. 2008)也遇到了類似實例化問題,所以才有了德索薩(2010)把翻譯視為文本二次實例化的研究。這兩方面的研究都在深入思考為什么語言使用者會以多種有趣的方式把系統實例化,因此一個全新的既考慮語言使用又考慮語言使用者的視角產生了。在我看來,這一時期提出的問題遠多于解決的問題,不過目前逐漸統一的認識是繼過去50年里對于語言系統層次的實現化層級(realisation hierarchy)的研究,包括軸關系(系統與結構關系)、級階、元功能與層次,兩個與之互補的層級關系(均亟待研究)——實例化(instantiation)和個體化(individuation)開始成為研究的焦點。我認為這個時期的重要性在于它給了新一代研究者足夠的前進空間。
當然,這里關于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歷史描述是我的主觀看法。我過去35年的主要工作地是悉尼,所以我很可能沒注意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發展,比如邁克爾·格雷戈里影響下多倫多的進展(Malcolm 2010)、加的夫的羅賓·福賽特(1980,2008)、中國與拉美洲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成長、珠三角研究區域(Pearl Delta research nexus)的出現等等,要談論這些發展有很多人比我更有資格(如Matthiessen 2007a,b,2009,2010中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發展的總結)。我的個人貢獻可參考《馬丁文集》(譯者注:王振華主編《馬丁文集》8卷本已于2012年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全部出版)。
王:謝謝您對系統功能語言學過去60年的發展做出的精辟總結。讓我們再次聚焦理論本身。您認為其發展歷程中產生或遇到的主要問題和挑戰是什么,問題是怎樣解決的,挑戰又是如何處理的?
馬:我認為必須從個人角度、政治角度,理性地看待這些問題。如上所述,歷史上有太多的個人及政治挑戰。我覺得可以從韓身上學習到的是他從不抱怨生活。我新編的訪談集中有例證(Martin 2013b)。對他來說,玻璃杯中永遠“還”有半杯水,而不是“只”有。無論世事無常,他都會說“嗯,我要向前看,繼續前進”。我在努力想象那該是怎樣一個場景:他帶著所有語料從廣東回到倫敦,準備研究廣東方言,卻由于政治原因被告知不允許,我想這對大多數博士生來說都是晴天霹靂,但他卻似乎覺得“好吧,我不能研究方言,那我就研究語法,研究《元朝秘史》”。他的一生無時不在體現這種精神,他被拒絕進入加拿大,卻不怨恨,反而說“謝謝你加拿大,讓我有機會呆在家里,分析我兒子的語言發展并寫出《了解如何表達意義》,謝謝”。在這些方面,我們與他不可同日而語。無論世事如何風云突變,他都視其為新的機遇,并執著前行。我想這是值得我們所有人學習的。
當韓退休、失去了悉尼大學的學科基地之時,我們不是潰不成軍,而是化整為零、從長計議。我想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抓住機遇繼續前進的契機。類似的例子還有英國的羅賓·福賽特,他于1974年的創舉成就了后來的國際系統功能語言學大會(ISFC)。當時第一個研討會好像只有14名學者,我那時還是艾塞克斯剛入學的博士生,未曾被邀請。后來組織不斷壯大成了國際大會(澳洲、亞洲、歐美),很多國家爭相申請成為主辦方,有時甚至不得不限制人數,因為主辦方實在沒有足夠大的房間或足夠好的方案來招待超過三四百人的規模!
這一經驗對中國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年輕學者學會互幫互助也有一定啟示。在中國他們可能要等很久才能教授語言學,等更久才能成為博士生導師或會議的邀請嘉賓,這之前他們該如何建立研究的人際關系和/或網絡資源以傳達他們的最新研究成果呢?這里我想說的是,雖然個人與政治挑戰無所不在,但機遇卻也與我們形影相隨,要好好把握!
王:據我所知,系統功能語言學受到或部分受到伯恩斯坦等社會學家以及拉波夫等社會語言學家的影響,您怎樣看待系統功能語言學與社會學的關系?
馬:先談拉波夫。韓非常推崇他的著作。我覺得部分原因是拉波夫做了韓攻讀博士時想做的那種研究,另外就是拉波夫的變體規則說(conception of variable rules)(1968,1972)與韓的語言是概率系統說(Halliday 2005c;Halliday & James 1993)彼此間存在共鳴。當然兩者是有區別的。拉波夫秉承美國結構主義傳統,把意義與形式二元化,保持意義恒定討論形式變體。而韓認為形式體現意義,并非二元關系。用哈桑的話說,這意味著保持語境恒定討論語義變體——分析的是語義變體而不是形式變體(Hasan 2009)。另外重要的一點是,拉波夫的社會語言學并沒有構建語境或社會關系模型,也沒有對社會學進行深入探討,他的語體(style)和語言使用者社會階層(social class of speakers)的概念只是常識性概念,而系統功能語言學顯然較好地發展了關于語言使用者及語言使用的理論模型,并與現實主義社會學(social realist sociology)有著長期富有成效的對話,起初是伯恩斯坦,現在是卡爾·梅頓(Karl Maton)。
系統功能語言學與現實主義社會學的合作開始甚早,其中涉及個人、體制及理論的合作研究。60年代早期韓在愛丁堡時便開始關注伯恩斯坦的理論,他驚訝于伯恩斯坦身為社會學家卻關注著語言(Bernstein 1971),這在其他社會學家中很少見。韓和辛克萊覺得可以借鑒伯恩斯坦的思想(Bernstein 1973)。韓去倫敦后與伯恩斯坦在同一所大學,兩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哈桑去倫敦后加入了伯恩斯坦的研究團隊。伯恩斯坦關于編碼取向及其與社會階層的關系、以及其對教育的影響等思想其實都是在思考:語言在其中的作用如何?所以合作初期的體現是對不同意義取向的語言學探索,即哈桑80年代所說的語義變體(Hasan 2009)。60年代的系統語法可能還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參見特納1973對哈桑研究趨勢的預測),直到80年代哈桑在悉尼構建出語義網絡,系統功能語言學才具備足夠的深度和能力解答伯恩斯坦的問題。哈桑文集的第二卷《語義變體》(SemanticVariation)(2009)記錄了系統功能語言學借鑒伯恩斯坦的這一階段—通過分析語言使用者的社會階級來探討語義變體(實質上是探討在關鍵的社會化語境下,一種文化的意義資源如何分配給使用者以及如何得到發展)。
接著是澳大利亞讀寫能力研究借鑒伯恩斯坦的階段(Martin 1999b;Rose & Martin 2012)。90年代,我們的研究頗具爭議。本質上來說,我們是在強調教師的重要性,而不是把學生放進一個教育環境中任由其自我發展,換句話說,通過探討我們應該教什么(語類)、怎樣教(設計出教/學循環課程語類),我們把教學變成了一個言語性及物過程。這些研究很有爭議。因為如果沒有伯恩斯坦,我們不可能明白中產階級是如何努力控制教育系統的(Bernstein 1975,1990)。我們對他的一些概念很感興趣,如可見教學法與不可見教學法,可見教學法與舊中產階級(地主與資本家)的聯系,不可見教學法與新中產階級(他所說的象征性控制機構[his agents of symbolic control])的聯系。我們做的是以語類為基礎的讀寫能力研究,他關于教育語篇的總體思想幫助我們構建了該理論模型。
這些研究與中國尤為相關,因為中國已經出現了迅速崛起的中產階級。同西方國家一樣,為了孩子,新中產階級將會要求教育改革首先建立專門的私立學校,然后爭取控制整個教育系統。他們可能會從美國引進進步主義、建構主義等教育理論,呼吁進步、民主、解放,以便“改革”傳統教育課程。但正如伯恩斯坦的警告(1975,1979),這些改變可能不會給孩子帶來任何好處,因為他們的編碼取向尚未從其社會階層中產生。從澳洲及西方國家來看,事實確實如此。這給我們推進更加公正的學術讀寫目標帶來了很大挑戰,換句話說,文化資本的再分配(redistributing cultural capital)每一步都是對我們的挑戰,如同政治活動中的金融資本再分配一樣—我們本應對此有所預見,我們更應以社會學家的眼光去審視這些現象。
接下來的一個階段以伯恩斯坦后期關于知識結構的研究為基礎(Bernstein 1996/2000)。伯恩斯坦的思想激發了開普敦大學的穆勒等社會學家關注教育及其他領域的知識盲區問題(上面談到的非及物性教/學方法),穆勒的《開拓知識》(ReclaimingKnowledge)(2000)對兩個00年代在悉尼大學由現實主義社會學家和系統功能語言學家成立的學術工作坊來說可謂是奠基性的。從Christie和Martin(2007)及Christie和Maton(2011)收錄的相關會議論文可以看出,這些討論促使著系統功能語言學家重新審視他們對語場的研究興趣。幸運的是,這時梅頓加入了悉尼大學社會學系,其位置就坐落在語言學系的對面。梅頓(2013)發展了伯恩斯坦的思想,創立了合法化語碼理論(Legitimation Code Theory,LCT)。現在,關于初級中學知識構建的LCT與SFL的合作研究正在開展,同時還有很多博士生也在做LCT與SFL的交叉研究。梅頓的研究使我們構建個體化模型受益匪淺,比如一個社區如何將話語資源(discursive resources)分配給不同群組,與此同時,群組又如何將其配置給不同次序的附屬關系(Bednarek & Martin 2010;Martin 2012c)。
當然,我們必須謹記社會學是另一個學科,伯恩斯坦、梅頓及其他社會學家的研究是另一個領域,我們不能簡單地拿來然后直接應用到系統功能語言學,這是萬萬不可的。但現實主義社會學家會提出語言學家未曾想提出的疑問,并有我們想努力獲取的答案。而作為語言學家我們必須思考怎樣用他們的思維方法來發展系統功能語言學。對他們來說,我們始終是帶著挑剔的眼光來提出一些我們認為他們可能或應該知道答案的問題。我想梅頓的語義引力概念(semantic gravity)就部分來自我們對語法隱喻及其在學術知識構建中的重要性的討論(Martin & Maton 2013)。繼續推進這種合作我們就會同呼吸共命運,方向一致地開展研究,韓的新馬克思主義語言學(Halliday 1993)便是這類合作的成功案例。
王:謝謝您的回答。接下來問一個關于語言教學的問題。您認為系統功能語言學總體上與語言教學,尤其是二語教學關系如何?
馬:好的。其實前面已經有所涉及。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社會公正的問題。無需深入觀察澳洲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教育系統,就能發現文化資本分配對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生來說有失公允,某種程度上這是對國家人才資源的浪費。1972年我同喬納森·芬尼開始了我的第一個教育研究。1979年我與瓊·羅瑟里合作,開始嘗試改變現狀(此方面研究現在被大衛·羅斯繼續發展著,成果豐碩)。我們的讀寫能力研究關注文化資本在校園的傳播,強調重視教師的作用,并以語言學家身份探討該教什么。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教學法和課程設置(Rose & Martin 2012)。
對于以上問題的解答就是后來發展的作為系統功能語言學語境層次之一的語類理論(Martin & Rose 2008)。我們由此把各類課程映射成為語類系統,又根據課程語類設計教學法(Christie 2002;Rose & Martin 2012)。我們強調讀寫能力(閱讀和寫作),因為寫作是蘊含學術知識的總庫,能夠發揮關鍵作用。這里我們參考了韓的語法隱喻(Simon-Vandenbergenetal. 2003),尤其是概念隱喻,以及他展示的在科技英語的范疇中如何產生我們所稱的物理知識的方法(Halliday 2004),換句話說,是寫作生成了所有學科知識。事實上,這里有一個比社會公正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語言和文化的生存。語言和文化要么促使寫作系統發展,要么依靠寫作系統發展,然后通過概念隱喻發展成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等知識體系。語言和文化共同作用可創造出強大的技術,也可造就強權的官僚主義。當這種強權文化開始侵占另一種文化時,倘若沒有語法隱喻,后者將無從抵抗,面對這類猛攻,那些相對較小的族群有時甚至無力為繼到下一代,殖民侵略便是如此。全球變暖意味著這種文化內與文化間對資源的爭奪早晚會出現,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里除了社會公正問題,還有實際的生存問題。中國與印度經濟的飛速發展,全球變暖的影響,都意味著如果想要應對挑戰,國家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不公正地分配文化資源了。
過去數十年來,語言知識在語言教學中的關鍵作用一直是個問題,韓和潘特已就此做了關于學前兒童家庭語言學習的研究(Halliday 1975,2003b;Painter 1984,1998)。照料孩子的家人、年長的兄弟姐妹以及幼小的語言學習者,在他們學習語言的過程中都在常識性地使用語言,但若在教育領域,僅涉及常識性話語的語言遠遠不夠,因為為學術語篇服務的書面語才是學校真正所教授的。總的來說,教育系統認識到了這點,由此發展出了傳統形式的語法和修辭來應對最初的挑戰,其中包括了教授少數精英學生從書面語中習得文化在其中所積累的知識。有些教育系統,比如澳大利亞,其實已經從課程中刪掉了語言知識學習(knowledge about language,KAL)——這得歸因于“進步主義”(progressivist)教育者,他們認為(其意見我不敢茍同)語言知識不僅是無用的(因為似乎沒有加強教與學的效果),而且是有害的(因為擠占了讀寫練習的時間)。在有些教育系統,比如澳大利亞,有一些像英語這樣的學科強烈抵制專業化的語言知識再進入課堂,但在其他國家的教育系統,傳統語法修辭教學則保留了下來(中國應該是個例子),或者被保守派議員再次推介(如英國)。
有時,我會說,唯一一個比傳統語法更糟的語法就是沒有語法。我堅信這句話。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能加深對語言、語域、語類理解的適合學校課程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即使在那些對此認同的國家里,要發展理論、開展培訓項目去傳遞這種理念仍是不小的挑戰。我們還尚未把我們需要的教學語言融入到整個教學系統,從入校之初一直貫穿整個小學、中學、大學教育,所以我們也不清楚學生的能力以及公正的教育資源分配將產生何種效果。我相信這個研究將有廣闊的空間。
王:再次感謝您的回答。中國現在有一個浩大的MTI項目,即翻譯碩士專業,在全國各高校廣泛開展。有一些大陸和澳門學者把系統功能語言學應用在了翻譯研究中,比如張美芳及中山大學的一些學者。您認為系統功能語言學在哪些方面可以促進翻譯研究呢?
馬:這里可以主要參考Steiner和Yallop(2001)。我個人只有一個博士生做這個領域,是來自巴西圣卡塔琳娜大學的拉簡·德索薩。她對葡萄牙語-英語互譯很感興趣,尤其是涉及應用評價系統的翻譯研究。她主要研究一些網上的評論類語篇,這些語篇是位美國評論員關于中東局勢的評論,已經譯成了26種語言。她的創新在于她并非從實現化角度(字系層、詞匯語法層、語篇語義層等等)對比兩種語言,而是聚焦實例化系統(de Souza 2010)。她認為翻譯是把一種文化及語言中實例化的語篇在另一種文化及語言中再次實例化,所以涉及兩套實現關系。這意味著必須把源文本“去實例化”,找出源文本所處的意義潛勢,然后思考如何將其移至目標語并再次實例化。我覺得這是個很有意義的視角,它與同樣是多套實現關系卻只有一個實例的多模態語篇研究密切相關。
拉簡并沒有采用從結構入手,實例與實例對比分析,即通常的翻譯研究方法,她更多地考慮聚合關系。她認為翻譯過程就是找出源文本所處的意義潛勢,直到發現一個與目標語意義潛勢交叉的點,然后從這個點順著目標語再次實例化。這對評價系統研究尤其重要,因為不同語言中的態度值是不同的,態度系統、介入系統、級差系統都是不同的,再加上詞匯隱喻可以觸發態度,這種差異就更大了,因此聚合角度的去實例化及再實例化(distantiation and re-instantiation)相關研究很關鍵,我認為很有價值。
拉簡還考慮了翻譯意識形態問題,探討為什么美國人的專欄在巴西出現了不同譯文,或者說政治目的不同的譯文。她關注的個體化層級(individuation hierarchy)是譯者的立場。這其中涉及翻譯過程中的意識形態問題,當譯者重新打開意義潛勢的時候,意識形態已經發生了,他們多少都會考慮源文語言社區的價值觀,再根據自身利益二次實例化。這類研究對發展個體化理論也很有價值。
與拉簡這樣的翻譯者合作讓我意識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從未接受過詞項關系分析的訓練。后來我們研究評價系統,對情感、判斷、鑒賞以及顯性、隱性評價分類時,這個問題便凸顯出來了。換句話說,翻譯者關注的始終是源文與譯文的詞項意義關系,他們的研究本質上是關系研究,因為他們處理的是兩種語言,并且往往有多種譯法可以考慮。當我和拉簡一起討論難譯段落時,總是她貢獻出解決方案,這讓我開始反思,我接受過語音、語法、語篇語義、語篇結構分析等訓練,但沒有詞項意義分析。這反映出目前關于詞項的語言學理論亟需發展——系統功能語言學中韓(1966)和辛克萊(1966)的開創性思想后人沒有繼承。我們的確開展了考察搭配的語料庫研究,但這也只能到分析詞項關系為止(Bednarek 2006,2008;Hunston 2011),我們還沒有足夠大的語料庫和足夠多的語料去獲得想要的分析結果。另一方面,作為語法精密階的詞匯研究仍處在相對主觀的階段,只有一些零星的、合理但未定的論述,如哈桑(1987)。系統功能語言學現在被更加廣泛地應用在翻譯研究中,我希望發展詞匯理論及相關論述的壓力能促成重大的發展,不只是為評價分析,更多是為了詞匯分析。
如前所述,如果從實例化、去實例化、再實例化(instantiation,distantiation and re-instantiation)視角考慮多模態語篇分析,翻譯研究可以與其很好地結合,從一個模態到另一個模態的二次語境化(recontextualising)可以視為模態間的翻譯過程。這個視角對教育中的多模態研究很重要,包括印刷品、電腦、面談等模態。課堂語篇通常涉及語言、肢體動作、圖表、數學或化學符號、3D模型以及影片,我們可以思考其中涉及了哪些去實例化、再實例化過程。我和梅頓(Martin & Maton 2013)目前已經注意到中學教師的一個傾向,他們把專業知識轉化為容易理解的日常用語,使用多種模態使知識具體化,但他們很少利用多模態告訴學生如何再把知識重新轉為專業性描述,寫出專業語篇。因此,翻譯研究與教育語言學間的更多對話將有助于推動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實例化理論發展。
王:翻譯涉及到語境,這是不爭的事實。就語境研究而言,您認為我們該如何建立一套將語境納入考量的語法?
馬:我個人認為“關于語境的語法”這個說法挺新奇。如果你的意思是指從系統的社會符號學視角,即通過軸關系、級階、元功能、層次關系研究語境,這樣說也可以。我認為,我們在語言分析的各個方面確實需要系統的研究方法。
這里涉及了很多問題。如你所知,我發展了一個層次語境模型:語域層(語場、語旨、語式)體現語類層。我這樣做有很多原因。首先,這是我唯一可以想到的繼續傳承韓氏理論并同其保持一致的辦法,即概念系統體現語場、人際系統體現語旨、謀篇系統體現語式的總體思想(可看作是內部功能到外部功能的鏡像反映)。我知道哈桑和邁西森在以不同方式說我的語類研究是語場研究的一部分(比如Hasan 1985,1999;Matthiessenetal. 2008),如果只考慮韓的內外功能關系的話,這等于是說要么語類關系大體上是概念意義的看法是錯的,要么就是韓的鏡像反映說是錯的。過去數十年中已經有很多人用我的層次模型進行研究,把語類看作是語場、語旨、語式變量的再配置,這又意味著把語類看作是概念、人際、謀篇三大意義的再配置,因此語類關系并不是甚至不主要是概念意義(Martin & Rose 2008)。一個理解層次模型與非層次模型區別的視角是,在語場、語旨、語式之上還有一個更復雜的層次可解釋語境關系,而哈桑、邁西森及其他學者認為,沒有必要再分出這個我稱為語類的層次來描述意義再配置,他們把這種關系視為語場的一部分。
另外,我擔心如果把語類關系視作語場研究的核心,那么就可能會忽略甚至完全抹掉社會符號學角度的對語場的應有研究,也就是現實主義社會學家所說的知識結構。就教育語言學而言,發展出一個完整全面的同時考慮到水平語篇和垂直語篇且垂直語篇與層級的、水平的知識結構相關聯的語場模型十分關鍵。如果我們想分析中學教學,僅有語類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將其置于對學科的理解之中,考察常識性概念和專業性概念間的差異,以及世界如何被識解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學科語篇。另外,還有很多其他問題也需要考慮,但如果只是討論作為系統功能語言學語境層級的語域、語類,這些解釋足夠了。
是否建立一個分層的語境模型,其實就是是否承認意義之上還有一個語境層,這是區分系統功能語言學與其他理論的一個標志,應該也是你問題的初衷。韓的老師弗斯把語境視為語言描寫的一個維度,他認為意義就是語言在語境中的功能,不過他的模型并不是層級性的(Firth 1957a)。韓的層級思想更多地來自葉姆斯列夫、艾倫、蘭姆,并延伸到了語境分析,這實際上意味著韓在意義層之外增加了更高層次的語境層。這種模型我稱為附生性模型(supervenient)(Martin 2013a,待出版),即整個層級系統被視作是由一個僅有一種系統或結構的單一符號系統層產生的突顯復雜性。這些簡單的單一層級系統包括幼兒的原型語言系統、動物的交流系統以及簡單的非語言符號系統(如交通燈系統;見Hjelmslev 1947)。韓的語言是概率系統思想(2005c)可以完美地與這個模型結合:語域和語類可以解釋音系層、語法層及語篇語義層的選擇概率。
附生性模型與語言-語境二元論截然不同。二元論認為語言嵌入在語境中。我們則認為這是一種嵌繞模型(Martin 2013a,待出版),在這種模型中,語境環繞語言,可以是物理的或生物的東西,或者是我們在頭腦中對這些東西的感知、認知的表征,即心理概念。用葉姆斯列夫(1961)的說法,附生性模型視語境為內涵符號系統,體現為語言這個外延符號系統(在他的理論中外延符號系統自身具備表達形式,而內涵符號系統必須通過外延系統才能得以體現)。嵌繞模型則不把語境視為符號系統,而是語言發生的現實環境,并非意義符號(Martin待出版)。這兩種語境模型被很多學者都混淆了,有的是在他們自己的研究中,也有的是涉及他人的研究。
目前,視語境為內涵符號系統的系統功能語言學語境論最大的壓力來自于多模態研究(Matthiessen 2007b,2009)。從實例化角度看,多模態語篇涉及了不同的外延符號系統,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實現層級,故多實例系統產出一個語篇(Painteretal. 2013)。這意味著該語篇的多模態語域/語類建立不能像現在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模型一樣簡單地在音系層、語法層、語篇語義層這三個余切圓上畫圈,現在的模型呈現的是單一符號系統,因此多模態的語域/語類不可能使用這個辦法,除非一個內涵符號系統可以被多種外延系統同時體現(Martin 2013a)。我期待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發展更好的實例化模型得到解決,目前實例化系統亟需發展。
若重新考慮語式與這些年呈現井噴之勢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多模態研究之間的關系,我們會看到同樣的問題。語式本來是語域的一個維度,體現為謀篇意義,是語言在某個語類下的功能變體。到了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00年代,很多人開始研究語言和其他模態的關系,出現了圖像語法、聲音語法、音樂語法、行為語法,現在還有了空間語法(Martinec 2005)。我們根據這些不同語法的互動關系研究多模態。因此,考慮到要負責解釋語言與其他模態的互動,關于語式的理論必須再次發展。但如上所述,我們不能簡單地依賴于我們現有的層次建構法,我們要將注意力集中在實例化關系上,這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索的開放式的研究領域。
評價分析的發展也導致了對語旨的挑戰。語旨本來是解釋人際意義如何建構權勢與親疏關系的。它早期主要通過語氣系統、情態系統、命名系統等分析得以發展,而評價系統的出現鼓勵我們從共享價值角度來推動它繼續發展。但是,態度并不只是態度,而是關于某個對象的態度——要么是概念意義激發的情感,要么是對概念意義的判斷和鑒賞。如瑙彌·奈特(2010)研究所示,我們在對話中進行這些態度/概念的耦合協商,一旦協商完成,說話者雙方就完成了伙伴關系的結盟或再結盟。這方面的研究讓我們從權勢關系、親疏關系走向了對身份認同關系的協商,同時涉及到人際意義和概念意義,因此又一次給實現化帶來了挑戰——韓的層級模型中語域與語言是鏡式關系(此處為語旨與人際意義)。這個挑戰暗示了存在新的層級,即個體化層級。個體化關注語言使用者,它將一個文化中的話語資源的分布以及這些資源的使用情況匹配給不同的社群(Martin 2010c,2012c)。同實例化一樣,個性化目前也是一個還未深入探索的開放的研究領域。
王:目前中國大陸學者對多模態研究很感興趣,您能介紹一下它的發展歷程嗎?
馬:從系統功能語言學角度來說,我是在80年代后期的紐鎮符號學小組上通過岡瑟·克雷斯和西奧·范立文的發言中初次接觸到多模態的。這個小組由悉尼地區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家和批評理論家創建,目的是增加交流合作。克雷斯和范立文把軸關系、元功能思想應用在圖像分析中,創立了后來的視覺設計語法(a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該成果在1990年由迪肯大學出版社出版、弗朗·克里斯蒂主編的《教育中的語言》中第一次出版發表,后來在此基礎上將其擴展成了影響深遠的經典之作,即1996年由勞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識解圖像》。
這一發展可謂是轟動的、驚人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如前所言,它在語篇分析領域掀起了一場革命。1996年之后,語言研究很難再忽視與語言共同構成語篇的非語言模態了,負責任的系統功能語言學語篇分析者不得不變成了多模態語篇分析者。其次,它充分說明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總體框架可以被用來分析交際語篇中的任何模態。當然對此可能有人質疑,但克雷斯和范立文的圖像研究奠定了后來一系列關于音樂、電影、建筑、印刷、顏色、副語言、身體行為等研究的基礎(綜述詳見Martinec 2005)。我對這個研究的主要顧慮在于,它并非完全建立在嚴謹的對系統/結構關系的描寫體系之上,而這種體系才是系統功能語言學對意義研究的核心。他們往往將級階、元功能、分層等一些二級概念從語言分析或者從初始階段的圖像分析中借用過來,分析勾勒出所發生的內容,而非通過構成這些維度不可或缺的系統和結構分析來進行系統性的描寫①(Martin 2011c)。級階、元功能、層次等概念并非理論基元,他們只是在涉及到系統/結構的系統獨立性分析時才使用的組織原則;因此,每涉及描述一個新符號系統,他們就必須被重新論證一次,比如上面提到的韓在60年代對語法的研究。
多模態研究的異軍突起直接導致了兩個問題的出現。第一,多模態語篇分析過程中涉及的高難度的標注問題。我們雖然有電子平臺可以處理多層標注,但當語碼過于復雜時,我們很難再從分析結果中找出有價值的型式。第二,隨著語篇生產,多種模態間產生了復雜的獨立性問題。系統功能語言學在20世紀下半葉使用的頗有成效的系統與結構表現方法一直是靜止的2D模型——通過系統網絡、功能/結構的圖表。這些模型都過于簡單,我們現在迫切需要的是使用3D技術的動態視覺化效果,目前此問題的研究者主要是香港城市大學的喬納森·韋伯斯特、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凱·奧哈羅蘭及其團隊、悉尼大學的米歇爾·扎帕維尼亞和班達·奧姆泰利。這種視覺化研究需要一個同時精通系統功能語言學、編程和數學的團隊。不容忽視的是,這些知識同時也是未來的語篇分析者處理復雜的多模態時需要通過學習去掌握的。若此時研究涉及到一種以上的語言,如多語語篇,那么研究復雜度當然還會更高。
王:您在90年代創立了評價系統,2000年發表了關于評價系統的第一篇研究成果。次年我在《外國語》發文將其引介到中國,引起了很多年輕學者、學生的研究興趣,他們通過寫信、電郵、面談等方式向我提了很多問題。幾年后,我和馬玉蕾博士基于自己對評價系統的理解就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于2007年將討論結果發表在《外語教學》,但之后提問的人反而更多了。我想問您的問題是,您覺得評價理論還有發展空間嗎?
馬:可能我們首先需要糾正的一個錯誤是把評價系統這個分析框架稱為評價理論,我自己也多次犯錯,實在不應該,因為這種錯稱具有誤導性。評價系統是理論的一部分,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的一部分。在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歷史上有過多次這種誤用的現象,比如最常被引用的銜接、語類、多模態以及評價系統。人們往往將這些分析工具脫離系統功能語言學語境應用在自己的研究中,因此當有問題產生的時候,系統功能語言學就無能為力了。比如一個常見的例子是,人們總把銜接當作連貫的模型來批判。事實上在系統功能語言學中銜接從未被認為是一個連貫模型;研究連貫,要考慮語篇織體的其他維度(如篇章格律),以及語域和語類。一旦銜接從SFL中被剝離出來,這些誤解是不可避免的。
剛才我們討論翻譯時,我提到了態度的分類,現在讓我們回到這個問題。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數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都是常識性的。他們從語境和上下文中剝離出一個單詞,然后去想它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他們不確定,就會去查詞典(還可能是網絡詞典)。這個方法和我們的常識、意義的指稱論(referential theory of meaning)有關,即認為詞語是有意義的,如果我們不認識一個詞,可以去查看這個詞的定義。這個方法一般都是不太奏效的,不能幫助厘清上述問題。
另一種方法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方法。系統功能語言學是建立在意義關系論(relational theory of meaning)之上的。如果我們要考慮一個詞的意義,比如adore,我們不是去問它的意思是什么,而是問它在一個可比領域中與其他詞的關系是什么,與love、like什么關系,與reallylike、likeverymuch有何區別,與hate、abhor,hug、embrace,adorable、lovable,worship、venerate分別又是什么關系。通過考察這些問題,我們會發現如果一個語篇中包含上述某個情感詞,對該詞的選擇其實就是對這些關系的選擇。我們甚至還可以由此建立起關于adore及相關詞匯的一個小型系統網絡,就像Martin和White(2005)中的情感分類一樣。如果我們想關注級差而不是范疇類別,我們可以通過拓撲關系把adore及相關詞匯表示為語義空間的一個區域。
我們還可以通過語料庫工具來考察adore的搭配和類連接。何種概念意義觸發這種情感,何種情緒者與adore有聯系,哪些詞項構成它的共現搭配(索引項),adore與這些詞項的關系如何?對這些問題的考察正是對系統功能語言學意義關系論中的組合、聚合概念的應用。我們是不看詞典的,看的是同義詞匯編(thesaurus),我們不問一個單詞的意義是什么,而是在語料庫中觀察它的用法。換句話說,我們的方法不是依賴常識,而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
除了分類之外,隱性、顯性態度(inscribed and invoked attitude)是困擾分析者的另一個問題。應該如何區分它們,又該怎樣看待隱性態度?要想回答這類問題,我們的視角要從實現化轉到實例化,要依靠并發展系統功能語言學對擔責(commitment)的研究成果(Martin 2010c)。擔責大體上是指我們的顯性化程度,即語篇的語義權重(semantic weight)(與Maton 2013的語義密度類似),用專業的說法,它指的是我們在系統選項中最終形成的精密階,以及我們選擇非必選系統的顯性程度。比如,如果我們說某人很kind,我們就是在通過判斷系統的選擇顯性地表達責任,但這個責任可以通過選擇一個習語進行下調(she’ssoft-hearted),或者還可以通過詞匯隱喻繼續下調(she’sanangel②),在這兩種手段中我們只能基于死隱喻(soft-hearted)和活隱喻(angel)推理得出判斷意義的類型。我們還可以把概念意義分級以此來旗示(flagging)更少的責任(shetookgreatcareofherrapidlyagingparentsforseveralyears),或者干脆只表達概念意義,不旗示我們的主觀性(shelookedafterherson)。就擔責的程度而言,這里我們要思考的仍然是不同選項之間的關系。
我們還需要結合上下文。如果是在分析對話,我們可以考慮“判斷系統”與“概念目標”(ideational target)二者的耦合是如何進行協商的。在回應時,耦合有沒有作為綁定被分享?或則言語上和/或行為上被嘲笑、被挑戰、或被忽視?(Knight 2010;Martin & Zappavigna 2013)如果我們是在分析獨白,這種耦合與其語篇相(its phase of discourse)有否共鳴,共鳴如何?有沒有產生正面的判斷和/或情感的態度韻?有沒有一個更高層次的主位或新信息來承擔該語篇相韻律的責任?我討論這些問題,主要想說明,當研究出現挑戰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從相應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維度思考,如果我們的理論也不夠全面,就像現在的實例化和擔責一樣,我們就需要以此為跳板,推動理論發展。所以我很高興現在還有這么多人在提出問題。
王:謝謝。據我所知,系統功能語言學已經發展了一系列層級維度,至少在您的研究中是這樣,比如實現化、實例化和個體化(Martin 2010c)。您近幾年在開展個體化的研究(Martin 2012c),引起了很多中國學者的興趣。您如何看待個體化的研究前景?
馬:我們可以從韓、麥金托什和史蒂文(1965)的合著《語言科學和語言教學》(TheLinguisticSciencesandLanguageTeaching)說起。書中有一個主要的章節叫做《語言使用及使用者》。過去數十年的事實是,系統功能語言學對語言使用的研究側重遠大于對語言使用者的研究。語域和語類理論的發展,尤其是涉及教育學的發展,很好地證明了這種側重(Martin & Rose 2012)。但往往我們所需要關注的是不同的兩個變量,一個是使用變量,比如地點、交際目的等,另一個是使用者變量,比如身份、背景等。這兩者的關系是互動關系,因為語言使用者是通過語言的使用進行互動的。
雖然大部分系統功能語言學研究都聚焦語言使用,但有一個例外,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與伯恩斯坦的編碼取向(Bernstein 1971,1975)相關的研究。在60年代后期倫敦出現了這種研究的跡象,后來韓離開倫敦,這點跡象也就隨之消散了(Bernstein 1973)。到了80年代,在悉尼的馬奎爾大學集中出現了一批主要聚焦學前語篇,及少量中小學生語篇的研究,研究者是哈桑及其同事。他們關注的是語言使用者的意義取向與性別及社會階層的關系(Hasan 2009)。我們可以把這個研究看作是既定文化下對意義資源分配的研究。用伯恩斯坦的話來說,這個研究與他所說的識別及實現規則有關(recognition and realisation rules)(Bernstein 1996/2000:104ff),即語言使用者對社會語境的解讀以及他們在此基礎上具備的產出所需語言的能力。
到了90年代,關于使用者的研究相對少了。但到了00年代,因為評價系統的出現,我的很多學生開始問我關于身份研究以及它如何在對話、說唱音樂、交友網站中被協商的問題。瑙彌·奈特分析了日常對話中的幽默以及被同齡人嘲笑的態度與概念的耦合,通過這個研究,她拓展了斯坦林的綁定概念(Stenglin 2008;Martin & Stenglin 2007),研究人們如何在社會團體中結盟(align in social groups)。這激發了對附屬關系以及復雜的契合關系如何構成同盟的研究,這里的契合是指共享的態度/概念意義的耦合。Bednarek和Martin(2010)中對這個研究進行了介紹。2013年,為了致敬韓禮德,杰夫·湯普森主編了合刊《文本與會話》(Text&Talk),其中的一些論文對這個研究進行了發展。我和米歇爾·扎帕維尼亞在關于青少年司法調解協商的研究中關注的是語言使用者(Martin & Zappvigna 2013),應用了梅頓的合法化語碼理論來分析這種形式化司法程序中的實際身份構建及理想身份構建間的差異(Martin 2012c)。扎帕維尼亞目前仍在繼續發展這個研究并將其命名為社會氛圍(social ambience)研究,使用的是網絡微博語料(Zappavigna 2012)。
這一系列研究是個體化研究的具體體現,它關注的是語言使用者,考察文化中的意義資源如何分配至個體,又怎樣被用來構建各種附屬關系,因此它涉及了分配與附屬(allocation and affiliation)兩個視角。這就意味著我們不能只把文化分析成是語域和語類系統了(即語言使用視角),還應該是一個共同成員組成的社區(即語言使用者視角)。簡言之,由實現化層級資源組成的文化通過語篇得以實例化,這些語篇同時構建了語類和社區。因此,實現化、實例化、個體化這三個維度是互補關系,同時進行三個維度的分析才能得到比較全面的研究。我認為這種研究的強大之處在于,它并不是將編碼取向僅僅看作是語言變體且通過這些語言變體語言使用者用同樣的方式表達意義,而是提供了一個更動態化的視角,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社區的成員關系是如何通過共享價值的協商構建出來的(即契合關系)。目前我們已經進入了后殖民主義與后福特主義的全球化時代,身份研究被給予了高度關注,因此,個體化研究很有可能是SFL未來數十年內令人激動的理論前沿。
王:謝謝。徐盛桓教授是一位中國學者,有一次在他報告結束后我問他,語言學研究的意義是什么?他沒有回答。后來,我學習了語言學并以此為業,我的一些學生問我同樣的問題。我只是說,這是我的工作。現在我想問您同樣的問題,您認為系統功能語言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什么?
馬:對“終極目標”的理解可能是多種多樣的。最近韓(2008)提出了“適用語言學”,這可以被看作是在討論一個理論與實踐辯證發展而來的語言模型,也是對把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強行劃分的一個回應。這種劃分把它們視為獨立的學科,而不是彼此依存關系。這導致的一個后果是,語言學課程往往只注重學生的純語言學知識,應用語言學課程則走中庸路線,什么都涉及但什么都不深入,既教授一些生成、功能、社會、認知等語言學知識,又選取分析二次語境化(re-contextualisation)后的測試、教育、課程等領域。結果,語言學家往往很狹隘,不能兼顧處理社會中的實際語言問題;應用語言學家則力不從心,不能很好地應用發展他們需要的理論。
在韓的初始構想里,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構建是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是他在英國共產黨“語言小組”工作的一部分(Halliday 1993)。在1983年的多倫多國際語言學大會上,他把這種構建稱為是一種忠于意識形態的社會行為(Halliday 1985b)。這在語言學領域是罕見的,因為多數語言學家都認為理論之所以發展是基于理論自身需要,而不是基于現實或政治的“操控”。但我并不這樣認為,我覺得當出現現實問題或某種政治動機要去解決問題時反而是理論發展的最佳時機。因此從韓的角度來說,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終極目標是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把語言及語言學研究放置在社會語境中,以此來解決現實社會中的語言問題(Martin 2013b)。如果我們去解決語言問題,我們必須思考為什么要這樣做,所以如果非要說明動機的話,意識形態必定是其中之一。
韓早年寫過一篇論文《句法學及其消費者》(“Syntax and the Consumer”)(1964)。他在文中稱一個語言學理論的構建取決于人們要用這個理論來干什么。這讓其他語言學家十分震驚,因為他們一直認為構建理論是為了追求真理,這應該是科學研究的唯一答案。我認為韓的這句話解釋了為什么系統功能語言學是這樣的一個面貌。首先,它的理論體系錯綜復雜,有很多層級和互補維度,超過了一個人描述某種語言或解決某個問題的需要,但這也正是它的優勢,它并非只為回答一個問題或解決一個交際障礙,它歷經演變,且現在為了多語言、多模態分析以及更廣泛的理論應用(教育語言學、臨床語言學、法律語言學、計算語言學、翻譯、博物館研究等等),這種演變仍在繼續。可能我們一生也學不完它,但不管你有什么問題,它都能幫到你。
這里要說的另一個方面,是它的意義關系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激進的社會符號論。這里的問題是語言科學需不需要考慮語言、神經科學、認知。換句話說,心智這個概念是不是多余的。韓的看法(1994)是如果我們構建了一個有足夠解釋力的社會符號學模型,再把它與同樣有足夠解釋力的新達爾文主義的大腦研究結合起來,如艾德爾曼(1992),那么我們不需要考慮心理因素。我們只需把生物系統看作是身體系統的衍生物,再把社會符號系統看作是生物系統的衍生物即可,不需要一個作為符號和大腦界面的心理因素。這一視角將系統功能語言學基于語言數據的實證之上,同時又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論提出了挑戰,即要構建一個有足夠解釋力的理論框架,能夠使認知模型成為多余(這里的認知模型指的是另一種獨立可選的符號模型,而不是整體模型的附生部分;其解釋力很弱,因為認知趨向于與語言形式模型合作,而后者與意義行為任意相關)。這使得系統功能語言學更容易去介入社會行為,改變世界,且不會糾結于語言和心理的偽命題。所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目標不是從語言形式中先推理出認知模型,然后再把它和大腦神經聯系在一起,而是構建一個可以直接結合神經學的社會符號模型。時間會說明系統功能語言學是怎樣朝著這個目標前進的。
王:接下來是最后一個問題。就語篇分析及語義研究來說,研究者有很多種研究途徑,語料庫語言學是一個,我們的系統功能語言學也是一個,它們之間有一些聯系。您能就語料庫目前的研究成果談一下您的看法嗎?
馬:我簡單說一下。辛克萊的搭配及類連接研究是其中之一,來源是弗斯對詞與詞組合型式的探索。這是個很活躍的研究視角,比如豪士頓(2011)總結的其中與評價系統及評價語言研究有關的成果。韓則更側重語法維度,發展了他作為概率系統的語言觀,他與詹姆士的合著(Halliday & James 1993)通過大型語料庫考察了英語中的時態與極性系統,證實了他的想法,語言系統的內在概率的確是有差異的(概率比是9:1)。
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料庫研究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一方面它需要的數據量太大,另一方面完全讓計算機自動標注系統功能語言學實現層級的描寫變量難度太大。如果時間成本與電腦硬件的條件都滿足,目前唯一可以操作的維度是書面語中的詞類及在此基礎上的橫組合描寫(詞類的語法序列)。如果條件再好點,那么部分功能描寫也是可以操作的(會有一些精確度損耗)。對計算機來說,它很難識別《導論》中及物性、語氣、主位系統的功能結構以及實現語篇語義系統的各種共變量關系,這意味著我們不得不依靠純人工的、半自動化半人工的標記,這嚴重限制了我們可以處理的數據量。另外,這也給上面提到的動態視覺化帶來了挑戰,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標記。
總之,“怎樣找到合適的語料庫得到我們想要的答案”是當前的主要問題。目前語料庫側重的多是書面語篇,因為口頭語篇轉錄的成本太高了,現在的電腦仍然需要轉錄,而語音自動識別技術又不成熟。舉個真實的例子,即使目前我們擁有全球最大的書面語篇語料庫,它也不足以幫助我們解決態度表達的意義關系問題,如Bednarek(2008)從語料庫角度對評價系統做了很有價值的探討,她其中一個分析是語篇語義范疇“surprise”是否屬于負面情緒,但幾乎她所有的例子都包含詞項“surprise”,因為它是核心詞項,與其他同類情感詞項的出現頻率有質的區別(比如startled,shocked,astounded,disturbed,shaken,rattled,dazed,takenaback,bowledover,caughtunawares,caughtnapping,caughtoffone’sguard等等)。我們缺乏足夠的數據來解決這個問題,即使我們用的是可以自動檢索的語料庫。
我曾憧憬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語料庫和標注技術的強大,從而基于語料庫證據,推動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但我也知道這絕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力。計算機程序替代人工應該是種解脫,但必須有天賦異稟、勤奮刻苦的人去努力實現它。我覺得計算機技術應該不是問題,它一直保持著日新月異的發展,人的理念卻始終是關鍵。我對于計算機、編程、數學的知識十分有限,說不出具體理念,但有人終將可以。有志者,事竟成。到那時,像我這樣人工分析的老古董就只能做些定性分析,一次只分析一兩個語篇,從中找尋零星的收獲了。
王:非常感謝。③
附注
① 一個可以回應這個批判的正面因素是,就系統/結構關系描寫而言,SFL學者發表成果的速度過于緩慢,學生和其他學者根本無從參考。Martin等(2013)的出版彌補了這個空白。
② 在其他語境中she’sanangel可能實現鑒賞意義(意思是she’sbeautiful)。死隱喻一般都體現固定的態度意義,而活隱喻則對語境很敏感,意義也更多樣化。
③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