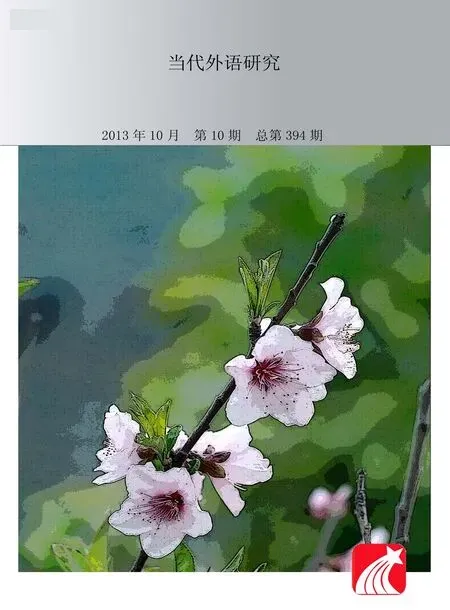從語(yǔ)義、語(yǔ)用和句法界面看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及其習(xí)得
張 琴 楊連瑞 高秀雪
(中國(guó)海洋大學(xué),青島,266100;青島農(nóng)業(yè)大學(xué),青島,266109)
1. 引言
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或中間結(jié)構(gòu)(middle construction)是英語(yǔ)中的一種特殊句式,一直受到語(yǔ)言學(xué)研究者的關(guān)注。宋國(guó)明(1997:273)把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定義為正好介于主動(dòng)句和被動(dòng)句之間的一種結(jié)構(gòu)。這就是說(shuō),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在本質(zhì)上有別于與其相應(yīng)的主動(dòng)句和被動(dòng)句。如下所示,例(1)、例(4)和例(5)是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例(2)和例(3)是例(1)相應(yīng)的主動(dòng)句和被動(dòng)句。
(1) The car drives fast. 這輛車(chē)開(kāi)起來(lái)很快。
(2) He drives the car fast. 他把車(chē)開(kāi)得飛快。
(3) The car is driven fast. 這輛車(chē)開(kāi)得很快。
(4) Bureaucrats bribe easily. 政府官僚賄賂起來(lái)很容易。
(5) This kind of book sells easily. 這種書(shū)賣(mài)起來(lái)很快。(宋國(guó)明1997)
顯而易見(jiàn),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在句法和語(yǔ)義上都與主被動(dòng)句有著明顯區(qū)別。盡管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和相應(yīng)被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主謂語(yǔ)義關(guān)系是一致的,或者說(shuō)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中的謂語(yǔ)動(dòng)詞和沒(méi)有施事的被動(dòng)動(dòng)詞類(lèi)似,但是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不能使用被動(dòng)態(tài),二者屬于不同的概念。所以很多時(shí)候,當(dāng)二語(yǔ)初學(xué)者遇到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時(shí)往往將其判定為語(yǔ)法錯(cuò)誤的被動(dòng)句式,因?yàn)樗⒉环铣R?guī)的句法結(jié)構(gòu)。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具有鮮明的獨(dú)特性,其獨(dú)特性主要表現(xiàn)在句法和語(yǔ)義兩個(gè)方面:“句法特性包括受事做主語(yǔ)、主動(dòng)形式表示被動(dòng)意義、及物動(dòng)詞呈非及物化表現(xiàn)、句子用一般現(xiàn)在時(shí)、有必要狀語(yǔ)修飾語(yǔ)等;語(yǔ)義特性包括隱含論元、非事件性、泛指性、情態(tài)性等”(高秀雪2013:13)。由于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在句法和語(yǔ)義上的獨(dú)特性給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的習(xí)得造成了困難,所以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習(xí)得問(wèn)題已經(jīng)引起了國(guó)內(nèi)外二語(yǔ)習(xí)得領(lǐng)域研究者的關(guān)注(Balcom 1999,2003;Birdsong 1992;Gao 2008)。其中,Gao(2008)通過(guò)調(diào)查研究以漢語(yǔ)和韓語(yǔ)為母語(yǔ)的英語(yǔ)學(xué)習(xí)者如何習(xí)得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及其他去及物結(jié)構(gòu),試圖探尋英語(yǔ)中動(dòng)及其相關(guān)結(jié)構(gòu)的發(fā)展路徑和習(xí)得機(jī)制。研究表明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對(duì)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習(xí)得并不是受某個(gè)單一因素的影響所致,如句法形態(tài)等,而可能受到多個(gè)因素的共同制約和影響,導(dǎo)致了學(xué)習(xí)者不同程度的學(xué)習(xí)困難。作為英語(yǔ)中一種比較獨(dú)特的句式,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習(xí)得研究能幫助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找到習(xí)得的困難所在,從而更加有效地習(xí)得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
近年來(lái),界面假設(shè)(Interface Hypothesis)的提出在二語(yǔ)習(xí)得領(lǐng)域引起了很大反響。中介語(yǔ)語(yǔ)法包含了各個(gè)模塊的知識(shí),如句法、語(yǔ)義、語(yǔ)用等等。在二語(yǔ)習(xí)得過(guò)程中,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如何整合這些知識(shí)并加以習(xí)得成為二語(yǔ)習(xí)得領(lǐng)域研究的焦點(diǎn)。界面假設(shè)認(rèn)為語(yǔ)言知識(shí)的各個(gè)模塊之間存在界面,而習(xí)得的難點(diǎn)就在于界面的習(xí)得(Sorace & Filiaci 2006)。本文試圖從界面假設(shè)理論這一新視角入手,分析和探究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習(xí)得問(wèn)題。
2. 理論背景
2.1 界面理論
模塊論(modular approach)認(rèn)為語(yǔ)言以及二語(yǔ)習(xí)得者的中介語(yǔ)包含了音系、形態(tài)、句法、語(yǔ)義、語(yǔ)用等一系列模塊。Chomsky生成語(yǔ)言學(xué)最簡(jiǎn)方案的提出,激發(fā)了語(yǔ)言學(xué)家們的思考:語(yǔ)言各模塊之間是否相互作用?相關(guān)性有多大?隨之界面(interface,也被稱(chēng)為“接口”)這一概念被引入到語(yǔ)言學(xué)研究當(dāng)中。盡管語(yǔ)言學(xué)界關(guān)于界面概念還沒(méi)有一個(gè)完整統(tǒng)一的定義,但是這并未影響學(xué)者們對(duì)界面研究的興趣和關(guān)注。相關(guān)研究表明語(yǔ)言各個(gè)模塊之間確實(shí)存在著交互作用,而作用的大小視不同的語(yǔ)言現(xiàn)象而定。Chomsky的原則和參數(shù)理論(P & P)就已經(jīng)涉及了語(yǔ)言系統(tǒng)中的界面問(wèn)題(Chomsky 1986)。在理論框架下提出了語(yǔ)言理論的三分模式(tripartite Y model)(如圖1所示),認(rèn)為句法的加工運(yùn)算必須滿(mǎn)足一定的條件——即語(yǔ)音輸出(phonological output)和語(yǔ)義輸出(semantic output)界面條件。隨著生成語(yǔ)法理論的發(fā)展,最簡(jiǎn)方案更加明確了界面研究對(duì)理解語(yǔ)言生成的重要性。最簡(jiǎn)方案句法操作要由輸出(output)來(lái)決定,而輸出則必須滿(mǎn)足界面條件(Chomsky 1995),界面概念在最簡(jiǎn)方案理論體系中得到強(qiáng)化。

圖1 Chomsky三分模式(tripartite Y model)
近年來(lái),研究者在Chomsky關(guān)于界面研究的基礎(chǔ)上做了更深入細(xì)致的研究和分析并提出了相應(yīng)的語(yǔ)言界面運(yùn)作模式。最有影響力并且在習(xí)得領(lǐng)域引用最多的便是Jackendoff(2002)的語(yǔ)言界面模式和Reinhart(2006)的語(yǔ)言界面模式。
Jackendoff認(rèn)為語(yǔ)言是由一些相對(duì)獨(dú)立的組合系統(tǒng)構(gòu)成并且各個(gè)系統(tǒng)又由一系列相應(yīng)的界面體系連結(jié)起來(lái),句法只是組合系統(tǒng)之一而已(如圖2所示,Jackendoff 2002)。在Jackendoff的語(yǔ)言界面模式中,盡管句法依舊處在中心位置上,但是與其兩側(cè)的概念結(jié)構(gòu)(conceptual structure)(Jackendoff沒(méi)有將語(yǔ)用、語(yǔ)篇和語(yǔ)義完全區(qū)分開(kāi)來(lái),而統(tǒng)稱(chēng)為“概念”)和語(yǔ)音結(jié)構(gòu)(phonological structure)是平等的,因此其它的語(yǔ)言模塊并不從屬于句法,這是Jackendoff的理論與以往研究最顯著的差異。

圖2 Jackendoff語(yǔ)言界面模式(2002)
Reinhart的語(yǔ)言界面模式(如圖3所示)盡管明顯受到了Jackendoff的影響,但是二者存在差異:前者如傳統(tǒng)觀點(diǎn)一樣十分強(qiáng)調(diào)句法的中心地位,注重“句法中心主義”(syntactocentrism),即語(yǔ)音、語(yǔ)義等其它語(yǔ)言模塊都從屬于句法。Reinhart認(rèn)為句法即語(yǔ)言核心的運(yùn)算系統(tǒng)(computational system),其本身就是相互獨(dú)立的不同思維系統(tǒng)的界面,這些思維體系包括概念系統(tǒng)、語(yǔ)境系統(tǒng)、推理系統(tǒng)和覺(jué)動(dòng)系統(tǒng)(Reinhart 2006)。在她的理論模式中,運(yùn)算系統(tǒng)只有獲得最佳的設(shè)計(jì)才能使信息在各思維系統(tǒng)之間合理快速轉(zhuǎn)化,才不會(huì)耗費(fèi)學(xué)習(xí)者太多的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和運(yùn)算資源(computational resources);反之,學(xué)習(xí)者則要耗費(fèi)大量的時(shí)間和精力對(duì)語(yǔ)言信息進(jìn)行解析。由此,Reinhart提出了“超負(fù)荷的學(xué)習(xí)者”(overburdened learners)概念,用于描述處在不同學(xué)習(xí)階段,不同類(lèi)型的學(xué)習(xí)者的習(xí)得狀況并且有效解釋語(yǔ)言習(xí)得中的一個(gè)普遍特征——兒童和成人都難以習(xí)得界面(interface vulnerability for acquisition)。Reinhart的這一理論研究對(duì)界面習(xí)得具有重要啟示。

圖3 Reinhart語(yǔ)言界面模式(2006)
2.2 界面假設(shè)理論(Interface Hypothesis)
近年來(lái),隨著二語(yǔ)習(xí)得研究的深入和發(fā)展,界面概念被研究者應(yīng)用到二語(yǔ)習(xí)得研究中,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是如何整合中介語(yǔ)語(yǔ)法的各個(gè)模塊,即如何習(xí)得各個(gè)語(yǔ)言模塊之間以及語(yǔ)言模塊與其外部認(rèn)知系統(tǒng)之間的界面,界面假設(shè)(Interface Hypothesis)應(yīng)運(yùn)而生(Sorace & Filiaci 2006)。從很大程度上來(lái)說(shuō),Chomsky最簡(jiǎn)方案框架內(nèi)的界面研究以及Jackendoff(2002)和Reinhart(2006)的語(yǔ)言界面模式等都為這一界面假設(shè)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尤其是Reinhart的界面研究發(fā)現(xiàn),即:無(wú)論是兒童還是成人都不易習(xí)得語(yǔ)言界面,因而語(yǔ)言各模塊之間以及與模塊外部系統(tǒng)之間的界面習(xí)得問(wèn)題成為界面假設(shè)理論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
界面假設(shè)理論認(rèn)為,在二語(yǔ)習(xí)得中,單純的句法、語(yǔ)義或語(yǔ)用特征是可以被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完整地習(xí)得的,但是各個(gè)語(yǔ)言模塊之間界面,譬如句法-語(yǔ)義界面、句法-語(yǔ)用界面的習(xí)得卻未必可以順利完成,甚至可以說(shuō)是相當(dāng)困難的(Sorace & Filiaci 2006)。習(xí)得不僅僅是習(xí)得語(yǔ)言系統(tǒng)的各個(gè)模塊和詞匯,還要利用這些知識(shí)來(lái)學(xué)習(xí)語(yǔ)用規(guī)則,即習(xí)得各個(gè)模塊之間的交互作用——界面(Bosetal. 2004)。Sorace界面假設(shè)的提出在語(yǔ)言學(xué)界引起了巨大反響,研究者關(guān)于界面及其習(xí)得的研究也越來(lái)越多,White(2009)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提出一個(gè)綜合的界面習(xí)得模式(如圖4),比較完整地呈現(xiàn)了語(yǔ)言系統(tǒng)中的各個(gè)模塊之間的界面。她把界面分為內(nèi)部界面(internal interface)和外部界面(external interface)。內(nèi)部界面主要指語(yǔ)言?xún)?nèi)部各模塊之間的界面,如語(yǔ)音-句法界面、句法-語(yǔ)義界面等;外部界面主要指語(yǔ)言模塊與其他認(rèn)知系統(tǒng)之間的界面,如句法-語(yǔ)篇界面,語(yǔ)義-語(yǔ)用界面等。與單純的某個(gè)語(yǔ)言模塊的習(xí)得相比,語(yǔ)言?xún)?nèi)部及外部的界面特征和影響因素更加復(fù)雜多變,因而界面的習(xí)得需要耗費(fèi)學(xué)習(xí)者更多的時(shí)間和精力,界面習(xí)得也就更加困難。

圖4 White(2009)界面習(xí)得模式圖
盡管作為一個(gè)較新的理論,Sorace和Filiaci提出的界面假設(shè)理論對(duì)二語(yǔ)習(xí)得研究領(lǐng)域影響頗為深遠(yuǎn),界面假設(shè)理論受到越來(lái)越多語(yǔ)言學(xué)研究者的關(guān)注,他們開(kāi)始以一種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語(yǔ)言的習(xí)得問(wèn)題,針對(duì)語(yǔ)言界面及其習(xí)得的研究也越來(lái)越豐富(Sorace & Filiaci 2006;White 2009,2011a,b;Rothman & Slabakova 2011;Rothman & Guijarro-Fuentes 2012)。這些研究不斷驗(yàn)證界面假設(shè)理論的可行性,發(fā)現(xiàn)理論中存在的一些漏洞和不足,從而推動(dòng)界面假設(shè)理論的發(fā)展和完善。Sorace和Filiaci認(rèn)為界面假設(shè)理論的應(yīng)用能夠幫助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達(dá)到接近二語(yǔ)母語(yǔ)者的水平,這體現(xiàn)了在二語(yǔ)習(xí)得領(lǐng)域進(jìn)行界面研究的必要性。
界面假設(shè)理論為研究二語(yǔ)知識(shí)的習(xí)得研究開(kāi)辟了一條新的路徑。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已有相關(guān)文章嘗試研究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關(guān)于具體的語(yǔ)言界面習(xí)得問(wèn)題,如韋理等(2010)從句法-語(yǔ)用界面的角度研究大學(xué)生英語(yǔ)定冠詞的習(xí)得情況。高育松(2009)從語(yǔ)篇、語(yǔ)義與句法界面的視角探討了中國(guó)英語(yǔ)學(xué)習(xí)者對(duì)英語(yǔ)空賓語(yǔ)結(jié)構(gòu)的習(xí)得。尹洪山(2012)從句法-語(yǔ)用界面看英語(yǔ)前置句式的習(xí)得。但是與國(guó)外語(yǔ)言學(xué)界漸趨成熟的界面習(xí)得研究相比,國(guó)內(nèi)關(guān)于界面習(xí)得的研究還是相對(duì)有限和滯后,尤其關(guān)于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界面習(xí)得研究更少。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是英語(yǔ)中比較常見(jiàn)卻不太符合常規(guī)語(yǔ)法的一種特殊句式,本文旨在以Sorace界面假設(shè)理論為基礎(chǔ),從一個(gè)比較綜合的語(yǔ)義、語(yǔ)用和句法界面角度,探討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語(yǔ)義和語(yǔ)用限制以分析其習(xí)得的困難和問(wèn)題。
3. 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語(yǔ)義和語(yǔ)用限制
3.1 句法-語(yǔ)義界面限制
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在開(kāi)始習(xí)得一個(gè)新的句法結(jié)構(gòu)時(shí),一般會(huì)基于語(yǔ)義上的相似性將母語(yǔ)語(yǔ)素映射到二語(yǔ)語(yǔ)素上,但很多時(shí)候二者并不是完全對(duì)等的,從而導(dǎo)致了句法-語(yǔ)義錯(cuò)配現(xiàn)象(syntax-semantics mismatch)(Slabakova 2008,2009),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特別是初學(xué)者會(huì)把“The car drives fast.”這樣的中動(dòng)句式判定為錯(cuò)誤的句子。他們?cè)诩庸だ斫庠摼渥訒r(shí),認(rèn)為主語(yǔ)car和謂語(yǔ)動(dòng)詞drive之間應(yīng)該是被動(dòng)關(guān)系,要使用被動(dòng)語(yǔ)態(tài),“The car is driven fast.”這樣的句子才是符合語(yǔ)法的,理所當(dāng)然地把“The car drives fast.”判定為不合法的句子。因此,在學(xué)習(xí)新的句法結(jié)構(gòu)時(shí)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必須要考慮語(yǔ)義因素的作用,而句法-語(yǔ)義界面則呈現(xiàn)了復(fù)雜的語(yǔ)義因素及其變異的影響。Slabakova(2010)認(rèn)為對(duì)于學(xué)習(xí)者而言,句法結(jié)構(gòu)的習(xí)得并不會(huì)太困難,真正的困難和挑戰(zhàn)在于習(xí)得句法-語(yǔ)義界面,因?yàn)閷W(xué)習(xí)者要使用自己的大腦運(yùn)算系統(tǒng)(computational system)將句法結(jié)構(gòu)與語(yǔ)義結(jié)構(gòu)關(guān)聯(lián)起來(lái)才能形成形式-意義的映射,然而在句法-語(yǔ)義界面上并沒(méi)有那種完全的一一對(duì)應(yīng),所以探究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習(xí)得必須要考慮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句法-語(yǔ)義界面限制并且主要是語(yǔ)義因素對(duì)句法構(gòu)成的限制作用。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在句法形態(tài)上相對(duì)簡(jiǎn)單,主要由三個(gè)部分組成:NP主語(yǔ),VP謂語(yǔ)和C附加語(yǔ)。筆者試圖對(duì)各構(gòu)成部分的語(yǔ)義限制條件進(jìn)行系統(tǒng)的分析,探究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句法-語(yǔ)義界面習(xí)得的關(guān)鍵。
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中的主語(yǔ)是由名詞性成分NP構(gòu)成,Kim(2001:551)認(rèn)為中動(dòng)句是絕對(duì)陳述句,主語(yǔ)必須能夠表達(dá)一個(gè)主題(topic)。因此提出了“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主題性主語(yǔ)限制條件”(The Topic Subject Constraint on Middles,簡(jiǎn)稱(chēng)TSCM),也就是說(shuō),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主語(yǔ)在語(yǔ)義上必須是確定性的對(duì)象或事物。而在“*A car drives fast.”這個(gè)句子中,主語(yǔ)“a car”是不確定的對(duì)象,所以該句是不合法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
句法語(yǔ)義界面研究領(lǐng)域的一個(gè)基本假設(shè)是動(dòng)詞詞義在很大程度上對(duì)句法形態(tài)有決定作用。“……論元的句法實(shí)現(xiàn)——其句法范疇和語(yǔ)法作用——經(jīng)證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從動(dòng)詞的意義預(yù)測(cè)出來(lái)”(Levin & Rappaport 2005),這與中心詞驅(qū)動(dòng)的短語(yǔ)結(jié)構(gòu)文法不謀而合,“詞語(yǔ)攜帶了豐富的句法語(yǔ)義信息,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所在的句子的句法語(yǔ)義結(jié)構(gòu)。反過(guò)來(lái),句子之所以表現(xiàn)出不同的句法語(yǔ)義結(jié)構(gòu),也正是因?yàn)槠渲兴年P(guān)鍵詞語(yǔ)不同。”(陸儉明2006:34)。因而就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而言,謂語(yǔ)部分VP,即中動(dòng)詞,是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核心,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gè)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句法構(gòu)成,是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成功習(xí)得的關(guān)鍵,因此國(guó)內(nèi)外關(guān)于中動(dòng)詞的相關(guān)研究頗多,當(dāng)中中動(dòng)詞的及物性問(wèn)題一直是學(xué)者們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Fagan 1988;Stroik 1992;熊學(xué)亮、付巖2013)。當(dāng)中動(dòng)詞的及物性問(wèn)題對(duì)解釋整個(gè)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起到關(guān)鍵作用,但是學(xué)者們關(guān)于這個(gè)問(wèn)題并未達(dá)成一致意見(jiàn)。對(duì)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持句法觀的學(xué)者認(rèn)為中動(dòng)詞是及物的;持詞匯觀的學(xué)者認(rèn)為中動(dòng)詞是不及物的;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中動(dòng)詞是介于及物動(dòng)詞和不及物動(dòng)詞之間的“間及物動(dòng)詞”(熊學(xué)亮、付巖2013:5)。基于眾多學(xué)者的相關(guān)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無(wú)論中動(dòng)詞是及物的、不及物的或是“間及物的”,動(dòng)詞進(jìn)入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必須保證說(shuō)話人或者動(dòng)詞相應(yīng)的隱含施事給受事帶來(lái)足夠的狀態(tài)變化,而這種狀態(tài)變化則體現(xiàn)在語(yǔ)義上。仍以“The car drives fast.”為例,中動(dòng)詞“drives”所映射的邏輯主語(yǔ)(隱含施事)不是句子表面上的主語(yǔ)“the car”,真正的邏輯主語(yǔ)可能是某個(gè)有生命的對(duì)象,并且這個(gè)對(duì)象能夠使“car”快速運(yùn)轉(zhuǎn)起來(lái),即給受事帶來(lái)了明顯的狀態(tài)變化。徐盛桓(2002)也指出:“從語(yǔ)義上來(lái)講,中動(dòng)詞要能夠表示一定的強(qiáng)度,對(duì)受事有重大影響或使其發(fā)生一定變化”。中動(dòng)詞習(xí)得的關(guān)鍵在于明確其語(yǔ)義上與隱含施事和受事的關(guān)系及其語(yǔ)義限制作用。
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句尾一般由附加語(yǔ)構(gòu)成,通常使用較多的是類(lèi)似“easily”這樣的性狀副詞,對(duì)前面的中動(dòng)詞進(jìn)行修飾,限定或補(bǔ)充說(shuō)明。性狀副詞一般緊跟在中動(dòng)詞的后面而且不能省略。如果沒(méi)有性狀副詞,句子通常在語(yǔ)法上不可接受。中動(dòng)詞和后面的性狀副詞共同組成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或者叫做中動(dòng)短語(yǔ),二者缺一不可。從語(yǔ)義上看,中動(dòng)短語(yǔ)“drives fast”、“bribe easily”、“sells easily”分別是說(shuō)話人對(duì)話題內(nèi)容“car”、“bureaucrat”、“book”的主觀感受和評(píng)價(jià),性狀副詞在語(yǔ)義上必須具備評(píng)價(jià)性和非意愿性(高秀雪2013),它不是指主語(yǔ)某一特定時(shí)刻的變化,而是指其所具有的一種相對(duì)恒定的狀態(tài),這種語(yǔ)義上的限制在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中是不可或缺,體現(xiàn)其獨(dú)特性。
以上分析表明各組成部分在句法-語(yǔ)義界面上的語(yǔ)義限制因素是二語(yǔ)習(xí)得者習(xí)得典型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難點(diǎn)。在習(xí)得過(guò)程中,學(xué)習(xí)者必須了解各部分的語(yǔ)義影響及其變異,實(shí)現(xiàn)語(yǔ)義對(duì)句法的合理映射。
3.2 句法-語(yǔ)用界面限制
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句法構(gòu)成與語(yǔ)用同樣密不可分,我們應(yīng)考慮語(yǔ)用因素對(duì)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習(xí)得的制約作用。近年來(lái),研究者關(guān)于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語(yǔ)用限制條件探討的焦點(diǎn)主要集中在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附加語(yǔ)(性狀副詞)上,尤其在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中,性狀副詞往往是強(qiáng)制性的并且這種強(qiáng)制性體現(xiàn)了語(yǔ)用對(duì)句法形態(tài)的限制。Steinbach(2002)認(rèn)為“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狀語(yǔ)修飾語(yǔ)不是由句法而是由語(yǔ)用允準(zhǔn)的”(轉(zhuǎn)自高秀雪2013),即語(yǔ)用因素對(duì)于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中附加語(yǔ)的存在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曹宏(2005)認(rèn)為中動(dòng)句具有特定的語(yǔ)用表達(dá)功能。句首NP是話題(topic),提供了言談的出發(fā)點(diǎn)(departure of discourse),中動(dòng)短語(yǔ)VP+C是針對(duì)話題內(nèi)容的評(píng)論(話題具備附加語(yǔ)所表達(dá)的性狀特征)。話題傳遞的是舊信息,而真正傳遞新信息的是附加語(yǔ),因而附加語(yǔ)不可或缺。這在很大程度上與Grice(1975)言語(yǔ)交際中的合作原則是一致的,合作原則要求我們所說(shuō)的話要滿(mǎn)足“數(shù)量準(zhǔn)則”(the Maxim of Quantity):在話語(yǔ)使用中,使你的話語(yǔ)如所要求的那樣詳盡,所需的信息量都應(yīng)表達(dá)出來(lái),不能缺少。就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而言,句尾表達(dá)狀態(tài)的附加語(yǔ)(如性狀副詞)一旦缺少,整個(gè)句子的信息量就是不完整的,違反了Grice數(shù)量準(zhǔn)則這樣的語(yǔ)用限制,所以類(lèi)似“The car drives.”這樣的句子是不合法的中動(dòng)句。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要成功習(xí)得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必須認(rèn)識(shí)到它的語(yǔ)用限制條件,語(yǔ)用作為語(yǔ)言的外部因素對(duì)句法構(gòu)成的限制可能是習(xí)得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又一關(guān)鍵。
以上從語(yǔ)言的內(nèi)部界面——句法-語(yǔ)義界面探究語(yǔ)義因素對(duì)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構(gòu)成的限制作用,這印證了Slabakova(2008)關(guān)于句法語(yǔ)義界面習(xí)得的相關(guān)理論和實(shí)證研究。她提出了“簡(jiǎn)單句法-復(fù)雜語(yǔ)義”(Simple Syntax-Complex Semantics)的說(shuō)法,即在二語(yǔ)習(xí)得過(guò)程中,相對(duì)于簡(jiǎn)單的句法形態(tài),對(duì)復(fù)雜的語(yǔ)義因素的考量才是成功習(xí)得的關(guān)鍵,因?yàn)檎Z(yǔ)義因素對(duì)句法結(jié)構(gòu)的映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同時(shí)從語(yǔ)言的外部界面——句法-語(yǔ)用界面集中關(guān)注典型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附加語(yǔ)存在的語(yǔ)用限制因素,表明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后補(bǔ)修飾狀語(yǔ)是滿(mǎn)足句式所需信息量的必要條件,是由語(yǔ)用允準(zhǔn)的。就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習(xí)得而言,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必須關(guān)注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句法-語(yǔ)義界面和句法-語(yǔ)用界面限制問(wèn)題。相比于純粹的句法特征,語(yǔ)義、語(yǔ)用因素對(duì)句法構(gòu)成的制約顯得更為重要,是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習(xí)得的關(guān)鍵。
4. 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變化發(fā)展——非典型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
語(yǔ)言的發(fā)展過(guò)程是動(dòng)態(tài)的、復(fù)雜的(Larsen-Freeman 1998),語(yǔ)言處在不斷的變化發(fā)展過(guò)程中,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也不例外,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要成功習(xí)得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就必須關(guān)注該結(jié)構(gòu)的變化發(fā)展動(dòng)態(tài)。根據(jù)研究者對(duì)語(yǔ)料庫(kù)的檢索和日常會(huì)話用語(yǔ)的觀察分析發(fā)現(xiàn),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是一個(gè)語(yǔ)用表達(dá)功能很強(qiáng)的句式,句式在不斷擴(kuò)張,從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演變出了非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這也表明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句法形態(tài)受到語(yǔ)義、語(yǔ)用因素的影響和限制。在現(xiàn)實(shí)的話語(yǔ)交際中,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語(yǔ)義、語(yǔ)用和句法都發(fā)生著一定的變化(曹宏2005;楊佑文2007)。
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一般包括受事主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The Patient-Subject Middle)和感事主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The Experience-Subject Middle)。典型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句首NP是中動(dòng)詞的受事(patient)或感事(experiencer),如例句(6)所示,“children”即為中動(dòng)詞“scare”的感事。
(6) Children scare easily. (孩子們很容易受驚。)
(7) The knife cuts well. (這把刀切起來(lái)很好〔使〕。)
(8) This truck loads easily. (這輛卡車(chē)裝起〔東西〕來(lái)很方便。)(曹宏2005)
(9) That whole wheat flour bakes wonderful bread. (全麥面粉烘焙出好吃的面包。)(Levin 1993)
而隨著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使用和發(fā)展,從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發(fā)展出了非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表達(dá),具體主要細(xì)分為工具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instrumental middle),處所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location middle)和材料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material middle)。非典型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句首NP相應(yīng)地演變?yōu)橹袆?dòng)詞的處所,工具或材料,如例句(7)、(8)、(9)所示,“knife”、“truck”和“wheat flour”分別是中動(dòng)詞“cut”、“l(fā)oad”和“bake”的工具、處所和材料。同時(shí),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在句法構(gòu)成上一般只有主語(yǔ),中動(dòng)詞和強(qiáng)制性的附加語(yǔ),而在非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中,有時(shí)中動(dòng)詞后的賓語(yǔ)是可以出現(xiàn)的,如例句(9)所示,賓語(yǔ)“bread”就出現(xiàn)在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中,這說(shuō)明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句法形態(tài)在語(yǔ)用過(guò)程中不斷演變和擴(kuò)充,相應(yīng)的語(yǔ)義、語(yǔ)用限制條件也在改變,值得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的關(guān)注。此外,還有一類(lèi)非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是指句中沒(méi)有使用強(qiáng)制性的副詞狀語(yǔ)而使用了表示強(qiáng)調(diào)、否定、情態(tài)、焦點(diǎn)的詞語(yǔ)或其它語(yǔ)境手段,如以下各句中的“does”、“might”、“not”(司惠文、余光武2005:3)。盡管這些句子在句法形態(tài)上不符合典型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要求,但是語(yǔ)義和語(yǔ)用上的變化使得它們順利演變?yōu)楹戏ǖ姆堑湫陀⒄Z(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這些變化給學(xué)習(xí)者判斷和習(xí)得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增加了難度。
(10) The bread DOES cut.
(11) The floor might wax.
(12) This bread doesn’t cut.
因此在習(xí)得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時(shí),學(xué)習(xí)者除了要考慮典型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構(gòu)成的語(yǔ)義語(yǔ)用限制條件,還應(yīng)了解非典型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各構(gòu)成部分在句法、語(yǔ)義及語(yǔ)用上的關(guān)系和變化,譬如在某些特定的語(yǔ)用環(huán)境下句尾副詞是可以不出現(xiàn)的,而這往往為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所忽視。非典型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突破了典型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在句法上的基本模式,但其句法形態(tài)仍受到語(yǔ)義、語(yǔ)用因素的制約,語(yǔ)義上的否定或強(qiáng)調(diào)自然地映射到句法上會(huì)使句法表現(xiàn)形式產(chǎn)生變化。對(duì)于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習(xí)得,無(wú)論典型或非典型,句法-語(yǔ)義界面和句法-語(yǔ)用界面限制一直存在并且是習(xí)得該句式的關(guān)鍵。學(xué)習(xí)者只有整合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句法、語(yǔ)義、語(yǔ)用及其界面特征,才能更加全面有效地習(xí)得變化發(fā)展中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
5. 結(jié)語(yǔ)
本文以Sorace和Filiaci(2006)提出的界面假設(shè)理論為基礎(chǔ),從語(yǔ)義、語(yǔ)用和句法界面的視角探討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語(yǔ)義語(yǔ)用限制條件及對(duì)習(xí)得的啟示。我們認(rèn)為,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要成功有效地習(xí)得英語(yǔ)中動(dòng)這一特殊結(jié)構(gòu)必須充分了解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句法、語(yǔ)義、語(yǔ)用及其界面限制和特征。筆者結(jié)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發(fā)展現(xiàn)狀對(duì)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句法-語(yǔ)義界面、句法-語(yǔ)用界面限制條件進(jìn)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分析和總結(jié),并對(duì)演變而來(lái)的非典型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做了相關(guān)研究和解釋。
這給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習(xí)得帶來(lái)一些啟示:第一,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特別是初學(xué)者在習(xí)得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時(shí),單純地習(xí)得句法無(wú)法辨析合法與不合法的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基于界面假設(shè)理論,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習(xí)得的難點(diǎn)在于語(yǔ)義、語(yǔ)用和句法界面,而語(yǔ)義、語(yǔ)用和句法界面習(xí)得的關(guān)鍵在于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構(gòu)成的語(yǔ)義語(yǔ)用限制條件的習(xí)得。第二,與句法結(jié)構(gòu)的習(xí)得相比,句法-語(yǔ)義界面上的語(yǔ)義限制因素復(fù)雜多變,其習(xí)得更加困難,更具挑戰(zhàn)性。因此在習(xí)得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過(guò)程中,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應(yīng)該更為注重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各組成部分中語(yǔ)義因素的習(xí)得。第三,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因其強(qiáng)大的語(yǔ)用表達(dá)能力,從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擴(kuò)展到非典型的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這就要求二語(yǔ)學(xué)習(xí)者在習(xí)得該結(jié)構(gòu)時(shí)懂得融匯變通,熟知語(yǔ)義和語(yǔ)用變化所引起的句法形態(tài)上的變異,以便更好地掌握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并提高其語(yǔ)用能力。
Balcom, P. 1999. These constructions don’t acquire easily: Middle construction and multicompetence [J].TheCanadianJournalofAppliedLinguistics2(1): 5-20.
Balcom, P. 2003.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of L2 English on middle constructions in L1 French [A]. In V. Cook (ed.).EffectsoftheSecondLanguageontheFirst[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Birdsong, D.1992. Ultimate attai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Language68: 706-55.
Bos, P., B. Hollebrandse & P. Sleeman. 2004. Introduction: The pragmatics-syntax and the semantics-syntax interface in acquisition [J].IRAL42: 101-10.
Chomsky, N. 1986.KnowledgeofLanguage:ItsNature,OriginandUse[M]. Praeger:New York.
Chomsky, N. 1995.TheMinimalistProgram[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Fagan, S. 1988. The English middle [J].LinguisticInquiry19: 181-203.
Gao, Y. 2008.L2AcquisitionofEnglishMCandItsRelatedStructuresbyChineseandKoreanLearners:TowardsanEventStructure-basedAccount[D]. Guangzhou: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rice, H.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A]. In P. Cole & J. Morgan (eds.).SyntaxandSemantics(Vol. 3)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1-58.
Jackendoff, R. 2002.FoundationsofLanguage:Brain,Meaning,Grammar,Evolu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im, Sungwook. 2001. English middles as categorical sentences [J].KoreanJournalofEnglishLanguageandLinguistics1(4): 537-60.
Larsen-Freeman, D. 1998. On the scop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J].LanguageLearning48(4): 551-56.
Levin, B. 1993.EnglishVerbClassesandAlterna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vin, B. & M. Rappaport. 2005.ArgumentRealiz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inhart, T.2006.InterfaceStrategies:Reference-setComputation[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Rothman, J. & R. Slabakova. 2011. The mind-context divide: On acquisition at the linguistic interfaces [J].Lingua121: 568-76.
Rothman, J. & P. Guijarro-Fuentes. 2012. Linguistic interface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childhood: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J].FirstLanguage32: 3-16.
Sorace, A. & F. Filiaci. 2006. Anaphora resolution in near-native speakers of Italian [J].SecondLanguageResearch22: 339-68.
Slabakova, R. 2008.MeaningintheSecondLanguage-StudiesonLanguageAcquisitionSeries[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Slabakova, R. 2009. What is easy and what is hard to acquire in a second language? [A]. In M. Bowles, T. Ionin, S. Montrul & A. Tremblay (eds.).Proceedingsofthe10thGenerativeApproachesto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Conference[C].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Slabakova, R. 2010. Semantic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AnnualReviewofAppliedLinguistics30: 231-47.
Steinbach, M. 2002.MiddleVoice:AComparativeStudyintheSyntax-SemanticsInterfaceofGerma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Stroik, T. 1992. Middles and movement [J].LinguisticInquiry23:1, 127-37.
White, L. 2009. Grammatical theory, interfaces and L2 knowledge [A]. In W. C. Ritchie & T.K. Bhatia (eds).TheNewHandbookof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C]. Bingley: Emerald. 49-65.
White, L. 2011a. Who is the Interface Hypothesis about? [J].LinguisticApproachestoBilingualism1(1): 48-53.
White, L. 2011b. The Interface Hypothesis: How far does it extend? [J].LinguisticApproachestoBilingualism1(1): 108-10.
曹宏.2005.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語(yǔ)用特點(diǎn)及教學(xué)建議[J].漢語(yǔ)學(xué)習(xí)(5):61-68.
高秀雪.2013.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的句法語(yǔ)義界面研究[J].外語(yǔ)教學(xué)與研究(1):13-23.
高育松.2009.中國(guó)英語(yǔ)學(xué)習(xí)者對(duì)英語(yǔ)空賓語(yǔ)結(jié)構(gòu)的習(xí)得——語(yǔ)篇、語(yǔ)義與句法接口的視角[J].外語(yǔ)教學(xué)與研究(6):438-46.
陸儉明.2006.句法語(yǔ)義界面問(wèn)題[J].外國(guó)語(yǔ)(3):30-35.
司惠文、余光武.2005.英語(yǔ)中間結(jié)構(gòu)致使生成研究[J].現(xiàn)代外語(yǔ)(1):1-9.
宋國(guó)明.1997.句法理論概要[M].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
韋理、戴煒棟.2010.大學(xué)生英語(yǔ)定冠詞句法語(yǔ)用接口習(xí)得研究[J].中國(guó)外語(yǔ)(2):47-53.
徐盛桓.2002.語(yǔ)義數(shù)量特征與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J].外語(yǔ)教學(xué)與研究(6):436-43.
楊佑文.2011.英語(yǔ)中動(dòng)結(jié)構(gòu):典型與非典型[J].解放軍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學(xué)報(bào)(4):18-31.
尹洪山.2012.從句法和語(yǔ)用界面看英語(yǔ)前置句式的習(xí)得[J].中國(guó)海洋大學(xué)學(xué)報(bào)(3):9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