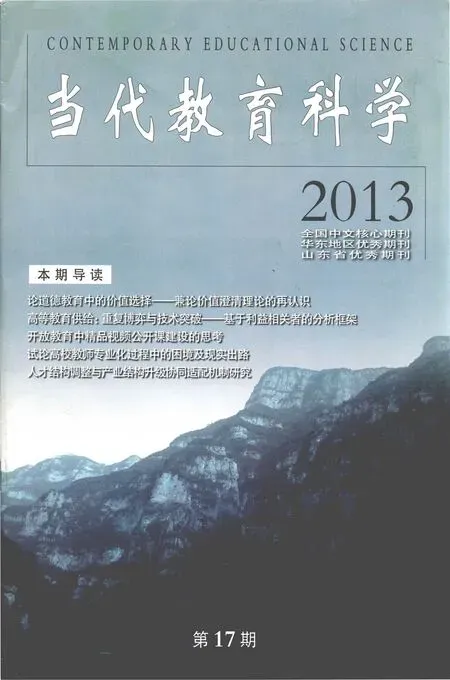高等教育供給:重復博弈與技術突破——基于利益相關者的分析框架
● 肖海燕
利益相關者研究日益受到重視,經歷了“利益相關者影響”、“利益相關者參與”和“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三個發展階段,并從企業管理的公司治理領域溢出,向政治學、社會學及管理學領域滲透,成為對制度或管理活動進行深層解析的重要理論工具。[1]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曼指出,利益相關者是那些能夠影響企業目標實現,或者能夠被企業實現目標的過程影響的任何人和群體。[2]由這個定義出發,學者們提出各自對高等教育事業利益相關者內涵的認識和理解,其籠統來看是基本類同的,為研究方便可以將其歸納為:作為權力性主體的政府、作為學術性權威主體的高校、作為權益性主體的公民(包括由公民組成的社會組織)等三個方面關鍵利益相關者。根據1977年Wharton大學應用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利益相關者分析框架可以運用于高等教育的三個不同層次上:第一層次是作為一種大學管理理論,第二個層次是應用于戰略管理過程,第三層次是作為利益相關者分析框架。[3]將利益相關者分析框架應用于高等教育供給研究能有效改善高等教育治理與激勵,減少機會主義行為和監督成本,減少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交易成本,同時也有利于利益相關者對自身利益的有效維護。本文嘗試從該視角分析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重復博弈的可能性、行為沖突、策略選擇等問題,為減少背叛、增強合作的技術突破提供方向。
一、利益相關者的重復博弈
地位不對稱、偏好分歧、策略的非穩定性等問題的長期存在,使得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之間圍繞高等教育供給問題不是展開簡單的單次博弈,而是持續的重復博弈。所謂重復博弈,是指“某些博弈多次(兩次以上,有限次或無限次)重復進行所構成的博弈過程”。[4]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之間存在沖突與合作,每個主體的利益不僅取決于自己采取的行動,還取決于其他人采取的行動。而每個利益相關者都期望在未來獲得較高的收益,當其獲得或失去某些利益后,訴求內容就會從一種形態轉化為另一種形態,從而產生新的利益訴求和期望;同時,利益相關者都趨于維持甚至擴大其既得利益,這種利益訴求及其交叉重疊增大了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分析,政府、高校、公民等多個利益主體往往能夠在重復博弈過程中多次進行策略選擇,從而使合作、背叛等策略選擇共同決定著高等教育供給模式、發展方向和水平層次。
(一)重復博弈的可能性
由于利益關系的牽制,各級政府可以對高校采取法律強制、政策引導、經濟支持、協同發展、監督管制等多種手段與措施,也會與社會組織一樣對高校人才培養、科研成果轉化、地方社會服務等具有直接經濟利益需求;而社會組織既是高校的直接競爭者,也會與高校結成伙伴關系。公民個體之間的互動及秩序構成了社會以及各種組織;高校、政府及各種社會組織可以集體的名義提出利益訴求,但集體訴求中的行動者也是個體,有可能因時間沖突、環境變更、技術制約、路徑優化、效價評估等因素轉變其利益訴求。因而利益相關者在人際互動關系中扮演的多重角色交叉與變更會誘使其在權衡利弊得失后隱藏部分利益訴求或者表現出非本位利益最大化訴求,而不是如在單次博弈中那樣選擇最適合于自身的方案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經過國家政策、法規的強制性引導與各方利益、關系、技術的誘致性牽引,多重利益訴求表現出動態、復雜的網絡互動關系,這種“角色多重性或角色重疊交集”現象為重復博弈提供了可能。[5]
(二)重復博弈的行為沖突
全體公民把對高等教育公共產品的需求委托給政府,政府又把部分高等教育服務活動委托給高校進行生產、管理,即公民委托政府提供的高等教育產品和服務是通過政府再次委托給高校這個平臺來生產實現的,這就產生了由全體公民到政府、由政府到高校的二環委托代理鏈。在“公民—政府—高校”委托代理鏈條中,對利益相關者重復博弈行為影響最突出的三個因素是“目標不一致”、“信息不對稱”、“權責不匹配”。
1.目標不一致
基于社會契約論的政府與公民委托代理理論認為,公民把屬于自己的一部分權利讓渡給政府,政府是公民基于信任基礎上委托的“利益代言人”,公民為其提供稅收上的支持,目的就是讓政府為其提供優質的高等教育產品和服務。[6]存在個體差異的公民對高等教育供給的數量、質量、結構、分布、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訴求也有差異,其根本目標是希望通過高等教育促進個人發展,從抽象層面看表現為對個人興趣愛好、智能個性發展、素質與潛能的培育等;從現實層面看,表現為通過教育手段換取更高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等利益回報。政府的目標追求就是持續獲得公民的信任和代理權。為實現目標,政府作為高等教育事業的決策者、投資者、管理者和監督者,通過立法、撥款、規劃、規制等重要手段來影響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從而滿足公民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所以作為委托人的政府希望代理人高校的策略和行為能滿足自己的目標:通過高等教育事業教化民眾、統一思想、培養人才、科技發展、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等,以實現政權維護與穩固、國家繁榮富強、社會民主和諧的目標。高校的三大職能是培養人才、科學研究、服務社會,其內在使命在于崇尚學術價值、提升文化品位、提高高校核心競爭力,外在使命在于適應社會需求、引領社會發展、提升高等教育的社會輻射力,因而其根本目標是追求真理與科學,崇尚學術自由與“象牙塔”式的圣潔,以傳承文明、創造文明。
2.信息不對稱
利益相關者中一些成員擁有其他成員無法擁有的信息造成的信息不對稱容易導致利益相關者行為沖突,如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在委托代理關系中,代理人屬于信息優勢的一方,委托人屬于信息劣勢的一方。因而作為終極代理人的高校相對于直接委托人政府、間接委托人公民,有著相對充分、完全的信息,清楚知道委托人的需求曲線,有關教育的政府政策、發展趨勢、教育質量、就業狀況、師資狀況等,而委托人卻并不清楚代理人的成本狀況、效率水平等,這樣就有利于代理人利用信息優勢,采取委托人政府、公民都無法觀察到的手段,獲得額外資源和收益。逆向選擇一般建立在委托代理關系之前,代理人利用信息優勢簽訂對自己有利的合同,而委托人則處于對己不利的選擇位置上,如代理人的選擇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等。因為信息不對稱造成委托人對代理人監督、懲罰、激勵等方面的乏力,使得其與代理人之間重復博弈行為沖突與矛盾的升級。
3.權責不匹配
高等教育供給利益相關者在重復博弈中的權利驅動與責任驅動并不一致。政府、高校、公民圍繞高等教育供給展開的重復博弈中,其責任驅動如圖1所示。公民必須要向“基于讓渡部分權利而產生的政府”納稅,期望政府提供高等教育公共產品,而政府受能力、精力限制,無法親自生產高等教育,就通過撥款的方式委托高校生產,因而高校承擔著實質意義上為公民提供高等教育產品和服務的責任。正如唐斯(Downs)在其經典著作《民主的一種經濟理論》中建立“理性無知”模型所分析的那樣,選民是否參加投票,主要取決參加投票的效益、成本以及其投票對公共選擇結果產生影響的可能性或影響程度。因而公民并不關心其所納稅的政府、政治家們是否真正的代表選民進行決策、制定政策等,其只關心從高校等公共組織所接受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水平、效率等是否滿足多數人的需求。根據尼斯坎南的壟斷官僚行為理論,高校是非營利性組織,其預算資金主要來源于主管人(政府和政治家們)的財政撥款,最終來源于稅收,而不是公共產出的銷售收入。因而高校并不真正關心其為公民提供的高等教育,而是追求預算最大化;其在信息上、制度上或技術上具有的相對于委托人的優勢更為其爭取預算最大化提供一個不容討價還價的壟斷地位。唐斯提出的理性政治人假說認為,政府(政黨)和政治家們,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主體,其最大的利益就是獲得公民信任,力爭在政治競選中當選以及再次當選。因而其并沒有動力去真正關心高校的生產效率、產品質量、生產成本等問題。高校作為“賣方”壟斷者是具體組織提供高等教育的唯一單位,政府則代表全體選民作為“買方”壟斷者是高校獲得預算撥款的唯一來源。這種雙邊壟斷關系所導致的信息不對稱、權力壟斷、權責不匹配將產生三個問題:公共產品的過度生產、資源配置缺乏效率、生產資源的過度投入而造成大量設備閑置。[7]
(三)重復博弈的策略選擇
從靜態、單次博弈的角度來看,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是簡單地背叛,這樣至少可以保證不會落到只有投入而無收益的境地;但是在重復博弈中,博弈被反復地進行,每個參與者都有機會采取“冷酷戰略”或“針鋒相對策略”去“懲罰”其他參與者的背叛行為,[8]此時利益相關者最佳策略依賴于對手可能的策略和對待背叛與合作的反應。因而重復博弈能在較大程度上約束背叛行為的出現,并可能導向一個較好的、合作的結果。[9]
二、高等教育供給問題的技術突破
高等教育供給的利益相關者實體地位的不對稱、目標偏好的分歧、策略選擇的非穩定等問題只要長期存在,各個主體之間就會有不間斷的利益訴求和博弈行為產生。因此,技術突破的關鍵是如何使重復博弈過程中不出現背叛行為,保障重復博弈過程中的持續均衡。對重復博弈研究較為突出的斯坦尼克(Steinacker)把影響利益相關者合作的因素歸納為合作的共同收益、偏好的多樣性、博弈者的地位和實力、博弈結構與參數等四個方面。[10]據此尋求技術突破的方向是:通過搭建目標利益的協調平臺,保障高等教育供給利益相關者之間合作的共同收益;通過制度環境建設使偏好分歧的表達更有效、信息溝通更順暢;通過探索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路徑,平衡博弈者的地位與實力;通過架構普及、開放、終身教育模式,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增強博弈結構與參數的穩定性。
(一)搭建目標利益協調平臺,保障合作共同收益
在重復博弈過程中,合作的共同收益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利益相關者之間通過“利益沖突-調整-階段性均衡-沖突-階段性均衡”進行重復博弈的前提就是合作的共同收益。如果沒有共同收益,或者說只有部分利益相關者的收益,那么合作就不可能達成。因而,只有充分尊重和考慮各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利益,實現利益主體之間某種相對的平衡,制度創新才能穩步有效地推進和實施。因此,為避免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造成利益總量的“漏損”,必須要求各利益相關者:(1)遵循利益均衡原則進行 “多次重復博弈”,促成各方達成合作,減少沖突;(2)完善內部利益協調機制和外部利益均衡機制,建立多方理性溝通機制,充分展現人性和生命特質;(3)建立超越具體利益的利益協調平臺,不能僅以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作為均衡各方得失的依據,避免因為政治、經濟的短期利益而被“工具化”。
(二)加強制度環境建設,拓寬偏好表達與信息溝通渠道
制度環境建設可以使利益相關者偏好分歧的表達更有效、信息溝通更順暢,弱化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委托代理風險。制度環境對公共治理制度安排影響的研究已經引起學者的重視,如諾斯將制度環境分為政治結構、產權結構和社會結構三個方面,政治結構是指一系列憲政安排,產權結構指確保私人產權體系得以界定和實現的規則體系,社會結構則是相對非正式的制度結構體系。[11]據此可以在制度環境建設方面:(1)協調政治權力結構安排與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的關系。社會選擇理論認為,達成社會最優解,實現公共治理制度創新并不是通過市場化來實現的,而是通過一系列反復的對話協商程序實現的。[12]因此,平等協商與對話使權力結構越開放、越多元,則利益相關者參與高等教育供給的制度空間越大,獲得的信息越充足,可供選擇的制度形式越多樣,制度成本越低。(2)重視產權結構調整對構建高等教育有效市場體系的作用,尤其要加強法律體系建設。眾多學者對我國公共治理制度安排的研究幾乎都認為我國有效法律制度的缺乏是公共治理制度創新失敗的重要原因。因此高等教育供給制度法制化中要明確劃分、規定各利益相關者權限和應盡義務,為各利益相關者相互監督、相互協調、行使和維護自己的權力提供法律依據。(3)借助社會結構資源拓寬利益訴求渠道。從社會資本論的視角來審視社會制度結構可以知道,其具體形態是在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制度實踐,是新制度安排的來源,[13]因而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可以借助社會制度結構安排的結構性社會資本與認知性社會資本,拓展利益相關者偏好表達與信息溝通渠道,增加參與程度,促進有效溝通與理解,確保規則和契約的有效執行。
(三)探索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平衡博弈地位與實力
國家權力、學術權威和社會利益相互融合的“公共理性”是促成制度變遷與創新的動力。美國學者伯頓·克拉克在《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1983)一書提出,高等教育發展主要受政府、學術權威及市場(本文理解為公民與社會組織)三種勢力的綜合影響,這三種勢力合成一個協調三角形。該三角架構思想為世界各國的研究者們參考、運用和推廣,并為高等教育供給制度創新路徑提供了一個思考框架:建立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高等教育供給體制,平衡博弈者的地位與實力。因而,在高等教育產品供給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結構中,參與主體間可以在服務功能上進行多種形式的替代,可以在投資主體、資金來源、組織形式、實現方式等方面合理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將各種主體所擁有的資源聚集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合力,共同參與高等教育產品多元化供給,以提高供給數量,優化供給水平。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模式中的參與主體通過協商、談判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這并不表明在共同治理綜合系統中,政府角色與其他利益相關者處于平分秋色的態勢。特別是在我國的市場運行機制還不夠成熟、市場操作規則還不夠完善、公民社會發育不充分的條件下,高等教育產品供給的多元主體合作治理結構不可能自發形成,因而在制度創新過程中,政府應當承擔網絡結構組織者的責任,并在網絡化合作治理結構的形成及其運作中居于“元治理”地位。[14]
(四)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增強博弈結構與參數的穩定性
對未來長遠利益估計與設想會驅動重復博弈各方選擇合作;但是,如果未來收益的判斷不樂觀,即貼現因子的影響力太小,博弈結構與參數的穩定性就會受到影響。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是增強未來收益貼現因子的重要舉措。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可以使權利和責任統一起來,公民的不僅要向政府納稅,同時也要監督政府,而不是只關心公共福利水平;政府不僅要向高等教育的具體組織與提供者撥款,同時也要負有績效評估與監督約束,而不只是選票最大化;高校不僅是向公眾提供高等教育產品與服務,更要關心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而不是只關心預算最大化。塞繆爾·亨廷頓指出,一個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他參與政治活動的可能就更大,政治問題的態度更堅定,也更有思想性,對社會文化和外交政策就會持更加“開明的”、“自由的”或者“靈活的”觀點。[15]因此,培養公民公共精神,除了要開放公共生活,鼓勵和推動公民積極參與公共生活實踐外,最重要的就是實施全方位的系統化的教育。這就需要架構普及、開放、終身教育體系,使利益相關者主體在高等教育事業發展中參與博弈的可能性、博弈行為的代表性、博弈結果的責任性等得以增強。
[1]韓鵬云,劉祖云.農村公共品供給制度:變遷、博弈及路徑創新——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分析框架[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2,(5):72.
[2]Freeman,Edward.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Boston:Pitman,1984:152.
[3]胡赤弟,田玉梅.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J].中國高教研究,2010,(6):15-17.
[4]趙小惠,孫林巖.寡占理論與重復博弈[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01,(3):42.
[5]張燚,黃婷,張銳.高校與利益相關者互動發展的關系模式研究[J].江蘇高教,2009,(1):61-62.
[6]米俊絨.論現代政府與公民關系的嬗變及其匡正[J].中國行政管理,2008,(5):59.
[7]郭小聰.政府經濟學 (第二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229.
[8]許源源.新區域主義視角下的市際重復博弈:問題與路向[J].中國行政管理,2012,(9):101.
[9]楊懋,祁守成.囚徒困境:從單次博弈到重復博弈[J].商業時代,2009,(2):14.
[10]Stephanie S.Post,Metropolitan Area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in Richard C.Feiock.Metropolitan governance:Conflict,Competition,and Cooperation.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04,66.
[11]North.Douglass C.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86.
[12]Hefetz.A andMildredWarner.Beyond theMarketvs.Planning Dichotomy:Understanding Privatization and its Reverse in US Cities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2007,(4):55-57.
[13]李文釗,蔡長昆.政治制度結構、社會資本與公共治理制度選擇[J].公共行政,2012,(11):6.
[14]姚德超,吳鋒.高等教育事業單位改革的若干問題[J].教育評論,2012,(2):25.
[15]塞繆爾·亨廷頓等.民主的危機[M].馬殿軍等譯.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