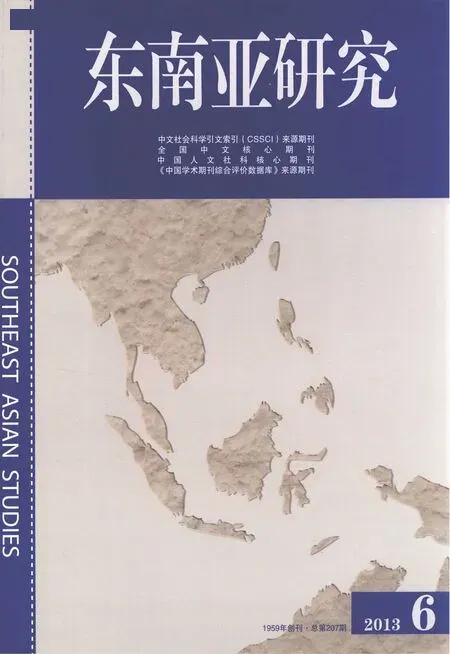美國的戰略東移對東亞地緣政治的影響
侯典芹
(煙臺大學人文學院 山東煙臺264005)
作為亞太地區的核心地帶,東亞的地緣特征非常獨特,海陸復合型的地理環境使之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長期處于重要位置。長期以來,美國作為地區乃至全球的戰略“平衡手”,一直慣于通過“均勢”戰略主導東亞事務。美國這次“重返亞太”,一方面加強并擴大在該地區的同盟關系,另一方面高調增兵,加大軍事上的“前沿威懾”。但是,后危機時代的美國必然要考慮經濟因素,因為東亞的中日韓三國都是美國的重要貿易伙伴,是美國商品出口的重要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政府主觀上可能并不希望東亞地區出現大的動蕩。但美國戰略東移勢必給東亞地緣政治帶來不穩定因素,加劇該地區的地緣競爭。2012年初,奧巴馬政府提出“戰略再平衡”,加快實施戰略東移,必將會給東亞地緣政治帶來許多不確定性。
一 美國的戰略“再平衡”—— “重返亞太”
冷戰結束后,在歐盟和北約不斷東擴的背景下,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空間受到很大的壓縮,已不再成為美國全球霸權的威脅。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調整發展戰略,經濟發展的步伐不斷加快,亞洲在新世紀開始顯現出超越歐洲的發展勢頭。不斷加強的多極化趨勢為美國戰略東移創造了大好時機。在2012年的香格里拉會議期間,美國防長帕內塔坦承,蘇聯解體后美國政府就曾要求將其戰略重點轉向太平洋地區[1]。
但是,海灣戰爭使美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中東,遲滯了美國的戰略東移計劃。克林頓上臺后,美國致力于在歐洲的“參與擴展”戰略,力爭使東歐國家的轉軌納入到美國的全球戰略中。美國為此介入波黑沖突,后來又發動了對南聯盟的戰爭。直到科索沃戰爭結束后,美國才得以再次實施戰略東移。美國當時計劃將其60%以上的核潛艇和航母群等戰略力量派往太平洋,并調整駐日、駐韓美軍,加強從關島到馬六甲海峽的美軍基地配備系統等[2]。但是,該計劃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就爆發了“9·11”事件。美國再次將戰略重心轉向中東,專注于“反恐”戰爭。奧巴馬上臺之時,正值美國深陷中東兩個反恐戰場難以自拔。更令奧巴馬政府感到雪上加霜的是,金融危機已經從美國向世界各地蔓延。全球性金融危機使美國的經濟和金融實力大大受損,奧巴馬政府被迫改弦更張,結束反恐戰爭,全力應對經濟危機。
奧巴馬上臺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美軍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退的具體計劃,并明確表示要把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以重振美國經濟,適應世界形勢的新變化。縱觀近年來美國政府的各種言行,以及美軍的戰略部署,其戰略東移已經開始全面實施。蔡鴻鵬把美國的戰略東移概括為三個主要方面,即“加強安全和穩定,擴大經濟機會,促進民主和人權”[3]。
政治上,美國在亞太地區極力拉攏日、韓、澳、菲、泰等盟國,加強同盟關系;同時還盡力把同盟關系推向印度、越南、新加坡等國,其目的在于對中國形成戰略“包圍”之勢,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霸權。在外交和安全領域,近年來美國積極參與東亞峰會,奧巴馬政府的高官們頻頻訪問亞太國家。同時美國一再宣稱是“太平洋國家”、 “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2011年10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奧巴馬在隨后的APEC 峰會上強調了這些觀點[4]。在2012年東亞峰會期間,連任后的奧巴馬總統首先訪問了泰國、緬甸和柬埔寨3 國,其目的是要給亞太地區留下這樣的印象:不管亞洲國家是否歡迎,現在美國騰出手到亞洲來了。
在軍事上,近年來美國始終保持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關注和投入,不斷強化軍事同盟。奧巴馬剛上臺,就宣布中東撤軍計劃,以減少軍費開支。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2009年聯邦預算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接近10%,而債務比重增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0%。自二戰結束以來,華盛頓從未面對過如此高的赤字[5]。為此,美國于2012年初公布了一個十年裁減軍費4870 億美元的計劃,并削減常備力量。不過美國同時高調宣布增兵亞太,國防部長多次出訪亞太。這表明,美國迫不及待地實施全球戰略重心東移。
與這種大戰略相配合的是軍事部署以及新的應對戰術。美國在實施這些部署時往往要尋找一些借口,以便師出有名。美國在東亞最常用的借口就是“中國威脅論”,近年來又借機提出“南海航行安全”。國務卿希拉里更是提出《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利用釣魚島爭端向東亞派出航母、核潛艇等戰略力量。早在2010年美國軍方就提出“空海一體戰”概念,并于次年8月正式組建辦公室,其主要目標是為了應對西太平洋戰區大國日益增強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美國按照這一作戰理念實施軍事部署,目的在于確保其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優勢,搶占未來軍事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內,美國已經把11 艘航母中的6 艘部署在以關島為中心的亞太地區,潛艇從282 艘增加到345 艘,目標是要把關島建成亞太地區的軍事投射中心[6]。
美國不僅在政治、安全、軍事等方面大力彰顯其在亞洲的影響力,而且還在亞洲展開經濟外交,爭奪亞太經濟一體化的主導權。面對亞太經濟的迅速增長和東亞地區日益密切的經貿合作,美國拋出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議(TPP)。最初,美國對TPP 協議并無太大興趣,后來不僅參與TPP談判,還邀請澳大利亞、秘魯等一同加入。到2009年11月,美國正式提出擴大TPP 計劃,開始重視該機制安排,力圖全方位主導TPP 談判。美國重視TPP 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東亞經濟一體化建設的刺激。隨著日益表現出的經濟快速增長的勢頭,亞太地區越來越成為吸引國際投資最具競爭力的地區。從地區經濟及結構來看,亞太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和分工日益增強,即使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仍表現出強大的經濟發展潛力和強勁的發展動力。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貿合作上升到一個新臺階。同時,中國與日、韓的貿易量迅速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著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的進程。事實上,奧巴馬第一任期的后期就已經將增加出口、增加就業,以應對金融危機作為重返亞太戰略的重要目標。有學者針對東亞峰會指出,“東亞一體化出現亞太趨勢”[7]。在世界“權力轉移”的進程中,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經濟力量中心的變遷。面對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為了防止被擠出亞太地區,美國“不能錯過亞太崛起這班車”[8]。美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經濟、貿易大國也因此加緊了從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轉身”。
2012年初,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戰略“再平衡”,加快實施戰略東移,力爭盡快“轉身”成為一個“太平洋國家”。
二 東亞在美國全球地緣戰略中的地位上升
東亞的地緣特點之一就是海陸復合型,它背靠歐亞大陸,面向太平洋。從地理范圍上講,東亞包括中、朝、韓、蒙、日等東北亞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美國作為該地區的域外國家,戰后一直通過美日、美韓、美菲同盟深深介入東亞事務,并成為東亞的主導力量。因此,美國也是東亞地緣政治中的重要力量。東亞地區既有多種利益的交織,又具有經濟和產業上的互補性。但由于歷史積怨太深,領土、領海爭端普遍存在,意識形態對立仍然非常明顯,冷戰陰影尚未完全消散,致使東亞成為全球地緣政治最為復雜的地區。
在兩極格局下,向來被美國決策者視為“邊緣地區”的東亞也被納入冷戰體系。東北亞曾是亞洲冷戰對峙的最前沿,朝鮮半島的冷戰甚至升級為熱戰。朝鮮戰爭使半島南北分裂,“三八線成了世界上最難以逾越的界線之一,無論是從意識形態上講,還是從政治、軍事或經濟意義上講”[9]。美國利用駐韓、日的軍隊和在兩國的軍事基地,以及臺灣與大陸的分立,對中國實施圍堵戰略。美國還利用東南亞防務集團介入印支地區,最終深陷越南戰爭。縱觀冷戰的幾十年,東亞一直是美國亞洲戰略的重點。美國利用其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的軍事同盟關系及在這些國家的駐軍,在東亞地區一直保持軍事上的優勢,形成戰略上的“遏制”態勢。越戰結束后,美國取消了在泰國的軍事基地,冷戰結束后又取消了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但美國一直利用軍事同盟關系保持對東亞地區的高度關注。
冷戰結束后,由于兩極格局瓦解,世界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組合,東亞地緣政治格局的外部環境發生巨變。中、美、俄、日等大國關系無論在全球意義上,還是在東亞區域關系上都經歷了戰略調整。美國追求“單極”霸權的努力在東亞地緣政治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它極力“遏制”俄羅斯和中國的發展,加大對朝鮮的軍事威懾。為此,美國不僅加強和改善了與日本的同盟關系,促動日本擴大所謂周邊事態的范圍,并通過戰區導彈防御系統計劃將東北亞納入戰略戰區范圍。同時,美國還通過美韓同盟關系主導朝鮮半島問題,借以制約中俄,限制日韓的作用。朝鮮半島問題是美國在東亞地區發揮主導作用的關鍵,因為“朝鮮半島問題是東北亞國際關系網的‘綱’,掌此綱而牽諸國,誰在朝鮮問題上居主導地位,誰就會在東北亞區域多邊關系中居主導地位”[10]。
冷戰結束后,時代主題發生轉換,國際關系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動機都發生變化。與冷戰時期相比,國家更多地受到經濟利益的驅動,商業利益成為國家利益的核心,安全利益成為國家生存的保障。國家的政治地位成為國家利益的根本保護,大小國家都在追求以經濟為主的實力的增長。不僅日韓成為美國的重要貿易伙伴,中國也逐漸成為美國商品的重要市場。進入新世紀,在中美貿易關系日益加強的形勢下,為解決雙方的爭端和貿易摩擦,中美戰略對話機制開始形成,并逐步向機制化方向發展。這表明,中國對美國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9·11”事件后,美國深陷“反恐戰爭”的漩渦,戰略重點在中東。這時美國需要東亞地區保持相對穩定的態勢。盡管發生第二次朝核危機,美國政府把朝鮮列為“無賴國家”,期間還不斷進行外交訛詐和軍事威懾,但在中國的積極斡旋下,中、美、俄、日共同致力于解決半島核危機。從2003年8月到2007年9月,六方會談共進行了六輪,雖未取得實質性成果,但該框架機制避免了危機的進一步升級,使東北亞地區保持了相對穩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整個西方經濟都開始呈現衰退趨勢。相比之下,亞洲經濟表現非凡。在東亞地區,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甚至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亮點。中國近年來把經濟外交擴展到對外關系的各個方面,成為促進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為加強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奠定了基礎。隨著中、印等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世界地緣經濟中心開始向亞洲轉移,世界政治中心也相應地從歐洲轉向亞洲。新加坡外交家馬凱碩甚至認為,中國崛起帶動整個亞洲地區經濟上的迅速繁榮,“重構世界秩序的時刻已經到來”[11]。
無論如何,亞洲經濟的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隨之而來的是亞洲地緣政治的日益突出。中國的崛起首先是在東亞地區的崛起。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西方世界的表現令東盟國家感到心寒。“美國在伸出援手前猶豫不決。日本也擁有刺激經濟復蘇的資源,卻沒有像中國那樣慷慨相助。”[12]相比之下,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獲得了東南亞國家的普遍認可。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建設在經歷10年談判后,終于在2010年正式啟動。與此同時,中國還主動參與地區安全合作,積極推動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中國在東亞乃至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不斷提高,使美國深感其在亞洲的主導權受到挑戰。在上個世紀末,為了實施“重返亞太”戰略,美國就開始在東亞散播“中國威脅論”,借機在中國周邊尋找機會和立足點。
總之,美國戰略東移是奧巴馬執政以來實施的重大對外戰略舉措之一,無論“重返亞太”,還是“戰略東移”,抑或“戰略再平衡”,都表明美國比以前更加重視東亞地區。東亞在美國的亞太戰略中始終占據重要地位。隨著亞洲的重要性日益超越歐洲,亞太地區將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而東亞將是整個亞太戰略的縮影。因此,隨著美國加快實施戰略東移,其在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存在將會更加突出。
三 美國戰略東移對東亞地緣政治的影響
長期以來,美國在東北亞戰略中充分利用該地區各國間根深蒂固的矛盾對立,廣泛實施“均勢”戰略,以充當該地區的“平衡手”。 “均勢”理論起源于歐洲,但美國的政治家在運用“均勢”外交方面毫不遜色。亨利·基辛格曾直言不諱地說:“美國必須保持它在亞洲的存在,它的地緣政治目標是必須繼續阻止亞洲結成一個不友好的集團(若是亞洲受到其中一個亞洲大國的影響,以上情形最有可能發生)。美國與亞洲的關系因此像是過去400年里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系。”[13]在東北亞,美國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對立,借助一方制約另一方,使彼此之間形成相互制衡關系。如中日關系,美國一方面需要利用日本來制衡中國,通過在日本的政治和軍事存在“遏制”中國;另一方面,美國不僅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需要中國的合作,而且還需要利用中國制約日本,阻止日本大力發展軍事力量,從而使美國在日駐軍長期化。再如韓日關系,雖然韓、日同為美國的重要盟友,但兩國的歷史積怨、領土爭端以及日本在教科書和靖國神社問題上的強硬立場時常引起韓國人對日本的反感。韓日矛盾也被美國所利用。正如美國著名地緣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所言,美日同盟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因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之一,有潛力發揮一流的政治影響。而韓國作為遠東地緣政治的支軸國家,對美國同樣重要。因為韓國同美國的密切聯系能夠使美國不在日本本土過多駐軍而保護日本,“從而使日本不會成為一個獨立和重要的軍事大國。”[14]可見,美國一直善于充當地區力量的平衡手,這或許就是摩根索所說的均勢“維持者”[15]。
美國之所以要實施戰略東移計劃是因為美國政府認為,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迅速,實力也隨之大增,特別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異常迅速。2001年中國的GDP 還僅僅是美國的1/8;2009年中國的GDP 就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2012年,中國GDP 更進一步上升到美國的1/2。隨著中國與韓國、東盟國家的經貿關系日益密切,其在東亞的影響力也隨之擴大。早在20 世紀末,布熱津斯基就已經把中國看作“一個主要的地緣戰略棋手”。“中國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地區大國。……中國的各種選擇已經開始影響亞洲的地緣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經濟發展勢頭必將使它有更強的物質實力和更大的雄心。”[16]所以,在美國智囊們看來,中國這個“最大的潛在威脅”越來越具有現實性。為了防止該地區的力量失衡狀態加劇,需要加強美國在亞太的力量,以實現該地區力量的“再平衡”。
雖然美國戰略東移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東亞地區的穩定,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但此舉勢必會產生許多不以美國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結果,畢竟最終結局將是多種力量相互博弈的結果。
首先,美國在政治上加強對東北亞的影響力,勢必會加劇東亞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美國要進一步加強與韓、日、菲等國的同盟關系,會使中美、俄美、朝美、中日、朝鮮半島南北關系等多種關系趨向緊張,最終導致地區緊張局勢加劇。
冷戰結束后,美國繼續保持與韓、日、菲的同盟關系,而且仍保持在日、韓兩國的駐軍,其東亞戰略中仍帶有濃厚的冷戰色彩。因此美國的戰略東移首先會導致朝鮮半島局勢更加緊張,加深朝韓、朝美之間的對立關系。同時,美韓、美日同盟關系的不斷加強也會加劇東北亞地緣關系的緊張。朝鮮半島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戰的產物,美國作為冷戰的主要角色,不僅是分裂的制造者,還是南、北分裂局面的維護者。在朝鮮看來,美國在朝鮮半島的駐軍以及美日、美韓同盟都是對朝鮮安全的巨大威脅,甚至是最大威脅。為了與美韓抗衡,朝鮮在經濟極端困難的形勢下仍保持一支強大軍隊。雖然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實力對比懸殊,朝鮮仍堅持優先發展核武器、生化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等威懾性武器,以便與美韓日進行對抗。美國進一步加強與韓、日的同盟關系,必然對朝鮮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引起朝鮮的過度反應。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加劇又勢必會引起相關大國之間的政治競爭,從而使東北亞地緣政治關系日趨緊張。
自20 世紀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初步成果時,美國就開始把中國看作“潛在對手”,并長期對中國采取“接觸+遏制”戰略。隨著中國經濟異常迅猛地增長,美國更加認為這種“潛在性”越來越具有“現實性”。甚至有美國智囊認為,“21 世紀的最大挑戰,就是要找到一種增強而不是削弱國際體系凝聚力的穩妥方式,將一個崛起的中國納入全球國家聯合體中來。”[17]可見,美國不希望崛起的中國挑戰自己的世界霸權,挑戰其主導的國際體系。為此,必須動用美國的各種資源和力量,加緊對中國的“遏制”,尤其是運用地緣關系制約中國的發展。近年來,美國除繼續保持和加強與韓、日的同盟關系外,還保持與臺灣的“準軍事同盟”關系,不斷向臺灣出售先進武器,維持兩岸的力量平衡。美國不僅支持“臺獨”活動,而且還把美日同盟關系擴大到臺灣。早在1997年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中,就暗含著將防御范圍擴展到臺灣的內容。2005年2月,美日安全會議首次明確表示,將臺海問題列入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在美國政府看來, “中國如何對待臺灣,不僅成為衡量中國在它崛起時如何處理各種爭議的一個重要尺度,而且將成為衡量美國——乃至世界——將如何應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的一個重要的尺度。”[18]可見,美國始終把臺灣當作制衡中國的重要手段。隨著美國戰略東移,臺灣的地位將會更加突出,臺灣問題仍將是美國制衡中國,維護其地區霸權的重要手段。
美國的戰略東移也極有可能加大日本與中、朝、韓等國的對立,甚至使有些矛盾激化。美日同盟關系作為冷戰的產物,在冷戰結束后曾一度處于“漂移”狀態。但隨著1995—1996年臺海危機的發生、“中國威脅論”的蔓延以及朝鮮半島局勢的發展,美日同盟關系開始得到加強,美日關系變得更加平等。這說明,美國冷戰時期在東亞所構筑的雙邊軍事同盟體系,尤其是美日同盟體系,仍然是美國對東亞政策之“錨”[19]。隨著美國的戰略東移,日本很可能乘機加快走向“正常國家”的步伐,尤其是擴大軍事行動的范圍。這勢必會給日中、日朝、日韓關系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日本與周邊國家普遍存在領土爭端,在歷史問題上一直缺乏坦誠態度。日本是“中國威脅論”的始作俑者,近年又蓄意挑起釣魚島爭端,引起東亞地區的緊張局勢。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強硬立場與美國長期的對華“遏制”戰略有密切聯系。日本右翼蓄意制造中日緊張關系,既符合美國的對華“遏制”戰略,又可借機加大走向“正常國家”的步伐。同時,日本還可以借此檢驗美國對日本的軍事保護,可以通過對華強硬態度滿足國內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的需要。冷戰結束后,日本的民族主義逐漸抬頭,其核心綱領之一就是使日本成為“普通國家”。日本的民族主義不僅在其國內有著深厚的認同基礎,而且國際局勢的變化也為其提供了發展空間。就美國而言,美日同盟是其亞太戰略最重要的基石,是“遏制”中俄的前沿陣地,是美國精心設計的“弧形島鏈”的重要環節。因此“對于日本國內的政治變化尤其是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呼聲,美國不能不予以認真考慮。與對韓國民族主義滿腹抱怨不同,美國對日本的民族主義可以說是連開綠燈”[20]。小泉內閣利用美國的“反恐戰爭”實現了日本海外派兵。安倍第一屆內閣將防衛廳改為防衛省,這次升格將進一步擴大日本的海外派兵范圍。有日本議員就擔心它使日本自衛隊海外派遣成為“基本任務”[21]。釣魚島爭端爆發后,日本前防衛相石破茂、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都曾表示要將日本自衛隊改為“國防軍”。日本國內在右傾化道路上越走越遠,其右翼勢力試圖通過增強軍事力量達到實現“政治大國”的目的,擴大其在亞洲乃至世界的話語權,其結果只會加重東亞緊張局勢。隨著美國戰略的東移,日本會更進一步通過與美國的合作加快走向“正常國家”。日本與鄰國間原有的矛盾,尤其是中日矛盾、朝日矛盾以及韓日矛盾,都會進一步加劇。這將不利于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不利于地區內的經濟合作和安全合作。
其次,美國戰略東移非常突出軍事因素,軍事“前沿威懾”的不斷加大將會加劇東北亞地區的軍備競賽,成為影響東亞地緣政治的極大隱患。
美國一直在東亞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存在,尤其集中在東北亞一帶。為了維持朝、韓之間的軍事力量平衡,美國一直在韓國駐軍,加上美國在日本的駐軍,共占美國在東亞駐軍75%以上的兵力。朝核危機爆發后,日本開始參與美國的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研制工作。小布什政府宣布推出《反導條約》后,美國開始在東北亞布置TMD。美日還計劃把TMD 擴展到臺灣,美國甚至推動韓國參與TMD。目前,美國正在東北亞地區積極推進TMD 的部署和完善。隨著TMD 的最終建成,美國將會在東北亞地區形成軍事戰略上的高壓態勢。這不僅會給朝鮮半島造成緊張局勢,而且會造成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緊張軍事對抗。
美國的這次戰略東移十分突出軍事戰略。近年來,美國除了繼續保持在韓、日的大量軍事基地和駐軍外,還有意將駐韓美軍基地向南遷移,強化駐日美軍的控制與指揮能力,在澳大利亞駐軍,強化關島海空兵力。此外,為了制約中國的發展,美國還加強與臺灣的“準軍事同盟”關系,向臺灣出售大量先進武器。天安艦事件以后,美國頻繁與韓國舉行軍事演習。2012年10月下旬,美國利用中日釣魚島爭端,把火力最強的攻擊型核潛艇“俄亥俄”號停靠韓國釜山港,兩個航母編隊出現在東海海域,有意威懾中國和朝鮮。對于至今仍缺乏一種多邊安全機制的東亞地區而言,地區緊張局勢會進一步加劇該地區內各國的“安全困境”,刺激它們加強軍備,從而引起地區軍備競賽升級,陷入更大的安全“困境”。
2012年6月,美國防部長帕內塔表示,將在2020年前向亞太地區轉移一批海軍戰艦,屆時將有60%的美國戰艦部署在太平洋。從而改變目前在太平洋與大西洋分別部署50%戰艦的格局,變為太平洋60%對大西洋40%[22]。帕內塔還表示,美國削減國防預算不會妨礙美國增加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部署。近年,美國還利用黃巖島事件與菲律賓搞軍事演習,大有重返菲律賓之勢。美國還試圖加強與越南的合作,使美軍進駐金蘭灣。中日釣魚島爭端發生后,美國派兩艘航母到達東海海域,進一步激化了日趨緊張的中日關系。繼去年美國火力最強的核潛艇“俄亥俄”號停靠韓國釜山,今年其“尼米茲”號航母又停靠釜山港。美國2020年完成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部署后,必然會對東北亞地區形成更加嚴重的“前沿威懾”,不僅會迫使中朝俄等國加強合作,而且會促使這三國加強軍備,以應對美國的軍事威懾。日本則會借機再次鼓噪“中國威脅論”,發展軍備。
可見,隨著美國戰略東移,美軍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將得到進一步加強。同時,美國還可以借機向東亞出售先進武器。這些都會加重東亞地區的“安全困境”,加劇地區內各國間的軍備競賽。
第三,美國的這次戰略東移也包含經濟因素,從近期來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美國需要加強與東北亞各國,尤其是中日韓等國的合作,擴大雙方貿易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的戰略東移有其“求穩”的一面。但從長遠來看,美國仍然要爭奪亞太地區的經濟主導權。這將會給東亞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帶來不確定因素。
對美國而言,近年來亞洲經濟的迅猛發展在安全上提出了挑戰,但在經濟上卻提供了機會。后危機時代的美國不僅要關注其在亞洲的主導權,而且必須考慮自身經濟的復蘇與發展。美國要擺脫金融危機的陰影,重塑美元的地位,需要借助中日韓等東亞國家的合作,需要東亞地區廣大的市場。目前,亞太地區成為世界經濟最富活力的地區,APEC 成員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54%,全球貿易量的40%,擁有27 億消費者。在東北亞地區,日本是發達的世界經濟大國,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先進技術;韓國在上世紀80 -90年代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現代工業的基礎已經形成,美韓自由貿易區在2012年初正式啟動;中國與美國都已經是對方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所以,中日韓都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出口市場。
美國的經濟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必然突出東亞的重要地位。近年來,美國拉攏東亞國家加入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議”,意在阻礙東亞合作的深入發展。美國戰略東移加劇了東亞區域合作的復雜性,中日韓自貿區進程面臨更多不明朗因素。在國際金融危機之下,貿易保護主義的“幽靈”重現,在2009年的APEC 會議上,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再次成為焦點話題,各成員國和地區對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長遠目標達成共識,著手推動APEC 逐步向FTAAP 過渡[23]。但華盛頓的智囊機構長期奉行雙邊主義,對FTAAP 不會有太大的興趣。簡而言之,美國經濟戰略東移將會給東亞的經濟合作帶來許多不確定因素。
總之,美國的戰略東移必然會給東亞地緣政治帶來不利影響。盡管美國戰略東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其地區主導權,主觀上有“求穩”的一面,但在客觀上可能會引起東亞地區各種復雜矛盾的激化,從而加劇東亞的地緣政治競爭。在經濟上,美國一方面仍然需要東北亞的廣闊市場,需要加強與東北亞各國的經貿合作。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不希望該地區出現因動亂而引發的經濟大倒退,因為這對美國經濟復蘇是非常不利的。另一方面,鑒于前一階段的戰略東移突出政治和軍事戰略,忽視經濟戰略,美國必然會在將來突出經濟戰略轉移,加緊爭奪亞太經濟一體化的主導權。這不僅會遲滯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而且會影響該地區的政治安全合作,從而加劇地緣政治競爭。
【注 釋】
[1]Jim Garamone,“Paetta Describes U.S.shift in Asia-Pacific”,Washington File,June,5,2012,p.3.
[2]林利民:《以攻為守:美國“戰略東移”的戰略本質評析》,《當代世界》2012年第9 期。
[3]蔡鴻鵬:《中國地緣政治環境變化及其影響》,《國際觀察》2011年第1 期。
[4]Staff Writer,“Obama to Emphasize U.S.Role Across the Pacific Rim”,Washington File,October 27,2011,p.3.
[5]〈美〉阿倫·弗里德伯格著,洪曼、張琳、王宇丹譯《中美亞洲大博弈》,新華出版社,2012年,第193 -194 頁。
[6]錢文榮:《奧巴馬政府的全球戰略重心東移》,《和平與發展》2011年第2 期。
[7]陸建人: 《東亞一體化出現亞太趨勢》,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 -11/29/c-124018589.htm.
[8]Joseph S.Nye.Jr.,“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1,p.3.
[9]〈美〉亨利·基辛格: 《美國的全球戰略》,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95 頁。
[10]劉清才、高科:《東北亞地緣政治與中國地緣戰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 頁。
[11](新加坡)馬凱碩著,劉春波、丁兆國譯《亞洲半球:勢不可當的全球權力轉移》,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第215 頁。
[12]同[11],第208 頁。
[13]〈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凌建平譯《美國的全球戰略》,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93 頁。
[14]〈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 頁。
[15]〈美〉漢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譯《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55 頁。
[16]同[14],第37 頁。
[17]〈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著,姚蕓竹譯《大博弈——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12年,第92 頁。
[18]〈美〉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著,曹洪祥譯《美國智庫眼中的中國崛起》,中國發展出版社,2012年,第217 頁。
[19]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Chasing the Sun:Rethinking East Asian Policy,New York:A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2006,p.84.
[20]趙立新:《東北亞區域合作的深層障礙——中韓日民族主義訴求及其影響》, 《東北亞論壇》2011年第3 期。
[21]劉壯:《日本防衛廳下月成省,將導致自衛隊性質變化》,人民網/軍事,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7/52987/5174744.html,2006年12月15日。
[22]王忠會:《美國防長稱將在2020年前把60%戰艦部署到太平洋》,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6 -02/3933841.shtml,2012年6月2日。
[23]馬濤:《大力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中國改革報》2009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