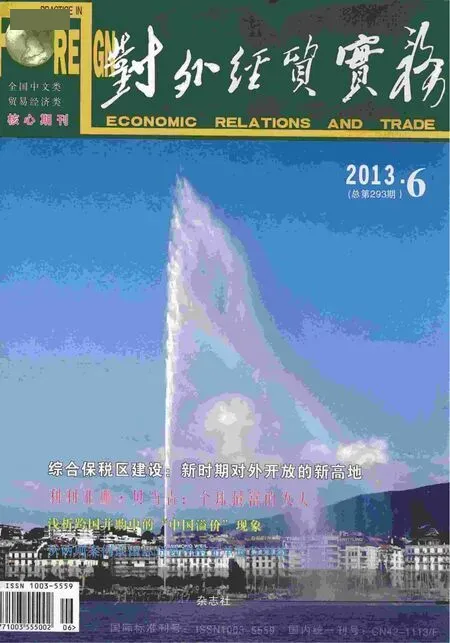中國稀土的國際糾結與管理新模式
■周俊 武漢紡織大學
2010年之前,中國以稀土資源占全球總儲量的23%,承擔著全球90%左右的稀土供給。中國稀土長期廉價、充足的供應全球市場,尤其是歐美日的高科技產業,使它們習慣了這種資源帶來的巨大收益,而中國卻要承受災難性的環境問題。當中國慢慢收緊過度松馳的韁繩,開始對稀土生產和出口加強管理時,歐美日卻拿中國的入世承諾說事,無端指責中國的稀土管理政策違背了WTO原則,左右了稀土的國際市場及價格變動。為什么西方列強認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左右全球的原油市場,中國就不能根據市場變化控制稀土的生產和出口?本文擬通過比較,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一、中國難以復制OPEC模式管理稀土資源
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兩者都是現代工業不可缺少的資源,但國際市場的地位卻迥然不同。在現代工業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原油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要能源,雖然現在各國都在大力發展替代能源,但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原油仍會扮演工業“血液”的角色。正是基于原油現階段的不可替代性,各大原油消費國也樂于看到OPEC的存在。因為,正是OPEC穩定了原油市場,當世界經濟蕭條時,OPEC通過壓縮產量來保證油格的穩定;當世界經濟步入高速發展時,OPEC通過擴張產能來保證市場供應,使原油價格不至于大幅漲升。
如果說原油是工業生產的基礎,那么稀土就代表了工業的未來。稀土資源全球已探明儲量不到一億噸,是既稀缺又重要的戰略性資源。在西方經濟整體持續低迷的狀況下,歐美日等寄望通過技術優勢,使經濟走出危機的泥潭,走向全面復蘇,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必然的選擇。而稀土功能材料在永磁、發光、催化、儲氫、拋光、乃至軍事高科技等眾多高新領域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是未來新材料領域的明星,是新能源、節能環保、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維生素”。有鑒于稀土材料的重要性,歐美日一方面大肆作戰略性囤積,一方面與中國對簿于WTO,希望通過WTO規則迫使中國繼續向國際市場提供廉價稀土材料。
(一)OPEC是多國合作的產物,中國稀土管理難以引入外力
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成立的宗旨是通過共同行動反對西方國家對產油國的剝削和掠奪,保護本國資源,維護自身利益。現有的11個成員國,原油儲量占世界上已探明儲量的78%,并為國際市場提供占總消費量大約40%的原油。OPEC通過在成員國內部分配配額的方式,控制原油產量和影響國際市場的油價;通過保持原油市場的繁榮,致力于向消費者提供價格合理的穩定供應,來兼顧生產國與消費國的雙方利益,避免引發紛爭和消費者國的不滿。
中國對稀土的管理卻難以通過國際合作來完成。首先,中,俄,澳,美等稀土儲量靠前的國家中,只有中國擁有完整的產業鏈條和大批量生產的能力,其它國家基本沒有開采本國的稀土資源;其次,中國過去罔顧環境的低成本開采模式迫使其它國家放棄了對本國稀土的開采,轉而使用中國稀土原料。所以,在稀土開采和早期提煉環節中,中國在世界上找不到合作者。當中國開始放棄原始的開采方式,加強管理和調控時,只能以一已之力,抗衡歐美日等主要使用國了。
(二)OPEC通過與非成員國合作定價,共同維護國際原油市場的健康發展
OPEC左右著全球原油市場,也經常被批評缺乏透明度。為了保障成員國的利益,OPEC始終堅持認為原油市場供給是充足的,提高產量只能是特定條件下的措施。然而,它的這些不作為,卻很少引來消費國的集中攻訐,其中訣竅就是國際原油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國際市場的原油價格主要由OPEC官方價格、非OPEC官方價格、現貨市場價格、期貨市場價格和易貨貿易價格等共同決定,在價格形成過程中,OPEC官方價格只是眾多因素中的一種,所以,能夠在市場中達成平衡。
反觀稀土的國際市場價格,中國作為最大的生產國和供應國,不能通過價格手段有效調節供需,在價格形成中無能不力。當我國開始通過行政手段調控稀土生產和出口時,使稀土的價值回歸正常時,飆漲的價格讓習慣于廉價使用的西方各國怨聲頻傳,也使中國陷入WTO規則的紛爭中。
(三)中國稀土缺乏OPEC的國際化
OPEC雖然擁有占絕對優勢的原油儲量,但OPEC各成員國的原油從勘探、開采、冶煉、運輸到銷售的各個環節,基本都是國際參與,眾多西方大牌石油公司都是其中的參與者和獲利者。換句話說,OPEC是一個限制較少,進入門檻不高的公開市場。
中國稀土經過了多年的無序開采后,國家開始通過取消出口退稅、征收出口稅、出口配額等措施控制稀土的開采和出口,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我國稀土出口的亂象。2007年12月1日施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07年修訂)》將稀土資源列入禁止外商投資產業目錄,雖然能有效保護我國的稀土資源,卻也在一定程度上關上了國際合作的大門,使渴望參與中國稀土開發和生產的國際企業,轉而成為攻擊中國政策的急先鋒。
二、中國稀土生產和出口中存在的問題
(一)短視和急功近利使稀土資源地飽嘗惡果
早在2008年,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多部委就聯合發文,規范稀土的生產秩序。然而在地方GDP增長和部門利益的驅動下,違規或越權審批稀土項目、無證開采、作坊式開采、超強度開采等現象多年來一直禁而不止,國家政策難以全面實施。加之許多稀土產區基本分布在經濟結構較為單一的縣市,利用稀土構建支撐區域財稅的系統產業,成為了這些地區走向小康的不二選擇。
由于缺乏技術和資金的支持,在稀土開采、選冶、分離等多個環節,落后甚至比較原始的工藝被廣泛使用,導致礦山被破壞性開發,地表植被被嚴重損毀,由此帶來的水土流失和土壤污染,使得農作物減產甚至絕收,給農業生產以毀滅性打擊。部分產區對稀土資源的過度開采,使礦區資源加速衰減和枯竭,并造成山體滑坡、河道堵塞、環境污染等事故和災難,給稀土產區的公眾生活、健康和生態環境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2012年6月2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表的《中國的稀土狀況與政策》白皮書,也證明了對稀土資源的盲目過量開采已經影響到稀土資源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缺乏具有采研產銷綜合實力的龍頭企業引導產業合理發展
稀土資源是一種由17種元索組成的金屬大家族,有輕重稀土之分。我國重稀土主要分布在南方的江西、廣東、福建、湖北和四川等省份,其中江西贛州被稱為“世界鎢都”。重稀土品種多,分布廣,單體礦山儲量有限,礦產地大多位于邊遠山區;而輕稀土則相對集中,內蒙古包頭的白云鄂博礦是世界最大的輕稀土礦區。由于稀土資源的自有特性和之前的管理松懈,我國稀土從開采到冶煉分離的全產業鏈中企業隸屬關系復雜,涉及中央和地方眾多管理部門。由于條塊分割和多頭管理,南方稀土產業基本以中小企業為主;北方雖然有包鋼稀土這樣的大型企業,但也處于中小企業的包圍之中。稀土“小、散、低、亂”的生產格局導致市場供求波動、監控管理困難、價格嚴重背離價值且在國際市場受制于人、國內資源浪費和生態污染等亂象。造成這些惡果的根源是全行業缺乏幾個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在稀土新材料開發和終端應用技術方面,也沒有具有超前研發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龍頭企業。雖然在國家政策不斷收緊的前提下,中國鋁業、五礦集團等央企和廣晟有色,中科三環等上市公司紛紛參與稀土開采,但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相關政策,也難以起到應用的作用。
(三)稀土出口管理政策粗放,配套法律法規缺失
為了保護我國日漸式微的稀土資源,國家加強了對稀土產品的出口管理,取消了出口退稅,設置了出口稅和出口配額,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我國稀土產品出口的混亂局面,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現行的出口管理措施依然存在很多問題:首先,稀土產品的稅則歸類設置和稅率級差梯度難以監管品種繁多的稀土出口產品。如我國出口的上百種主要稀土產品中,僅有45個10位稅號的稀土產品涉及配額許可證管理并征收15-25%的出口關稅,其它稅號的商品則不涉及。其次,海關監管查驗手段單一,難以管控嚴重的稀土走私。稀土產品品種多、體積小、價值高、物理外觀難以分辨,雖然中國海關將稀土列為重點打私項目,但稀土產品的出口走私現象仍然猖獗。2006年至2008年,國外海關統計的從中國進口稀土量,比中國海關統計的出口量分別高出35%、59%和36%,2011年更是高出1.2倍。第三,配額管理措施不到位且存在非法買賣,配額管理沒有取到應用的作用。目前我國稀土出口配額簡單地分為稀土氧化物、稀土鹽類和稀土金屬三種,不能涵蓋各種用途的稀土資源出口管理。同時,出口配額的非法買賣不僅擾亂了稀土的正常出口秩序,也折射出目前配額管理和分配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
三、建立我國稀土生產和出口管理新模式的思考
(一)充分利用WTO平臺,與消費國協商解決相關問題
稀土資源出口管理是中國稀土產業可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既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利益,又牽涉資源安全和生態環境。對于歐盟、美國、日本等稀土消費“大戶”無視稀土產業損毀性開采給中國國內帶來的生態災害,無理指責中國限制稀土出口政策,甚至提交WTO仲裁的做法,中國要充分利用WTO的規則,予以堅決的回擊。其一,根據《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20條、第21條“安全例外”的規定,在特定安全利益受到威脅的情況下,WTO成員國有權暫時停止施行WTO特定義務,對這些資源的生產、銷售、出口采取相應的出口管制和出口限制等規定,中國管理稀土出口合情合理。其二,WTO認為,保護可用盡自然資源有關措施在與限制國內生產或消費一同實施時,不違反WTO?規則。所以,我國應將限制國內生產和使用、打擊非法開采和非法走私等情況通報WTO和相應國家。其三,積極與稀土消費國協商,將自主配額轉變為協商配額,并要求消費國協助中國打擊稀土產品的非法走私活動,使稀土貿易回歸正常渠道。
(二)建立稀土資源出口的全產業鏈管理體系
我國應對稀土資源實施戰略性保護,一方面充分利用資源優勢,保護生態環境,合理開采;另一方面適度控制輸出,保護國家經濟和資源安全。為此,在稀土產業備受國內外關注的情況下,必須做到:第一,將稀土產業整體納入國家的監管之下,稀土礦產資源的勘探、開采必須經由國家部委和省級人民政府批準;選冶、分離等生產過程也要在技術、安監、環保等部門的監督之下進行。要有切實可行的稀土產地山體、植被恢復系統。第二,將稀土產品全部納入出口管理清單。稀土資源及其產品范圍廣、品類多,需要對各個稀土元素及產品種類進行細致分析,根據既往開采、應用、資源儲量和現在礦體礦山的實際情況分類管理并適時更新管理清單。第三,綜合運用多種出口管理手段,繼續控制出口總量并通過出口經營登記、稀土產品出口許可證、出口稅和出口配額等形式管理稀土出口。
(三)加快產業整合,加大科研投入,多路徑保護我國的稀土資源
中國參與國際市場程度日益深化。在這一過程中,兼顧國際市場和國內就業、生態保護、產業結構調整等多重目標,難度越來越大。要突破當前的稀土困局,必須從以下方面全面權衡和考慮:首先,加快產業整合,組建多個綜合實力占優的專業化公司。目前,北方稀土已確定由包鋼稀土領軍完成,而南方稀土分布多個省份,涉及地方國企、民營企業、央企和上市公司等不同主體的企業,情況比較復雜,需要國家強力部門介入(如國家發改委、國土部等)、主導稀土產業的整合,組建幾個集開采、生產、科研和貿易為一體的大型專業化礦業集團。其次,大幅增加科研投入,集中科技力量,攻關核心技術,研發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專利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迅速改變我國只能出口稀土初、中級產品而大量進口稀土高端產品的局面。第三,充分利用國家政策,提高行業準入門檻。各稀土產地政府部門應該依據2011年5月10日國務院《關于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2012年7月26日工信部《稀土行業準入條件》和商務部對外貿易司《2006年稀土出口企業資質標準和申報程序》(征求意見稿)的規定,嚴禁搬山式開采,淘汰土法選冶工藝,嚴格環保門檻,阻止資金、技術流向不達標的稀土企業,完善企業的環保配套措施。第四,構建全國性稀土開采、生產、貿易和科研信息系統,廣泛收集、研究、交流國內外各類信息,為管理部門決策提供準確依據,為企業傳遞開采、生產、研發和貿易等綜合信息。
(四)建立國家部委和地方省市政府共同管理的聯動機制
國家和省市政府部門在合理運用法律、行政和經濟手段管理稀土產業的同時,也要面向企業做好協調和服務工作。首先,應該在國家層面成立全國性的稀土產業協調部門,該部門有責有權,可以全面協調國家發改委,國土部,環境部等部委和內蒙古、江西、廣東等省份,強化聯合管理工作。第二,加強國家稀土辦和稀土行業協會的職能,使其在資源管理、企業審批、制訂出口最低限價等方面發揮強有力的作用。第三,加強央企和稀土產地的合作,充分利用它們的資金、技術和企業管理經驗,加強稀土生產鏈條的縱向和橫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