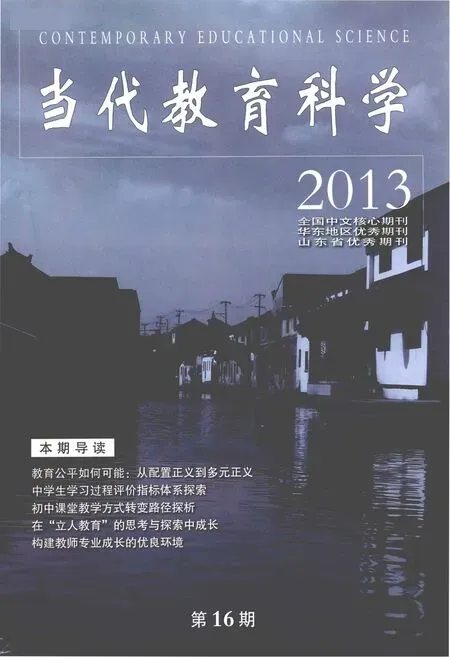“教學超速”的危害及其轉變*
●羅祖兵 王艷香
在當今這個瞬息萬變的信息化社會中,生活節奏越來越急促,人們的心態也變得越來越浮躁、越來越急功近利。“全球重大事件發生的節奏和頻率加快,社會中各種時尚來去匆匆。”[1]這種現象在教育中表現得也相當明顯:“現在我們的教育都在 ‘搶跑’——幼兒教育小學化,小學教育中學化,中學教育大學化……”[2]整個教育界都在搶跑,在具體的課堂教學中也是如此,本文用“教學超速”一詞概括此現象。所謂“教學超速”,是指為了快速實現教學目標,使用“超前”的教學內容,并在教學過程中過于追趕進度而忽視學生身心發展規律的現象。
一、“教學超速”的表征
中小學教學中,“教學超速” 主要是從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過程等幾方面體現的:
(一)重結果的教學目標
所謂重結果的教學目標,是指那種以數量的方式來精確度量的教學目標,具體而言主要是指知識、技能類目標。其實,教學目標不僅可以是結果性的,也可以是過程性的,還可以是情感性的。在現有考試制度的指引下,考試成績事實上成了評價教學好壞的唯一依據。這就指引著教師們在設定教學目標時,純為“分數”而設。試卷考什么,教師就預設教什么,無形之中,加強了“分數”(結果)在教學中的地位,而過程性目標被大打折扣,情感性目標更是無地可容。省略了“過程”,教學自然就“超速”了。正如杜威所言,“過高的期望程序的一致和過度要求迅速取得表面的結果是學校虛心態度所要對付的敵人。”[3]為了取得好成績,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甚至不擇手段,不惜犧牲學生的長遠發展來取得眼前的“分數”。最終“成績”確實是提上去了,于教師而言是“好”的結果,但對于學生的發展而言未必如此。此外,重結果的教學目標還體現為把“三維目標”都轉化為知識目標。轉化是這樣實現的:把過程目標、情感目標轉化為關于過程和情感知識的目標。表面上看,三維目標都有,實際上的三維目標都是一類,即知識目標。這樣,掌握知識成了教學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任務。因為較之于三維目標中的其他兩維目標,知識目標可操作性強、利于量化,更為重要的是,它易于速見成效! “在知識導向型目標下,學習的目標指向性就是獲取更多、更難、更高深的知識,因此學生的學習目標是尋找正確的答案,教師沒有時間讓學生自己去探究。”[4]由于實際上要實現的教學目標就是知識目標,所以教師僅憑“灌輸”就可以獲得滿意的結果,過程性、情感性的目標似乎成了沒有必要的存在。如此,在重結果的教學目標的指引下,教學無形之中就“超速”了。
(二)超前的教學內容
所謂超前的教學內容,是指教學內容遠遠超過了學生的實際經驗和接受能力,導致對其而言,所學內容偏難而顯得“超前”。主要表現為以下兩點:首先,教學內容本身偏難。教學內容偏難,主要是因為里面絕大多數內容脫離學生的需求與已有經驗。“學校的教材和學生的需求和目的脫離,僅僅變成供人記憶、在需要時背出來的東西。”[5]中小學一些計算公式與定理便是如此,許多內容其實都是學生無法理解的,但即使是采用死記硬背的方法,也得“掌握”。也許學生當下可以倒背如流,可是對于他們而言那只是一個陌生的符號,與他們的已有經驗沒有任何關系,所以結果是記得快,忘記得更快。研究者指出,“西方人一般是從‘貓’‘狗’之類的詞開始他們的學習……中國人采取的方法是讓八九歲的孩子讀一本有深奧倫理觀點的書,由此開始學習的生涯。”[6]可以看出,這樣的學習內容明顯超越了學生實際經驗和可接受水平,對于該階段的學生而言偏難而“超前”了。其次,表現為在教學內容本身難度過高的基礎上,教師在教學中還會進一步提升教學內容的難度。在激烈的考試競爭下,部分教師為了使得自己的學生比別班略勝一籌,會有意識地提高教學內容的難度:一方面把在當前學習中涉及到的一些在后續學習中要遇到的問題提前教給學生;另一方面,過于拔高當前內容的掌握標準。但此時教師犯了一個錯誤:忽視學生的實際需求與接受水平。“成人的材料是學生的材料的可能性,而不是學生材料的現狀。”[7]所以,“教師不應該注意教材本身,而應注意教材和學生當前的需要和能力之間的相互作用。”[8]要知道,對教學內容采取如此地“超前”處理,學生是難以接受的。
(三)急促的教學過程
急促的教學過程是“教學超速”最核心的表現,是指為了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完成教學任務,教學過程急促,導致學生自主學習這一過程被僭越的現象。“結果(表面的答案或解決方法)也許可以加速,但是過程不能強制。”[9]急促的教學過程具體體現為:其一,調快教學節奏。為趕進度,部分教師在教學中急于調快教學節奏,使得整個課堂過于緊張。但是教師關注的僅是“教節奏”,而忽視了“學節奏”。在過于緊繃的教學中,容易使得“學節奏”與“教節奏”失衡,導致學生跟不上教師的進度。“教節奏理當因應學節奏,并根據學生的身心發展節奏來確立自己和調適自己,形成科學的教節奏。”[10]其二,替代學生學習。為了最佳利用課堂45 分鐘,教師不愿意把時間留給學生“浪費”,而是在教學中直接“替代”學生學習:課堂提問時,學生若不會,便直接呈現答案,替代學生思考;教學內容中出現需要學生親自實踐并感悟時,直接告訴學生道理,替代學生體驗;課堂教學中,充分利用每一分鐘進行“灌輸”,學生只負責“靜聽”,替代學生表達等等。但“……‘學’是學生自己獨立自主的活動,教師包辦代替不了。”[11]其三,有意忽視課堂生成。中小學生的思維其實很活躍,很容易出現課堂生成,但是現實是隨著年級的升高課堂幾近“萬馬齊喑”。其中主要原因在于課堂生成問題與考試內容不成“正相關”,而且處理課堂生成問題耗時耗力,影響教學進度,教師認為不劃算。在急促的教學過程中,容不得這樣的“揮霍”,于是教師有意忽視甚至扼殺之。
以上三方面的“教學超速”表征是密切聯系的,重結果的教學目標是問題的根源;超前的教學內容是條件與保障,急促的教學過程則是手段與方法。
二、“教學超速”的危害
“教學超速”違背了教育的基本規律,給學生帶來了諸多危害。一方面,“教學超速”是對學生生理以及心理的巨大的摧殘。中小學生正處于長身體的時期,若長期處于這種高度緊張的“超速”教學中,易造成身體發育不健全。此外,可能因為趕不上教學進度,易產生恐慌、焦慮、恐懼等消極心理,滋生挫敗感、喪失自我認同感,久而久之,對學習失去興趣而厭學、逃學。另一方面,“教學超速”也許能獲得眼前的“分數”,但對學生的長遠發展存在莫大的隱患。
(一)阻礙了學生的深度發展
學生作為一個“人”的存在,“教學超速”最直接的危害是阻礙了其深度發展。所謂深度發展,是指相對于僅掌握符號性知識的淺層發展而言,獲得一種在情感、態度、思想、價值觀等方面更加豐富而深層次的發展。但是在整個“超速”的教學體系中,更多的是淺層次的發展,學生的深度發展被嚴重地邊緣化。具體體現在:其一,過于重結果與速度,深度發展無從談起。在此,獲得最終的結果是師生的共同追求,或者說考試獲得“高分”是教學的終極目標。在這樣的教學體系下,容易陷入二元對立的局面,即重結果,忽視過程。導致部分教師走入極端:只要有利于提高本班成績,可以不管過程,不擇手段,甚至犧牲學生的健康發展!這樣學生的情感、態度價值觀等深度發展的需求幾乎被漠視了,而且在急促的教學過程中,根本就沒任何利于學生深度發展的空間與平臺。其二,狹隘的知識觀,使得知識的深層價值被扭曲。郭元祥認為,知識有三層內在結構:“符號表征”、“邏輯形式”、“意義”。其中知識的“意義”為:“知識蘊含著對人的思想、情感、價值觀乃至整個精神世界具有啟迪作用的普適性的或‘假定性的’意義。”[12]而在“教學超速”中,更多地是追求表層的符號教學,“符號表征,被看作是知識的全部和教學的唯一。”[13]知識對人發展該有的深層意義被埋沒,知識被狹隘化了,導致只見知識不見人,人成了知識的奴隸。
(二)抑制了獨立學習能力的形成
學生作為一個學習者,“教學超速”抑制了其獨立學習能力的形成。為何會造成這樣的后果?第一,獨立學習的時間無從保證。為了趕教學進度,課堂節奏急促,可以說課堂大部分時間都被教師所“霸占”,學生幾乎沒有多少獨立學習時間,學習權利被剝奪。教師應該明白:“學校和教師的責任并不在于“上好課”,而在于:實現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權,給學生提供挑戰高水準學習的機會。”[14]“教學超速”中,連最基本的獨立學習時間都無法保障,那么學習能力的形成只能是空談。第二,獨立學習的空間喪失。教師習慣將教學內容進行超前地精細加工、而且在課上詳細地講解。如此,學生獨立學習的空間就不存在了,因為他們幾乎可以不費什么功夫就能掌握。這就剝奪了學生自己探索加工的活動過程,而這一過程恰恰是學生學習能力養成非常重要的環節,卻讓教師越俎代庖了。教師完全忽略了學生身心發展機制和教導機制,“教導只是引起、促進學生能動而有效地活動的條件,但它不能占用、代替學生的能動活動過程本身,因為學生的身心發展是通過自身能動活動過程完成的,學習活動過程必須由學生去經歷和完成,任何人不能代替。”[15]第三,獨立學習的質量無法保障。在課堂上,即使學生會有少量的獨立學習機會,但是那也是在教師嚴格控制范圍內的,他們只需要認真地按照教師的要求去做就可以解決問題。因為學生并沒有真正主觀能動地參與學習活動,這就導致在質量上無從保障學生獨立學習能力的形成。總之,“教學超速”從學習時間、空間以及質量上抑制了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的獲得。獨立學習能力對一個人的一生發展具有長遠作用,在倡導終身學習的今天,一個沒有學習能力的人很難立足于當今高速發展的社會!
(三)擱置了學生社會性的發展
學生作為一個社會個體,“教學超速”擱置了其社會性的發展。其一,脫離實際生活經驗的教學內容,使學生的社會性發展缺乏基本條件。社會發展日新月異,而我們的教科書內容要么陳舊要么深奧難懂,遠遠脫離生活實際。學生把大量寶貴時間都花在了學習這些枯燥乏味、缺乏社會現實感的教學內容中,而同時本應發展起來的其他方面的能力,如社會能力卻被擱置了。最終學生走入社會時,發現自己所學與社會需求大相徑庭,易產生一種“徒勞無功”、“英雄無用武之地”、被“欺騙”之感。學校培養的所謂“高才生”,為數不少是不能較好適應社會、片面發展的“高材生”亦或是“庸才”。其二,單一的學習活動形式限制了學生社會性發展的基本機制。為了實現學生社會性的發展,必須有與之相應的具體機制保證其運作。泰勒提到,“為了實現既定目標,學生必須有這種經驗:它提供機會讓學生去實踐目標所隱含的行為。”[16]言下之意即是一定的活動發展一定的素質,不同的素質發展與不同的經驗存在相關對應性。在“教學超速”中,學生學習活動主要是單一的聽講、回答問題、做練習等。而社會性的發展是需要其他與之對應的活動才能進行的,例如交往的活動、社會實踐的活動、操作的活動、反思的活動等等,但是在當今的課堂中顯然鳳毛麟角,那么學生社會性發展的缺失定是必然。
三、“教學超速”轉變的幾點建議
馬克思基本原理告訴我們應該按客觀規律辦事。在教育教學中,就是要遵守教育教學的基本規律,尊重學生身心發展規律,教學應循序漸進,張弛有度。
(一)建立“發展為本”的教學評價體系
造成中小學“教學超速”,罪魁禍首是“以分數定成敗”的片面教學評價制度。為了抵制“教學超速”,亟需改變這種評價方式,建立“發展為本”的教學評價體系。所謂以“發展為本”的教學評價體系,是相對于僅注重結果的靜態評價而言,轉向以一種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評價教學體系,更加尊重師生主體的成長過程性表現,是一種發展性的評價。其一,改革考試評價制度。改變把統一考試成績作為學生升學、教師績效考核和學校教育教學水平的唯一標準的考試制度,實行綜合性的評價機制。小升初、中考和高考等考試成績只是學生升學的依據之一,還應加強對學生其他方面進行考核,如品質、實際動手能力、心理素質、交流能力等等。另外,平時的過程性表現也應納入評價體系之中。這就緩解了師生應付最終考試的教學壓力,導向性地使得教師在平時的課堂中放慢教學的腳步,更加重視發展學生多方面的能力。其二,轉變“教”的評價方式。改變以“成績”優劣來評定教師教育教學水平,而是從“發展”角度進行評價。可以通過推門聽課、上公開課、課例研究等形式對教師教學進行評價。評價的主要依據為:教學理念是否“以學生為本”;教學內容是否符合學生接受水平;教學過程是否保障每個學生的學習權、學生是否真正參與學習等等。其三,豐富“學”的評價標準。按照加德納的多元智能理論,評價學生時應當更關注學生的發展過程,評價標準應多元化與差異化。所以,不僅要評價學生知識、技能與智力等認知方面的發展,還應該評價學生情感、態度、價值觀、人格、品質等非認知因素的發展。另外,在如今過于偏向量化評價的情況下,我國在過程性評價方面應該加強:成長記錄袋、觀察、表現性評價等等,爭取量化與質性評價之間達到平衡。
(二)樹立“慢”的教育信仰
“慢工出細活”,為了教學不“超速”,在教育觀上,應轉變急于求成觀,樹立“慢”的教育信仰。教育是需要信仰的,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言,“真正的教育應先獲得自身的本質。教育須有信仰,沒有信仰就不能稱其為教育,而只是教學的技術而已。”[17]教育是培養人的活動,最終目的是促進入的全面發展。正如農作物的生長有其內在規律一樣,育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如果人們反其道而行之,如盧梭所言:“大自然希望兒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兒童的樣子。如果我們打亂這個次序,就會造成一些果實早熟,它們長得既不豐滿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會腐爛。”[18]教育工作者們亟需轉變浮躁的教育心態,“慢”下來,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當中去。意識到真正好的教育不是只重最后的結果,而是需要尊重教育基本規律的前提下,用愛心與耐心去澆注學生,促進其自然、健康地發展!在此,需要建立教育信仰:教育是塑造人靈魂的活動,“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理應是“慢”的。正如郭永福所言,“教育是有規律的,孩子的成長也是有規律的。教育周期長、見效慢、后勁大,是一種慢的藝術,需要耐心等待,不能急于求成。”[19]郭元祥教授也提倡慢教育,“教育,作為一種慢的藝術,需要留足等待的空間和時間,需要有舒緩的節奏。高頻率、快節奏、大梯度,不利于學生的有序成長和發展。”[20]
(三)形成“學為導向”的教學方式
為了防止“教學超速”,在具體教學中,構建“學為導向”的教學方式。所謂“學為導向”,不是以“學生”為導向,而是以“學習”為導向,以“學習規律”為導向。“教學要根據學來定,怎么學就要怎么教,以學定教。”[21]傳統的教學方式主要是學生被動地配合教師,才易導致“教學超速”,而“學為導向”則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第一,把學生的現有經驗作為教學出發點。學生雖然處于未成熟的狀態,但是并不代表“缺失”,他們有自己的履歷經驗,教師在教學中應該充分尊重它,并以此為教學出發點。在此,教學內容應符合學生的接受能力,教學方法也應該是基于學生經驗的方法。“從學生的經驗開始,從經驗發展正當的科學處理方式,常常稱做‘心理學的’方法……”[22]第二,以能動學習活動作為教學重心。按照發展機制原理,學習的達成,最關鍵在于學生的能動活動。“教導對學生身心發展的作用一定要通過作用于學生的活動才能發生。”[23]杜威也強調,“除教育者的努力同兒童不依賴教育者而自己主動進行的一些活動聯系外,教育便變成外來的壓力。”[24]因此,教師應該充分尊重學生學習主體的地位,讓其積極地參與能動學習活動。第三,實現學習活動方式多樣化。“不同的活動與不同的素質發展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對應性,”[25]教育者應該創設條件,保證活動的多樣性。鼓勵與引導學生進行多樣的活動:交往活動、操作活動、觀察活動、反思活動、實踐活動等等。這樣才能保障學生多種能力發展的可能性。
[1]謝登斌.21世紀學校道德捍衛的使命[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82-86.
[2]兩會語錄.中小學管理[J].2012,(4):60.
[3][5][7][8][9][22][美]杜威(Dewey,J.)著,王承緒譯.民主主義與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92,201,199,200,192,237.
[4]王紅.中美教育比較:我們真的贏在起點了[J].遼寧教育,2012,(3):89-90.
[6]麥高溫.朱濤,倪靜譯.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M].北京:時事出版社,1998:83.
[10]紀大海.論教學節奏[J].中國教育學刊,2000,(4):34-37.
[11]王策三.教學論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380.
[12]郭元祥.知識的性質、結構與深度教學[J].課程·教材·教法,2009,(11):17-23.
[13]姚林群,郭元祥.新課程三維目標與深度教學——兼談學生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培養[J].課程·教材·教法,2011,(5):12-17.
[14][日]佐藤學.鐘啟泉譯.學校的挑戰:創建學習共同體[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1.
[15][23][25]陳佑清.教學論新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301,300,210.
[16][美]泰勒(Tyler,R.w.).羅康,張閱譯.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8:57.
[17]雅斯貝爾斯.鄒進譯.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44.
[18]轉引自姜英杰.非理性的超前教育:關于早期教育科學性的思考[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6)9-14.
[19]郭永福.別讓孩子累倒在起跑線上[J].中國教育學刊,2011,(07):卷首.
[20]郭元祥.教育是慢的藝術[J].今日教育,2010,(9):1.
[21]吳紹萍,羅祖兵.“教師配合學生”的理性選擇與實踐訴求[J].當代教育科學,2012,(8):14-20.
[24]杜威(Dewey,J.).趙祥麟等譯.學校與社會·明日之學校[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