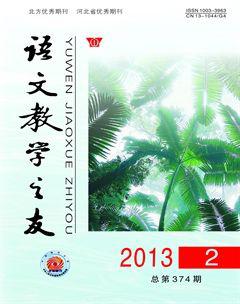談稼軒詞作“登望興悲”的藝術魅力
康亞偉
詞境指詞之意境,是作者的主觀情意與客觀物境互相交融而成的境界。優秀的詞境更象詞人畫的一幅畫,或者搭建的一個舞臺。當讀者品味詞句時,會不由自主地徜徉其間,從而獲得人在畫中游,身為劇中人的審美享受,因此王國維認為“詞以境界為最。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并以此為標準,將辛棄疾尊為兩宋詞人之翹楚,稱“幼安佳處……有性情,有境界”(《人間詞話》)。而最能體現辛稼軒高格、境界的正是那“登高望遠,使人心瘁”的悲情詞境。在此,本文就其登臨詞的詞境試做分析,以搏大方之家一笑。
登望興悲的傳統濫觴于宋玉,他在《高唐賦》中寫道:“長吏墮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嘆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由此開登高望遠,抒發心中壯志悲情之先河。漢代劉向《說苑·指武》又記:“孔子北游,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喟然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汲取發揮了登望興悲的深韻。自此,登望興悲呈現出兩種態勢:一是抒發生命活力不能舒展,理想才能不能盡施的入世者之悲;一是表現生存狀態不自由,世事無常,盈虛有數的出世者之悲。稼軒身具英雄本色,氣格剛毅果大,充滿現實功利追求,所以對高大全的物象、境界愛不擇手;而他熾熱的入世激情又經常在冷酷的現實面前碰壁,不斷地尋求又不斷地被拒絕,只能“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使辛稼軒酷愛登高,登高必賦,賦則蒼涼沉郁。辛棄疾現存登臨詞有三十六首之多,涉及登望情懷的詞更是多達六十余首,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在宋代登臨詞中均首屈一指。通過對這些詞的分析我們會領悟出其登望興悲詞境的三個層面:
第一,登上高臺,北望故土,迸發出“夷甫諸人,神州沉陸,幾曾回首”(《水龍吟》),恢復中原而不得之悲。
此種悲情是以悲憤恨怨為主色調,而且與他一生以恢復中原為己任,認真執著,至死不已卻壯志難酬的心境一脈相承。稼軒自幼生長在金朝統治之下的中原,其祖父辛贊,本仕趙宋,不得已轉而仕金。他黍離凄涼的故國之思,驚悸自危的仕金苦惱始終影響著稼軒。同時耳聞目睹金人燒殺搶掠,蹂踐漢人,槌剝同胞的強盜行徑,使得辛稼軒的心靈上打下重重的烙印。所以當1161年金兵再次侵略南宋時,辛棄疾即率部起義抗金,最終率眾南歸,并一生以恢復中原為己任。但朝廷早已失去了中原及其在11世紀所有的民族與文化的自信,北上抗金,恢復中原只能是一個口號。這怎能不使一世英豪的辛棄疾悲憤怨恨,正如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斯人北來,喑嗚鴦鷙悍,欲何為者,而讒擯銷沮,白發橫生,亦如劉越石”。
上述情緒反映在詞中則如:“郁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向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此詞通過對北方失地的凝望和父老鄉親的關懷,表達收復中原的理想不能實現的悲憤。“卻憶安石風流……兒輩功名都付與,長日唯消棋局”(《念奴嬌·登建康賞心亭》)此詞則揭露了南宋統治者兵馬入庫,做著外患無存的太平夢,怨恨南宋的投降派; 最能表現這種悲憤怨恨之情的是《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
此詞寫于淳熙元年(1174年)此時距其南歸已過了十二年。這其間他多次向朝廷提出收復北方領土的建議,卻如石沉大海。所以當他登上賞心亭時不禁百感交織。詞的上片主要是即景抒情。他登樓先見千里江南,秋光如水水如天,祖國山河不但壯闊而且秀麗,無邊秋色在引起詞人對祖國無限深情時也觸發了詞人對中原淪陷,南宋朝廷不思恢復的“愁”和“恨”。但他并沒直寫自己滿腔愁恨,而是用移情手法把感情轉移到客觀景物上,使那秀麗的山峰似乎也滿含憂愁悲恨。至此作者的豪情壯志終不免拋物線般地跌落于憂患現實中。
“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句,將鏡頭又移向賞心亭上的江南游子。家鄉淪陷、國家殘破而自己浮萍一般飄零于他鄉,徘徊于落日余輝映照的樓頭上,耳邊傳來失群孤鴻的陣陣哀鳴,一見一聞渲染出詞人的孤寂悲苦。隨后作者由即景寫情轉入人事人情,借用張翰因見西風而念家鄉鱸魚膾,竟掛冠歸去的典故與劉備、陳登鄙棄沒有大志,只想建屋買田的許汜的典故表達自身不愿像張翰、許汜那樣不顧國事、鉆營私利,而是渴望身帶吳鉤,征戰南北,保家衛國,建功立業的遠大志向。但他凌云壯志偏偏無處施力、無人回應,陷絕失望的詞人不禁悲憤地將欄桿拍遍,想起數次北伐中原均因東晉茍安導致坐失良機、英雄失路的桓溫手撫楊柳時的慨嘆,男兒熱淚不禁潸然而下。此詞由登臨送目觸發故園之思再轉入壯志難酬的悲痛。千回百轉,沉郁頓挫,顯示出熱血英雄的靈性孤獨。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曾贊《水龍吟》曰 “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沉郁”,此評價不僅點出此詞的妙處,更是這類詞的總體特色。
第二,獨上高樓,無處建功,激發出“老我傷懷登臨際,問何方、可以平哀樂”(《賀新郎》)生命活力不能舒展之悲。
此種悲情區別于第一種以悲壯激烈為主色調。最能代表這種悲情詞境的當屬《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范開曾說辛詞:“故其詞之為體,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滅,隨所變態,無非可觀,無他,意不在于作詞,而其氣之所充蓄之所發,詞自不能不爾也。”由于稼軒從功利主義出發對霸道較為認可,因此他的詞向來有一種豪氣、狂氣、霸氣,這首詞就是例證。開頭一句“千古江山”, 上來即爆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激情,顯得虎虎生威,橫掃千軍。似乎只有景物壯大還不能表達他的豪霸情懷,于是他又引出兩位霸主人物——孫權和劉裕,“舞榭歌臺”風流情事只是過眼煙云;考取功名,安邦治國只是筆下文章;金戈鐵馬,槍林箭雨才是生命意志高昂的競技。值得注意的是稼軒在這首詞中描寫了三個英雄:孫權,劉裕,廉頗,而這三人都是能平定天下造福一方的人物。孫權在漢末乘亂擁兵自立,一統江東,保護了江南百姓的安寧;劉裕在東晉末靠戰功崛起,最終篡奪了帝位,而他在篡位之前曾數次北伐,收復不少中原失地,為民族統一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廉頗憑借卓越的軍事才能,屢次為趙國抗擊強秦的入侵,成為維護一國安危的棟梁之臣。作者在這里仰慕孫權、劉裕、而以廉頗自居,正是表明他渴望像這些人那樣轟轟烈烈地做一番事業,能夠恢復中原,可說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但無奈生不逢時,文韜武略卻報國無門,熱切用世卻倍受壓抑,注定其一生是個悲劇,只能悲壯激烈地喊出:“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第三,登高而返,徹悟滄桑,引發出“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丑奴兒》)這段似輕松實沉重的生命本體之悲。
這類詞中既有短小精悍的佳作如《丑奴兒·少年不識愁滋味》、《生查子·朝來山烏啼》、《浣溪沙·寸步人間百尺樓》等等。又有長而有韻的力作如《木蘭花慢·題上饒郡圃翠微樓》、《新荷葉·再題傅巖叟悠然閣》、《西江月·和晉臣登悠然閣》、《賀新郎·題傅巖叟悠然詞》兩首、《水調歌頭·賦傅巖叟悠然閣》……它們似癯實腴,表面平淡,內里蒼涼之韻充塞其間,因此是以悲涼為主色調。茲舉《水龍吟·過南劍雙溪樓》為例:
“舉頭西北浮云,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憑欄卻怕,風雷怒,魚龍慘。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系斜陽纜?”
此首登覽詞,即景抒情,賦中有比,象中含興,描繪出一幅寂寥迷茫的圖畫,傳達出稼軒郁悶的情懷。志士登樓,目眺西北,遙望那里烏云蔽日,不禁念起烏云下的故園父老;憂憤滿懷,向往著長劍出匣龍吟響,一朝掃平民族仇。但潭空水冷的現實如一瓢冰水澆在詞人頭上,他不由得從“風雷怒,魚龍慘”的朦朧怪誕中聯想起嚴酷的世態:主和君臣,投降賣國;清談鄉愿,萬事可可。于是抑郁不平之氣不禁而起,使他無法展開心靈的雙翅翱翔于天際,只能欲飛還斂,轉而思慕隱居高士,歸棲云山。這之中有報國無門、壯志難酬的心灰意冷,又有不愿逆來順受、同流合污的憤激。一時間,千古興亡的人類歷史,百年盛衰的家國命運,數十載的自身浮沉,盡從心底淌過,伴隨著漁舟唱晚、沙岸歸帆的澹泊風光,讓他對宇宙人生大徹大悟。但即使是在徹悟之中,依然有萬般的無可奈何與欲說還休郁結其間,最終隱隱地透出此類詞作固有的滄桑悲涼之意。
眾所周知,辛棄疾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二十幾歲即率眾起義抗金,此后力殺叛僧義端,鋒芒畢露;闖入金營,徑取叛徒張安國,雄震南北;歸宋之后,平賴文正之亂,威懾江左;出守滁州,政績頗佳;晚年出知鎮江,積極備戰。一生“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的政治實踐顯示出他的人生選擇——成為一名參與社會沖突,傳世千古的豪杰式人物。但由于外在環境,自身性格等種種制約,終其一生他的人生理想并未達成,自我價值也未實現,從而導致他悲劇性的人生。因此,辛棄疾心中充滿了悲哀、悲傷、悲憤、悲苦、悲痛等以悲為主的情感。在作詞時很自然地會對自己的所有悲劇性遭際反復進行吟味,而在這種吟味中他感受到了一種對自身的敬畏、憐憫、同情,從而在庸凡的日常性中為靈魂找到一個出口,保持了與現實世界的距離,最終獲得重生般的自由升華。
這也就是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所說的 “酒神的迷醉和沖動”。在它的作用下,具有強力意志的辛棄疾就從憂國傷時的沉重中,從追求理想而不得的企慕情境中,體驗到了生命的悲壯美,崇高美,感受到了作為英雄的輝煌與快感。對于讀者來說,則自然而然地從其登臨詞中品味到他那些憑借多種藝術技巧抒發出來的壯情、豪情、柔情、憂情、悲情。應當說是創作者與接受者的雙向互動,創造了稼軒登臨詞獨樹一幟的悲美交融的藝術特色。
參考文獻:
1.《辛稼軒年譜》鄧廣銘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稼軒詞編年箋注》鄧廣銘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辛棄疾詞文選注》辛棄疾詞文注釋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辛棄疾詞鑒賞》齊魯書社編輯出版發行1986年版。
(作者單位:宣化科技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