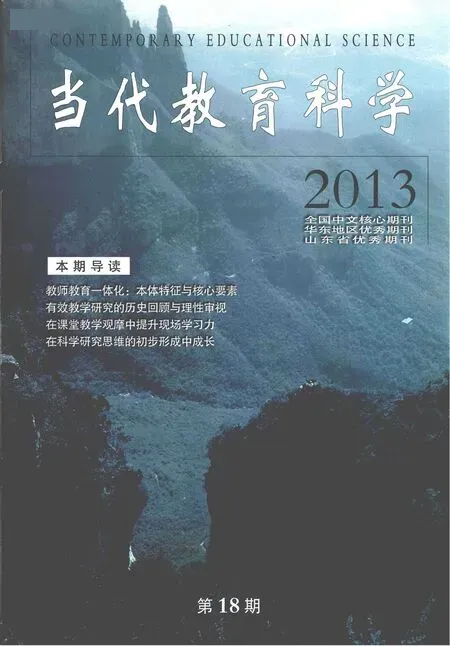課堂教學場域內的另類博弈:生本沖突的社會學歸因
●李 平
教師、學生、文本三個基本要素的互動是課堂教學場域內最主要的互動,歷來教師和文本幾乎是統一戰線,教師依據文本進行教學,文本通過教師的教學為學生所深知。師生關系也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各種理論層出不窮,但是學生與文本的關系卻很少被關注。筆者在學校見習時觀察發現,學生與文本之間是存在沖突的,尤其在課堂教學場域,生本沖突更是大量存在。據此,筆者認為可以從生本沖突產生的原因入手,了解到其中的利害關系,從而促進文本與學生在課堂場域內達到共生。
一、課堂教學場域內生本沖突的概念及表現
“場域”一詞是布迪厄在社會學研究中對關系空間的一個隱喻。主要是在某一個社會空間中,由特定的行動者相互關系網絡所表現的各種社會力量和因素的綜合體。即“位置之間客觀關系的網絡或圖示”[1]。這個場域里,我們不容忽視的三要素便是教師、學生和文本,這里的文本主要是指在課堂教學場域內,用以溝通教師和學生的中介,雙方都默認使用的教材。因此,教學場域內的生本沖突即是在教學場域中學生與所使用的文本之間一種不和諧的互動。
在課堂教學場域這個充滿著各種關系交織的場所,文本作為集體意志綜合的靜態物體,學生則是在課堂生活中的動態主體,生本沖突主要體現在動態主體對靜態物體的態度和方式的不和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階段:
(一)漠然,置之不理
文本經由學校派發到學生手中,學生對文本的處理雖然有自己的主觀方式,但是卻幾乎被強制在課堂教學中的使用。如若文本與學生的自身經驗相差太遠,對學生沒有任何吸引力,那么學生即使在課堂上拿有教材,卻完全只是做做形式,對文本的內容并不會進行認真而深入的閱讀,也不會利用文本而增長學識。這一階段,學生對文本會“束之高閣”,將其作為敷衍教師和教學的面具,藏在面具后面的學生對其的漠然態度充分體現,文本與學生在課堂教學場域內沒有任何實質交集,是一種空白的聯系。例如很多學生在上課時會專心地記筆記,但是教材在課堂教學結束后仍然是嶄新的,幾乎是沒有翻動過的痕跡。此階段的生本沖突并沒有激化,學生對教材的內容毫無興趣,在課堂教學場域出現的教材只是一種任務式的擺設,二者在可接受的范圍內保持相安無事,它是一種隱性的沖突。
(二)抗議,肆意涂鴉
前段時間風靡網絡的“杜甫很忙”事件便是此階段生本沖突的充分體現。“杜甫很忙”,是2012年3月,一組對中學課本上杜甫插圖的“惡搞”走紅網絡,被涂鴉的杜甫呈現出時而扛槍,時而開車,時而揮刀切瓜等各種動作與形象,并引發更多網友創作上傳,進而被戲稱為“杜甫很忙”的網絡文化現象。杜甫作為課堂文本上的插圖人物,其本身存在是為了學生能更深刻理解文章和作者而提供的較為形象的表述。但是由于我們的文本內容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相背離,僅僅作為考試的一部分內容,這首先讓學生提不起興趣,其次作為考試內容必須背誦的壓力,讓學生的憤懣之情油然而生,以至于釀造成全民關注的惡意涂鴉事件。“杜甫很忙”事件只是生本沖突激化的一個縮影,他是學生對文本與其生活脫離而進行抗議的一種表達方式,所以在此階段的生本沖突,學生與文本儼然成為對立的雙方,幾乎是彼此不理解,不相容。
(三)憤慨,付之一炬
學生在考試后撕書燒書的新聞早已屢見不鮮,據海南在線新聞網報道《學生高考后撕書場面壯觀如六月飛雪》,很多高中生在高考結束后將課本作為發泄對象,大肆地將其撕毀。文本書籍本是學生應該珍藏的良師益友,它不僅給予學生方方面面的知識,更是學生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見證者。但是撕書毀書事件,嚴重地表明了學生與文本的扭曲關系。在此階段生本沖突已經升級為惡性沖突,付之一炬的文本成為學生獲取解放的標志,二者完全成為敵對者,發展為勢不兩立的態勢。
二、課堂教學場域內生本沖突的歸因
課堂教學場域內的文本是集體意志的綜合體,它包含著各個階級尤其是上流階層的意志,而學生在課堂教學場域內作為獨立的個體,雖然在理論上是教學的主體,但是因其自身在生理和占有教學資源等等方面的相對缺失而處于教學場域內的弱勢群體,那么,生本之間本應相互促進的友好關系演化為沖突的原因究竟何在?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考慮。
(一)在生本接觸前,基于虛擬學生群體生成的文本與現實學生生命體驗差異而引發沖突
在生本接觸前,文本的生成也即課程的研制。我國現行的課程管理制度是由國家課程、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組成,雖然課程研制地方上已經有了很大的自主性,但是不同層次的課程研制所依據的政策性文件皆是由教育部組織制定的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和各學科課程標準。其中,前者主要是對中央對于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整體把握,后者則是各門學科課程知識研制所依據的主要標準。所以,課程的研制并沒有突破“中央集權”的限制,依然是統一標準下的眾生一相。文本的生成的宗旨仍然是處在上流階層的意志表現,與現實教學中學生群體的意志有著差異。出于上流階層好的出發點的課程標準并不一定適應全國各地學生群體的課程需求。
另外,“課程的研制人員中,有的來自高校,有的來自中小學教研部門,有的是中小學一線教師。其中來自高等師范院校、教研所的教師、研究人員在設計團隊中占相當大的比重”[2]首先,這些研制課程的人員很大程度上已經脫離一線教學,對一線教學中師生對文本的需求自己親身感知較少;其次,課程標準依據整個國家的基礎教育狀況所確定,雖然在課程研制之前會有大量的基層調研和試驗,但是,“當從一線收集上來的信息經過審議進入課程標準的時候,它們已經脫離了本來的屬性,即從具體的情境下總結出的信息被提煉抽象成一般的規則性信息”[3]。據此,依據課程標準所研制的課程的過程也是如此,課程研制人員頭腦中的學生是虛擬的群體,他們已經被概念化和抽象化,不再是獨立的、本真的個體,這樣研制出來的課程缺乏了學生真實想法的話語表達。因此,在此課程研制的過程中,幾乎沒有學生群體——文本所要服務的重要群體的參與,即使有一些關于學生需求的調查,但是經過研究人員的處理等等中間環節,已經無法真切地反應學生群體的渴望與要求。
在這樣的課程編制過程缺少了真正的使用者——學生群體的參與,因為他們不是想象中概念化的、抽象化的,而是鮮活的、有思想、有感情、有價值傾向和發展潛力的生命個體,他們將會依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對文本進行第二次選擇,當基于虛擬的學生群體對象而選擇的知識和真實的學生個體需求產生過大的差異時,學生個體就會產生抵觸情緒,引發沖突。
(二)在生本接觸中,課堂教學場域內文本被固定強制使用以及師生沖突的遷移造成生本沖突的生成
當文本抵達學生手中,它已經不僅僅是一種靜態的存在,作為課堂教學必不可少的媒介,學生會對其產生第二次選擇,但是選擇并不能改變結果反而被要求強制使用。根據吳康寧老師的《課堂教學社會學》可知,文本屬于主動文化,“即處于主導地位、能夠自由表達并且對其他文化能產生影響、控制、支配作用的文化。而學生群體文化則屬于受抑文化,也即處于被控制、被支配地位,不能自由表達的文化”[4]。課堂教學領域的文本,是一種規范性的主動文化,是與統治階層相吻合的文化,而學生群體文化則是社會價值取向之外部分的非規范性的受抑文化。所以在課堂教學場域中,生本沖突也就是為不同文化之間或隱蔽或公開的旨在阻止對方實現其目標,從而實現自己目標的社會互動。二者因其所代表不同階層的文化,所以在課堂教學場域相遇時,學生群體所代表的受抑文化對文本所代表的主動文化進行抵抗,卻仍然無力回天時,極易產生生本沖突。
另外,在課堂教學場域中,文本的代言人即是教師,所以有時生本沖突是由課堂教學中的主體師生之間的沖突遷移而引發。根據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可知,慣習和資本是確定行動者在場域中位置關系的關鍵。布迪厄將資本分為四種形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符號資本。課堂教學場域的主導資本是文化資本,課堂教學是生產文化資本最重要的活動方式和途徑之一,文化資本因而成為課堂教學場域主要的爭奪對象。而在課堂教學場域中文本的代言人——教師所持有的文化資本(主要是知識)相對于學生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師生之間在文化資本上的差異,一方面是教學得以存在的前提,教師持有的文化資本其根本作用在于促進學生文化資本的增長和增值,學生之間也就存在相互之間的文化資本的爭奪,當教師對學生之間文化資本爭奪所施予的引導和影響遭遇合法化危機時,極易引起師生之間沖突”[5]。因此,誰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本,誰就可能占據差序格局中的有利位置。教師因擁有更多的知識(包括教師對學習內容的認識和教師對學生的認識兩個方面)資本處于優勢地位,學生則因身體、經驗等方面的自然落差而處于相對被動的地位。由文化資本占有差異而造成課堂教學場域內師生沖突的遷移是生本沖突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在進入現代信息化的生活以后學生獲取文化資本的途徑日漸多元化,教師在促進學生文化資本增長方面的作用有所下降,因此,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對立偶爾表現為“文化的掌管者”與“文化的創造者”之間的對抗,前者是主流的、正統的文化的再生產者,而后者是新的、非主流文化的創造者或再生產者。二者對知識的不同見解容易使得師生在認識上與教師產生沖突。但是,制度賦予教師絕對的權威,學生對教師的不滿一般不會直接尖銳地表現,轉而將這種不滿遷移到既定客體——文本的身上,從而促成生本之間的沖突。
課堂教學場域內,在學生眼中,文本是教師的文本,教師是文本的代言人,師生沖突被遷移到被教師強制使用的文本上,這時生本沖突本質上不是由于文本本身的不足,而是教師與文本的關系,促使學生將文本作為一種不滿情緒釋放的場所,從而引發生本沖突。
(三)在生本接觸后,考試作為最終檢測,分數成為核心標準,無疑加劇了生本沖突的引發
生本接觸后,為檢測學生對文本的理解和掌握程度,通常的辦法即以考測學,小則平時的測驗、期中考試、期末考試等等,大則中考、高考等等,學生在對文本的學習后最終面臨的都是考試,考試后唯一簡單明了的分數告知人們學生對文本的了解情況。
受應試教育的影響,考試內容拘泥于書本知識,與之相適應的學習形式一般是講授學習、機械記憶、被動模仿、重復性操練,學生對此毫無疑問產生了惰性和厭惡感,在課堂教學場域內,作為考試內容的文本知識缺乏生命活力,那么生本沖突的產生自是不足為奇。
另外,考試分數象征著學生的學習情況,在這種背景下,學生實際背負的是分數的壓力,以文本為依據的考試,最終的分數帶給學生好與差的標簽,“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學生自然希望自己能夠取得好的分數,這也就令他們倍感壓力和焦慮,最后這樣的不平情緒轉移到靜態的文本中導致了生本沖突。
三、結論和啟示
課堂教學場域內的生本沖突的發生,主要是由于在文本的生成前缺乏學生的參與,同時也就缺少了學生群體的話語;以統治階層意志制定的文本與學生日常經驗相差甚遠;作為課堂教學場域內文本的代言人——教師,也因其自身所占文化資本與學生群體差異較大;考試后的分數標準對學生個性的忽視,加之考試所帶來的壓力和焦慮等不平情緒,最終導致了生本沖突的引發。
科塞認為“沖突可能有助于消除某種關系中的分裂因素并重建統一。在沖突能消除敵對者之間緊張關系的范圍內,沖突具有安定功能,并成為關系的整合因素。”[6]因此,意識到課堂教學場域內的生本沖突的存在,實際上更是促進了生本雙方所代表的群體成員的團結和進步。我們可以在生本之間,加強彼此成員的對話,多方位考慮彼此之間的資本、權力和慣習的差異,從而在對話和理解中生成文本。
[1][美]戴維·斯沃茨.陶東風譯.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136.
[2]呂立杰.國家課程設計過程研究——以我國基礎教育“新課程”設計為個案[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158-160.
[3]齊軍.教學場域中的課程知識:對象、呈現方式及價值取向[J].教育導刊,2010,(4).
[4]吳康寧主編.課堂教學社會學[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12:121-122.
[5]王愛菊.走向主體間性的生存——教學沖突研究[D].2010.
[6]劉易斯·科塞.孫立平譯.社會沖突的功能[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67.
[7]高宣揚.布迪厄的社會理論[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141.
[8][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43.